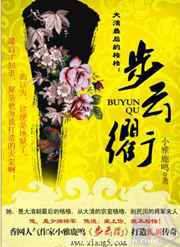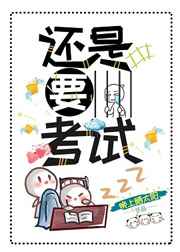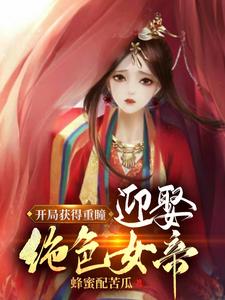大清最后的格格:步云衢 第17章
与此同时,在二门外的左边,竖起了一根约三丈的高幡(这是满俗,早年满人在草原游牧时,因人烟稀少,死了人就在帐篷前竖立红幡告丧),幡杆漆以杏黄色,柱顶则为金漆,上挂荷叶宝盖,杏黄寸蟒。幡下垂拂长约一丈的飘带,含引魂之意。高幡一经竖起,前来探丧的亲友,便在吉祥板前悲泣,牵动丧家上下悲思,于是,众皆又恸哭不已。
第39章 日落紫禁(四)
接着就要选择吉时,抬了妈妈的遗体至大殿入殓。抬时,由府里的六名官员,握紧金箍杏黄棒头,我们众尾随其后,再由仆役四人提着遗体下边所垫棉褥的四角,平平稳稳,徐徐而行。
经过神殿前的“祖宗杆子”(此乃吉祥之物,亡者则视为凶物)时,要用红绸将遗体包得严严实实,然后才许经过,这是“吉不见凶”的常规,不得违背。
到了大殿正中,即移了妈妈的遗体入棺。阿玛近前用筷子夹着一团棉花,蘸上清水为死者擦洗两眼周围,谓之“开光”。随之将盛清水的碗狠狠砸在地上。
接着由大阿哥捧一朱漆坛(也有用木雕盒子的)至前,内有妈妈的殉葬殓物,如翡翠般指、怀表、鼻烟壶、白玉别子……以及宝石顶朝珠一串,和妈妈生前平日爱用的各种物品,一一塞进棺内,占据了棺内的所有空间。还要用一根红线穿上一颗大珍珠,系在妈妈的衣襟纽扣上,并把珍珠塞进妈妈口内,这叫“亲视含殓”。
然后由杠房司役者盖上棺盖,至此,入殓仪礼宣告结束。
此时,全府上下失声恸哭。奶奶有交代过,盖棺之前,是绝不许我们哭泣的,怕泪水掉落棺中,影响妈妈安息。
府里的规制,举行殡礼葬仪不搭客棚,不吹打鼓乐,不备酒筵,不发讣文,而以经单代之。
妈妈去后的第三天,家祭、念经同时开始了。
和尚、道士、喇嘛念经,府里的执事在一旁看经,看他们是不是敷衍了事。这叫念管经。家祭分为早、午、晚三次,先在堂罩前设灵床,其前再设空桌备摆祭席之用,再前设置烛台、香炉、花瓶等物。所谓“五供”,供桌前设饽饽桌子(注:饽饽桌子,亦称满筵,是以硬质饽饽,如白点子之类的食物,分层分罗有三至十五层不等,上摆鲜花、鲜果,亦有以纸花代用的。统称“饽饽桌子”。),一般为三截金桌。
祭时,要在供桌上再摆设一桌祭席,四个墩子分置两旁。一日三次,次次如此,并由阿玛在灵前奠酒,被指派在灵前服务的仆众都要跪在院子里举哀。我们则跪在灵右,大阿哥和二阿哥跪在灵左,阿玛则跪奠酒池前,听和尚、道士、喇嘛上胎念转咒。
府里的规制,在府停灵为五七三十五天(二十一天或十五天亦可),最多为七七四十九天。没有出殡之前,都要念经超度亡魂。
饽饽桌前设有奠酒三事(奠池、杯、壶),奠者跪,执壶、持杯者半跪,以三莫(将酒洒池内)三叩为准。依辈分而论,还有“高莫”、“坐奠”之分,统称奠亲友赠送的。分禅(和尚)番(喇嘛)道(道士)三种。每念一坛经循例要送一次库。库为纸糊高大楼阁,三座(一楼二库),金碧辉煌,宏伟富丽,送至府外空地焚烧。送一次库,所费不赀。
各府里办丧事,所收丧礼只有饽饽桌子、祭席(外附四墩子)、冥活(如花盆、金山、银山等)等等。从无挽联、祭帐、花圈之物。即有送“奠敬”(现金)者亦为数甚少。
第40章 日落紫禁(五)
王府和世家望族,在丧事中放焰口时,除不放音乐焰口外(嫌其俗陋),还有一种形式,叫“传灯焰口”。所传之灯,称作法灯,数为一百零八盏,外加亡者年岁若干盏(一岁一盏)。两数相加,再以十除之,中间加法物十种:为灯(红色灯花一盏)、花(石榴花一朵)、香(小炉燃线香一炷)、果(苹果一个)、水(清水一盏)、茶(茶叶一包)、食(中式点心一块)、宝(小元宝一个)、珠(火珠一颗)、衣(红绸一块),统称“十宝。”传灯时不准有哭泣声,气氛十分肃穆。每放一次“传灯焰口”,都要闹到子夜之后方止。
出殡的前一天,叫做“伴宿”,傍晚送最后一次库,也是停灵最后一次高潮。这天从早到晚,宾客不绝,“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虽然隆重,却不备酒席,只用香茗待客,谓之“清茶恭候”。这是王府与各大世家不同之处。
出殡这天,又是丧礼的高潮。事先要选择吉时发引。起柩出府时,先把棺材抬出府门,放入“小请”,先由杠夫起棺到胡同口,继而换用特许的太福晋用的黄杠(杏黄色),杠夫分三班轮换,一一剃头穿靴子,衣分绿蓝二色,每班不同。大殡最前的停灵门前竖立的那大幡,由杠夫抬行。两列仪仗,为清制‘头品执事’组成,故有鹰、狗、骆驼、刽子手等。并有两杠门纛、八根驱路,其形如戏曲舞台上龙套所执之物相似。以其颜色之分,即可看出隶属哪一旗。
仪仗外还有影、伞、小轿以及太平杠和松人、松狮、松鹤、松鹿、松亭等等。加上禅、番、道三堂执法器送殡,真如同《红楼梦》所形容秦可卿出丧时的那种“漫天盖地而来”的情景。棺前另有一队“小嚷”。他们身着孝袍,手捧木盘。盘内放些亡者应用纸活,如鼎、炉、瓶、碗之类,人人必需发出似哭似喊的“有声无泪”的凄怆之声。阿玛则在‘家人’左扶右架之下,在棺前走着。凡是送灵者,不管官阶多高都要步行。我们女眷则乘素轿或马车,跟在棺后。
棺后有后护仪仗队,由二十组成,各执兵器,谓之后护,随棺而行。
灵柩所经之地,亲友在路口自动搭盖‘路祭棚’,内设供桌和座位。桌上摆满祭奠品,如香烛、鲜花和干鲜果品等。每当灵柩行经路祭棚前,长约一里的送葬行列,全都停止前进,接受亲友祭奠。阿玛和哥哥们必需一齐跪在灵柩之旁接受亲友吊唁,并叩头致谢。
奠酒之后,尚需念经。待至起柩继续前行,所花时间少说也要二、三十分钟。这样三番五次的奠酒,反反复复地跪拜,无休无止地念经,悠悠荡荡地前行,坟地离城十数里,到达时所费的时间至少大半天。
丧礼至此,全府上下号啕痛哭,与和尚、道士和喇嘛的念经声交织在一起,确有悲怆之感。
第41章 平地起波(一)
这时,杠房人等把全部烧活一齐焚烧,府里的丧礼殡仪才宣告礼成。
这场丧事,所收的祭礼,如饽饽桌子、祭席、祭果,不计其桌,各种冥活,不计其数,而府中自制的冥活种类更多。除用绫绸糊制的灵人外,还要按照妈妈生前日用器皿及其所爱的古玩文物,依形糊制。这种复制品,技艺精巧,可以乱真。凡此种种,在最后送库时,同一楼二库,付之一炬!办过妈妈的丧事后,府中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银子了。
由于大哥岁数也不小了,可是府里先是给大格格备了嫁妆,妈妈身子那时已经不成了,所以后来又备下了治丧的银子,大阿哥这才迟迟没能成婚。
早早便定了亲事,直到妈妈临终前嘱咐,让他赶在百日里成亲,所以丧事结束了没有多久,府里头便又要给他张罗娶亲的事情。
不得已,阿玛和奶奶商议,卖了府里在关外的两座庄子和六百多顷地。这一举,无疑是杀鸡取卵,那些庄子和地租的收入一直供给着府里庞大的日常开支,现在……
大阿哥成亲后,便和我们分了出去,自己单过了。分出去的一些产业,也都从府里的账簿上交给了他自己打理。
府里就剩下我和二哥这两个孩子,而二哥也定了亲事,在不久后也要娶亲了。
没过多长时间,隆裕太后也薨逝了。从皇上退位后,一股阴云一直笼罩在了大家的心里,这接连发生的事情,让各府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能称得上热闹的事儿,便只有隆裕太后的寿辰和丧事,隆裕太后的寿辰是三月十五日,仅仅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辰当天,奶奶也进了宫。
袁世凯还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前去为隆裕太后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如此可笑的称呼,真是令人觉得讽刺。大清亡了就是亡了,这些虚浮的东西,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罢了。
梁士诒走后,国务总理赵秉钧又率领全体国务员前去行礼。
隆裕太后去世后,袁世凯不仅亲自在衣袖上缠上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他还派了全体国务员前去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的‘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也举行所谓的”全国陆军哀悼大会”,主持人是袁世凯的另一心腹,上将军段祺瑞。
在紫禁城,在太监们的干嚎声中,清朝的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脸上,洋溢起了得意的神色。最让宗亲王公们感到兴奋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来了,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
凡此种种,在遗老旧臣中引起了诸多的推测和议论。
“袁世凯究竟是不是曹操?”
“项城(袁世凯的号)当年向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说过,对民军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徐、冯、段这才同意办共和。也许这就是智取?”
第42章 平地起波(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