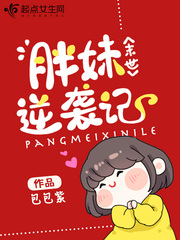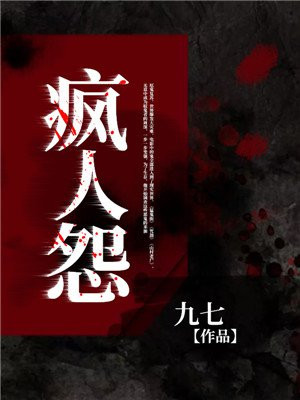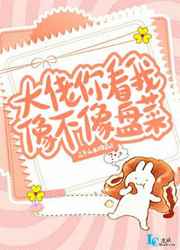反派公主走向权力巅峰 第106章
薛雯笑了笑,微微欠身道:“是,绿蜡是指芭蕉。”
薛昌韫便点一点头,若有所思道:“用得有趣儿,难为这些人想得到啊。”
——倒是别有一番坦坦荡荡的为君者风采。又道:“绿蜡不是蜡,灯绿也许也不是灯呢?也未可知啊。”
薛雯便也看向了张子初,稍显客气地道:“皇兄和沈元麒当初说的一模一样···那就要请张先生解惑了。”
张子初冲二人行礼,道:“回皇上,回公主,这一句不曾录错,也的确就是灯、的确就是绿——若不能理解,可在夜间紧盯灯火,再将目光移到暗处,眨一眨眼睛,就能看到‘灯绿’了。”
说着,又吟道:“‘竹简百卷短,灯绿五更寒’,学子苦读,哪一个不是读到头晕眼花,昏沉沉见灯绿耶?故而有此一句。”
原来如此。
张子初风度翩翩言语文雅,倒让薛雯一时间,又想起了年少的沈三的胡言乱语了。
“百卷还道短,五更天愈寒——看灯都是绿的,这人估计是读书读傻了,要不,就是疯了···疯子有什么逻辑,看我给他续两句:方月天上挂,元日闻鸣蝉。啧,好诗好诗,这意头可就足了······”
第92章 算心 翻过年去,万象更新,薛昌韫……
翻过年去,万象更新,薛昌韫御驾亲征之事,也基本准备停当了。
薛雯也走马上任——一回生、二回熟,又做起了监国公主。
饶是边关局势紧张,饶是出征在即,薛昌韫离京之前也仍有几分闲心,将张子初封了个御前应答······
——官不大,与薛雯的小表弟胡伏宜乃是同级。
当时下旨的时候薛雯也在,她因内心仍是有些忌惮马祖昌,想着这张子初到底是马祖昌的师侄,瞧着也得马祖昌的看重疼爱,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便问薛昌韫,应答可是封低了。
薛昌韫却满不在乎,随口答道:“不过是个意思,又不是真指着他做官,低便低些了——低不要紧,要紧的是能时时在你跟前儿,你便多留心看着,若好了,也给皇兄一个准话儿。”
但也不知是怎么又动了念头,竟真的给薛雯这一句话的面子,转过头就又封了张子初光禄寺少卿。薛雯被他这一手整得还挺别扭···但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若再反悔,则也未免啰嗦,便只得稀里糊涂的就这么着了。
择良辰、选吉日,薛昌韫虽然明明不信这些,但也免不了安定军心搞这一套了,故而马监正亲自圈了日子,祈福祝祷、太庙告先——二月初九这一日,西征大军开拔离京。
薛雯与文太后相偕同送。
薛昌韫再次嘱托薛雯便宜行事,道:“朕知皇妹这些年谨小慎微方得保全,但哥哥面前不必如此,除了与朕有关的军机送到前线,别的一应事由,无论大小,皇妹皆可自专。”
薛雯乖巧笑了笑——将这一番话左耳怎么进来的,右耳怎么倒出去,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
薛昌韫自然看出她敷衍,揉了揉她的脑袋没再啰嗦,振臂一呼,上马出发了。
回宫时二人同乘,文太后拍着她的手道:“蓁娘,你是知道你四哥的,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他的话一丝儿不掺假,哀家也是同样的心思,咱们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来的,如今何妨放开手脚,若不然,还不如就做你的长公主,莳花弄草找乐子,也省的窝里窝囊的不自在,你说呢?”
薛雯笑了笑没接话,只是作出了一副贞顺的样子,表示虚心接受,但并没有给文太后一个准话。
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比快乐和自在更重要,何妨吃力不讨好?文太后的话,薛雯不能苟同,文太后劝她之意,多说也是无益,薛雯自有思量。
见状,文太后也没有再揪着这个话题不放,而是转而又提起了张子初——一连两个话题都和薛昌韫一模一样,不愧是亲母子。
薛雯有些无奈,故意反客为主打趣道:“娘娘难道心态老矣,怎么如今一门心思在家长里短上了?皇兄的话母后也听到了,我精力有限,要顾着前朝,妙言呢,到底是初初上手,卓氏又···后宫还要娘娘盯着管着呢,且有您的操心······”
文太后微微挑起柳眉,依然明媚端艳的眼眸中显出了些许疲态,半晌,她笑叹了一声,唏嘘道:“是啊,哀家老了···都是做祖母的人了,焉能不老?忽悠悠半生已过,再回首已过半生······老了啊。”
感慨到一半,态度又闲适了起来,话锋一转回到原点,笑道:“哀家老了,蓁娘却是花期正好,有花堪折直须折,可不要辜负了韶华时光啊。”
薛雯差点儿没跟上太后的思路,愣了半刻,才无奈笑道:“是。娘娘的话,雯不敢不放在心上,只是还在孝期中,守孝守孝,既守期也守心,实在不是想这些事的时候。”
不管她是不是找借口在搪塞,把这个抬出来了,文太后就实在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笑了笑,没再接话。
那之后,果然如薛雯所说,后宫中极少有薛雯的身影,与太后,也是少有碰面的时候了。
——反之,倒是张子初常见······
见得多了,与一开始相比,两人也渐渐熟稔些了,可也仅限于“些许”,皇上与太后的意思,这两人心里都明镜一般,也都不抵触,有亲近的意愿,但,都不甚得其法。
若碰巧找着个话题了呢,便你来我往谈半日,大多数找不着话题的时候,就君臣奏对疏离寡淡——毫无进展。
再加上薛雯平素也实在是忙。
薛昌韫几回剖析内心真情流露,薛雯“咬定青山不放松”,皆没有往心里去,不是因为她冷情多疑,实在是没有人比她更门儿清这个监国究竟是怎么回事、薛昌韫为何朝中初定百废待兴之时就要离京了。
——当初那些风风光光走马上任的代行职大臣们,如今早已是死的死关的关,少数好运气的,才能赚一个全家流放,这些都是明面上的薛昌煜的心腹,当然要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但并不代表这些就是全部了。
朝中,废帝余孽犹存——怎么查?查多深?查出来以后怎么处置?都乃是烫手的山芋。
别人登基施仁政,薛昌韫登基,兴牢狱?
不能这么办啊!
所以这件事,薛雯做起来最合适——她涉足朝事多年,满朝文武早已经默认了她的存在,又曾是先帝钦点的监国之人,又不曾做出打进紫禁城这样的留有争议之事···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比薛昌韫更用得上“名正言顺”这四个字······
再加上当年,诚安长公主与胡伏宜为了在薛昌煜的手底下保全薛雯的性命,曾促成了薛雯当着八辅臣的面与薛昌煜两相对峙,一度剑拔弩张。
从立场、从身份、从能力、从资格、从动机,舍她其谁?
用人朝前,薛昌韫当然要对她说好听话儿了,倒不是说薛雯就觉着他对自己连定点的兄妹情分都没有、都是做戏的,但真要为他的话感动,豁出自己去还报此情···那就成了大傻子了。
说白了,君君臣臣,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那所谓的“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这始终是臣子的思路。
薛雯不是。
先天后天的一切都决定了,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置身什么样的境地,薛雯永远都会是君主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