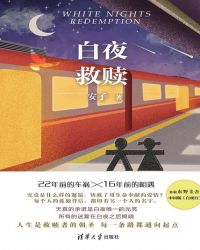感谢天感谢地,打开门的时候,我看见了毫发无损的老杜,虽然他不省人事,但至少没有血肉模糊的惊悚场面,至少鼻翼还在颤动,呼吸尚存。
不过老杜的沉睡让我颇为不安,任凭我和物业小伙拼命摇晃,他依旧瘫坐在凳子上,人事不省。从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激动不安,手忙脚乱,直到物业小伙叫来了120,我还是心神不宁,六神无主。
老杜,你怎么了,你究竟怎么了!
老杜,你醒醒,醒醒啊!
这是我第一次坐救护车,听着救护车刺耳的鸣笛声,看着身旁担架上生死未卜的老杜,突然有一种命运叵测的恐惧。
始料未及,我会如此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寻找老杜,并且真的找到了他;未曾想到,此时此刻,我会成为他身边唯一的“家属”,十万火急地送他去医院。
昏迷中的老杜,也一定想不到吧。
更不可思议的是,811房间的业主,竟然是我——安晓旭!
然而此刻,对我来说,老杜究竟是谁,老杜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老杜是不是还会给我带来重重劫难,已然不再重要。
811的业主到底是谁,更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我要老杜活着,活着!
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的时候真的很微妙,老杜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天天对自己说,这个老男人真讨厌,我要摆脱这个老男人;这个老男人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他又老又丑;这个老男人用几杯豆浆几根油条几个包子就想打动我的心,做梦去吧。然而,当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逼近他时,却像母鸡看见老鹰扑向小鸡一样,拼命张开翅膀飞奔过去,尽管,这样做很可能是自取灭亡。
我爱老杜吗?
不,当然不。
那我为什么有这种天然的不可抑制的冲动,去寻找他,救助他?
不知道。
这和受人点水恩必将涌泉报也没有太大关系,这真的是天然的惦念,在一年多的日子里,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关切。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有时候,力的作用真的是相互的,纵然我再排斥老杜,他施予我的所有关切,也在此时此刻,反弹了回去,正如佛教里所说的报应。
也许,正如老杜那天所说,“抬头三尺有神灵”,冥冥中,我和老杜,注定纠葛。
然而在入院时,我却为了难,救护人员迅速将老杜推进了急救室,嘱咐家属去急诊窗口办理各项手续,可站在窗口前,我却说不清自己和老杜的关系。我只好说:“给我五叔挂个号。”老杜的年龄,做我的叔叔绰绰有余。名字就写杜长天吧,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个。
回到急救室门口,医生的询问却令我又一次如坠冰窟。
“家属,病人有没有吸毒史?”
“呃……”
“请如实回答!”
“我,我不知道。”
“病人来院之前头部有没有受过撞击?”
“呃……”
“请如实回答!”对于我的一问三不知,医生颇有些着急。
“我,我不知道。”
他没有再说话,递过来一张单子:“看好了,家属签字。”
《手术通知单》——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传说中的黑白无常,意味着老杜即将被推往生死之门。
面对脸色煞白的我,医生毫无情感地催促:“尽快,越快手术越好。”
我突然觉得,老杜的生命,就这样交到了我的手上,一种命定的沉重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必须手术?”
“必须。”
“不手术会死吗?”
“不会死,会脑死亡。”
“手术会死吗?”
“单子上写的有,自己看。”
我眼前一片惨白,尽管我集中了全部的注意力,那些白纸上的黑字还是闪烁不清。
突然,一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响起:“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不赌会死,赌了就可能生。”
医生接过我签好字的手术通知单,转身进急救室,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我终于回过神来,声音颤抖:“医生,他到底怎么了?”
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脑出血。”
对于我来说,脑出血并不是一个特别陌生的词汇。曾经有一位高中同学,上学的路上从吊车下经过,脑袋被大吊车沉重的挂钩撞到,当时并没有什么不适,但下午第二节课结束,课外活动时,他就叫唤脑袋疼,后来老师打电话叫了家长,送医院急救。后来,那位同学就再没有出现在校园里;再后来,老师对我们说,那位同学,脑出血,没了。从那儿以后,我只要看见吊车,都会躲得远远的,生怕有什么意外降临。
所以,听到“脑出血”三个字的时候,我的脑袋嗡了一声,心猛然就提到了嗓子眼里,我真怕下一刻,医生就走出来,生硬地递给我一份白纸黑字的死亡通知单。我的生命何其年轻,怎能承担太多死亡的重量,尽管这份死亡和我无关,但它必定会让我的内心又一次陷入长长久久的黑暗之中。
急诊室的门合上了,我被关在了门外,仿佛被晾在了生命的关口上。我真的不是一个勇敢的人,真的不是,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雷海生住的那套房子的那个小阳台,想起自己从小阳台向下看时,那种眩晕的感觉,那完全不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高冷,而是恨不得屁滚尿流的惊恐。此刻,我的感觉恐怕就是常常被人嘲笑的那种“吓尿了”的惶恐。
全世界过得最慢的地点,恐怕就要算急诊室外那块地儿了,时间在这里凝滞不动,任凭谁也推不动,只有命运可以引领时间穿越这方寂静的空间。这种时间之外的感觉,让人抓狂,让人惊恐。
不知过了多久,急诊室的大门终于向这个世界敞开,我的心脏激烈地跳动着。
“老杜,老杜!”没有人理睬我的呼唤。
老杜的脑袋被白色的纱布缠得严严实实,双目紧闭,依旧昏迷,身上插满了管子。
“医生,医生!”
“病人状况稳定,快去办住院手续。”
站在缴费窗口前,我才意识到,这一次,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仅仅是勇气和胆量,还有金钱,我来北京一年多来省吃俭用存的两万块钱,就要在此时,全部拿出来,交住院押金。幸而我一般都将身份证和信用卡装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否则此刻,我只有把老杜一个人扔在病房里,火速回去找老杜的母亲了,而这正是我最不放心的,我真怕我一旦离开,回来就是一个再无声息的老杜。
我怕,怕极了,怕老杜死掉,就像十四年前,怕那个肮脏的垃圾婆死掉一样。我哆嗦着冲向缴费窗口,攥着钱包的手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颤抖。我挤到最前方,惶恐不安地央求:“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太害怕,对不起,对不起……”身旁交费的人,默默地让出了位置。
交完钱,攥着一堆单子,来到病房,医生的话,终于让我不再像风摆杨柳一样颤抖。
“出血量不多,大约三到五天能清醒过来,家属注意夜间陪护,有事按铃。”
不过后面的话,还是让我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病人血液检测异常,不排除吸毒或者被强制注射毒品的可能,醒来后注意观察,有异常反应随时按铃。”
想起老杜平日里亘古不变的没精打采,我打了个冷战,难道,老杜他……
目光落在老杜死灰般的面孔上,瞬间,所有的疑问便都被我抛在了脑后。
之前的老杜究竟是谁,究竟怎样,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现在的老杜,只要他活着走出医院,我就完成了自己的责任。这不仅仅是我对老杜的责任,更是我对自己的责任。
做人,就算是弱女子,也要将“人”字做端正、做沉稳、做磊落、做坚定。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杜不管,即便是他走出医院之后,和我再无联系,再不见面,我也必须照顾他,直到他出院,这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只有这样,我才心安。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因为我有多关心老杜,换个陌生人,我也一样会出手相助。
我不愿离开医院,生怕老杜有什么变化,只好拨打房东家的电话。女房东除了每天早晨出去卖报纸之外,白天都在家里待着,除了同事和办公室的电话,我也只知道她家的电话和西皇庄筒子楼的那个房东的电话了。电话拨通,接电话的先是女房东痴呆的丈夫,在电话那头呜呜哇哇叫嚷,接着,是她收养的女儿接过电话,然后才叫来了女房东。
“阿姨,你能去老杜家一趟吗?”
“啥事?”
“跟老杜他妈说下,老杜在西直门的北大医院住院,请老太太来一趟。”
“啥病啊?非得叫老太太去?”
“呃,就是摔了一跤,磕了脑袋。”
“我可有日子没看见老太太了,保不准没在家。”
“就请您帮忙去看看,如果在,帮忙捎个信。北大医院住院部,811病房。”
上帝,我这才意识到,竟然是811病房,这个倒霉的数字。
傍晚时分,看着老杜心电监护仪上规律的波动,我略微松了一口气。
我感到异常疲惫,饥饿感袭来,这才说服自己放下心来,到医院外的小饭馆去吃碗面。
落日的余晖里,我有些恍惚,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是不是在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