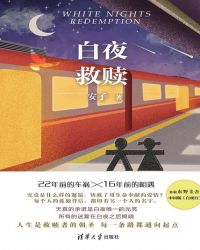我和雷海生的婚姻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事实上,和结婚前的同居生活相差无几,不算明朗,也不算凶险,只是,我们多了一些心照不宣的避讳,比如我们从来不谈童年,从来不谈过往,从来不谈父母。他有他的秘密,我也有我的秘密。比如那张从老杜的房子里带来的照片,虽然已经不见踪迹,但雷海生见过,他以为照片中的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那是谁,我只知道,我的生母是芭蕾舞演员,所以在我的想象中,她决不会比照片上的女子逊色,至少和她一样靓丽多姿。
在婚礼后的第三天,雷海生终于还原了婚礼前的他,又和原来一样唠叨和挑剔起来,不过我却因此感谢上帝,因为他至少不会像婚礼前一天一样变成令人生畏的怪兽,也不会像婚礼第二天清晨一样变成狂躁的雄狮。当然,这样的回归也意味着无尽的指责和狂暴的“男女”,不过这总比叵测而冷漠的生活让我心安多了,至少,生活的下一秒,不会让我胆战心惊、不会让我猝不及防。
婚礼后的第三天,雷海生拉我去了婚姻登记处。
在婚姻登记处门前,雷海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认真、真诚而严肃地拉着我的手,问我:“安子,你不会后悔吧?”
事实上,在雷海生拥有我之前,他是温柔的、可爱的、多情的男子;在拥有我之后,他是霸道的、温暖的、顾家的男子;在他住进西皇庄之后,是专断的、强硬的、守家的男子。然而无论什么时候,他那张精致的面庞都不会出现严肃和真诚的笑容,倒不是说他不真诚,只是他那张脸,永远是雕塑般凝滞、精美,以至于我从来都只想把他那精致的面孔当作工艺品来欣赏、来把玩,却从未在内心深处生出强烈的冲动,想要被他拥有,想要和他成为一个人。
此刻的我,虽然已经在雷海生的浸熏下,谙熟人事,但是灵魂的肉欲始终未曾开启,纵然那样精致诱人的面孔,也不能让我的身体在他的怀抱里柔软起来,不知道这是我的无能,还是他的无能,所以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的眼神,永远充满了征服的欲望,永远彰显着占有的企图,这也许是男人惯有的表情,他们永远希望征服女人,征服整个世界。
在我和雷海生之间,似乎从未真正平等过,他永远只想降服我,从身体到灵魂。
然而这一天,这一刻,他却站在我对面,严肃之极,眼神像十一岁那年一样真诚,一样认真,以至于我呆呆地盯着他,半晌无言。
他第一次在我面前窘迫起来,他放开了我的手,低下头,喃喃地说,“安子,这一次,我不逼你,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等,等你真的愿意嫁给我。”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梦中的那个画面:
他像个撒娇的孩子,把头埋在我的胸口里,目光深邃而迷离,喃喃地说“宝宝,我想和你……”我抚着他柔顺的头发笑着摇摇头,抬头满天是星星的眼睛。
我们身下是长长的站台,两边是笔直的铁轨。两列火车从两旁的铁轨上面对面呼啸而过,强烈的风吹得我的耳朵生疼。
我突然觉得心里生出了一团火,灼热的火焰烤得我焦躁不安,我迫不及待地抓住了他的手,像个热烈的情人一样,踮起脚,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不,海生,我想要你,我现在就想要你……”
我亲吻了他的耳根,宛如近一年来,近百个夜里,他噙住我的耳根,在我耳边喃喃一样。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的,为他,动了情,从灵魂到身体。
他的身体如受惊的小鹿,猛然颤抖了一下,我看见他眼中慌乱的眼神,在片刻之后,才恢复往日的强硬。
这一天,应该算是我和雷海生,真正相爱的第一天,却也是,真正相爱的唯一一天。
我们走进婚姻登记处的时候,十指相扣,我不能断定他内心的感觉,但是我的内心,却真的是要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依托在这个名叫雷海生的男人身上的,就算他一无所有,就算他一无所能,就算是他真的身负命案,我也要在这个命定的男人身上,成就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弃不离生死相依的爱情梦想,既然今生的轮回中,让我们再次相遇相爱,那么,无论前路多坎坷,无论未来多叵测,我向命运举手投降,我决定降服在他的脚下,做他的妻子,做他未来的孩子的母亲。
那一天,那一刻的我,就像教堂里虔诚的信徒,内心卑微而热烈,真诚地将自己的全部以及未来,奉献给他。
那一天,那一刻的雷海生,应该和我一样吧,他从未那样严肃而郑重、真诚而紧张,他一定也怀抱着和我一样的爱情梦想吧,尽管他心里还有一个小小,尽管他并不知道眼前之人就是当年的小小,但是至少,他一定是打算和我共度余生的吧!
不过上天总是喜欢戏弄我,虽然这次的戏弄无伤大雅。
填好了表格,按手印的时候,我忐忑起来,突然有一种即将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以及自己的梦想和未来售卖的感觉,我抬起头,去看雷海生,却发现他也正看着我,目光里满是探寻。我咽了口吐沫,狠狠心,闭着眼睛,按下了手印。再睁眼,看见他,如我一样,狠狠地在自己的表格上,按下了一个重重的手印。
就在我的内心终于像一条死鱼一样不再挣扎,举手向命运妥协之际,登记人员的声音传来:“怎么停电了!”
雷海生愣住,眼神不复温柔,我看见狂躁一点点爬上他的眼角眉梢。
我的内心,却像被扔进了水里,想要游动起来,想要喘气呼吸,这是命运的暗示吗?
这是老杜的诅咒吗?
老杜,老杜,你在哪里?
老杜,老杜,我现在需要你,我害怕,我真的觉得害怕,不是恐惧,是害怕、慌张、无措。
“你们要不先回去吧,明天再来,停电了,出不了结婚证。”
就在我和雷海生缓缓转身,即将走到门口之际,命运的钟声突然响起:“回来吧,来电了!”
雷海生没有转身,他伸手抱住我,像托举一个孩子般将我向上举起,眼睛里满是激动,满是兴奋,以及胜利的光芒!
那一天,是我真正值得回忆一生的一天。
那一天,我眼里的雷海生,宛如那个十一岁,穿着别扭的新衣裳,小鹿一样跳跃着跑过站台,向我跑来的男孩。而我这二十四年来所有的苦难,所有的不堪,所有的压抑,所有的纠葛,包括所有的坚守,所有的追逐,所有的梦想,仿佛都在这一天,为他,绽放。
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我将老杜忘掉了,真的忘掉了,虽然只忘掉了一天,然而,我却在这一天里,完完全全成了命运的信徒,完完全全成了那个十一岁男孩的新娘。是的,没错,当晚,我在他的怀抱里绽放,这是我第一次,不再拒绝,不再生硬,我终于不再觉得那张贴近我的面孔冰冷,不再觉得覆盖在我身体上的那个男人陌生。
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幸福的,它将我心中所有的不满和不甘,挤得粉碎,以至于第二天早晨,当雷海生重新恢复了那张精致而凝滞的面孔时,我不禁觉得,恍若隔世。
第二天一早,雷海生就命令般对我说:“安子,我们今天收拾收拾,明天就搬家。”
我愕然:“搬家?搬到哪儿?”
“蒋宅口”。
对于搬家这件事,雷海生不是没有提过,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我从没意识到,自己真的要搬到雷海生的房子里去住,每次我们谈到这件事,我都以上班路途太远来搪塞。
事实上,我根本不想搬家,一则上班的确有点远;二则,我不想住在他的房子里,尽管他已经是我的丈夫,可我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能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哪怕只是自己租住的房子;三则,也是我内心深藏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不想离老杜太远,我已经离他很远了,不管我是否已经为人妻,为人母,我都希望,能够离他近一点,仿佛近一点,就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他的温暖。四则,我还有811,老杜说它是干净的,就一定是干净的,我不能离它太远,我得找个机会,把它还给老杜。
我以为,以雷海生专断而霸道的脾气,一定会对我的拒绝暴跳不已,一定会千方百计强迫我搬家,然而这一次,我竟然猜错了,他并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强迫我,他只是如常地发挥了自己唠叨和指责的本能,啰唆了很久,然后就如常地做饭去了。
雷海生的反应让我觉得有些莫名,难道是我昨夜的绽放,柔软了他的内心,让他终于可以和我平等相处,不再居高临下,不再独断专行?
这一天,雷海生扯着我,在家居市场逛了很久,选了一张宽敞的大床,运回了西皇庄,取代了之前那两张破旧的床垫。这张有着硕大床箱,可以放下我所有被褥的大床,就成了我和雷海生婚姻生活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