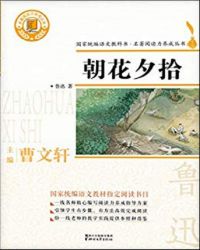第二章 牵萝补屋蔽苦雨
第二章
牵萝补屋蔽苦雨
老妇人让婢女扶她走到雪信近前来,说:“你敢让我摸摸你吗?”不等雪信回话,老妇人又说道,“伸手。”
雪信把自己的手放到了老妇人的手里。老妇人的手背保养得比她的脸还要细腻,白皙、枯瘦而十分有力。她将雪信的双手一点点摸过来,虽然双眼看不见,但摸一双手足以了解一个人了。雪信的双手没做过粗活儿,一条伤疤、一个老茧也没有,柔润得有些脆弱。当老妇人的手掌心中干硬的裂口擦过她的手背,雪信感觉似有一把锉刀正在磨花她的皮肤。老妇人的一双手,正反两面是两个极端。
老妇人收回手,在鼻下一闻:“你手上有血,你是杀了人跑出来的?”
“没有,只是把人打昏过去了。”雪信老老实实地说了。
老妇人的双手又伸过来,从雪信的脸颊摸到脖颈、肩膀、腰肢、腿脚,她摸到了雪信只穿了袜子的双脚。
“你学过舞吗?”老妇人问她。
“学过。”雪信不知老妇人关心这个做什么,还是小心地回答了。
“你随我进去吧。”老妇人终于认可了她。
送老妇人和婢女回来的马车掉了个头,走了。看来马车并不是她家里的,若家里养不起马车,景况不会太好。
果然,老妇人的家门漆剥落,只是个宽敞的一进院子,房间虽多,但闭窗锁户,从旁经过就是一股霉味,只有正对院门的正房是供人起居的。看正堂上,没有什么装饰,连家什也仅是日常必须的几样,客人多了连座位都安排不了。
老妇人在正堂里坐下后,从袖子里摸出一串钥匙交给那个叫羽儿的婢女:“你去厢房给她找双鞋来。”
羽儿去了不久就提着双灰扑扑的鞋子回来,交给雪信说:“你试试,看合脚不?”
雪信把鞋子上的灰尘拂掉,见是一双鞋尖翘起作凤回首状的六寸弓鞋,鞋面丝绸光泽暗淡,年久质脆,上头绣的牡丹也褪了颜色,尽是一处处断开的线头。
“这不是双舞鞋吗?凤头牡丹弓鞋。”雪信连试都不敢试,只怕它在套上脚的瞬间化成几瓣破绸子。
“你这粗笨的丫头,让你找双能穿的鞋,你怎么把那些破烂翻了出来?”老妇人责备了羽儿,打发她再去找找。她又对雪信说:“你说得上这鞋的名字,还说得上它的来历吗?”
雪信反复端详舞鞋,看着老妇人的神色道:“这双鞋子不但久了,还坏了。本来鞋身每朵刺绣牡丹的花心里,要用黄金线缀上五颗小珍珠,凤首衔一颗莲子大的珍珠,最是珍贵。可以想见,这鞋子在多年前也见证过一场宫廷变乱吧。”
“可恨那些没眼力的宫人,只知道抽金线,剥珍珠,并不在乎当初费了苏城来的娇贵丝绸,选了染成十样花瓣颜色的绣线,一个绣娘费了三天,才绣成一朵牡丹。她们更不需记得它在一曲丹凤舞中的风采。只有灵动的舞蹈,才会使死凤凰变活,令假牡丹成真。”老妇人叹息。
“还未请教大人的身份。”雪信随着羽儿称呼老妇人。
“我姓月,明月的月。”老妇人说。
话音刚落,雪信手中的凤头牡丹弓鞋就掉到了地上,她激动地站起来:“大人可是在宫中掌管了三朝乐舞事宜的女乐官?”她曾在内教坊甲库的历年人员调动升迁记录总册上见过这个名字,月环瑶,她的事迹写在本朝新编账册的第一页上。雪信因为害怕确认了自己的低贱出身,不敢查下去,所以不再坚持出宫来找这位可能知道许多掌故的女乐官,没成想,她不愿找的时候,自己却撞到女乐官的门上了。
“你也知道我?以你的年纪,恐怕不会关心我们这些老家伙过去的事了。”老妇人淡淡地说,但听得出她还是欣喜的。她的时代过去了,可人们没忘记她。
“但凡学习乐舞的人,谁不知晓月大人的名字。”雪信扯了个善意的谎。
羽儿又慌慌张张跑回来了,抱了一堆鞋来,“哗啦”扔在地上,让雪信自己挑。雪信忍着好笑,在里面翻来拣去。都是些陈年的舞鞋,大小不等,形式不一,原本越是装饰得华丽的,如今残破得越厉害,那些素面的练功鞋反而落了个全尸,只是七零八落的,从中找齐一双鞋来很是不易,有的鞋根本只剩了一只。
雪信从中提出一只三四寸长的小弓鞋,骇然:“听说有人买了小女孩教习歌舞,学舞前先要把脚趾折断,用绫子缠裹,不许脚长大。习成后,穿上尖尖的小鞋子,在六尺高的金莲台上起舞,我以为是编出来吓唬人的。居然,真的有这样小的鞋子!起舞的人,岂不是步步都踩在刀尖上吗?那女孩子长大了岂不成了残废,这辈子再也跑不动了吗?”
月大人又叹了声:“如今这年月,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都可能是真的。世风奢靡,乐舞盛行,本来是好事,可在家中蓄养舞姬的一多,那些人便以为自己也能折腾乐舞了。他们不但乱改曲子和舞步,还怂恿舞姬们作些低俗危险的表演,舞姬们为了讨得主人欢心,也心甘情愿自残。凡事都有个成住坏空,它要坏了,谁都拦不住。”她并没多少抱怨,平静得像面对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
她又说:“我留你,是因为你身上除了有些香气,并没有残疾。你的身体、你的灵魂还知道逃跑。”她以为雪信是从大户人家家中逃跑的舞姬了。
月大人起身,摸索着走进自己的卧房里。她走得熟了,没撞到任何家什,只听见钥匙开箱子的声音,不多时就捧着一双鞋子回来了。鞋子虽也是旧的,却明显没有被穿过,鞋底不脏,只是微微泛黄,鞋面是粉色的,也许绣了一只蓝黑蝴蝶吧?说也许,是因为那蝴蝶实在不像,轮廓古怪,针脚也乱糟糟的。
“眼睛看不见,摸索着绣的,你若不嫌弃,姑且套一套吧。”月大人递过来鞋子。
雪信哪里敢说嫌弃呢,她接过来试了试,不肥不瘦,除了鞋面的蝴蝶丑了些,大小是正合适的。
“今晚你和羽儿睡。早些歇息,不要多想什么。”月大人又走进卧房了。
羽儿给月大人打了洗脸水出来,对雪信不好意思道:“我睡觉磨牙说梦话,你可别嫌弃。”她又给雪信打了水,洗掉脸上手上的血和灰土,找了自己的衣服让雪信换上,还问雪信吃了没,又把人拉到厨房,从纱柜里搬出几碗中午剩下的菜来。
雪信早饿了,可是一看粗糙的碗盘,碗底飘着油星的汤,还有那黄黄的粟米饭。她按了按肚子,说不饿,只是累了。
不知道自己的一香炉有没有砸死苍海心,他到现在还没追来,是不是已经死了?沈先生下令谋害太子,为什么故意露了那么大的马脚?雪信是个心事重的人,只要有没想明白的事,她就会睁着眼睛想一夜,想不通时睡不着,想通了依然睡不着。她听着羽儿的磨牙和咂嘴声,捱到了平明。
羽儿的习性倒是和鸟儿一样,不爱睡懒觉,起得早,越早越欢快。天灰蒙蒙亮的时候,她便站在院子里练声了,清亮高亢,婉转低回,比鸟儿的啼鸣还好听。谁听了这不染尘埃的妙音,都会幻想声音的主人会是一位怎样灵动的佳人。看来月大人离开内教坊后,也不肯闲下来,哪怕对世事抱了伤心的态度,也愿意把婢女教成一名上好的音声人。
又练了几曲,羽儿提水生火,熬粥切咸菜,忙个不停,伺候月大人和客人吃了早饭,又挎着篮子出去买菜。
雪信饿得饥肠辘辘,耐着饥火,喝了一碗白粥。
月大人问雪信:“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有什么亲人可投靠吗?”
“在华城还有亲人,可既然把我送出来,就没想过我还能回去吧。”雪信没有拿被庶母卖掉的老谎话骗人,她望着月大人,忽然拜倒说,“请大人收下我吧。我愿和羽儿一样做您的徒弟,侍奉您。”
“羽儿不是我的徒弟。”月大人说,“什么师徒名分都是玩笑的。做徒弟的又有哪个是真心侍奉师父呢?还不是盼着讨好师父把绝学传授了,早日取代了师父吗?羽儿是我的婢女,她和我搭伴过日子,能相依为命一天是一天。不过,我也是越来越怕,若有一天我死了,那些乐舞的正宗也就此失传了。能学就学去,不必拜我作师父。”
“我能学?”雪信没想月大人先拒绝了她,又爽快地答应了她。
“你能不能学,舞一段来,我就知道了。”
雪信看着月大人的眼睛,迟疑着不说话。
月大人自嘲道:“你在想,我这个老婆子眼睛看不见,不会分好坏了吧?”
她领雪信走到院中东排一间库房门口,用腕上的钥匙开了门进去。房间正中摆着十几面鼓,墙角的箱盖上斜躺着琵琶、筚篥、横笛等乐器。她打开一只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舞衣来,叮叮当当,缝满了铃铛。
“过去,我会让女弟子穿上半透轻纱,好好看清她们衣裳底下的动作。现在我不能看,却还能听。这件舞衣本是北狄女神巫的法衣,衣上缀有七十二只鎏金银铃铛,每只发出的声音有细微不同,你穿上它,赤足踏在鼓面上,一举手一投足,宛在我眼前。”
雪信看着散布的鼓面,圆圆的,平展展的,如一张一张荷叶,在上面作《踏莲曲》是再合适不过的,其实踏莲舞本就脱胎于前朝的盘鼓舞。鼓面比荷叶还要稳定结实,不需要花太多气力就能稳稳立于上面。她依言,换上金铃舞衣,脱了鞋袜踩上鼓面,却发现并不似她想的这般容易。
北狄游牧部落的人都喜欢结实沉重的东西,连舞衣上的铃铛也打造得沉甸甸的,七十二个铃铛挂在身上整个人似乎顿时被坠矮了几分,很难舞出衣袂飘飘的仙人之姿,只是在鼓面上来回跳跃,也花费平时所用力气的好几倍。
不过,到底不用担心鼓面会像荷叶一般倾斜翻倒,就算稍有晃动,也能很快稳定下来。她跃起,落下,宛如蜻蜓点水般轻盈,她在鼓面上的滑步,也只如衣裙扫过地面,动作柔缓时,由动入静,忽然停住,身上的铃铛微颤,发出细小琐碎的杂音,像夏虫低语,可到了节奏分明处,铃音分外铿锵,如雨声打在荷叶上,居然别有意趣。
雪信可惜着,想她上一回跳这支舞时,身姿轻曼如云中飞燕,若自己在宫里没挨那顿打,没受过伤,此刻能将鼓声和铃声控制得更好些吧?那时候,只有她看不起人,哪里轮得到别人挑剔她。
雪信偷偷看月大人的脸色,是柔和的,含着淡淡的笑意,这样她便放心了。可是月大人怎么还不叫停呢?路远无轻担,何况她坠了一身金铃铛,本来就觉得吃力了。渐渐她力不从心了,舞姿僵滞,脚下踏漏了一步。月大人是真能听出来的,脸色一下阴了,像在一桌美味珍馐里挑出一只死苍蝇。雪信心里一慌,脚下更乱了,一步踏空,竟然从鼓上摔了下来,“哗啦啦”的满地金铃颤响,像一下摔碎了个瓷美人。
月大人几步便准确地走到雪信摔倒的地方,把她拉起来,厉声责问:“你怎么回事?跳着跳着就失魂落魄,若在御前表演,你摔下来,你所在的整个班都活不成了!”她比雪信还痛心疾首,甚至忘记了雪信不是教坊子弟,没有什么御前表演的机会。
“是我冒失了,让我重来一遍吧。”雪信凄凄惶惶地说,这一阵她受的打击够多了,没想到现在她会废物到连一支舞也跳不好。
“不必了。你连跳完一支舞的力气也没有,再来一遍也一样。”月大人听出雪信气力不足,加上心有旁骛,才会摔了个一塌糊涂,“不过,开头一段还算不错,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意境是有了,可还差一口气。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你的舞只是尽力舒展身姿,炫耀技艺,反而比不上东市上攀杆蹬缸、西市上吐火吞剑的百戏家们有精神。”
雪信一听,自己被说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放在以前抬腿就走了,可今日她是下了决心要留下来的,便准备再次恳求。可月大人话锋一转:“没力气,可以慢慢练;没感触,总有一天会悟的。找个有根骨有底子的人教,总比再去选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容易吧。何况,女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娇柔可爱的,长大了却什么千奇百怪的性子都出来了,还不如找个已经有了性子的,没那么容易变坏。”
“谢谢师父收留。”雪信听着话里的风向,忙不迭改了称呼,琢磨着要不要行个拜师礼?她记得在华城沈先生门下,没有办过正经的拜师收徒手续,只是跟着回去,住下就算了。
月大人说:“不必叫我师父,你和羽儿一样,也只是与我搭伴过过日子,令我不用整日老怀悲凉。以后,你叫商儿吧。”她没有问雪信的名字,而是重新给了她一个名字。
雪信这也才明白,羽儿的名字,不是来自飞鸟的翎羽,而是音律中的宫商角徵羽。
羽儿买菜回来,高兴地直嚷:“今天运气好,张屠户便宜卖了我一根带肉的大骨头,一会儿我熬了高汤,给大人做面条吃。屋后我种的葱长得可好了,拔两根剪在汤里,更香。”
月大人对羽儿的大嗓门是听见一次教育一次的,可羽儿就是改不过来,因为月大人的教育总是不痛不痒。
“给商儿另做一碗全素面,不要放葱,不要放荤油。”月大人淡淡地嘱咐。
羽儿还没闹明白商儿是哪儿冒出来的。
月大人又无奈地说羽儿:“我说过,切葱之刀,不可以切笋;捣椒之臼,不可以捣粉。你啊,勤快的时候是勤快,懒的时候又懒。你用切过葱段的菜刀切咸菜,吃素的人是不会碰的。”
“大人,咱家就一把菜刀……”羽儿瞪圆眼睛,“我都用水冲洗过,闻着没味道了啊。”
“再去买一把,分开放,别搞混了。”
“那做面条,也用两个锅吗?”羽儿又请示,“咱家就一口锅。”
“再去买一口。”
“切菜的案板……”
“买去。”
“大人……钱不够啊。”羽儿嘟囔。
雪信把羽儿拉到正堂外头,摘了腕子上那只嵌着三色宝石金镶玉的镯子,递了过去。
“这个能卖多少钱?”羽儿接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真漂亮,不会是什么家传宝物、定情信物吧?卖了可惜,我看着都舍不得。”
“你喜欢就拿去戴好了。”说着雪信又抹下悬在手腕的一条丝绳,“把这个卖了,也能换不少钱。”丝绳上穿着几颗白腻如鹅脂的玉珠。
“这个你给我了?这么贵重,不行不行。”羽儿捧着镯子一副喜欢又不敢要的模样。
“我以后长住下来,怎么好意思白吃白喝?镯子当是见面礼,玉珠就暂且贴补贴补家用吧。”雪信也觉得自己到处给人添麻烦,才进门就让人翻箱底给自己找鞋子和衣服,住下来的话更需要额外给她添一套炊具,还让这个实心眼的婢女挨了批评,她过意不去,只好拿礼物小小地安抚一下了。
羽儿放下菜篮子,兴冲冲地上街给玉珠找买家了。
走回正堂,雪信问月大人:“我并没有告诉大人我吃素,大人是怎么知道的?”
“你身上的的香气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得到这样的体香,需要自幼服用香料,吃全素。前朝,曾有外邦进献给那时的皇上两名美女,身上也是带着这样的香气,可惜不得宠爱,宫中也没继续供给她们服食的香料,渐渐地香气就散了,与常人无异了。”月大人说,“在我这里,只能照顾你继续吃素,你若想保持体香不散,只能回你原来的地方。”
“我若回去,不是白跑出来了吗?”雪信当然舍不得香气散尽,像是一份伴了她十余年的骄傲被剥夺了,可为了维持体香而回去,才是真正丢掉了骄傲。
“那么从今天起,你每天早上把厨房里的水缸注满,夜里睡前把水倒空。”月大人承认她是家里的一员了。
月大人对雪信的期望不可谓不高,她只教羽儿唱歌,多数时候羽儿依旧在做婢女分内的事,而分派雪信的家务,是要她练出气力来。
雪信晨起与羽儿一同练声,羽儿买菜做饭,她便挑水洒扫。午饭后,羽儿陪月大人去外教坊走走,雪信在家中练舞。夜里羽儿没事儿了,雪信还在记谱练琴。
据说两个外教坊,左右分工不同,左擅歌,右工舞,可见术业有专攻,能专精一样便不错了,可月大人偏要培养个全才出来。
雪信就这么住了下来,家里的屋子虽破旧了,地方却很大,许多空房间被当作仓库存放教坊淘汰丢弃的旧东西,也只有月大人才会对这些常人眼中的破烂恋恋不舍吧?雪信和羽儿合力收拾出一间屋子,让雪信搬了进去。
那天夜里,雪信从库房里捡了支笛子,擦干抹净后,抵在唇边试了试,一丝声音也无。曾经看秦王世子苍朝雨吹笛子,易如反掌,随心所欲,只要他一吐气,音律就源源不绝地从笛管里流淌出来,却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难,不会的人连一丝声音都鼓捣不出来。
羽儿鬼鬼祟祟地在门边张望,轻轻叫:“商儿?你忙着吗?”
雪信忙收了笛子,她试吹笛子,憋得脸红头晕,还是不出声,觉得很是丢脸。
羽儿蹭到她身边,往雪信手里塞东西。那是个再粗糙不过的瓷盒子,里面盛的也是廉价不过的胭脂。
“我攒了三个月的工钱买的,自己舍不得用。看你随便摘下的镯子就知道,你以前待的地方用的一定都是好东西,可是到了这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若不嫌弃,就拿去吧。”
女孩子之间若频频相互馈赠妆奁之物,再不熟的两个人也能迅速成为闺蜜的。
“有件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羽儿看雪信痛快地收了礼物,扭扭捏捏地提了个请求。
月大人的左邻,是当朝宰相李弗岺的别宅。李弗岺是皇上身边李昭仪的父亲,他还有个儿子,也在朝中做着什么官。李家的儿子前不久与父亲吵架,搬到别宅住,每日清晨听见羽儿的歌声,如痴如醉,听了几天后,在一个早上溜到月大人门前。正巧羽儿挎着篮子出门,李家儿子便向羽儿打听,府上是不是住着一位歌喉玉润的娘子?能不能冒昧求请一见?羽儿望着俊俏的李家郎君不敢说自己便是每日早上唱歌的,矜持地点点头,答应回去传话。
过了一日,李家的儿子又在门外等着,羽儿故意粗哑了嗓子告诉他,娘子同意与他隔着墙说几句话。到了夜里,羽儿在墙根下冒充李家儿子幻想中的那个美女,她对自己如珠如玉的嗓子还是有信心的,与对方聊得很是开心。他们隔着墙聊了一个月,李家儿子又提出想见一面。羽儿怕他失望,以礼法推脱,推了好几天了,李家儿子越来越着急,说羽儿再不答应,他就上月大人门来求娶,成了一家人,总能相见了吧。
雪信听了就笑了:“那你就等他来求娶好了。”
“不行不行,那不是打闷包,骗人吗?”羽儿急忙摆手。
“那你就以真面目示人,是死是活,由他去。”
羽儿用脚尖搓揉地上的灰土,看来是舍不得。
“那你要如何呢?”雪信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女人还是不爱上什么人好,苦蜜参半的滋味不仅折磨着自己,也让旁人不消停。
“我想要的也不多啊。我只想隔三差五地与他隔着墙聊聊天。我不想骗他,也不想他再也不来。你替我去,让他看一眼,看一眼就回来,不需同他说话,可以吗?”
雪信不客气地戳破她的梦想:“怎么可能,男女之情怎么可能安安分分地在一个地方止步不前。不满意的,掉头就走;满意了,就会越加求之若渴,思之若狂。下一步不是要求你去他家中私会,便是向月大人求娶。你还是绕不过去的。”
“如今都火烧眉毛了,还是先顾眼前的吧,过了这一关,就又能拖上些日子。我去和大人说,我也要习舞,勤动少吃,也练出个玲珑的身段来。我已经准备起来了!”羽儿说着,指着自己的腰。她的腰带勒得紧紧的,拼命想要束出个楚腰来,反而显得上下两端更肉鼓鼓的了。
羽儿那憧憬无限的样子让人不忍拒绝,雪信随着她走到墙根下。羽儿早在那里准备好了一架梯子。她先低低咳嗽了一声,墙那头有个男声惊喜道:“是羽娘子来了吗?”也是低低的,如同耳语。羽儿把梯子架上墙头,扶好了梯子,雪信“咯吱咯吱”地顺着梯子爬上去,扒着墙头往外看,见是一个圆领袍服的男子,斯文俊秀。她向他笑了笑,又缩回头,从梯子上下去了。
墙外,那个男子一迭声地叫羽娘子,声调里尽是惊喜。
羽儿藏好了梯子,贴着墙小声说:“偿君一愿,点到为止,莫再提非分要求了。”口气与她平日里说话大相径庭,怪不得她一会儿是羽儿,一会儿是羽娘子。墙外的男人也没听出来,也许是骨子里就不相信一个粗眉大眼又虎背熊腰的丫头能唱出如此清妙的歌声吧。
雪信走回自己房里。这间新布置的屋子里还有灰尘的气味,不是一两天的洒扫擦抹能去掉的。放眼看去,一点都看不出这是女儿家的闺房,没有甜润的熏香,也没有一个能让人坐下就消磨掉半天时光的妆台。房间里有一面有背钮的小镜子,都花得照不清人影了,也是从月大人的仓库里淘来的,也许是当年舞姬们在场间补妆用的吧。
雪信打开胭脂盒子,一股南方柚花的香气从中传来。柚花香气馨烈不输茉莉,在岭南,柚花是不值钱的,但做成胭脂,从岭南到安城,跨过千山万水地运来,还是会比本地香花制作的妆品贵些。她用银簪子挑了少许,对着镜子匀在唇上,从镜中被月光照冷的一抹红艳里找到了在儿时第一次涂抹胭脂的记忆,那时的她笨手笨脚的,寄希望于一盒胭脂能让一个小女孩瞬间变成千娇百媚的美人。天底下哪有这么神奇的胭脂呢?可是大家都相信有,还不停地找,不停地试。也许现在手头这一盒就是了,只是一点点红,就让苍白憔悴的脸生动起来了。
雪信拾起竹笛,对着书上画出的手势按住上面的孔窍,又是使劲吹,这回好些,发出了嘶嘶的漏风声。快了,马上就能吹出声调来了。她听见身后有人笑,是那种忍俊不禁的笑,带着善良的恶意。
一回头,她看见了玄河。
玄河蹲在窗外,扒着她的窗户,笑眯眯地看着,见她回头,便打招呼:“学吹笛子呢?”在一连串突变后,他突然冒出来,怎么还像是上午才见过一样?
雪信把笛子藏在背后,奔过去问他:“你怎么找来的?你也信我是谋害太子的同谋吗?”
“当然不信,如果那也算谋害。说到找你,那也费了好一番周折。你失踪了,自然先去越王二公子家里找,他家里没有,又派人去往华城的路上来回找,又满大街撒人找,谁知道你会跑来女乐官家里呢。因为怕被株连,所以你吓得连门都不敢出了吧?”
据玄河说,他那几颗玉珠孔芯里涂了曼陀罗花粉,他是用蜜蜂找到了收玉珠的首饰铺子,又顺着首饰铺子伙计的形容找到了羽儿,跟着羽儿找来的。
“他没事吧?没被我敲死吧?”这个“他”指的自然是苍海心,雪信还是有些提心吊胆。
以苍海心的鼻子,到街上走一走就能循着气味过来了,他不来,要么是被敲坏了脑子,要么是被敲死了。
“那个人,”玄河又笑起来,“我看见他时,包了一脑袋白布昏睡着。不过我试了试他的脉,一点事都没有,大概是不想见我,才装重伤不醒。”
果真有他说的那么轻松吗?
雪信疑惑,又问他太子被谋害到底是怎么回事?崔婕妤还好吗?
玄河便说了他所知道的、他推断的。有人在太子东宫中打篆用的香末里作了手脚,掺入雄黄与雌黄,二者混合共烧生成砒霜,散在烟中的毒性不大,但长久吸入,毒性在体内积累,不消一年太子也会咳血而亡。
这回太子随皇上到长生苑秋猎,身边有个宫女劳累脱力,又感了风寒。她听说香灰也是药灰,被烧成灰的药材也存药性,那些江湖术士动不动便给病人喝香灰水,也有治好的。宫女生病也不是大事,省得去请御医,不如先用香灰冲水试试。她一说,太子也来了兴致,亲手挖了一大勺香灰,兑了蜜水让宫女服下,他要验证效果,不想那宫女喝了香灰水不久就七窍流血而死了。东宫的人大惊失色地禀告了皇上,没等大理寺的人调查,另一个宫女站出来,说受了崔婕妤的指使,在香灰中下了毒,说完,拔出金簪刺喉自尽了。
雪信便糊涂了,这说法与她从苍海心那里听来的不同,案子里死了的两名宫女都是死士,一个自己把自己毒死了,另一个站出来指证崔婕妤后也死了。沈先生还是要对付崔婕妤肚子里的孩子吗?可用毒烟除掉太子,岂不是收益更大?为什么舍本逐末呢?
玄河说:“砒霜毒烟的毒性在体内慢慢积累,中毒症状也会逐渐显露,只要太子有任何不适,找御医诊断,用银针刺穴一试,便知是中毒,所以用此法谋害太子,也不会成功。其实构陷崔婕妤,也不是幕后人的目的。腹中孩子还不知道是皇子还是公主,便对太子下手,崔婕妤胆子也太大、心也太急了些。崔婕妤一个半月前便奉旨去长生苑安胎,太子体内积累的毒性却不满一个月。”
“若崔婕妤命人在她搬出永安宫后开始动手呢?”雪信又问。
“那也是可能的。但崔婕妤的承恩殿与太子东宫素无往来,想插手也插不进去,唯一可钻的缝隙,就是你。你是唯一在东宫待过,又去崔婕妤身边的人,而你妹妹曲尘,曾在一个半月前入宫与你相会,宫女被毒死那天,你妹妹曲尘又出现在长生苑,与太子的帐篷相距不远。”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说来说去,依然是我洗不掉嫌疑对吗!你想说曲尘传信,我下手布局,栽赃给崔婕妤,最后曲尘督阵,我得手后跑了,对吗?”雪信怒了,说着就要关窗户。
玄河抬手把窗户支好,说:“急什么。皇上说,幕后人只是想惩罚他两个不听话的徒弟罢了。一个还没到进皇宫的时候就冲进去了,另一个奉命进宫却不肯进去。现在一个躲在宫外不敢冒头,另一个把她的心上人牵连进去了,连秦王世子也成了谋害太子的嫌疑人。”
“秦王世子,也不是不可能吧?毕竟他比太子年长,比太子沉稳,声望也比太子高,有了念头也应该啊。”雪信故意说。
“不可能,秦王世子身有残疾。”玄河的话令雪信大惊,“他的耳朵听不见。托你师父的福,是他下令刺聋的。”
“可是我在他府上住过一阵子,并没有看出他耳朵听不见,他说话应答如常人。”
“他会读唇语,你说话,嘴唇一动,他就知道你说什么了。但你在他背后说话,他是听不见的。”玄河说,“这也不算秘密,只是大家都尊重秦王世子,不愿多提起。”
雪信感到悲凉,当初在秦王世子府里,曲尘一到夜里便要与苍朝雨琴笛相和,原来是自作多情。对方听不到,怎么感受她的心意呢?
“事情总会找个说法了结,但现在还在风头上,不会那么快。”玄河把事情都解释完了,总结道,“所以,也不能把你接回宫里去。你若不习惯住在女乐官家里,我可以帮你换个地方。”
“我在这里住得很习惯。”雪信不想走,她留在月大人身边,期盼得知些什么,又不敢贸然问上去。也许时机到了,那件事的谜底自然会揭晓的吧。
“真的是习惯吗?”玄河把那串白玉珠拎了出来,“你身上没有别的东西好卖了吗?”
“别的东西都不如这串珠子值钱。我想多筹些钱交伙食费。”她不理会他的半含责备半无奈。
“你知道女乐官的婢女用它换了多少钱,这笔钱又够你在这个地方住几日的?”
雪信愕然了一下,她向来只管用,不管采买,珠子价值多少她没个准数,也不知道安城的柴米价钱几何,但眼力是有的,这串珠子足够这院子里三个人省俭着过一年的吧。
“首饰店的伙计看婢女不识货,说是赝品,随便扔给她几个钱,不够你一个人过三天的。”玄河说。
那家首饰店简直是黑店,坑了羽儿不说,又把玉珠抬了个天价,编了个天花乱坠的故事去骗玄河,玄河着急问雪信的下落,没还价便买了。
“可是羽儿回来并没有告诉我……”雪信顿了一下,明白了,羽儿以为她给的是假货,怕回来说了,她没面子,就装着若无其事。这几日她的吃用,都是月大人和羽儿在贴钱。
玄河看她有些黯然,又说她愿意住下也无妨,用钱的事并不是大事。对他们这些没精打细算过过日子的人来说,钱果然不是什么大事,尤其是他这个只要闲逛就领双饷的人,怎么把钱花掉才是个大问题。
“我在这里的事,还有谁知道?”雪信问玄河。
“没了。高兄去华城找了,等他回来我再想想要不要告诉他吧。”他瞥了眼雪信的神情,慢条斯理地说,“你想学笛子,何不来问我?”
“你也会吹笛吗?我只知道安城里,秦王世子的笛子是一绝。”雪信就是不让他满足他好为人师的恶癖。
玄河但笑不语,长臂一舒,从她背后摘走笛子,举起却愣了一下,雪信也看见了,笛子上印着半枚胭脂唇痕,她把笛子抢回来,用袖子抹干净,交给他。 听香录(全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