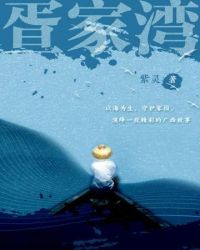“开饭咧!”随着郑大鱼一声大喊,所有拼接起来的船上酒肉飘香,喜庆非凡。过年的气息,就这样降临到了疍家湾。觥筹交错之间,他们似乎把一年来所遇到的苦难与悲伤都忘了,只有彼此间温暖的依靠和欢乐。
苏喜妹坐在席间,开心地看着阿爹,似乎也忘了今天所遇到的不快与纠结。
酒饭过半,花婶朝苏喜妹笑道:“平常都是你的歌最脆,现在可以给大家唱一个了吧?”
听到花婶这么一说,苏喜妹的脸红了起来:“花婶子,你这是拿我打趣呢!谁不知道你才是我们疍家湾的歌后,哪要等我来开头啊?”
“你婶子我真是老啦!要唱,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先来呢!”
“好啦!喜妹,你就别推辞了。哪个不知道,你的歌声是疍家湾里最甜的?唱吧!”郑大鱼也跟着说道。
“那好吧,我就给大家唱一个。”随着她的话音落下,一阵细长的歌声便从船上悠悠飘起:
清水扑面携青甘,
风猛浪大难煮饭。
肚饿望海呱呱喊,
出海寻吃实艰难。
喜妹的歌声刚一落下,郑大鱼便看着她说道:“喜妹,今晚可是小年夜,哪来那么悲的歌啊?咱们唱些好的,明年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大鱼叔,我没开好头,你来吧。”苏喜妹说着,幽幽地低下头来。本来她也想唱一些喜庆点的,不知怎的,开口却把那忍不住的悲伤唱了出来。
她正在低头寻思着,吴二却跟着唱了起来:
虎死虎骨在深山,
龙死龙鳞在深潭。
心中有了不平事,
好比滩头上水船。
他这一唱,更是引起疍民们常年压抑在心底的悲伤,弥漫了好一阵的热闹气氛渐渐消停了。
“你们这是……”郑大鱼刚开口说话,苏老爹便拉住了他:“由他们唱吧!这一年来,苛捐杂税又重,大家风里来雨里去的,很难吃上一顿饱饭。让大伙儿唱出来,心里也好过些。”
听苏老爹这么一说,郑大鱼黯然地低下头,默默地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空。
花婶看着大伙儿渐渐情绪消沉,起身说道:“你们这是怎么了,悲啊,苦啊,平时还唱不够吗?今晚可是小年夜,咱们唱个喜庆的。”花婶说着便开口唱了起来:
阿哥阿妹有情意,
唱个情歌定新人。
亲朋好友来相助,
有心人儿要开口。
她这样一唱,郑福春便明白了个中的意思。他往苏喜妹那边看了一眼,便开口唱道:
哥在海上望妹归,
望见阿妹远路来。
阿妹俏相哥常想,
哥想阿妹口难开。
花婶听到福春开了腔,就急忙扯了扯喜妹,意示她回应。喜妹抿了抿娇俏的红唇,心底却闪过一张白皙的面孔。不知怎的,她远远地遇上了福春的目光,却唱不起来。
苏老爹看了看苏喜妹,又转头看了看郑福春,内心也涌起一阵阵不安。他沉思了一会,开口唱了起来:
住在高山望四海,
疍家阿哥好人才。
若到阿哥堂上去,
阿哥阿妹幸福来。
听到阿爹这么一唱,苏喜妹愣住了。她傻痴痴地往郑福春看去,只见他满脸笑意,看向她的眼神里充满柔情。她转而望向爷爷,苏老爹朝她微微点了点头。苏喜妹低下头,左右看了看,轻声说了句:“今天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说罢便要起身离开。
船上的人都没想到她会提前走。花婶见她要离开,伸手一把拉住她,说道:“喜妹你是真累了还是有了心事?一会儿还要包粽子,你就不帮花婶了?”
苏喜妹朝花婶微微欠了欠身子:“花婶婶,我是真的不舒服。”说着就挣脱了花婶的手,跨过船舷,往自家船上去了。
回到船上,苏喜妹更是觉得心烦意乱。当她听到爷爷要把自己嫁给郑福春,内心里不但没有欢喜,反而感觉到说不出的压抑与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