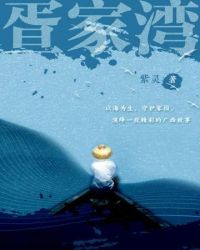此时已是入夜,疍家湾泊船上的女人们早已点上船灯,燃起袅袅炊烟。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鱼鲜味,还有淡淡的糯香。这是疍家湾过年前特有的味道,海鱼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的菜肴。每当空气中飘荡起糯香,就代表着他们正在包粽子,要过节了。粽子是过节时祭祀神灵用的,同时也方便带着出海。
看见他们一行回来了,船上的人都兴奋了起来。特别是小孩子们,一个个像猴子似的从船上窜下来,朝这群人围了过来。郑大鱼他们小心冀冀地从背篓里拿出一些用彩纸包着的糖果,分到孩子们的手上。
苏喜妹看着孩子们拿着糖果,欢天喜地地奔跑着、叫喊着,心里却莫名地多了一分忧愁。她曾经也和这群孩子一样,拿到一颗糖果就会开心一整天,每次只是偷偷地撕开一点纸,到了晚上还会把糖果小心地藏起来,因为这是他们不可多得的东西。可是这次出去以后,她才知道这是县城最便宜的一种糖果,是苏老爹他们唯一买得最多的东西。尽管说最多,也只意味着疍家湾里的孩子每人能分到两颗,每个老人则分得小小的一把。
“喜妹,上船了。”苏老爹在喊她。苏喜妹抬起头来,看到阿爹的眼睛落在正往自家船上搭梯子的郑福春身上,脸上满是喜色。
“噢!”苏喜妹应了一声,踩上梯字上了船,又听到阿爹对郑福春说道:“过了年,你让你妈过来说道说道。”
“知道了!”听到这话,郑福春的脸一红,赶紧低下头来;又朝苏喜妹看去,脸更红了。苏喜妹的脸也红了,朝苏老爹娇嗔着瞟了一眼,转身往船舱里钻了进去。
等苏老爹上了船,郑福春也跟着上去帮着苏老爹把梯子收好。他这才背上自己的背篓,踩着那些头尾相接的船舷,往自家的渔船跳过去。
苏喜妹坐在船舱里,把装在背篓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当她的指尖触碰到那包银子,心底里又是猛地“咯噔”一下跳开了。林浩然那张白皙的脸,如同初春的海藤花,就这么不经意地,一朵朵地闯进她的心底绽开了。
我这是怎么了?苏喜妹红着脸低下头,心想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放下手中的银子,透过船舷上的窗口,茫然地看着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她双手合十,郑重地拜了拜,心里默默祈祷:“三婆神,是不是我的魂丢了?”
每当一个人魂不守舍的时候,老人们就会说,这个人的魂丢了。看来这次出门,自己一定是把魂丢了。祈祷完毕,喜妹把那包银子小心翼翼地收好。
这时却听到船外有人喊她:“喜妹,在里面不?”
“在呐!”苏喜妹应了一声,拉开窗帘探出头去。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妇女撑在相邻一条船的船舷上,冲她这边喊着话。这个人正是花婶,郑大鱼的媳妇。
“花婶婶,你怎么过来了?”
“饭做好了,等一会跟你爷爷过来一起吃饭。”
“好!知道了。”
在疍家湾里,大家彼此之间总是相互照应着。这家忙着,没有空做饭,另一家做好了就会喊着他们过去一起吃。不过今天是小年夜,按照往常的惯例,疍家湾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吃饭。今天没有外出的男人们,早早地就把十几条船横排着拼在一起,每张船上都围坐着一圈人。
等苏老爹和苏喜妹他们到了花婶船上,就听到了船上已人声鼎沸,外出的渔民都回来了。渔船中间摆着大大小小的盘子,装的都是刚刚煮好的鱼、虾、海菜……都是海上能抓捕到的东西。看到苏老爹他们过来,郑大鱼立刻把苏老爹让到中间的位置坐下。
苏老爹从背后拿出一个油纸包递给花婶:“这个,拿去煮煮!”花婶拿过来打开一看,那是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唉哟!这是留着过年用的,哪能这时候吃呢?”
“过年时候也是大家一起吃,现在也是大家在一起吃,都一样,都一样!”
“那我就拿去了?”花婶手里拿着猪肉,眼睛却瞟向郑大鱼,有点犹豫。郑大鱼朝她微微点点头,花婶这才拿着猪肉往船尾的厨房走去。由于条件的限制,猪肉对疍家人来讲是一种奢侈的食品。
这时候,海岸上又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初一拎着个竹篮,在疍家棚旁边的小菜地里摘青菜,身后跟着一帮小孩在吵着闹着,要他讲县城里的花灯、鲜果,还有那令人垂涎欲滴的小糖人……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疍家人在海上为生,船便是他们唯一的家。后来为了生产生活的方便,疍民们便在依岸临水的地方建造房子,植木为柱、架栋为椽,上覆竹瓦、围以竹壁、地铺木板,被陆上的人称为“疍家棚”。疍家棚的面积一般在四十平方米左右,外观有点像少数民族的吊脚楼。疍家人虽然上岸建起了疍家棚,但船艇还是他们主要的家。疍家有举家随船出海的传统,俗称“家口船”;船艇是流动的家室,棚户则是基地。平时,疍家棚以老弱病残孕者留守,仅逢年过节或遇婚丧大事,才合家聚宿在疍家棚。
日常在疍家棚居住的人们,为了让长年出海的人吃上青菜,便在海岸边开辟一小片土地,种上一些蔬菜、瓜果之类的东西。由于海边的泥土均为咸涩沙泥,无法种植这些东西,疍民们便到附近的山上一点一点地背来泥土,慢慢累积起来,这才种出了一点东西。所以青菜跟猪肉一样,在疍家人眼中尤为珍贵。
初一摘得青菜,便拿到郑大鱼船上交给花婶。这才耐着性子,把城里繁华、热闹的气氛,给小孩们添油加醋、慢悠悠地渲染讲述了起来。不过,他把受到那两个无赖欺凌的事瞒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