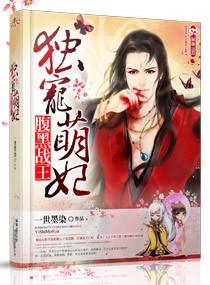圣旨一下,大昌一片震惊,宫妃从未有过流放之罪,更无流放之后还被召回的先例。
只朝中无人反驳,即便民间仍有卫道士深觉不妥,却是诉诸无门,只得悻悻作罢。
关培亲自带了亲信护送了一辆空马车回去,因着此番奉旨入京,声势十分浩大,路上竟也被旁人盯上,射了封信过来,却是要递给安息十四公主廖天吟的。
关培不敢声张,仔细收好,打算先禀报轩辕琤再做打算。
张皇后被困在坤仪宫,虽保住后位,张航却始终没找到机会与之相见,他越发谨小慎微,原先大逆不道的念头,经此一番,颇有些偃旗息鼓的打算。
眼下张皇后经着此事,便是日后膝下有子嗣,也会受牵连,先前费心思营造的名声,彻底毁了个干净,即便此时有空子可钻,朝臣也未必愿意一个有污点的太后上位。
张航自觉大势已去,前程无望,未避免再出岔子,倒不如干脆借着守孝,彻底退出朝堂。
他这厢正事无巨细,仔细思索,谢家却是发生了大事。
起因是谢孟一个开了脸的丫头生了个女儿,长相酷似谢含仪,崔氏一瞧就魔怔了,非要抱到自己院子里去,侍妾不肯,竟被崔氏生生打死了。
谢孟大怒,非要崔氏偿命,谢老夫人呵斥不住,竟是直接报了官。
谢孟颜面扫地,对母亲横眉怒目,立刻便被御史参了一本,轩辕琤将人招进宫命张尽忠骂了半个时辰,谢孟自宫里出去的时候,脸色难看的厉害,眼神凶悍,全然不似一个文雅读书人。
待回到府里,谢孟不好与谢老夫人发作,便将崔氏关进柴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受尽羞辱。
崔氏奶嬷嬷耗尽了积蓄,才央着一个年轻后生往昌宁伯府去报信。
昌宁伯细细思索,如今谢家大势已去,谢栖迟即将回朝,谢凤还更是前程似锦,此时与谢孟沾染关系,无异于自掘坟墓。
何况谢氏兄弟曾在崔氏手上遭受颇多磨难,此番扬眉吐气,怕是不会善了,崔氏出自昌宁伯府,若不及时撇清关系,极容易被牵连。
昌宁伯打定主意,便命人唤了崔正奇来,他自己是不想做这个恶人的,然而这庶兄的长子听说曾被谢常安欺辱,也被崔氏算计过,这现成的机会放在他眼前,他难道不会把握?
昌宁伯一脸愁苦:“侄儿来,你可听闻你姑母家的事情?”
崔正奇想起上回崔氏要他做替罪羊的事,心里只觉得痛快,面上堪堪维持住不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俩,他微微垂头:“侄儿最近闭门研读诗书,并不知外头发生了何事。”
昌宁伯一笑,眼底不屑一闪而过,这崔正奇虽说出自崔家,却着实不像是世家出身,学业上不见成绩也就罢了,活了这么些年,竟连权贵子弟也不曾结交一个。
活生生草包一个。
昌宁伯叹了口气:“你姑母近些年顺风顺水过的痛快,这些日子却是频频受挫,眼下与你姑父闹了起来,托人来报信,让咱们府里去接人。”
崔正奇隐约明白了昌宁伯的意思,也不说话,只垂首听着,一副恭敬模样。
昌宁伯不耐烦起来:“你姑母都这个岁数了,还要回娘家,也不怕旁人笑话,再说夫妻间的事情,不过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咱们也着实插不上手,你去劝一劝,让她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崔氏原本儿女双全,如今一死一残,残的还丢了,重击之下已然有些疯癫,即便是被关在柴房里,也不觉得如何,整日只想着以往,想谢含仪坐在闺房里绣帕子,想谢常安出门还不忘给她待点心。
这一番浑浑噩噩,待回过神来时,已然几天过去,奶嬷嬷偷偷送来的包子都硬的咬都咬不动了。
崔氏饿得蜷缩起身体来,缩成一团,靠在柴草上。
崔家来人时,奶嬷嬷高兴的一路小跑了过来,隔着上了锁的柴房门喊崔氏:“太太,太太,咱们府里来人了,您的苦日子就要结束了。”
崔氏茫然的点了点头:“嬷嬷,你的卖身契在我床头暗格下边,你带着你那一家子,都在里头,你去官府消了奴籍……”
奶嬷嬷心里一跳,却是止不住欢喜起来:“太太,这可真是……”
崔氏没看她,仰着头看柴房简陋的屋顶,外头的光照旧亮的很,自屋顶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她身上,反倒越发让人看不清她的神情。
奶嬷嬷一时也顾不上许多,匆匆去拿了卖身契消奴籍,待他回来,便瞧见崔正奇往正房里去了。
想必谢孟也顾忌着脸面,宠妾灭妻可不是什么好名头。
即便是轩辕琤,也时常因此被诟病,千百年后,怕是会成为他不可抹去的污点。
只是即便回到了正房,崔氏的脸色也没有变化,她将枕头抱在怀里,一下一下的拍,神情难得温和。
崔正奇仍旧恭敬的喊了一声姑母。
崔氏侧头看着他,眼神忽的狰狞起来:“你怎么自己来了?安儿呢?他是不是在你哪里?你怎么不带他来见我?!”
崔正奇推开扑倒自己身上的崔氏,伸手弹了弹衣摆:“姑母是糊涂了吗?谢常安早就不见了,兴许是从马车上掉下去摔死了,兴许是自己逃走后摔死了……”
崔氏满脸狰狞:“闭嘴!闭嘴!闭嘴!我的安儿不会死,该死的是你们,是谢栖迟,是谢凤还,我的安儿不会死,他不会死!”
崔正奇嗤笑:“姑母,你这是真疯了还是装疯呢?”
崔氏还在念叨那句话,满脸癫狂,崔正奇上前一步,声音压低了些:“姑母,不管你是不是真疯,崔家都不会管你了。”
崔氏动作一顿,崔正奇继续道:“你们兄妹的性子如出一辙,都是十足的小人,你当初仗着谢家的势对崔家诸多挑剔,如今谢家倒了,伯府却还屹立着,以昌宁伯的脾性,你该知道,他会如何决断吧?”
崔氏死死抓住手边的被子,几乎要将被面扯破,将里头的棉絮扯出来。
崔正奇后退一步:“姑母,你如今墙倒众人推,若想活着,只能靠自己,我举步维艰,可你已经无所顾虑,何必再这么窝囊?”
崔氏仍旧垂着头,哆嗦着身子扯着身边的棉被。
谢孟自外头进来,身边还带着个娇怯怯的美人,瞧见崔正奇,也没有给个好脸:“你若是想把人接走,那就赶紧,我随后就将休书奉上,若是任他自生自灭,你一走,我就把她送到家庙去。”
崔正奇弯腰拱手:“大人说笑了,既然嫁入谢家,那就是谢家的人,如何处置,叔父的意思是,莫要伤了两家的和气。”
谢孟没想到昌宁伯是这么个意思,一时间竟有些回不过神来,等崔正奇走了,他才看了一眼崔氏,也不知想起了什么,竟也没再发作,甩袖走了。
崔氏的日子却并未因此而好过多少,谢孟自通山书院下来之后,似乎就明白自己的仕途到了头,也懒怠再走动关系,只顾自己痛快,短短几天功夫,竟连着抬了七八房小妾,且都是府里的丫头,先前曾被崔氏整治过的也不在少数,此次一番身份变故,皆是卯足了劲要报复。
崔氏奶嬷嬷消了奴籍,带着一家老小回了祖籍东山县,之后便没了音讯。
至此,崔氏身边得用的,算是没了,府中人知晓她如今失事,也没了儿女娘家依仗,作践起主子来,十分猖狂。
谢老夫人出面斥责几回,谢孟充耳不闻,兴许还记着上回谢老夫人报官,让他丢了脸面的事,态度十分不逊,谢老夫人一怒之下搬去了侍郎府。
府中没了压制,彻底闹腾开来,不过几日便听说崔氏坠湖,险些一命呜呼,又被人救了起来。
谢老夫人前去探望,与大理寺新上任的寺卿胡子怡在谢家门口碰了头。
胡子怡隔了马车问好,谢老夫人一愣:“真是贵客,大人所来是……”
她心里觉得不好,问得便急切了些,胡子怡不曾在意她的失态,只含糊道:“一些琐事,不敢劳老夫人挂心。”
大理寺寺卿亲自登门,怎么可能会有小事,谢老夫人虽早有准备,心下却仍旧有些慌乱。
“既是公事,老身就不打扰了,大人请便。”
胡子怡道了谢,也未推辞,径自带着人进了谢家,老夫人脚下不稳当,嬷嬷连忙扶住她:“当心,什么事也比不得身子重要。”
谢老夫人摇摇头,心道这回怕是大事……
她还未将心中猜测说出半个字,便瞧见大理寺的队伍中一人瞧着很是眼熟,不由自主的多看了两眼,那年轻人竟是径自走过来对她拱手作揖:“老夫人安好。”
谢老夫人总算想起来这人是谁:“你是……仅儿身边的书童?”
青鸾腼腆一笑:“老夫人好记性,奴才鲜少在府里露面,老夫人也能记得。”
谢老夫人顾不得与他寒暄,只瞧着他跟在大理寺众人身后,便觉得事情不对劲,语气便严厉了些:“你不在侍郎府呆着,跑回来做什么?”
青鸾笑了笑:“奴才来替侍郎办件事,待差事完了,也就回了。”
谢老夫人心下更加忐忑,却下意识不敢问下去,青鸾却是不避讳:“听说府里如今乱的很,侍郎命奴才回来帮帮忙,先前夫人身边缺人手,奴才便帮着跑了跑腿。”
这跑腿,却是去的大理寺。 谢君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