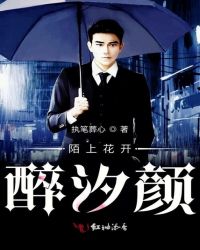“回禀陛下,有一队人马正向行宫靠近。”
陈启源脸色骤变,脱口而出:“再探!”
“报——”斥候匆忙而来,单膝跪地回禀道:“陛下,是留王殿下和李将军。”
闻得此言,紧攥着陈景遂的手,慕思妍显得有点慌张,若是陈景熙趁机发难,她不敢继续往下想,恰在此时,听得不远处传来:“陛下,若不愿看到景宜宫再受战火荼毒,可派商王殿下和王将军带凤台大营的兵马前往迎候。”
瞥眼打量着苏白,陈启源眉头一挑,自觉他说的在理,闷声传令:“景琦、王师钧听令:着你二人领兵宫外接应。”
“诺,儿臣(末将)领命。”
望着二人渐行渐远的身影,慕思妍顿悟,她向苏白投去了敬佩和感谢,四目相对时,她总觉得那双眼隐约的藏着一种别样的情愫,熟悉、陌生,亲切而又冷酷,慕思妍被牵着往大殿内走,犹豫间,她回首又瞧了一眼苏白,映入眼帘的却是他孤寂的背影。
大殿内,陈启源正襟危坐,慕思妍站在陈景遂身旁,远远望见陈景熙风尘仆仆而来,他拱手道:“儿臣拜见父皇,长乐未央。”
“终于风平浪静了。”慕思妍见陈启源缓缓站起身,踏阶而下,朝自己这边而来,只见他轻拍着陈景遂的肩膀,笑道:“景遂,朕知道这几日你辛苦了,原本打算让你休整几日,可朕现在想让你安排一下回銮的事宜。”
陈景遂清楚父亲为何急于回到京都,更清楚他又在试探自己,不假思索道:“父皇放心,儿臣立刻安排。”
“恩,好。”陈启源露出欣慰的笑容,视线转向陈景熙,冷淡道:“景熙,起来吧,一路赶来,定已疲惫,你就将所带兵马的调配权交给景禹处置。”
“这?”陈景熙一脸诧异,心不甘情不愿的应允道:“诺,儿臣遵旨。”
“行了,朕乏了,你们都退下。”
各自散去,众人回了原先居住的庭院。
连日来,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了,陈景遂的腿肚子突然一软,若非慕思妍在旁一把托住,恐怕早就摔倒在地,她关切的问道:“景遂,怎么了?”
“无,无妨。”
慕思妍听得他声音颤抖着,鼻尖一阵酸楚,哽咽道:“走,我带你回去。”
晚间,宫女过来传话,说宸贵妃有请,慕思妍见沉睡中的陈景遂,小声的和茗儿叮咛了几句后,匆忙而走。
正殿内,陈启源歪身靠在垫枕上,闷声道:“宣果南王。”春福不敢怠慢,亲自前往宣传,果南王步入大殿,见陈启源指着凳子,懒洋洋的道:“坐吧。”
“陛下,臣?”果南王欲言又止。
慕思妍见宸贵妃站在殿门前,走近刚想问安,却被制止,依稀听得殿内传来:“景培叛乱,朕寒心不已,他是长子,又是嫡子,朕对他的期许甚高,可他?哎,有勇无谋,心气又高,目中无人,以前干下的那些勾当,朕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倒好直接带兵逼宫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陈启源痛心疾首,手捶打着枕头,叹息道:“养不教父之过,可说到底,是朕以往太过纵容了。”
果南王忙劝道:“陛下,景培大错已铸成,您得保重龙体,大晋社稷离不开您……”
“启崇薨逝,景培谋反罪无可赦,王兄,你看将来何人可入主东宫?”
“陛下,老臣向来不问政事,立储干系重大,老臣岂敢贸然断言。”
“王兄不必紧张,你权当是和朕聊聊家常。”陈启源见南果王伏地叩首,笑着摆手示意他起身,“你觉得安王如何?”
慕思妍听到‘安王’二字,心不免一纠,她透过窗纱瞧见南果王起身,斟酌片刻,犹豫的道:“景遂,仁孝忠勇,这次平叛,他又身先士卒,抵御强敌,保卫陛下和我等周全,功不可没。”
“恩,景遂这孩子平日不声不响,以前倒是朕忽视他了。”陈启源收回视线,闷声道:“经过这件事,朕倒是看清了谁是人,谁是鬼。”
“鬼?”南果王凝视着陈启源。
陈启源向他靠近一点,有意压低声音道:“王兄,你说,景遂对那龙椅到底有没有动过心思?”
南果王身子微微一震,尴尬的笑道:“若说谁对储君之位没动过心思,那一定是假话,不过,陛下何出此言?”
“王兄,你想啊,叛乱平息,行宫守卫又在他的手里,若是他有不臣之心,带兵杀入。”陈启源语顿,抬眼看着南果王,“他大可说朕被叛军所杀,尔后矫旨登基。”
“额?难怪陛下当时不让人开门。”
陈启源突然放声大笑,用力拍着兄长的肩膀。
那笑声传来,慕思妍觉得刺耳,无奈叹息,她见陈启源用眼尾扫视,淡定道,“宣商王、定王。”
南果王一愣,慌忙起身:“陛下,那老臣先……”
“别忙,你且坐下,陪朕说会话。”陈启源脸色变得凝重:“祸起萧墙的悲剧,朕不想再重演,大晋禁不起他们的折腾。”
“那留王?”南果王试探性的问着,可见陈启源双目紧闭,不敢再言。
不多时,慕思妍远远瞧见商王和定王走进去,二人行礼完毕,陈启源又是赐座又是赏点心,嘘寒问暖一番,他就突然问道:“景琦、景禹,朕若是立景遂当太子,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大殿内一片寂静,兄弟俩相视,他们有点吃不准陈启源的心思,不敢贸然开口。
“怎么,你们不赞同吗?”
陈景琦定了下神,跪倒在地,挺直腰杆,诚恳道:“父皇,您是知道儿臣和十弟向来和二哥交好,您突然这么一问,儿臣倒是有些不知所措了。”他笑道:“父皇,您若是觉得二哥觉得合适,儿臣们自然不会异议。”
“景琦,你难道不想坐上这至高自尊的位置吗?”陈启源的视线落在他的身上。
“儿臣?父皇,您可千万别开玩笑,儿臣性子散漫,难当大任。”
陈景禹附和道:“父皇,儿臣也有自知之明,只愿跟从哥哥们为您分忧。”他挠挠头,笑道:“父皇,儿臣年幼,担不起社稷重任。”话音落,兄弟俩像是商量好似的,叩首,异口同声道:“儿臣恳求父皇择贤而立。”
“择贤而立?”陈启源亲自将他们扶起,温和而笑,捋着胡子道:“好孩子,难得你们两有这份胸怀,朕心甚慰。”君臣四人又闲话家常了一番,临末了,陈启源说了句:“恩,朕也困了,景禹,该给你母妃叩头请安了。”
他们朝陈启源一拜,转身而走。
暖阁里,慕思妍见宸贵妃欣喜不已,表面虽开颜而笑,心里却开始担忧,她边斟茶,边想为何他不召见陈景熙,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失了圣心?
“母妃,安好。”陈景禹走上前,郑重其事的拱手贺喜道:“恭喜二嫂,贺喜二嫂。父皇有意立二哥为太子,你就等着做太子妃吧!”
“定王请慎言。”慕思妍俯身施礼,有意压低声线道:“陛下尚未发明诏,一切都未成定数,若是您方才的话传到陛下耳里。”她见陈景禹连忙拍打着嘴巴,连连说‘该死’,不觉好笑,朝宸贵妃施礼,请辞道:“母妃,王爷也该醒,臣媳先行告退。”
她回到别苑时,陈景遂已醒,将茗儿打发走,慕思妍接过碗,边亲自喂他吃粥,边把刚刚听到的、看到的告诉了陈景遂。
慕思妍见他要起身,慌忙摆下碗搀扶,又给他披上一件锦袍,听得一声叹息,知他心中苦闷,相伴站在轩窗边,“妍儿,这几日经历的事,或许比我以往加起来的还要多,鲜血飞溅,尸横遍地。”慕思妍见他牵过自己的手,继而柔声道:“妍儿,若是能重新选择,我甘愿生在寻常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你一起相守终生,平淡生活。”
闻得此言,慕思妍宛然一笑,依偎进陈景遂的怀里,望着外头皎洁的月光,心却变得越发沉重了。
京都外,留守文武众臣以丞相为首恭候天子回銮的,陈景琦封旨接管禁卫军,在李平柏的协助下接管着龙撵周围的防卫事宜,王师钧率凤台大营人马在郊外安营扎寨,等候着撤军的旨意。
进入皇城,陈启源踏阶而上,心在那一刻才算真正的安定下来。
时隔数日,慕思妍站在小池边,似乎并未有劫后重生的喜悦,听闻燕王阖府上下不管男女都被羁押在天牢之中,陈景培也被关进“悔字号”牢房,慕思妍的脑海里顿时浮现了他囚衣铁索蜷缩在石制地板上时的容颜,或许是憔悴、或许是失落、又或许会带点悔意。
“小姐,奴婢听说燕王的舅舅上折子请求削去爵位,以示赎罪。”
荷儿说的事,慕思妍也听说了,好像还是陈景遂帮忙求的情,加之陈启源对已故皇后仍由旧情,不忍对其娘家人赶尽杀绝,国舅爷所递的折子没有被允准,倒是让许多人松了一口气。
望着枯树枝,慕思妍暗自揣度着陈景培的心思,多年来,他都处在争位的风口浪尖,对于皇权的眷恋与执念早已蒙蔽了他的双眼,好似他活着就是为了能够有一日登上那把宝座,他永远不可能像陈景琦和陈景禹一样,向别人俯身称臣。加上这些年来,陈启源的纵容让他变得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或许现在他会后悔,后悔不该贸然起兵,不该争夺,现在他输了,换来的结局只有一个:死。
“妍儿,你怎么站在这儿发呆?”
“殿下,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她见陈景遂眉头不展,犹豫的询问道:“城防营和骁骑营那边的事都处理妥当了吗?”
“二哥现在的身份尴尬,不宜上表保荐任何人,不过,你放心,我已经上奏向父皇荐了几个人,父皇觉得冯海不错,已经接任城防营的都统了,他是以前是王师钧的部下,是个老实人,靠得住。至于骁骑营,父皇把他交给十弟统辖了。”
她见陈景琦负手站在不远处,而陈景禹笑着凑过来,压低了声音道,“二嫂,臣弟这儿先道贺,内廷已下传旨给礼部占卜吉日了,行册立大典。二嫂,臣弟听闻父皇特意下旨,同时册封你为太子妃。我朝能获此殊荣,你可当属第一人了。”
“明日,内廷便会将吉服送来,到时你选一个颜色。”
陈景禹倚栏而坐,“父皇近来身体时常有恙,不能处理政务。二哥,等你入住东宫了,可就能名正言顺地监国了。四哥那帮人再想闹腾都是徒劳了。”
慕思妍见陈景遂默然不答,抬头望向天空,低声唤了一声:四弟。
缓步前行,陈景熙越想越不甘心,他强压着怒火,负手紧握成拳,对于丫鬟仆役们侧身问安一概置之不理,沿着回廊直径奔书房:“退下。”
丫鬟们停下手中的活计,面面相觑,不敢抗命,有序的退到屋外。
木门被关起,陈景熙不再强压怒火,他发疯似得砸东西,一阵阵‘噼噼啪啪’的响声,吓得屋外的丫鬟们连大气都不敢出,慕思娴闻讯赶来,焦急的问道:“郑帼,怎么回事,殿下为何生气?”
“这?”郑帼视线转向书房,拱手犹豫道:“陛下已经下旨礼部挑选吉日,册封安王为太子储君,安王妃为太子妃。今日,陛下又因一点小事责骂殿下,还……”
“还什么?”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慕思娴猝不及防,原本的设想可不是这样的,她一个箭步走到郑帼跟前,抓住他的衣襟。
“陛下还降了王爷的爵位。”
“这?怎么可能,燕王叛乱,殿下带兵救援有功,为何会如此?”
“王妃,殿下带兵救援时遇上了叛军,几番较量后,殿下才摆脱纠缠。我们赶到行宫时,凤台大营的人早已赶到,可能是因为……”郑帼凑上前,压低声线道:“王妃,末将打听过,陛下回宫后秘密召见了李平柏,也不知道他说了些,陛下的态度就变了。”
慕思娴挥手示意众人离开,她推门而入,‘啪’一个瓷罐在她的脚边摔的四分五裂,耳边响起一阵咆哮:“滚,都给我滚出去。”
“殿下,是我,思娴。”她一把将陈景熙抱住,轻抚着他的后背,安慰着他那一颗焦躁不安的心:“殿下,臣妾知晓你心有不甘,可,可你自怨自艾,又有何用?”她擦拭着陈景熙的脸颊,柔声道:“景熙,看到你这样,我的心有多痛你知道吗?”
陈景熙木纳中回过神,看着慕思娴,不觉冷笑,将她一把推开,没好气的问道:“贱人,本王当初以为慕万生死乞白赖的把你嫁入王府,是有心扶持,就欣然答应了这门亲事,呵?可是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朝堂上他处处偏帮陈景遂。”他托住慕思娴的下巴,恶狠狠的说:“同样是女儿,他为何偏心至此?”突然冷笑了起来:“我忘了,你是庶出。”
一字一句犹如一把尖刀插在了慕思娴的心上,尤其是‘庶出’二字,对于她而言,简直就是耻辱,泪水模糊了视线,望着陈景熙佛袖而走的背影,心下暗自记恨,手掌触地时,只觉得一阵钻心疼。
“王妃,不好了。”一个小丫鬟急匆匆而来,气喘吁吁道:“殿下把小世子抱去偏院了,还,还下令说不许您靠近,若谁敢抗命,决不轻饶。”
“什么?”慕思娴连滚带爬,仓皇奔向偏院,见两个兵卒拦住了去路,恶狠狠道:“让开!”她见兵卒们未曾动弹,顾不得手掌的伤,推搡着想进偏院看孩子,突然屋里传来一声哭叫声,她的心被纠了起来,哭喊哀求道:“殿下,你把孩子还给我好吗?”
“闹够了吗,哭够了吗?”陈景熙站在台阶上,冷声道:“滚。”
“殿下,父亲所作所为,与臣妾无关,与孩子无关,您把孩子还给我好吗,他离不开我。”她拼命的拽着陈景熙的下衣摆。
陈景熙肚子窝着一股火气,正没处撒,想踹开她时,一个丫鬟抱住了他的腿,哭泣道:“王爷,您,您脚下留情,免得伤了孩子?”
“你说什么?”
“王爷,王妃有喜了。”
缓缓放下脚,陈景熙的视线转向慕思娴,闷声问道:“她说的可是真?”见慕思娴点了下头,他暂熄怒火,唤来郑帼小声吩咐了几句,“淑儿,扶王妃回去。”
慕思娴被淑儿搀扶起,视线一直盯着院子里,听着孩子的哭声,她仍不愿走,只听得淑儿劝道:“二小姐,王爷正在气头上,我们还是先回去。”
回到苑内不多时,郑帼就领着一个长者进来,拱手道:“王妃,王爷吩咐命刘大夫过来诊脉。”
望闻问切后,刘大夫并未多说什么,跟郑帼一同离开了,没过多久,慕思娴看到郑帼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进来,一把抱住孩儿,泣不成声,抬眼时,她远远望见陈景熙站在苑门口。
“王妃,王爷说:让您好好安胎,至于别的事,您就不要再操心了。”
望着陈景熙离开的背影,紧紧的搂着儿子:深儿,没人能把你从母亲身边夺走,谁都不能。
九月初九,册立太子、太子妃,行太子加冕礼,太子妃授玺。
清晨,太监丫鬟洒水清扫宫径,宫殿两边旌旗烈烈,仪仗森严,乐府众司役早已等候一旁,宗亲文武齐集于浩天正殿。
春福抖动着拂尘,清嗓叫喊道:“吉时已到,宣!起!”
礼乐骤然响起,陈景遂着紫色储君朝服,在礼部官员的引领下,入丹埠,进殿室,缓步近御座前拜位,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事先计算好的,从宫门口道御前一共是九十九步,必须一步不差。
陈景遂跪在蒲团上,双手高举俯身叩首:“儿臣恭祝父皇,长乐未央。”
“宣。”
一个宗亲展开册立太子诏书,高声朗读,陈启源起身踏阶而下,亲自将太子玺绶交到了陈景遂的手里,陈景遂接印,交东宫捧册官后,再次跪倒俯身一连三拜后,挺直腰杆,高声三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储君册封完毕后,新太子入座,接受百官朝贺。
直至辰时三刻,礼乐再次响起,这一回吹奏的已经更换成《有凤来仪》,慕思妍走下马车,抬眸望去,只见陈景遂立于殿前,她独自一人缓缓而上,紫色的朝服更加凸显了慕思妍的雍容华贵,她踏上倒数第二个台阶时,见陈景遂伸手而来,宛然一笑,将手搭在他的掌心。
殿门口,一个太监读着册封诏书,他俩并肩踏入殿内,慕思妍跪在蒲团上,双手交叉叠加而放,她一连俯身三拜,柔声道:“臣媳叩拜父皇,安泰永康。”
“宣。”
春福展开册立诏书,高声宣读,礼部尚书将太子妃金册、印玺交给陈景遂,他又转而交给慕思妍,交东宫捧册官后,她再次跪倒俯身一连三拜,柔声三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午时初刻,陈启源携同陈景遂驾临太庙,父子二人上香敬告祖先,回城时,沿途接受百姓拜谒,场面甚是壮观。
册封仪式的最后是皇帝亲自宣告大赦天下,陈启源在儿子的搀扶下登上奉天阁,慕思妍看着陈启源两鬓斑白,身躯佝偻,颤颤而行,暮气沉沉,父子俩站在一起恍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不得不暗自感叹:曾经何时,陈启源也有过年少英姿,勃勃生机。
回首时,她的视线恰好落在了陈景熙的身上,只见他嘴角抽动着,笑的极为僵硬,双手紧握成拳,看似极为不服,他仿佛是察觉了什么,四目相对时,慕思妍看了一丝刻意,刻意的松弛,刻意的微笑……
一整日的大礼,让慕思妍觉得有些疲累,她环顾颐清苑,想起今夜是自己在这儿的最后一日了,心有不舍。一双手从背后环搂住自己,柔声道:“不舍得了吗?”
“恩,这儿毕竟是?”慕思妍没将‘家’字说出口,耳边响起:“妍儿,雨过天晴了。”
“安王,不,现如今该尊称一声太子殿下了。”一道人影犹如无人之境,笑问道:“您真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帝颜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