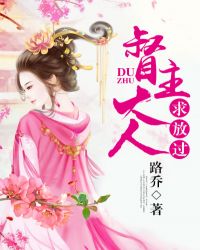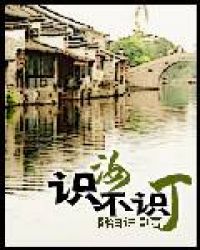都抚司
杨风匆匆走了进来,对着案后的殷绍揖首:“督主,出事了!”
“何事?”
“苏钰儿死了。”
殷绍题字的笔微微一顿,眸底锐利光芒一闪,随即恢复如常:“埋了。”
一句简单的埋了,意味着苏钰儿辉煌的一生永远落下帷幕。荣华富贵也好,宠冠六宫也罢,都已是昨日的尘烟,化作今日的一捧浮土,永远的埋进历史的长河中……
他日,史书记载,寥寥数句,终落笔在“废妃”一词而结束。
室内一时安静,唯有阳光从窗户漏进时,飘浮在半空中的细尘在微微抖动。
“还有何事?”殷绍头也未抬。
杨风一愣,他刚刚有些失神,本以为督主听了苏贵妃的死讯,多少会有些意外。况且,她还死得那般惨。
一夜之间,红粉变骷髅。他也算久经沙场见惯死人,可看见苏钰儿的死状,还是心惊。
谁知,督主竟半点都不感兴趣,连问都懒得问。
不过作为殷绍的属下,即然上司对那女人是生是死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自然不会追问,很快,便将此事抛在脑后。
“喔,还有一事。属下不明白,为何忽然要撤走追杀宁王的人?宁王此次上京带的人手不足,前番被我们和定国公府联手伏击死伤大半,甚至宁王本人都受了伤。为何不乘胜追击?”说着,杨风有些激动。他们也损伤了不少兄弟,才终于有所成就,眼看都快成功了,却忽然要撤离,多少有些不甘心。
“督主,此时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
殷绍终于搁下笔,目光淡然的瞥了眼杨风:“不放,你们也拿不下。”
“不可能,若再加派些人手,定然……”
“如何加派?”
杨风一噎,他们明面上可动的人手根本不够。
“再者,你当真以为宁王只有明面上这些人?”
“我……”杨风哑然,心底却有些不服,如果宁王真有后手,怎么直到他自己负伤都没出现援助?
“如今,定国公府倒台,他那一脉的人自然要撤。你们若一意孤行孤军深入,恐会中他埋伏。”
“可我们已经有兄弟落在他手上,属下担心会泄了口风。若真这样放他进京,万一他在陛下和太后面前挑拨离间,让陛下对您起了异心,可如何是好?”
“他不会进京!”
“为何?”
殷绍冷冷的看了他一眼,杨风一惊,迅速的低头。他竟然在置疑督主的话!
“属下多言,请督主责罚。”
殷绍提笔继续书写,一边淡淡然道:“以宁王多疑的性子,定然以为我会在京师布局,想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杨风心底将他几句话理了理,深觉有理,之前还一路追杀不停歇,眼瞧着马上要进京了,突然全撤了,说京师里没有阴谋诡计等着他,拍死他都不信。
“可万一那些被抓的暗卫嘴风松动,岂不是……?”
“松动又如何?谁又能说这不是陛下的意思?”
杨风:……
督主这是故意的!绝逼故意的!这是要挑起那两兄弟的争端啊!
很快,昭明皇帝接到信息,说是宁王一行临近京城时遭了伏击,便调头回东夷去了。
昭明皇帝很恼火,火速召殷绍进宫,责令其尽快查清谁在幕后坑他兄弟?
太后冷笑,这还用查?自然是定国公那老贼干的好事!至于为何没了后续,当然是因为定国公府被查没了啊。
对于定国公这个千年死对头,即便是定国公府现在已倒台了,在太后娘娘心里,依旧是一根刺。
年事已高精神却抖擞的太后娘娘斜靠在八宝椅上,转着手中的护甲,目光森冷的吩咐下头:“传哀家旨意,苏氏犯人贼心不死以下犯上,就地格决以儆效尤。”
“是!”
虽说昭明皇帝留了他们一命,可她真杀了,他又能拿她如何?
只要一想到当初昭明皇帝登基时的情景,太后想一次恨一次,若非苏老头,今日皇位之上的人选,还待两说。
至此,定国公一脉最终有没有走到边疆,已很明了。
不得不说,太后还是很精明的,这一猜就猜中了。
昭明皇帝很是过意不去,他大体也猜出了方向,老母亲过寿,小兄弟走半路被人截糊了,据说伤得不轻,他很是内疚。早知道当初就不将宁王的封地选在那么远的地方。
正准备派人前往东夷慰问一番,不想,竟接到辽东都司八百里加急线报,道是东夷突然起兵攻打辽东都司,并迅速占领了辽东一域。
辽东都司伤亡惨重,请求支援!
昭明皇帝只觉得啪啪啪不停的巴掌呼在他脸上,呼得他昏头转向,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那脑子有坑的宁王三弟,在半路被人伏击后,竟调转枪头去攻打他的哨防兵线?
他还记不记得他们是兄弟?以及,他遭受的埋伏跟他有个毛线关系?
辽东都司为皇朝左军,原指挥使司苏令远随着苏家的倒台,一并下了狱,后经大理寺卿推荐,选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将士继任新的总指挥使司,名为苏青。
已于月前赴辽东上任。
结果新官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竟与隔壁邻居发生火拼?
不管如何,左军身为皇朝军,昭明皇帝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虽然他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但这股内火要先给灭下去。
他准备等双方平熄之后,将这左军指挥使司和宁王再一同约上京城,大家坐下来和和气气的谈一谈,指不定这内里有什么误会。
只是,昭明皇帝这乐观的想法注定得不到实现。
这边朝殿之上文武百官还在争吵着是集体拔军去东夷灭了宁王那老王八蛋,还是直接宣旨将任职不足两月的指挥使司给撤职查办并向宁王赔礼道歉。
又有新的战报飘进了京师。
一封一封接一封,雪花一样的飘着。
每一封都是八百里的加急信,内容大体相同。
辽东都司沦陷,剩余将士撤出辽东,如今驻扎昱岭关。宁王回到东夷,便拉起了大旗,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向京师挺进了!
清什么玩意儿?
这下,不管是赞成和解的还是赞成狠狠呼宁王巴掌的朝臣都蒙圈了。
历史上,凡着打着这种旗号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都是想“清君”!
说白了,就是打着好听的旗帜谋反!
这清的过程中,如果能一不小心将皇帝也给清没了,那是最好不过的。
昭明皇帝还没震惊完毕,乌衣卫所又呈上新的奏折。
言道,查了两年的科举舞弊案的幕后之人终于浮出水面。
都快要内战了,谁还有心情关注科举舞弊?昭明皇帝不耐烦的将奏折直接给掀丢在一旁。
王安好声好气的去拾了起来,随意瞄了两眼,顿时尖着嗓子嚷了:“陛下,是宁王,竟然是宁王!”
原来,一直失踪的苏州刺史出现在东夷一带,乌衣卫顺藤摸瓜查出他与宁王有勾结,逮捕之时被阻,一气之下向辽东都司请求支援,两边一合计,将小刺史给包圈了。
虽然这小刺史是抓住了,不过东夷的宁王府兵也惹火了,于是,两方交战了。
至少明面上看起来是这么回事,至于内里,谁能知晓?
昭明皇帝快吐血了,就为了一个小小的刺史,竟用上数万大军互殴?这宁王军和左军都吃错药了吗?
这倒屁倒灶的小刺史,若不是现在提及,他都快忘了那舞弊案的事。
这真是芝麻绿豆样的小事,昭明皇帝自认还是可以跟他弟弟沟通好的,谁知,又一份线报呈了上来。
一个苏州刺史,与封地东夷的王爷,根本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乌衣卫觉得有猫腻,细审之下,竟得一个惊天秘闻。
原来那几个替名上来的会试三甲都是宁王的人。
这本是小事,可这小刺史列出了一长串的名单,都是他所知与宁王私下往来的朝中重臣。且这些重臣每年都要收下宁王许多节礼。
至于这位小刺史为何要替宁王的人舞弊?只因他官轻言微,一直凑不到宁王跟前,便想借这个法子,在宁王面前露露面。
谁知他那么倒霉,第一次犯案便东窗事发。
说来宁王也挺冤的,他连这小刺史是哪个旮旯角的人都不清楚,只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再结合当时的主考官刘秀吉的那份供状,满朝文武,竟或多或少都牵进这件事里。
经乌衣卫的深入调查后,更是震惊。
一个外封的王爷却和京师重臣私相收授往来密切,时刻关注京师动向,这代表什么?
说明他有野心!
代表他随时可能踩着当今圣上的脑袋问鼎宝座。
这不,真拉了大旗起义了!
昭明皇帝真是糟心死了,再一听他那好弟弟竟用了这么个旗号,清君侧?他有这么糊涂这么混蛋?他身边哪个是奸逆?需要他来清?
偏偏太后还要来跟他说兄弟情深,说什么宁王定然是看出陛下身边有奸臣,才不远万里的来替他平乱,真是兄弟情深可歌可泣。
这话若换成任何人来说,昭明皇帝巴掌都要呼上去!
他还没死,都真刀实枪的要打上门了,还兄弟情深?深他娘的祖宗!
他粗喘了气,让人将太后送回宫,言道,在战争未结束前,都不要让她出现在他面前。他还得留着口气,收拾他那不省心的弟弟。
这么多的证据摆在眼前,由不得昭明皇帝不相信,他那个弟弟不是在跟他玩过家家的小游戏,他真的真的,在觊觎他屁股下的位置。
这一系列的事情下来,昭明皇帝觉得整个人都摇摇欲坠,只觉得一口老血嗝在心头,不吐不快,事实上,当他看到乌衣卫那串长长的名单后,真的一口血喷了出来,昏了过去…… 督主大人求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