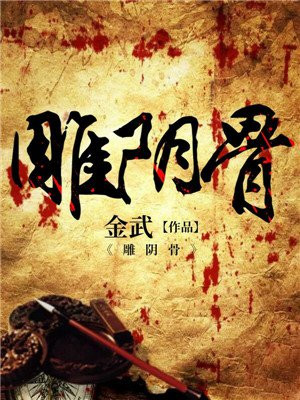安斯年的声音振聋发聩,飘荡在充斥虚假腐臭的广场之上,像惊蛰时分震耳欲聋的滚滚春雷试图唤醒冬眠的万物。
他的嗓音有些嘶哑,他的每一句话几乎是大声喊出来的,以至于他由于情绪激动而面色潮红,且声嘶力竭。
幻觉蒙蔽了他的双眼,即使摒弃幻觉,也有浓烈近乎实质化的气体白雾遮挡视线。
言语的力量是否有效?他不知道。
可他知道的是,伴随着他最后一句话的结尾,空气中那种甜腻的奶油味正在逐渐消散。幻觉世界的死寂像退潮时的海水那般退散,袅绕的烟雾愈发稀薄,像被开水冲淡的牛奶,视野也一点点在朦胧与模糊之间重新恢复。
摆脱幻觉,回归现实。
睁开双眼,他看到了……
他看到的,还是满地的死尸和一地的狼藉。
区别在于,涂了蜂蜜的烤肉依旧色泽金黄,冒着热气,而色彩缤纷的瓜果也鲜嫩得仿佛刚从枝头采摘下来一般。
毫无疑问,这是现实没错。
同样的,一具具尸体也没有腐烂,看上去才刚死不久。
人们穿着祭祀时穿的衣服,和幻觉世界到来之前时一模一样,只是他们的心脏不跳动,他们的眼神不再有光。
信徒们倒在地上,身上遍布着抓痕和刀伤。他们的瞳孔已经涣散,死不瞑目的双眼睁得大大的,只是眼里没有幻觉中的那种仇恨和痛苦,唯有一片令人心碎的空洞和茫然。
一具具死尸围成一个大圈,安斯年处在圈中心,因为在这之前,他是他们敬重的神明。而波尔金就在安斯年面前祭坛的不远处,他还活得好好的,好得不能再好。
可波尔金的表情却并不轻松,他皱着眉,叹着气,眉眼耷拉着,颓丧得像俄罗斯版的安斯年。
毫无疑问,这的确是现实,可问题是……
“这是怎么了?”安斯年看着周遭混乱的一切,惘然道,“波尔金,你做了什么?”
“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致幻气体是我唯一的手段,我已经黔驴技穷,倒不如问问你自己做了什么?”波尔金捏着眉心,讥讽道,“你不会以为自己能像影视作品和小说里那样,靠着一番嘴炮,就强行逆转结局吧?”
波尔金怪笑一声,不屑道:“醒醒吧!安斯年,你叫我们面对现实,可你自己也在逃避现实!这些家伙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否认自己不是神明,所以他们的信仰就崩溃了。”
“信仰崩溃……”安斯年喃喃自语,眼神微惘。
他抬头,扫视了一圈周围。从死法来看,人们都是自杀的,但并非所有信徒都选择自杀。
绝大部分异种人活了下来,还有五六个普通人,他们是一大堆狂信徒中少数几个清醒过来的家伙,只是此刻眼神深处还挂着些许迷茫。
信徒们死去,选择自杀,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崩溃。安斯年看着这一切就发生在他四周,心里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他想,他甚至希冀,自己是否还在波尔金编织的幻境之中呢?
可内心鹿圆用异能和情感为他构建的“心灵盔甲”,无不时刻提醒着他——这,就是现实,真真正正发生的现实,且绝对不是幻觉。
那些主角对着坏人或者群众一番煽情与一通嘴炮就能挽回一切,拯救所有人的故事,只发生在屏幕之上和小说之中。
可这是现实,他所处的就是现实。
现实就是黑暗的、冰冷的、残酷的,是不会因为他的一番长篇大论就有所改变的。
他错了,他又一次错了,可问题是,他真的做错了吗?
拒绝当那些信徒所狂热崇拜的神,并试图做出改变,改变现状,将他们从虚假的信仰中捞出来,这难道就是错误的吗?
或许,没有人可以叫醒自己,只有自己才可以叫醒自己。
“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很喜欢,也很赞同。真看不出来,像你这样惯于逃避的家伙也能说出一番颇有见地的中肯话语。”波尔金看了一眼四周,忽然说道,“现实的确无法逃避,人要嘛正视自己,要嘛因为接受不了现实进而逃避、疯狂或者死去。人生是一条赛道,我想,他们只是不能接受现实,又失去了信仰的依托,已经无法再奔跑下去了,连驻足原地也做不到。”
血流成河,猩红的血液从一具具自杀身亡的信徒尸体上涌出,在布满粗粝小石子的地面蜿蜒曲折,最终蔓延至安斯年的脚边。
安斯年低头看着那因与空气接触发生氧化而显得粘稠且发暗的血迹,这些血迹,此时此刻在地上流动廉价得甚至不比臭水沟里的污水好到哪里去。
他沉默,不语,只是低垂着眼睑,像在凝望着血肉铸就的深渊。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流逝,直到钟声再次响起,静得吓人的死寂才被飘荡在整家医院上空的钟声扼死。
“你曾经和我说过,你所释放的气体幻觉并不是你所能控制的,幻觉由当下每个人心中的恐惧所折射,因为人心才是人类最大的弱点。”安斯年沉默片刻,忽然轻声说道,“你知道吗?在你刚才用致幻气体笼罩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幻境预见了人们的自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安斯年说着说着便弯下腰,他将食指和中指并拢在一起,抹了一点地上的鲜血。他将被鲜血染红的指尖凑到眼前,细细打量了一番。
暗红色的血液粘稠得像是污泥,安斯年盯着手上的鲜血,直到黏腻的血在空气中已经微微有些发干,他才随手在身上抹去。
“这意味着,其实我内心的某一部分也许早已洞察到了这个糟糕的结局。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越是害怕某样事情的发生,那件事就越有可能发生。”安斯年眨了眨眼睛,眼皮的颤动抖落了眼里的茫然,“可问题是,像哈巴狗一样不自由地活着,真的就比自由地死去来得好吗?我见过太多把死亡当作解脱的家伙,我内心的那一部分也许预见了所有的悲伤,可我还是这么做了。”
“我否认神明,我做出行动,我想,也许那些信徒并不是死于信仰崩溃而生无可恋呢?我想,也许他们只是因为厌倦了这个世界,并厌恶做出努力的姿态,才决定自我了结的呢?”安斯年耸了耸肩,木然说道,“事实上,当我这么做了,我就不能后悔。我当然可以扮演他们的神明,但我不会那么做,他们不是我的哈巴狗,而且他们的死亡未必是一件坏事,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自由地死去。”
“你……你这家伙……”
安斯年的话语显然令波尔金愣了一下,他呆滞片刻,随后嘴角忍不住露出一缕笑容。他的右手按着胸口心脏地方,嘴角咧得大大的,到了后来,他甚至笑了起来。
他直接笑出声来,像一个小丑,笑得比哭还丑。
“你这家伙脑子明显和我们一样,都坏掉了。我们或许疯,你也好不到哪去。不过你这个说法我也喜欢,那些家伙,死去的那些人都是罪有应得,他们都曾加入声讨格温妮丝的浪潮,如果犯错而不需要支付代价,那么这个世界早该毁灭了。”波尔金大笑道,“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他们也死得很好。想想看,信徒信仰的神说自己不是神,多么奇妙的一幕!多么美妙的死法!”
“不,我不是和你开玩笑,也不是自我安慰。就像一个痛苦得生不如死的病人求你杀了他帮助解脱,难道你答应他的要求就是错误的吗?”安斯年摇了摇头,诚恳地说,“我是认真的,他们的确是做出选择的,我明白那种感受,你因为格温妮丝夺走了他们的身体器官,他们拥有得甚至比我还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凡人难逃一死,我们被迫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有选择主动提前退场的权利。”
提到格温妮丝,波尔金的笑容在一瞬之间收敛,眼神深处泛起最纯粹最直接的冰冷。一场暴雨不期而至,黯淡的天空不满云雾,一场小雨突如其来淋湿了衣衫、眼角、大地和万物。
在雨中,波尔金看了安斯年一眼,随后挪开目光,弯腰抱起躺在地上的格温妮丝,用那件被雨滴打湿的半透明的白大褂,勉强为昏睡中的女孩遮风挡雨。
他看着安斯年,哂笑道:“既然这样,你还在等什么?我们都得做出选择,来吧,杀了我,致幻气体对你不再是问题,信徒们也相继死亡,我已经没有对付你的武器了,只要你破得了格温妮丝的不朽的话。”
安斯年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没人知道他点头又摇头的意思。他只是抬起低垂的头颅,用闪烁着瑰美蓝光的瞳孔注视着波尔金的双眼。
“就像我能了解那些信徒的感受一样,我也能体会你的感受。如果有人伤害了你的女孩,像我们这样的人大概是十倍奉还回去都不够的。”他低声说道,“犯错的人就必须支付代价,你砍断他们的身体部位,用虚假的信仰炮制他们,这已经是天大的惩罚了。”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波尔金皱起眉头,不耐烦地咂了咂嘴,“想动手就动手吧,我和格温妮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向你屈服的。”
伴随着波尔金的话音刚落,灰暗的天空在这一刻亮堂了起来。沉重的夜幕黑压压的,像压在心头的一座大山。可在这一刻,数道白光照耀天地,那是来自云层的电弧在击打大地,就像宙斯的矛头指向人间。
先是电闪,后是雷鸣。
淅淅沥沥的小雨在这一刻非但没有停止,雨势反而愈发大了一点。很快,在深沉的夜幕下,小雨演变成了一场大暴雨,恼人的雨水连绵不绝,像珠帘,像幕布。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安斯年再一次摇头,瞳孔里的蓝芒与闪电相得益彰,“你看,这没完没了的大雨,就是现实啊。”
他向前迈了一步,黑色的靴子踩在满是血泥的土地之上,激起一阵阵的水花和血花。血水混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比深渊还要漆黑、比泥泞还要浑浊的颜色。
像是某种不可告人的罪恶。
黑夜在绝对的黑暗之中伸出了它的爪牙,撕毁了人间绝大部分的色彩。在滂沱大雨中,万物的颜色都显得微弱而黯淡,就像蒙上了一层深灰色的滤镜,即使是鲜艳亮丽的瓜果小姐和色泽金黄的烤肉先生也因为大雨而露出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一切就像死了一般,天地之间呈现出一种近乎单调而乏味的黑白,宛如一部上世纪拍摄的黑白电影。
但这也并非绝对。
雨声轰鸣,像一千万头野兽在黑暗中咆哮。安斯年漫步在暴雨之中,行走在血水之上,身上散发出一种幽蓝色的近乎梦幻的光芒。
这光是如此的唯美,简直就像一株蓝色妖姬在雨夜之下的淤泥中绽放。
透过连绵不断的厚重雨幕,这漂亮的蓝显得有些朦胧,可光线在模糊的同时,因为每一滴雨水的折射,却显现出一种繁星点点的美感。
这光是如此梦幻,又如此美妙,以至于当安斯年开始行走的时候,就好像夜空中的星星都伴着他前行。
他迈动步伐,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缓缓朝着波尔金走去。
波尔金看着他,就这么看着他朝着自己走来,像一朵散漫的云,像一个缄默不语的孤独行者。
诚如自己所言,波尔金已经没有任何手段抵抗了,他只是抱着格温妮丝站在雨中,身体因为暴雨无情的打压而显得有些佝偻。
漆黑的夜空中,狂雷一次又一次炸响,在每一次闪电点亮时间的刹那,在安斯年和波尔金的脸庞借着光亮出现在彼此视线中的瞬间,波尔金忽然想起了尼采的一句名言——谁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瓢泼大雨压低了附近的气温,就像冰冷的水浇在了干燥而沉闷的大地之上。伴随着电闪和雷鸣,狂风梳理雨线,使其倾斜,也使得安斯年身上的黑色长风衣猎猎作响。
雨水打湿了他们的发,他们的脸,他们的衣,在这一刻,毫无疑问,两人都是落魄的、狼狈的,就像两个相近的灵魂在雨中默然对视。
波尔金抱着格温妮丝,已经懒得再去做任何抵抗。安斯年的话没能惊醒所有信徒,却喊醒了他,更确切地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只能让格温妮丝依靠麻痹性的沉睡来确保大脑中的芯片不被激活,可是,这样昏睡不醒的格温妮丝就像植物人似的,和活着有什么区别呢?
于是,他抱着她,生平第一次。
他站在雨中,认命了。
他已经向命运屈服了,只求能和格温妮丝死在一块儿,寻求早日的解脱。
安斯年在雨中行走,脚步愈来愈快,像发起冲锋的骑士。而波尔金置身于一堆破碎的镜片之上——零重力环境的消失摔碎了那面镜子——只是静静等待宿命的裁决。
如果不是抱着格温妮丝,他甚至可能张开双臂,用两只胳膊迎接走向他的命运。安斯年是他和格温妮丝命中注定的克星,所以他知道所谓的不朽,也许对方也早已找到破解的办法。
在这一分,这一秒,波尔金看着安斯年发亮的眼睛,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刀和剑向他的胸部刺来,甚至觉得刀刃已经穿过白大褂和女孩,留下一串令人窒息的疼痛,最终扎进他那颗冷酷、疲惫而麻木的心。
最终,安斯年来到了波尔金面前,带着一道凛冽的蓝光。
的确有东西进到了他的心里,是一种奇妙的从未有过的东西。
没有尖刀也没有利剑,安斯年来到他的面前,只是笨拙而可笑地打开胳膊,试图一个人拥抱波尔金和格温妮丝。
安斯年要做安斯年要做的事,他从来不是什么复仇的天使或仁慈的魔鬼,他只是一个孤独地徘徊在漆黑的暴风雨之夜的孩子。
他用两只胳膊勉强抱住波尔金和格温妮丝,手紧紧抓住那件皱巴巴的白大褂,就像沉沦在海洋中的落水者试图抓住一块木板。
波尔金闭上眼睛,可他等待的终结并未到来。
在这一刻,根本就没有使人解脱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没有刺入心脏,没有胜利的呼唤或憎恨的叫声。
安斯年以一种滑稽的姿态搂着波尔金和格温妮丝,雨声冲刷着他那颓丧的脸庞,落魄得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狗。
“知道吗?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以保护格温妮丝的名义而退缩,那是懦夫才有的行径,和我一样。”安斯年低下头,在波尔金耳边说道,“我和格温妮丝在水牢里有过一次交谈,我想,你的逃避无济于事,不是保护,而是变相伤害。如果是格温妮丝的话,她宁可死,也想和你真真正正地在一起。”
“和我真真正正地在一起?可是啊,你不懂,她是不能和这样的我在一起的。”波尔金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我是黑市上畅销的可卡,表面上纯净且诱人,实际上却是使人堕落的根源。格温妮丝喜欢我的气味,已经对欢愉上瘾,和我在一起只会让她沉沦。你以为拥有那样的异能是一件好事?致幻气体甚至已经影响到我自己的神经,并促使我对自己的异能产生依赖。你知道吗?我经常在四下无人的时候讨厌自己。”
“不,不懂的那个人是你。你不能和女孩一起躲在屋檐下然后抱怨自己为什么笨到出门而总是忘记带伞。”安斯年摇了摇头,平静说道,“你不能一直做一些烂事,然后在事后埋怨并怪罪自己。真正的爱需要你付诸行动,而不是躲在屋檐下后悔,弄得好像后悔就有用似的。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缺少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你需要做的就是变得更好。”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波尔金哀伤地说道。
“一切,都还不算太晚。”安斯年回答道,“你还可以弥补,在伊甸和格温妮丝相聚吧。”
他说话,然后松开攥得紧紧的手掌心。
恼人的雨水不停地坠落着,自高空凝结,坠落,又化作一条条晶莹的珠帘,串起了天地一线。
在他松手之后,皱巴巴的白大褂被雨水压迫着,黏在波尔金的身体表面,像一层白色的皮肤。
于电闪雷鸣之间,幽蓝的亮光经过安斯年皮肤表面的纹路汇聚手掌,掌心亮起,一个细微的肉眼不可见的黑洞出现。
微型黑洞出现,像饕餮张开了大嘴,吞噬一切。
包括涂了蜂蜜的烤肉、鲜艳可爱的新鲜瓜果、薄如蝉翼的白色大褂和睡美人般的呼吸。
还有不朽的荣光,以及易腐败的肉体。 生来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