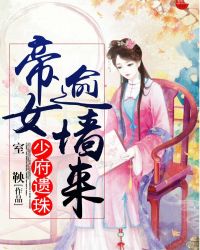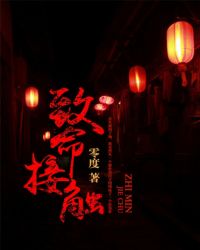第八十七章 转危为安
章邯和蒙毅赶在宵禁之前出了宫,回去的路上二人一言不发,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快到上将军府的时候,章邯忽然停了步子,懊恼不已:“方才只顾着扶苏的事情,也没来得及让你和容兮多说几句话……”
“大事当前,我的事不足挂齿,以后再说。”蒙毅言辞闪躲,寥寥数语将话带了过去。
章邯觉得奇怪,昨晚说起容兮他还大有念念不忘之意,今日却突然有些避而不谈的意味。但他说的没错,眼下最重要的事还是搭救王后。想到这里,章邯便也没再多话。
二人回到府中,见王翦还未回来,便耐心地在书房中等着。待王翦行色匆匆进了门,二人又将扶苏所言和自己的分析如实告诉了他。
王翦听完,脸色比进门时舒展了许多。他微微点着头,眼角的皱纹在烛火的映照下如沟壑纵横。
“这么看来,王上不过是一时动怒,并不是真的存心要惩治王后,更没有要故意牵连扶苏的意思。等他消了气,这件事自然就会平息下去。”
听他这么说,章邯似是吃了颗定心丸,忐忑之情消了大半:“您那边怎么样?李斯大人他愿意帮忙吗?”
王翦捋着胡须轻轻一笑:“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加讨好王上。放心吧,明日他定会劝谏王上的。”
章邯还想再问,王翦抬手制止了他,满是笑意地朝蒙毅颔首谢道:“今日多谢蒙将军相助,天色不早,你还是早些回去,免得府里的人担心。”
听出话里逐客之意,蒙毅偷偷瞄了章邯一眼,随即拜别离去。
待他走远,王翦幽幽舒了口气,盯着章邯的眼睛带了些警示的意味:“虽然王上命你和蒙毅一起辅佐扶苏,可你还需注意分寸,不要在人前与他走得太近,以免惹人非议。”
章邯觉得王翦此言过于谨慎,但没有直接反驳他,只轻轻点头算是听了进去。
见他没有分辩,王翦又担忧地说道:“你在王上身边这么多年,将他的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甚至比朝中重臣更能揣度他的心思。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君主都喜欢聪明的臣下,但又不喜欢过于聪明的臣下。以后,尽量不要在他人面前肆意揣测王上的心思。你懂我的意思?”
章邯很是郁闷,他想了想,心中有些不甘:“我知道大父是为我担心,我也明白您说的道理。可是,扶苏和蒙毅是我最好的朋友,难道对他们我也要保留一份戒心吗?”
王翦似乎有些不悦,但还是耐住了性子,低声解释:“扶苏迟早会成为新的秦王,他同样不喜欢自己的臣子把一切都看得太透。至于蒙毅,他是蒙氏的人,蒙氏一族树大招风,所以你要谨慎一些。我知道你很反感,但身在朝堂,你不可能只凭一腔热血活着。兵法有云,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周旋庙堂亦是如此,每做一事,你必须要看清它可能导致的危害,懂得避害方能成功。我这么说并非要你成为一个两面三刀的人,而是希望你在严守原则之下可以站得更稳更牢,这样你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英雄可以死在战场上,但绝不可死在自己人手里。”
说着,他长长吐了一口气,半宿的奔波令他疲倦不堪:“好了,明日朝会之后,这件事就会有个定论。既然你已经说服扶苏不再生事,有李斯在,王上应该会顺势下个台阶,给彼此留些缓和的余地。明日你该回宫值守了,早些去休息吧。”
见他微闭双眼,没有再继续说话的意思,章邯只得悻悻地退了出去。借着清亮的月色,他缓步回到自己的住处。隔壁的房间黑漆漆一片,想来王离押送昌平君去郢城还得几天才能回来。
他心下纷乱,想到这几天王翦对自己说的话,怎么也睡不着。平心而论,他无法完全认同王翦的想法,可是王翦在秦王身边待了大半辈子,一定比自己看得更加透彻。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章邯索性坐了起来,恍惚间又猛地想起今日在沅茝殿里扶苏冲自己发火的情景。
他有些动摇,或许王翦说得对,自己没能处理好周围的关系,才令扶苏对自己横生不满。今天是因为有蒙毅替自己说话,才将扶苏的怒火平息了下去。若是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呢?若是没有蒙毅在身边呢?自己该如何理顺这复杂多变的局面?
只凭赤子之心不足以应对身边潜伏的危险。除了要面对赵高、赵夫人等人的暗箭,还要维护好与扶苏之间的信任,更要在秦王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一种力不从心的无奈将他整个人吞噬殆尽。
章邯不记得自己到底挣扎了多久,待他一觉醒来,天色已经微明。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
秦王给他的休假已经结束,他来不及多想,迅速穿戴整齐往羽林军中赶去。
自从荆轲刺杀秦王未遂,嬴政加强了戒备,即使日常朝会也会命几名羽林军戒备在侧。身为中郎将,章邯便成为了秦王最为贴身的护卫。
朝会之上,嬴政果然向廷尉李斯提起将王后贬往郢城之事。李斯似乎早有准备,如往日一般慢条斯理地站出来。他只字未提扶苏,也没有强调此时处治王后会带来的后患,只一板一眼依照秦律说话,到最后,王后所犯之错根本连律法都未触及,将她迁谪实在是小题大做。
李斯说完,众大臣都不由替他捏了一把汗。昨日政事殿里的事早已在朝臣间传了个遍,谁人不知秦王暴跳如雷,誓要将王后和昌平君一起赶走?嬴政对楚系的忌惮由来已久,秦楚之战近在眼前,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若是蒙恬还在咸阳,或许只有他敢劝上一劝,如今他不在,谁敢贸贸然站出来替王后说话?
正当所有人等着看李斯被秦王痛骂时,嬴政却出人意料地沉默了下去。他盯着李斯看了许久,末了才缓缓舒了口气:“你精通秦律,寡人该听你的才对。”
众臣皆错愕不已,李斯却已高举玉笏谢道:“王上圣明。”
章邯站在王座一侧,面朝群臣,将他们脸上的变化悉数看在眼里。李斯虽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情绪,但那不经意上扬的嘴角已经泄露了他的得意。
章邯不由对王翦心生敬佩,这一切全如他所料。虽然远离咸阳多年,可他依旧能精准地猜到嬴政的心思,从战场回归朝堂,他依旧还是那个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的将军。
章邯背对着嬴政,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是从他那平稳的语气便可以猜出,眼下他并没有任何动怒的迹象。
嬴政抬手示意李斯且慢,又接着说道:“王后之举虽然不涉及律法,可她的所作所为不顾大局、不足为天下人的表率。寡人可以不将她贬去郢城,但罚还是要罚的。”
李斯俯着身子,脑子里飞快转过几圈:“王上所言甚是。不过大战在即,还须以安定人心为上,臣认为小惩大诫即可。”
嬴政沉默片刻,轻轻点点头:“也罢,就让她闭门思过一个月,之后再说吧。”
乌云排山倒海,却在暴雨将至的最后一刻倏然烟消云散。众臣皆是人心惶惶,以为王后这次必难逃一劫,然而眨眼间事情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散朝之后,嬴政将李斯留了下来,传他进了书房。
四下无人,嬴政也就不再与他婉转迂回:“你在朝中向来洁身自好,不与后宫之人有什么往来,这次怎么竟帮王后说起了话?”
李斯一愣,匆匆忙忙跪下身去秉直答道:“王上明鉴,臣只是依律行事而已,并无偏袒之心。”
“行了。”嬴政见不得他那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抬手示意他起来,“你心里怎么想的,寡人还能不知道?”
李斯小心翼翼地朝他探了几眼,面带愧色:“若说私心,臣确实有一些,臣不敢隐瞒。秦楚之间不日便会有一场大的厮杀,李信和蒙恬两位将军皆是首次挂帅,他们是王上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此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这个时候国中绝不能出一丁点的乱子,必须要确保二位将军在前线能安心杀敌。满朝上下何人不夸赞王后贤良淑德、温柔聪慧,您与她多年夫妻,更深知她的为人。您严惩昌平君,为的就是杀鸡儆猴、以儆效尤,朝臣们心明眼亮,谁都不敢替他求情。可王后不同,她与昌平君同宗同族,这个时候她若为了自保而一言不发,那才说明她平日里的贤良都是装出来的,骨子里其实是个无情无义之人。臣身为廷尉,不敢徇私枉法。臣的判定皆秉持秦律,但臣心里却忍不住为王后而叹惋。王后所为虽是无理,更多的却是无奈。”
这番话嬴政听在耳中很是受用。本来他也没想怎么惩治芈昭彤,没想到她一怒之下竟说出“众叛亲离”那样恶毒的诅咒。回首来时路,嬴政无时不刻不是活在被亲近之人背叛的痛苦之中,这四个字就是久久萦绕在他心里的魔咒。芈昭彤这么说,就等于是将他心底里的伤疤血淋淋地撕裂开来,令他无法忍受。
情绪失控之下,他放出了狠话。虽然事后冷静下来他忍不住懊悔,然而骑虎难下,事态已经远离了他的控制,急转直下。
今日早朝,他本打算探一探李斯的口风,若是情况不妙,他便会暂时将事情压下来,待与李斯私下沟通之后再做处置。没想到李斯的态度正好暗合了他的心思,而且言语间皆是秉公办理,令旁人找不出任何破绽。
嬴政很是满意,便刻意将他留了下来,想再仔细探探他的心思,看看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李斯看起来倒也诚实,一股脑将心中所想全说了出来。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明则是为王后叹息,实则是在大力赞扬王后的品性。
嬴政心里高兴,可脸上却没有显露出来。他故作不悦地拧着眉头,指着李斯说道:“她为情义所累,枉顾自己王后的身份。只顾小情小义,不顾大节大道,这样愚蠢的做法难道还应该赞颂不成?”
李斯素来谨慎,他竖着耳朵听着嬴政的话,虽然表面上看似谴责,可语气里却没有一丝凌厉。他心下了然,连连摆手:“臣并非此意。臣的意思是,王后对昌平君已经仁至义尽,楚系那些人也就没道理再苛责她什么了。她毕竟是个深宫女子,对朝中大事所知不多,王上与她好好说说,她定然能转过这个弯来。君后和谐才是一国之福啊。”
嬴政似乎认同了他的说法,沉默了片刻,又无奈地长叹一声:“扶苏渐渐大了,不能总待在他母亲身边无所事事,寡人像他这个年纪,已经坐在秦王之位上学着操持政事了。”
“王上所虑甚是。”李斯晃着脑袋,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之前蒙恬将军在咸阳,会经常领着公子去羽林军熟悉军务。眼下将军虽领军出征,但公子的历练不可荒废了啊。”
嬴政一手撑在书案上,盯着他看了片刻:“我秦国以武力和律法立国,既然蒙恬不在,寡人就先送他去你廷尉府,你要先将重要法典传授与他,三个月之后,寡人会亲自考核。” 少府遗珠:帝女逾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