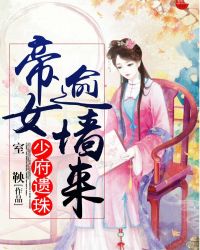第八十八章 滴水不漏
秦王王令既下,沅茝殿里的内卫悉数撤了去。芈昭彤虽然可以与自己的儿女相见,但一个月内不许踏出宫门半步。至于沅茝殿外的人,没有得到嬴政的允许,也不许擅自入殿探视。
一干人等终于将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不管怎么说,眼下沅茝殿终究还是个敏感的地方,章邯不便再去探视扶苏,一待休值便速速回了上将军府。
王翦早已得到消息,好整以暇地在书房里等着他。见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不由摇头示意他收敛一些:“过几日阿离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我让王茅准备些酒菜,咱们爷孙三人一定要好好聚聚。”
听他这么一说,章邯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大父回来这么久,我还没能为大父接风,是我疏忽了。”
“这怎么能怪你呢?”王翦站起身来,笑着走到他身边,“刚一回来就遇到这么棘手的事,谁都没这个心思。好在一天的乌云终于散了,我也终于能彻底喘口气了。只可惜王贲不在,不然咱们祖孙三代就能团圆了。”
章邯遗憾地点点头,继而问道:“听说王贲将军率军由燕地南下,准备和李信、蒙恬将军一道合攻楚国?”
王翦不置可否,一手捋着斑白的胡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攻楚有李信和蒙恬就够了。”
章邯一时没能明白过来,盯着他玩味的笑意愣了片刻,忽然拍手说道:“王贲将军是要去攻打魏国?所谓南下攻楚只是个幌子而已,为的就是麻痹魏国君臣,让他们坐以待毙。”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无形,神乎无声,方为敌之司命。”王翦赞许地看着他,“看来魏缭的兵法教得很好,你学得也很好。”
提到魏缭,章邯不觉有些难过:“以前我们最喜欢听他教授兵法,只可惜后来战事一起,他便没有机会再来教我们了。”
“这有什么?”王翦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如今我也赋闲在家了,你要学,我可以教你。”
“真的吗?!”章邯不由睁大了眼睛,“大父愿意教我?王上总说您是当世战神,若能得您的教导,我……我……”
兴奋之下,章邯竟有些语无伦次。王翦好笑地看了他一眼,转身指着墙边书架上的书:“这里面的书你随便看,不懂的地方就来问我。不过兵法这种东西只是一种规则,并不能尽信之。战场之上瞬息万变,还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若是墨守成规那就和纸上谈兵的赵括没什么两样了。”
“我记下了!”章邯几步跑到书架边,爱不释手地抚着那一摞摞厚重的书简,忽然想到一事,又激动地说道,“大父您灭了韩国,又将赵国和燕国打得只剩最后一口气,若是王贲将军再一鼓作气拿下魏国,您和他可就是为王上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勋,这份荣耀无人可敌。只不过,灭楚一战您和王贲将军都无缘参与,想来着实是一大憾事。”
王翦轻声笑了一下,他虽年近古稀,可眼神却依旧明亮如炬:“为将者在战场上厮杀的太久,就容易被输赢蒙住眼睛,争一时之气。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合利于主,乃国之宝也。若是我退下能助李信和蒙恬一举攻下楚国,这本身也是一种功劳,没什么可遗憾。再说了,难道魏缭没教过你良马有策,远道可致,贤士有合,大道可明的道理?”
“这个倒是说过。”章邯低头想了想,“人若要有作为,害得需要遇上些好的契机才行。”
“所谓时势造英雄,便是这个意思。顺势而为方可成功,眼下我能做的也就是养好身体罢了。”王翦一脸轻松,抬脚准备往外走,“屋里闷了大半日,去后院走走吧。”
章邯应了一声,将书房的门关好,三步并作两步追了上去。有句话他在心里憋了半天,踌躇多时终于还是小声问出了口:“大父,您到底怎么说服李斯的?他今日在殿上虽然只是依照律法说事,可明里暗里一直在替王后摆脱罪责。”
王翦顺着小径缓缓前行,听他这么一说忽然转身反问道:“你觉得呢?”
章邯咬着唇想了片刻:“我之前想过,李斯这个人算不上君子,只拿道德节义是说不通他的。能让他伸出援手,必然这件事对他有莫大的好处。比如……比如可以拉近与扶苏的关系。”
王翦不置可否,但眼中明显闪过一丝赞许之意。他回身继续往前走,声音低沉而缓慢:“孔子说过要因材施教,这四个字放在李斯身上也同样适用。你说的很对,他不算君子,做事必以利字为先。不过光凭扶苏还是不能打动他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位置摆的很正,他只认定一条,他是王上的臣子,凡事必以王上的好恶为准绳。所以,我只要告诉他三件事。其一,王上与王后感情深厚,王上盛怒过后必然后悔,可他是君王,言出必行,所以这个时候谁能帮他找个台阶缓和局面,他必然会感谢谁。其二,正如你所说,这件事看起来棘手,实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上为什么如此坚决地赶走昌平君,真的是因为他烦透了楚系,誓要将连同王后在内的楚系一网打尽吗?其实不然,王上所作所为还是为了扶苏。他打压楚系外戚,就是为了能让扶苏和王后摆脱这些人的束缚。从这一点上来看,王上并非要放弃王后和扶苏,反而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么一来,李斯只需秉公执法就可顺水推舟将这个人情送出去,既在扶苏那里留了名,又暗暗契合了王上的心思,一举两得。其三嘛,我也是听你说的,正好用在李斯身上。既然赵高已经攀附在胡亥这棵大树上,同样没什么背景的李斯若是知道这个消息,还不得赶紧给自己找个护身符?锦上添花的事没什么人记得住,若是雪中送炭那就另当别论了,尤其是这个热炭送得还如此悄无声息,不会引人怀疑。”
听完这话,章邯不由叹服:“大父思虑如此周全,难怪一直气定神闲。”
“也并不尽然。”王翦轻轻扬起嘴角,“关于王上对扶苏和王后的真实态度,我心里一开始也没什么底,所以才会让你去向扶苏问清楚,看看王后到底是因何获罪。等你回来说完经过,我心里也就有了大概的猜测,也是多亏了你能及时猜中王上暴怒的原因,这才让我多了分把握。李斯不是傻子,虽然被我说动了心,可他绝不会贸然就站在王后这一边。想必今日上朝时他已暗中察言观色多时,直到确认王上的心思确实如我所说那般,他才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说到这里,他似是自我解嘲般地大笑几声,然后又压低了声音看向章邯:“能在王上身边站稳脚跟的,个个都是老狐狸。”
经此一事,章邯虽然仍未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却也不得不被他擘肌分理地分析所折服。
见章邯毫不掩饰内心的敬佩之情,王翦又语重心长地说道:“大父不求你显达于人前,但既然你接受了王命,就更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以求利于不败之地。保护自己,并不是要你学一些蝇营狗苟、尔虞我诈的手段,而是要懂得因时制宜、顺势而为。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朝中同样适用。你要了解自己,了解同伴,也要了解对手,方能处变不惊。”
章邯听得心悦诚服,信誓旦旦地说道:“我懂大父的意思,君子也需懂得如何安身立命,才能谋求更大的作为。”
见他这回终于听了进去,王翦放心地点点头。
“哦,对了!”章邯忽然想到一事,慌忙开口说道,“王上让扶苏去廷尉府了,说是让李斯教他律法典章。三个月之后王上会亲自考核。”
王翦丝毫未觉得意外,反而戏谑地笑了笑:“李斯本是楚人,容易与王后和扶苏公子相处,而且他在楚国并无资深背景,与楚系外戚并非同道中人。我秦国向来以武力和律法为立国之本,李斯精通秦法,无人可及。王上让他亲自教授扶苏公子,一来彰显了扶苏王储的地位,二来也是告诉那些有着楚国背景的官员,不要因为昌平君的事就惶惶不可终日。李斯也是楚人,可照样荣居高位,可以做王储的老师。王上思虑周全,可谓滴水不漏啊。话说回来,李斯求仁得仁,他应该来谢谢我才对。”
对于让扶苏去廷尉府熟习司刑一事,章邯并没有想得太深,但听到王翦一番分析,他才恍然大悟:“是啊,除了与华阳太后和昌平君同气连枝的外戚,朝中的楚人还有很多。昌平君被贬谪,他们定然也会人心惶惶。大战前夕,国中不可出现一丝一毫的骚乱,王上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借着李斯来安定人心。”
见他一点就通,王翦欣慰地舒展开眉头:“所以说,咱们的王上聪明过人,在他身边做事除了要尽心尽力之外,一定要多看、多思,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章邯使劲点点头,继而又笑着搀过他,“说了这么久,您也该累了,我扶您回去休息吧。”
又过了几日,王离从郢城回了咸阳,昌平君的风波终于彻底平息。
王后虽然还在禁足中,但扶苏俨然已经以王储的身份进入廷尉府,开始学着处理秦国最为重要的政务之一。朝臣们心中如明镜一般,不仅一如既往地尊重扶苏,更是连带着对李斯也越发刮目相看。
章邯听从王翦的劝告,没有立刻再去沅茝殿见扶苏。其间虽然扶苏也曾去政事殿向嬴政禀告自己在廷尉府里的情况,但都只是擦肩而过,或是匆匆一面,根本无暇细谈。
章邯的心里始终放不下。除了担心扶苏的近况,章邯更想亲自去见他一面,将赵夫人的事情和他解释清楚。
忍着捱了小半个月,终于轮到章邯休值。他早已打听到扶苏每日进出廷尉府的时间,酉时一过便躲在廷尉府门外耐心地等着。
没过多久,远远看见扶苏的身影从厚重的木门后走了出来。他走动的时候,大袖随着步幅轻轻飘动,一阵风吹过,外衫略显松垮地贴在身上。
只是半个月而已,扶苏比之前瘦了许多,但言谈举止间仍是一派雍容的气度。他快步上了马车,刚准备掀帘而入,就听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扶苏!”
他寻声回眸,但见章邯正站在马车前满是笑意地望着自己。
“你怎么来了?”扶苏微微一愣,继而反应过来,抬手招呼他近前上车,“来吧,我们边走边聊。” 少府遗珠:帝女逾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