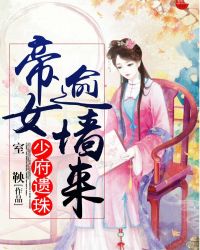第四十章 以暗见疵
嬴政微微颔首,将韩非的遗书从蒙恬手中拿了回去。他轻轻摩挲着柔软的布帛,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歉疚:“方才看了他的信,我本不想告诉你真相,毕竟韩非以命为注,赌的就是寡人可以顺天应命,以大局为重。可你方才一番分析已是入木三分,与韩非所想不谋而合。他被血脉身世所缚,虽识得天下大势,却不能辅佐于我。那日与他分别,他向寡人说起郑人买履的故事,只恨寡人那时不能领会他的苦心,竟还嘲讽他不识时务,因循守旧。现在想来,先生在秦国的这段时日,必是时时刻刻深陷两难绝境,天人交战、无法自拔。可笑寡人太过自负,竟还大言不惭与他定下两年之约……”
“两年之约?”蒙恬第一次听说这件秘事,忍不住心中好奇。
嬴政点点头,却又自嘲地苦笑一番:“那日决定要送他去云阳,怕他误解了寡人之意,以为是要杀他,所以寡人亲自去见了他一面,并告诉他两年之内秦国必灭韩国,到那时寡人会再去问他心之所向。他闻言之后笑而不语,恐怕从那时起便存了必死之心。寡人甚是后悔,若非当初执意请他入秦,也许就不会将他逼上绝路了。”
经过这番解释,蒙恬才明白过来。嬴政心高气傲,既是放眼天下,必然以为小小韩非早晚必是囊中之物。可这世上最难估量的恰恰就是人心,韩非之心坚如磐石,不论他死因如何,都会让从未被人拒绝的嬴政体会到深深的挫败感。
想到这里,蒙恬缓言劝道:“天下之势已定,若韩非先生誓死守护韩国,即便王上不请他入秦,待韩国国灭之时,他依旧会选择以身殉国。若他仅仅只是一个忠心为国之人,臣也只会将他看做一个宁死不屈却又固执守旧的迂腐名士罢了。可看到他的遗言,臣才真正被他的睿智和气度所折服。他不能以身侍秦,襄助王上完成千秋霸业,便以这种方式替王上扫除障碍,使您避免困陷于两难之境。依臣看来,先生之死并非殉国,而是殉道。”
蒙恬之言乃是发自内心,字字竭尽真挚,听得嬴政不由动容。
“以韩非之才,他定然早已洞彻了天下之局,往来古今怕是再无人可望其项背。今他虽身死,可寡人却会谨记他的教诲。寡人定要灭了六国,这才不枉与他一场风云际会,不让他白死。”嬴政重重拍在蒙恬肩头,似是说与他听,更似说与自己,“寡人要将他厚葬,这绝非单单是做样子给天下俊士看。他的操守足以令天下折服,寡人定要好好祭奠他。”
蒙恬亦是感佩在怀,忍不住请命:“是,韩非先生高义,他的葬仪就请交给臣去办吧。”
嬴政满怀谢意朝他微微颔首:“好,当初你迎他入咸阳,如今就劳烦你再亲自送他一程。”
蒙毅抱拳领命,忽然想到一事,又有些迟疑:“王上,先生遗书一事是否告诉李斯大人?从遗书内容来看,李斯大人似乎也知道些内情……”
“不必了。”话未说完,嬴政抬手阻止了他,“先生说得很清楚,他只是替李斯分析了眼前的形势,怂恿他成了一把杀人的利器而已。韩非未将遗书交给李斯,而是小心谨慎隐匿起来,这就说明他并不想让李斯知道寡人也知晓了这全部计策,否则他大可让李斯替他将遗书呈上来。”
蒙恬沉下心来思索片刻,虽若有所得,却依旧不甚明白:“韩非本来就是想让李斯出手杀了他,好替王上解除困境。既然他都已经决定送给李斯这天大的人情,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
嬴政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转身回到书案边坐下,将那幅帛书又铺在案上仔细叠好。蒙恬不敢催促,只好耐着性子等着。过了片刻,他见嬴政抬头看向自己,眼神不再似先前那般明亮,迷迷蒙蒙如隔了一层细纱。
“韩非与李斯同窗数载,以他识人的能力,定是早就将李斯看得透彻。说到底,韩非应该还是不能完全信任李斯这个人,比起李斯,他倒是更愿意相信你,或者说是更相信你对寡人的忠心。”
论及忠诚,蒙恬猛地一惊,可又不知韩非心思到底有多深,只好微微俯着身子听嬴政继续说下去。
“韩非在信中说了,他知道自己一死必会震动秦国朝堂,而你正是负责看管他的人,所以你一定会及时拘下李斯,并彻底搜查他生前的一切用度。他将遗书藏在自己身上,就是等着由你蒙恬来发现,然后亲手交给寡人。寡人猜想,他愿意让你得知这整盘棋局的实情,是因为他相信你的人品会比李斯可靠,也相信你与寡人之间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信任。”
听到此处,蒙恬有些惶恐,忙开口推却:“臣以为,韩非能够说动李斯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毒杀他,论其根本还是因为他和李斯都坚信王上绝非暴虐之君,不会一怒之下便草菅人命。王上尊法、奉法,气度、胆识、智计皆是举世无双。他们相信王上在震惊之余定会冷静处之,趋利避害,对李斯法外开恩。”
蒙恬一口气说完,可嬴政却似乎陷入了沉思,直直盯着那一副帛书没有言语。蒙恬不知何故,一想到李斯还在殿外戴罪,只好又小心翼翼唤了一声。
嬴政猛地惊醒过来,略带尴尬地对蒙恬点点头:“无论如何,寡人相信韩非识人辨人的本领,他既不愿向李斯透露,寡人便遂了他的心愿。你就当未曾见过这幅遗书,绝不可向外泄露半分。寡人暂时不想见李斯,你将他送去廷尉府暂且拘禁几日,待韩非下葬、风头过去,寡人会找个机会放他出来。当然,你只将他关押,对他就说寡人震怒,其他的什么都别提。”
蒙恬心领神会,随即明白了嬴政的意思:“王上放心,臣一定会好好震慑李斯一番。”
“嗯。”嬴政舒了口气,又叮嘱几句,“将李斯囿于狱中,只按照普通犯人对待就好,让他吃点苦头也不是什么坏事。反正他料定寡人不会杀他,绝不会自寻短见。”
“臣明白。”蒙恬抱拳答道,再看嬴政似乎也无其他交待,这才退了几步掀帘出去。
待蒙恬走后,嬴政又一次陷入了汹涌的思绪中。
韩非此人,竟可将他的心思看得如此通透。虽然他们仅有数面之缘,而他面对韩非时又刻意隐藏了自己的情绪,却依旧没有逃过韩非的法眼,一点一滴,无处遁逃。
或许从嬴政决定让李斯去韩国亲请韩非时,他便已经看出了嬴政对李斯若即若离的态度。嬴政不能完全相信李斯为国之心,所以才会借此机会试探李斯的内心,看看在他心里到底是私利重要还是秦王的大业重要。李斯在朝堂混迹多年,工于心计,必定也能感受到嬴政的用意,所以才会刻意压抑住心内的妒意,佯装大方之态。
可嫉妒这种恶魔,一旦生出便会如野草疯长。即使李斯凭着谨慎的处世之道躲过了嬴政的试探,可他对韩非的恨意却再也无法消散。
之前一力劝谏嬴政处死韩非,虽说确也是为秦国着想,可其中到底掺杂了多少私愤,嬴政猜不出。嬴政越是提防他,他就越是忐忑不安,越会想利用一切机会来表露自己对秦王的忠心。
而韩非也恰恰正是利用了他这份惶恐不安却又无计可施的心态,才能半劝半吓地哄着李斯替他完成了这个周密的局。
连堂堂的秦国廷尉大人都已经成为了韩非手中的棋子,嬴政想到这里,不由暗自苦笑。这样的高人,不能为他所用,确为千古之憾。然而,若是韩非真的愿意归入秦国麾下,他又是否真的能驾驭得住?
嬴政一手伏在帛书之上,尽力想象着当日韩非留下这些绝笔时的神情。
韩非知他心意,亦懂他心忧。李斯之才,可堪重任,李斯之心,却留有余地。韩非要打破他最后的幻想,将他逼入绝境,从此再不敢与秦王嬴政兜耍心计,只能一心一意成为殿下之臣,为秦王之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所以,韩非才要费尽心机将全部实情告诉嬴政,并对李斯刻意隐瞒了部分真相。蒙恬分析的没错,李斯敢冒险,一方面是可以公报私仇除掉劲敌韩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坚信嬴政的才智和心性。李斯犯法在前,嬴政宽宥在后,不论嬴政出于何种考虑,对李斯而言都不啻于劫后余生,宛如重生。除了感佩秦王不杀之恩,他从此以后更会胆战心惊,不敢再生事端。
韩非如此煞费苦心,除了是为嬴政解除困境,免遭六国士子口诛笔伐,更是替他牢牢控住李斯,使其尽心尽力,再无退路。
可韩非的这些心思太过隐秘,只能为人君所知。所以方才蒙恬问起时,嬴政刻意回避了这最为深沉的隐情,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过去。
嬴政细细回想着与韩非为数不多的过往,一阵伤怀竟兀自由心底而起,难以自抑。
初得韩非著书,他如获至宝,那书中的话醍醐灌顶,直将他心中的疑惑悉数解开。他不眠不休、夜以继日,只为能多领悟一些个中奥妙。无数个灯影婆娑的夜晚,他看着韩非的书,宛如迷途羁旅之人寻得了方向,他知道,若要成就心中的霸业,就一定要借此之说,秉此之学。
书非人,却如人一般娓娓道来。以至于那日在驿馆中,他初见韩非,却毫无陌生疏离,竟如老友重逢一般。
嬴政想起与韩非的最后一面,那时他站在院门外,听韩非与章邯说笑,说若有来世,自己只愿做一愚人,饱食遨游,泛若不系之舟。
思绪一路漫无边际。可嬴政心里清楚,即便他再珍惜韩非之才,然逝者已矣,他也绝不能再多做停留。征途已在脚下,太多的事还在前方等着他。
嬴政忽然微怔,重又摊开书案上的帛书,似要将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印在脑中。
半晌,嬴政默默靠在凭几上,闭目仰天,似乎韩非就在眼前。他缓缓张口,声音细微几不可闻。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不可一无,皆帝王之俱也。王图霸业绝非一朝一夕可成,也绝非寡人一己之力可成,法彰于外,术御于内,寡人若要成事,就不得不驭臣于下。韩非,你是用自己的性命为寡人讲授了最后一课吗?寡人受教了。” 少府遗珠:帝女逾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