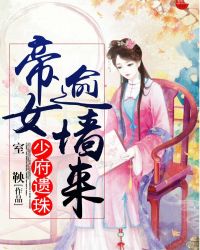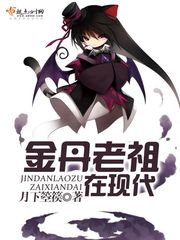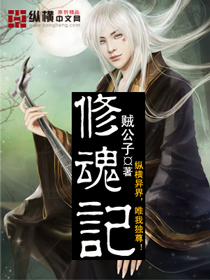第二十五章 金风玉露
“好一个务实不务虚!”
韩非话音方落,就听一阵明快的笑声从门外传来。他抬眼一看,一个瘦高的人影挑帘而入,步态稳重,方寸间自有一股乾坤之气。
那人站定,眉目含笑,嘴角上扬,微微颔首:“寡人来迟,先生勿怪。”
他虽是笑着,但举手投足间皆隐着不容忽视的王者威仪。韩非迅速反应过来,来者正是秦王嬴政。
秦王谦和,韩非自是不敢怠慢。他弯腰拱手,落落大方地施了一礼。
嬴政忽然从天而降,也让蒙恬吓了一跳。他领着扶苏三人行了参拜之礼,疑惑地问道:“王上?您怎么过来了?”
之前嬴政只是吩咐蒙恬带着扶苏他们来探望韩非,并未说自己也会过来。见蒙恬一副被蒙在鼓里的诧异神色,嬴政故作淡然地笑了一声:“军政繁杂总也忙不完,不能因为忙不完就怠慢了贵客。寡人也是刚到而已。”
蒙恬这才明白过来,他听懂了嬴政话里的意思,连连点头:“王上所言甚是。”
嬴政满意地瞄了他一眼,继而又朝韩非走近几步:“先生既是务实之人,估计对那些繁冗虚华的迎宾之仪亦是头疼。寡人之前还怕怠慢了先生,如今看来,却是寡人多虑了。”
面对天下谈之色变的强主,韩非却无丝毫畏惧之情。他直直盯着嬴政的目光,嘴角挑起一抹戏谑的笑意:“秦国之强、秦王之威天下皆知,王上不管如何对待外臣,外臣都不敢有任何怨言。”
这话里带着极强的讽刺之意,只听得蒙恬一身冷汗。岂料嬴政却丝毫没有介意,只佯装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先生还是嫌寡人礼数不周了。”
说着,他转首看向扶苏,不由地皱起了眉头:“如此娇气,寡人不喜。”
莫名其妙被指责,扶苏觉得委屈,却又不敢违逆父王的意思,便伸手脱去外衫,双手捧着还给韩非,红着脸说道:“谢谢先生。”
对这对天家父子的举动,韩非未做置喙,只伸手接过外衫,将它随意地重新搭回衣架上。
本以为韩非会做些议论,没想到他竟一言不发。
嬴政暗自有些好奇,又意味深长地望了蒙恬一眼:“蒙恬,寡人还有些话想和韩非先生说说。这里太冷,让人送个铜炉去厢房,你带扶苏他们过去等着吧。”
“是。”蒙恬拱手领命,刚要离去,又犹豫了一下,“王上,这里需不需要添些炉火?”
“不用了!”嬴政挥了挥手,大步走到主位坐定,“寡人不冷。先生愿意生于忧患,寡人陪他一起便是。”
蒙恬得了令,转身带着扶苏、章邯和蒙毅退了出去。
本来一屋子人,猛然间只剩秦王与韩非在内。偌大的屋子空了下来,气氛莫名变得有些冷。
嬴政似乎并未将这些放在眼里,他微微抬手,示意韩非先坐下。
“看样子蒙恬带来的这些菜肴都已经凉了……”嬴政低头看着满案的盘碟,可惜地撇撇嘴。
“王上屈尊前来,又岂能让这些饭菜喧宾夺主?”韩非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让蒙恬将军来送菜,本就是个引子。王上有心试探外臣,又何必欺骗蒙将军?看他一头雾水的样子,实在令人于心不忍。”
嬴政一怔,随即无奈地摇了摇头:“寡人来向先生求教是真心实意,给先生送来家乡菜肴亦是真心实意,先生不要多心。”
说着,他唤来几人将盘碟悉数端了下去,又仔细叮嘱:“这些菜拿去温热,之后再请先生品尝。”
待下人鱼贯而出,嬴政这才回过头来,却见韩非正神色讶异地盯着自己。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轻声解释道:“寡人素来不喜铺张浪费,这一米一粟皆是百姓辛苦劳作得来。只是凉了而已,待重新热过一样能食。寡人如此做绝非怠慢先生,先生可不要嫌弃寡人抠门寒酸。”
韩非顿了顿,面上忽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复杂神色:“想我韩国如今国力渐衰、民生凋敝,可宫中靡衣玉食却从无间断。王上此言若是被我韩王听见,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韩王无道,有眼无珠,不识大才。”嬴政悄悄探身向前,试探地望着他,“嬴政真心仰慕先生,想请先生助我一臂之力,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韩非的眼光沉了下去,他紧紧闭着嘴唇,一动不动盯着嬴政,胸前快速起伏几下,似乎在平复着某种心情。
韩非生来一副淡然的模样,眉眼中看不出任何情绪,却常常掩着些许哀愁。屋内光线昏暗,他的半张脸都隐在阴影中,只有那漆黑的双瞳闪烁,如星汉灿烂,璀璨耀眼。
嬴政默默等着他的回应。过了片刻,韩非轻轻舒了口气,又恢复了之前的轻松模样。
“王上对扶苏公子太过严苛了。”
听出韩非避而不答的意思,嬴政也没有逼他,只是微微叹了口气,重又坐了回去:“他是王储,是秦国的未来,寡人不敢有丝毫放松。”
韩非听完,稍稍垂下眼眸:“王上可曾想过,秦国数百年来偏居崤函之西,军力、财力皆不及山东六国,备受欺凌,何以从秦孝公以来后来者居上,一跃成为天下至强?”
“自然是因为商君变法,我秦国之强由此肇始。”嬴政朗声答道。
韩非重又抬起眼眸,意味深长地继续问道:“商君变法,强秦肇始。可秦孝公死后,商君却被孝公之子惠文王车裂。若是将此事放置六国,早已国中生变。然而秦国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孝公之后五代秦王,皆奉商君之策为圭臬。即使五任秦王天资有别,却都未出现大的过错,这又是为何?”
“这……”嬴政迟疑片刻,“嬴政不知,请先生直言。”
“商君重法,为秦国立下国策,五任秦王皆以秦法治国。只要法不变,即使主君有变,亦可保社稷永固。”韩非之声虽不大,却字字铿锵,直叩进嬴政心中。
见嬴政面上忽显恍然大悟的神色,韩非又轻轻笑了一声:“所以,只要王上的继任者依旧遵秦律而行,秦国便绝不会有差。否则,就算王上日日对扶苏公子耳提面命,也毫无意义。”
一语既毕,嬴政静默沉思。他望着韩非嘴角处那一抹尚未彻底消散的隐隐笑意,忽然又睁大了眼睛:“先生所言如醍醐灌顶,寡人必当谨记于心。寡人曾拜读先生大作,记得先生说过,治国者需将法、术、势三者合为一体。如今,先生又让寡人奉法为尊,寡人糊涂,法、术、势到底该以何为重?”
嬴政向前倾着身子,似乎整个人都要凑过来,琥珀色的双眸里闪动着期待的光芒。那光芒过于耀眼,却又真诚无比,令韩非不得不动容着将心中所想和盘托出。
“法者,国之权衡;术者,人君驭臣之计;势者,乃为威权。法之本身并无权威,写在简牍上、或刻于钟鼎上,只不过都是文字而已,赖何可以使天下悉数遵从之?当然是君主之威。君主制法、而后推行于天下,所以,尚法必先尊君。冠虽贱,头必戴之;屡虽贵,足必履之;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但君主高高在上,常不知臣下心中所想。人之本性乃趋利避害,人臣亦不例外。害己利国之事他们不会乐意去做,所以臣子之利难免与国君之利相悖。君主要树立律法权威,就必须要控制威权、驭臣于下,使其不敢欺瞒于上,一切皆以君主之意为准。人君掌握术、势,皆是为了维护法之威严。法术势三者兼重,却要以法为本,以术势为辅,绝不可舍本逐末,颠倒轻重。”
韩非的话音刚落,嬴政便忍不住抚掌赞叹:“法为本,术势为末,无法则国乱,无术势则法无威,寡人记下了。”
说到这里,他又稍稍顿了一下,继而压低了声音:“若是……寡人可将华夏一统,该用什么来统御天下?”
韩非一愣,疑惑地反问道:“自然还要以法治天下。王上何来这一疑问?”
嬴政收起笑意,眼神变得凝重起来:“六国若灭,难免人心不服。我秦人早已懂法、守法,然六国却以礼来教化于人,并未形成奉法为尊的习惯。寡人是怕用法过急,无法稳定人心……”
“原来如此。”韩非闻言,立刻便洞察出嬴政的隐忧,“王上其实是想问,待天下一统,到底是该用礼来教化六国遗民,还是该用律法来约束他们。”
“正是!”嬴政连连点头,“请先生赐教!”
韩非凝神想了想,复又缓缓开口:“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所以单凭仁义之礼不能治天下。好利恶害乃是人之本性,人既懂得趋利避害,则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则天下可治。王上志在天下,待六国一定,这些遗族们最担心的就只有一条,那就是能否被秦王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法为国之权衡,明令著于官府,公开、统一、赏罚明确、一视同仁。比起虚无缥缈的仁义教化,成文定律才更能让六国遗民安心。王上要稳定人心,就该知道人心最怕的是什么。六国若被秦国所灭,六国之人最怕被不公平对待。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能比‘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的律法更能安稳人心?”
嬴政紧紧抿着嘴唇,认真将这些话听入耳中,一边颔首一边感慨:“看来,寡人若要得天下,就必须一手秦剑,一手秦律了。”
韩非缓了一口气,轻轻扬起下颌:“明君以明法、责实而治天下。除此以外,别无良策。”
嬴政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良久不语。韩非也不再多言,只挺直了腰身垂首望着地面,似是想着什么心事。
过了半天,嬴政才回过神来,见韩非一副默不作声的模样,忍不住自嘲地笑了一声:“瞧瞧寡人,真是失礼!让先生口干舌燥说了半天,竟连杯水都没有!”
说完,他又唤了下人进来,送上两盏热茶。
韩非盯着那冒着热气的茶盏,神思却依旧没能收回来。他幽幽地长叹一息,竟似自言自语一般苦笑:“灭了六国,韩国何存?”
韩非声音极低,却被嬴政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
原本漾在脸上的笑意不自觉地僵了一下,嬴政却很快遮掩过去,只当自己没有听见。他举起杯盏,朝韩非遥一相谢:“先生倾囊相授,知无不言,寡人甚为感动。此处无酒,寡人便以茶代酒,敬先生一杯!”
韩非这才惊觉自己失言,他有些慌乱,一抬头却见嬴政仍旧和颜悦色地看着自己。他迅速整理了一下思绪,方要举杯却手中一滑,将杯盏打翻在地。 少府遗珠:帝女逾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