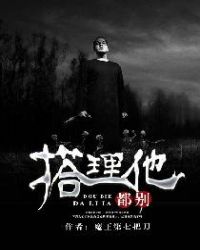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都别搭理他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甘露村,这也算上佳的名字了。
就像戴眼镜的叫眼镜,长得高瘦的叫麻杆,戾气的叫魔王,沾花惹草的富二代叫王子,颛孙小梅叫狐狸,妹妹叫小点点一样,甘露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干涝滩。绰号除了让人感觉亲切外一般还非常精准。干涝滩的意思非常明了,一般情况下都是旱天,好不容易盼着下场雨吧,还不能下大了,一大了就涝,尤其水沟地那边。
涝的轻的话一般就是叹叹气摇摇头,等着老天止雨晒地,老天湿了老天晒嘛。不达观也没办法,靠天吃饭就得忍着点。卷起旱烟,三三两两又天南地北的海阔天空。重了,还是没办法,除了长吁短叹就是背着手回家。人们不再闲谈了,哪里还有那份兴致?明明昨天看过了,今天还要去看看,怕看的不准似的。
井里的水漾上了一尺来。
甘露村有三口井。北井,东井,南井。南井东井都在小河边上,沿河取其水的意思。北井取的是地下水,水质清冽甘甜。北井就在我家西园的东面,隔着一道院墙。也就在那小广场的西面。东面有一盘石碾,天天有人在那里碾东西,石碾骨碌骨碌的转。
关于井,甘露村有谚语云:干涝滩干涝滩,一根井绳秤十三。井绳都十三斤,你可以想想那井得有多深。绳头的铁钩勾住水桶,顺着井沿慢慢把水桶滑到井底水线那里,摇摇绳子突然一松,水桶翻身扣住井水,水打满了,就往上拔井绳。力气大的一个人,力气小的还得有一个稍活的,就是站在拔井绳的人后面,他使劲你也使劲。小孩子不能靠近井口,大人朝井底看都眼晕。
井口用四块石板砌成口字型。下桶的时候为了省劲并且和其他来打水的人说闲话,就让绳子顺着井口的石板倒腾着手往下滑。日积月累,井口的石板上就产生了道道凹槽。据说有搞收藏的人对这些个石板也瞄准了眼光。
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党的情。这是为了感恩。挖出井来本来就是用于取水用。但井绝对还有另外一种用途,这和“升困井革鼎震继”《易经》中的“井”没有关系,那就是用来跳的。
跳井,是自古以来自杀的方式之一。
父亲去蹲他的大狱,他的妻子带着四五岁大的孩子和公婆一道焉焉巴巴过着日子。
长期以来她都不愿意把人想得很坏,但事情本身却会超出她的认知范围。她受到了惊吓,老有影影绰绰的鬼影子出现,在大门口,在墙头,在庄稼地里。也有那不相干的人来搭个讪说个风话什么的,她避之唯恐不及。晚一点在胡同道子行走,都有人蹑手蹑脚跟在后面,她认出了是谁,但和谁也没说过。现在谁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怀疑归怀疑。好在那人现在也已经命赴黄泉,只好都对这件事情缄默着。
惊吓是处心积虑的,也是要命的。假如你忽然发现你原先认识的一个人转变了另一种模样,呲牙咧嘴,斜眼歪鼻,说一些最恶心最伤天害理的话,你会拒绝承认,接着你会颠覆你对这个人甚至人这种物种的看法。我们现在叫崩溃了,倒塌了。她吓得都不敢出门,呕吐和流眼泪。
爷爷略有察觉,也曾拐弯抹角提醒过那人。但一个人如果做了魔,尤其在一个人面前做了魔,他会在这个人那里一直的恶魔下去。我用魔这个词来形容,是说极坏,卑劣,无耻之尤,猪狗不如,和人的修心养性中的魔南辕北辙有云泥之别。
这个人是不是家族中的人,还是曾经和父亲称兄道弟的好友还是不相干的人,知道的人绝不会说,不知道的人再也不会知道。那下面就是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说,她是病死的。也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自然也没受到什么惊吓。父亲的入监对她打击很大,伉俪情深,思念如刀。面黄肌瘦,逐渐枯萎下去,22岁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瘦弱的肩膀担不起也不用再担家庭的重任。这个版本说,跳井的是大哥的母亲,不是她,只是又给救起了。后来才发生了甘露村历史上的第一件离婚案。
一个版本说,她跳井而死。有人恶鬼般地拦缠她,不如愿后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择手段地吓唬她。冷月迷蒙,野风肃杀,她觉得自己走到了穷途末路。“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于是“举身赴清池”,双眼一闭,一了百了。
那时父亲刑期未了,铁窗度日。人走时洒泪而别,归来时已经燕子楼空。
过去了的事情再刨出来寻根问底,这也是一种亵渎。就此打住。
暖冬这个词现在已经不被郑重其事的提出,暖冬这种现象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暖冬按着自己的规律自转着也因着世界环境的指标公转着。它常说的语言是肯定句式,“是这样”。它适应了市场规律,在被人们广泛应用。暖冬好啊,不用吃饱了饭提溜着小板凳缩着脖子一老一少的去晒太阳。
晒太阳是在西场,懒懒地靠着南墙,半开半阖着眼,做着蝴蝶穿过花架秧子的梦。阳光冒着热气撒下来,如同热恋。爱情是给予,你挥霍是爱,珍惜是情。阳光无私大度一视同仁,穷通寿夭,智愚贤劣,都在这场恋爱里。长久的爱需要的就是永不枯竭的心,义无返顾的长久热情。
靠着的这堵墙后面就是老穆大娘的家。朝东的大门,门口一颗核桃树。夫家姓李,延字辈。好像头上没多少毛,常年戴着个帽子。一顶布帽的时候多,夏季的时候会卡一顶竹笠。高个,没人引诱,也说不了多少话的主。
老穆大娘据说是来自于东北,什么省什么县这可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她回去过老家。就算拖儿带女的回去过一次,估计都剩下了些远房,故址连模样都没有了,一代新土盖旧土,别人家正在那里盖房呢。或者人没找到,地方没找到,偶尔进一家问问情况吧,恐怕那茶水比冰还凉。是啊,人一走,茶就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老穆大娘性格开朗,人长得虽然不是很美,但模样极端的周正。没有架子,爱说话,爱打招呼。我少年成长的时候,步步坎坷,从没有大人像孩子一样和我说话。大人和你说话,主要的是问,你回答。再就是他们发布命令,你执行。而老穆大娘说话的方式不是这样,她会从琐碎的事物中找出乐趣来,拿你像孩子一样来关怀和交流。任何时间,任何场景都能开出通道来,也许还会“小色孩子”的骂,但那更多的是亲切。
印象中,她一直是短发,头发刚好把脖子盖住,头上用几根黑色的小发卡别住头发,脸颊两侧的就往耳朵后面一抿。看到别人倒腾着干活,她会立刻蹲下来帮忙,不管她自己的事情紧急不紧急。据说,她还救过我一命,我不记得了,那时还不大,没有记忆,也许比晒太阳的时候还小些。
西井是甜水井,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西碾在路口,需要碾压些东西的时候也来这里,压豆扁子,轧花生糁子,谷子赶成小米,小米坉成米面,花生饼压碎,磕玉米等都来这里。大石滚子围着大石盘转,拿个短棍插进铁把手里,一路推着走,转着没有完结的圈。我不知道怎么一来二去的就到了井边,双腿还伸在井里面,一摇一晃的。井沿上应该很湿,也很滑溜,那就是说一不小心我就会掉进去,当然不会游泳了,掉进去就是个死。
根据经验这时候是不能喊不能咋呼的,孩子一激动,情绪升温47。5,没被淹死也烧坏了。母亲在斜前方说着不温不吐,和孩子交流的那些话,老穆大娘藏藏匿匿的摸过去。一把抱住孩子,“我的儿呀,你怎么这么祸害人呢。”有惊无险,但也千钧一发。后来觉着老穆大娘可亲可敬,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臭丫头成瑶子是她的女儿,高中之前我就爱偷偷看她,也只是看看而已,那未必是爱。看着的时候,心里很平静。离的不远,又是一个生产队,七队,很多的交往,看的机会也多,暗暗的喜欢。
和母亲站在一个时代,印象较深的女性很多。姑母是冰冷的训斥,还带着一点厌烦。老穆大娘是和蔼可亲,叫人如沐春风,能消除年龄的距离。如今也有八十余了吧,当年的干净利索,不知道变成了现在的什么样子?
原先真的不知道泰山还和长白山牵上了关系,都是山不假,说的似乎是地理风水什么的,那大约是一个势,头在这里,身体蜿蜒在那里。把照片从某些角度拼合,还能看出更神秘的东西。老辈人闯关东,遗民遍地。现在也该换换时代了吧。
泰安城里的东北人不少。老穆大娘几十年前就过来了,是有先见之明,还是不小心的就成了先驱? 都别搭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