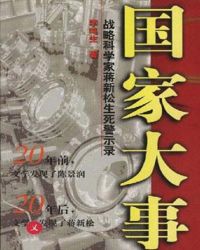参考段:关于蒋新松的另一种阅读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参考段:关于蒋新松的另一种阅读
本文写到这里,似乎也可以结束了,却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我停下敲击电脑的手指问自己:你写出一个完全真实的蒋新松了吗?我回答自己说:没有!历史从来不能复制,也永远不可复制。我又问自己:你想传递的意思和想说的话也全都写进去了吗?我肯定地回答自己说:没有,也不可能!
于是,关于蒋新松——或者应该说关于中国的科学家,便有一些问题需要也很有必要同我的读者们坐下来一起来探讨探讨。由于有些问题一时很难用“对”或“错”来做简单的判断,更不可能让某个部门或者某个权威人士下个标准、做个定论什么的,故,我将本段称之为“参考段”;而有关“参考段”中涉及到的问题,我们则可将它看作是对蒋新松或者说是对中国科学家的“另一种阅读”。希望你在这种阅读过程中,真正参与进来,随时发表或者保留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意见——第一个问题: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为什么总死?
蒋新松去世后,国内国外,几百乃至上千封唁电像雪花般飞向沈阳。主要单位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机械部、北京市科委、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安徽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等。此外,还有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及香港地区的有关部门。主要知名人士有: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国务委员李铁映,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键,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上将)沈荣骏,辽宁省委副书记王怀远,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副院长胡启恒,清华大学老校长张光斗,清华大学现任校长王大中,美国华盛顿大学机器人教授(美籍华人)谈自忠,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翁史烈,哈尔滨工程大学校长吴德铭,重庆大学校长刘飞,以及航天专家杨嘉墀、火箭专家屠善澄、自动化专家吴澄、信息专家汪成为等。
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列出上述权威单位和权威人士,是因为他们对蒋新松最有发言权;所发唁电和书信尽管形式不同,但在对蒋新松的评价上,措词却是惊人的一致:蒋新松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巨大损失!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科技带头人、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而感到无比悲痛和惋惜!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唁电中说:蒋新松同志是一杰出的科学家,也是科技界优秀的组织管理人才。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高科技事业,他为我国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在唁电中说:惊闻噩耗,五内俱伤。多年来新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我国自动化事业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技术骨干人才。我与蒋新松多年同事,深知他才高出众,并有着困难压不倒、挫折推不垮的顽强斗志与蓬勃的朝气,如今突然辞世,实在使我难抑悲伤。
是的,蒋新松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一位难得的科技帅才,一位真正的民族荚雄!他用他的一生,甚至用死,证明了他人生的价值,同时也证明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与忠诚。从他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一个科学家用科技这个杠杆撬动历史巨轮时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也看到了新一代科学家在这个大时代中的奋斗身影、科学精神和独具光芒的智者品格与人格魅力,同时还看到了一个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沉重与艰难。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还把战场摆在了他那台几乎彻夜不停的便携式电脑上。他去世后,当我们打开他电脑里的所有文件时,便不难发现,蒋新松的一生实际上是由多种角色统一而成的,而贯穿他多种角色始终的,是他身上那一腔永生不灭的爱国赤诚,以及与生俱来的智慧和百折不挠的勇气。他鄢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灵和一副疲累不堪的身躯,本身就是一座纪念碑,而碑文全都刻在了他为国家所做的那一系列大事上。他是一个自觉的先行者,一生追求的实际上只有四个字:国家大事!他爱国是自觉的,主动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被动的;他爱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国,而是体现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层次上,体现在他的帅才上。他的爱是一种大爱,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爱。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也并非只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和整个时代。他不仅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科学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是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生命方式。他的生命方式其实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罕见的博大胸怀和非凡的人生姿态。他很像一团看不见的火,始终照亮着他周围的人和他生存的这个世界;他又像一束无形的光,总能让他身边的人感到现实的温暖和明天的希望。他在到达生命终点前的那一时刻,还依然想着国家的事情,仅此一点,便令我们高山仰止,一生汗颜!我想,不管是谁,只要走近他生命的岸边,一定会感到自己生命的河床里肯定缺点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蒋新松首先是一个隐形英雄,一个精神斗士,一个活着的现代的罗米修斯,然后才是一个科学家!
然而,我要提出的问题是:蒋新松还不到66周岁,为何转瞬间却溘然长逝?!
1997年4月3日,是蒋新松出殡的日子。这天,在沈阳通往殡仪馆的文翠路上,拥满了众多的人群。为了不让过路的车辆惊扰科学家沉睡中的思考,沈阳市破例出动警车,为科学家护灵;而民政局长一早便赶到路边,含泪捧着蒋新松的骨灰,亲自为他所敬重的科学家送行。灵车启动时,蒋新松的妻子、儿女、亲属、同事、学生以及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们,万分悲痛,泣不成声。这时,一位前不久刚刚参加了邓小平逝世追悼大会的老年知识分子,面对悲伤的人群,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唉!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为什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地死?”
蒋新松的岳父,已是一位80岁的老人了,他得知蒋新松去世的消息后,匆匆赶到蒋新松的灵前,面对蒋新松的遗像,忍不住泪流满面:“新松啊,你是一位世纪科学家,你还不到66岁呀,可为什么会是我这个白发人来送你这个黑发人呢?”
丁岩,这位85岁高龄的老太太(就是我在前文中写到的为蒋新松平反的那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当她在重病中得知蒋新松去世的消息后,让人搀扶着来到蒋新松的灵前,面对蒋新松的遗像连连鞠躬致哀。她一边抹着泪水,一边感叹地说:“新松啊,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呀!可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偏偏先走了呢?”
是的,所有认识蒋新松的人都在感叹:蒋新松死得太早了!
1997年5月21日晚,我专程来到沈阳蒋新松的家中。蒋新松的家充满了心酸与悲凉,他的妻子张丽珠一见我,便泪流满面,痛不被生。她指着一盆花对我说,不知什么原因,这盆花原来开得好好的,老蒋一去世,它就枯萎了。她又说,老蒋去世都一个多月了,可我每天都觉得他还在我身边。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沏上一杯茶放在他的灵前。他的公墓里,我还给他放了一把最好的刮胡刀。他生前太忙了,工作就是生活,生活也是工作,连胡子也没好好刮过,现在总算歇下来了,可以有时间好好刮刮胡子了!她还说,老蒋去世后,小儿子蒋雨扬把他爸的头发剪了一小撮下来,带回清华大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每天都要看上几眼。儿子说,他要让他爹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他去奋斗,一定要争取在他的学科里干到他爹那个份上。太遗憾的是,他爸死得太早了!……
我站在蒋新松的灵前,默默地向蒋新松鞠躬、默哀。面对蒋新松的遗像,凝望着他那双充满了苦难与幸福、激情与智慧、希望与自信的眼睛,怀想着两个月前在清华大学同他交谈的情景,我想了很多很多。而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还是:此前我们曾经死了一个科学家蒋筑英,现在我们又死了一个科学家蒋新松,那么明年或者后年,我们会不会又再死一个“蒋翠竹”或者“蒋秀花”呢?蒋新松还差,6个月才满66周岁,按照南方人的算法,他实际年龄才只有65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轮不上该他死的时候,可为什么他会匆匆别离人世呢?当今社会,有那么多该死的人——如一些贪官、凶手、骗子等;可这些该死的人非但不死(据说有的被判了死刑也能用金钱把人从监狱里买走),反面还活得潇洒自由,有滋有味,而像蒋筑英、张鸣歧、孔繁森、蒋新松这样的好人却偏偏一个接着一个地死?这究竟是为什么?
病,固然是最直接的“杀手”,但仅仅一个“病”字,就是唯一的答案吗?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蒋新松26岁时不被打成右派,他生命的小舟会被磨损得如此之快吗?假如他探索的利剑不去穿透科学的迷雾,追求的战车不去冲破真理的秘密,他生命的防线会有如此脆弱吗?假如他平反后不是拼命地追赶时间,为国家的事情过度操劳,而是一心一意地保养自己,他生命的链条能这么容易就被折断吗?假如他被送进医院后,病情能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或者能用专机送到北京,使他能接受到更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更高明的抢救水平,他生命的发动机能这么快就熄火吗?
然而,历史拒绝假如。
现实是,建国以来,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包括所有的知识分子)英年早逝者大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尽管党和政府重新为知识分子落实了政策,科技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大有改善,生活待遇也大有提高,尤其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对科技知识分子尤为关心和重视,但自蒋筑英、罗建夫等科技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之后,近十多年来科技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悲剧依然还在不断上演着。仅以蒋新松所在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为例,我从采访中得知,在已经去世的一二十个专家和技术人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年龄超过了60岁。而同蒋新松起最早搞机器人的吴继显和谈大龙,一个(吴继显)去世时才59岁,另一个(谈大龙)虽然有幸还活着,但在担任“863计划”专家组组长期闻,两只眼睛也几乎全给熬瞎了,现也成了一个活着的盲人!而年龄还不到60岁。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几份“死亡报告”:
1986年3月8日,新华社讯: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共去世134人,这些人的平均寿命仅53.3岁。1995年,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人员患病率高达80%;动物所体检时未见异常者仅5%(即是说95%的人都有问题);数学所患高血脂症的高级知识分子占71%。
1988年,国家体委科研所的李力研先生。曾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对北京中关村的科技知识分子做过调查。此次调查结果显示:科技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8.52岁,而且在岗的知识分子中有61.08%的人正患着各种疾病。而早在1982年,有关部门在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推算出来的全国人均寿命已达68岁!10年后,当李力研先生对这一问题再一次进行调查时,其结果令人不寒而栗:中关村的科技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3.34岁!即是说,比10年前不但没有上长,反而还降低了5.18岁!
1997年8月,中国科学院为摸清职工因病死亡状况的底数,以便进一步做好增强职工身体素质方面的工作,院工会对中国科学院全国在所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的死亡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此次调查的时限为1991年1月1日—1996年底,调查的人数约为71964人,其中科研人员为48458人;行政管理人员为7651人;工人为15855人。其结果表明:6年来在职科技人员因病去世的共有707人,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23岁!离退休科技人员因病死亡人数为1383人,二者加起来的平均死亡年龄也才只有63.33岁!大大低于1990年北京市人均73岁的期望寿命数!
显然,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读到这一份份“死亡报告”时,都不会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总死?都不会不为我们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们深感惋惜和遗憾,都不会不引起心灵的强烈震撼。然而,这一份份可以震撼全体国民的“死亡报告”,能不能震撼某些决定科学家命运的部门和领导人呢?能不能震撼那些不利于科学家生命健康的各种“红头文件”和条条框框呢?能不能震撼那些长期以来总把科学家(包括所有知识分子)当工具面不当人才的错误认识与“左”的观念呢?
邓小平早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说得有多好啊!但我们的各级领导是否全都准确地理解了小平同志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呢?“科学技术”既然放在了“第一生产力”的位置,科学家的生命健康问题当然也应该放在“第一”的位置。否则,又用什么去保证“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呢?
所以我很想说的是,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但愿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变成真正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但愿今后不要再出现第二个蒋新松;但愿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个个都长命百岁!但愿这个世界尽死坏人,不死好人;但愿该死的全死,不该死的一个也不要死!
然而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又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是不是到了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第二个问题:凡人成为“典型”后,该是什么命运?
我在采访蒋新松的过程中,曾先后遇到过两种情况,一种是蒋新松的事迹还没有在全国各大报纸、电台广播宣传之前,也就是说,在蒋新松还没有成为全国科技界学习的“典型”之前,我每到一处采访时,人们谈起蒋新松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几乎是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想谈什么就谈什么,想给我谈什么就毫无保留地谈什么。那感觉,真实、可靠而又显得亲切,绝对像是在自豪地谈论一个民族英雄。然而奇怪的是,当蒋新松的事迹被宣传之后,即蒋新松成为所谓的“典型”之后,我再采访时,似乎感觉一下子就变了,总觉着有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障碍”,不少人——尤其是蒋新松所在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人与我谈起蒋新松来,舌头好像一下子就变得不那么利索了,总是显得顾虑重重,不很痛快。
显然,问题出在“典型”二字上。
建国后,我们有树“模范”、树“典型”、树“英雄”的传统,而且我们树立的不少英雄模范,像雷锋、王杰、焦裕禄、孔繁森等,应该说都是成功的,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人教益人的作用。但有的“典型”,也不尽然。尤其是在“四人帮”统治时期,随着“英雄”或“典型”的泛滥成灾和一些假“英雄”、假“典型”的屡屡出现,人们对“英雄”或“典型”开始由崇拜到疑问,从迷信到不信,甚至人们对“英雄”或“典型”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于是,凡人成为“典型”或者“英雄”后,命运受到了威胁。一方面,有的人在成为“典型”或者“英雄”之前,还是一个人,可一旦成为“典型”或者“英雄”后,自己就不那么像个“人”了;另一方面,有人在不是“英雄”之前,人们还把他当人看待,一旦成为“英雄”之后,人们似乎就再也不当普通人看待了。因此,有的人本来活得好好的,一旦成为“典型”后,日子反而开始不好过了,也很难再像一个正常的人那样继续工作、学习、生存下去了,甚至有的命运从此一落千丈!
这是为什么呢?
本来,蒋新松这个人物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是一个上上下下都一致给予肯定的人物,他的出现,也属正常。在1997年4月9日国家科委组织召开的“学习宣传蒋新松事迹座谈会”上,我就亲自听见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的同志明确表态说:我们提倡全国科技工作者学习蒋新松,是为了倡导一种时代精神,这并不是我们硬要大家去学习蒋新松,人为地树一个什么“典型”。这种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典型”一旦进入现实生活后。有些问题为什么就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了呢?
比如,蒋新松被定为全国科技界学习的典型后,各大报纸开始整版整版地刊登了他的事迹,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有人说了,为什么蒋新松死了一年之后才宣传呢?怎么死了才说他这也好那也好呢?难道蒋新松是因死才显得非凡与伟大吗(因为蒋新松刚去世时。他的学生提出,能不能在报纸上发上一小块消息?有人说不行,理由是蒋新松还不够格。蒋新松去世时有人还主张不写悼词,说写个事迹材料就行了,但多数人认为应该写悼词,最后还是写了)?假如他没死,全国人民能知道有个蒋新松吗?能知道他是哪里人和干什么的吗?假如他没死,他的人生会有如此光彩照人吗?他的事迹能流传于世吗?假如他没死,全国能有这么多人知道他、关心他、感叹他、议论他、感激他、尊敬他、崇拜他、怀念他、牵挂他、学习他吗?如此说来,蒋新松的死,是不是比他活着更有意义呢?
又比如,蒋新松成为典型后,各种会议层出不穷,不步科技人员频于参加各种会议,于是有人说了,要是蒋新松一旦醒来,看见这么多人坐在这儿开会,不上班干活,是肯定要大发脾气的!因为蒋新松生前最反对的,就是务虚不务实,光开会不干活!据说,辽宁方面为宣传好蒋新松的事迹,还专门拿出了100万人民币?应该说这对宣传蒋新松是件好事。但也有人说了,这钱怎么早点不舍得拿出来呢?如果这100万在蒋新松生前就拿出来,用在蒋新松和其他科学家所从事的科技事业上,不比现在更实用更有价值吗?我们对一些“英雄”或者“典型”为什么总是雨后送伞呢?
再比如,蒋新松在没有成为“典型”前,人们对他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但蒋新松忽然成为“典型”后,尤其是一些报道出现某些夸大、失真或片面后,一些人便有了一种逆反心理,反而不怎么说蒋新松如何如何好了。有的开始对蒋新松另眼相看、敬而远之,甚至干脆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有的本来对蒋新松的看法是不错的,可请他谈谈蒋新松时,他却说,蒋新松现在是全国学习的“典型”了,不能“乱说”。这所谓的“乱说”,实际上就是不能完全讲真话的意思;甚至有的还会冒出一句:蒋新松都被“吹”上天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像是已经去世的蒋新松又犯了什么错误似的。
上述说法未必正确,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典型是什么?典型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全体民众学习的标志。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一种安慰,同时也是死去的人对活着的人的一种寄托和激励,而决不是一种政治工具!毫无疑问,每个民族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该有自己学习的英雄,都该有自己学习的典型,没有英雄和典型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但如果出现了假英雄假典型的民族,则是一个可耻的民族!历史进入90年代后,中国人开始变得成熟了,变得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看别人、也看自己了,同时也变得会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了。所以,关于“典型”和“英雄”的问题,并非一个轻松的话题。应该塑造什么样的“英雄”和“典型”?怎样才能塑造好“英雄”和“典型”?宣传典型、支持人才到底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最佳时机?是生前多关心多支持好,还是死后隆重悼念、频繁开会好?对典型的宣传,该如何把握好宣传的方式、宣传的尺度以及宣传的分寸?尤其当凡人一旦成为“英雄”或“典型”后,我们该如何善待“英雄”或“典型”,该如何营造一个适合“英雄”和“典型”生存的社会空间,让英雄的精神更好地得以发扬光大,让典型的命运少些坎坷,让“典型”和“英雄”有个正常的命运……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重大社会课题。第三个问题:科学家该不该有一辆小汽车?
蒋新松生前拥有两辆车,不过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一辆是他获“五一”劳动奖时奖励给他的新车,在沈阳家中。他每次在沈阳时,出门买菜或者干别的什么,便总是骑着这辆车;另一辆就是我曾在前文中提到过的他用60元钱买的旧车。这辆旧车他在北京工作时使用,至今仍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车棚里。
我之所以再次提起蒋新松的自行车问题,并非是想说蒋新松很穷,穷得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这绝对不是事实,也不是我感兴趣的话题,而是说,蒋新松只有自行车,没有小汽车,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像蒋新松这样的科学家,应不应该有一辆小汽车?
据我的调查,在中国,科学家能有自己专车的,几乎寥寥无几。像中国的氢弹之父王淦昌、光学之父王大珩、航天之父任新民、水稻之父袁隆平,以及“863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和别的领域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等,统统都没有自己的专车。
为什么?
级别不够。
按照我国国务院有关方面的规定,必须部长一级才有资格配专车。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只要你投当上部长一级的领导,无论你有多高的水平,不管你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一哪怕你造了一架飞机、一艘航空母舰、甚至一颗原子弹,也没有资格配小车。当年,钱学森回国时,也没有小车。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出于对他的特殊照顾,想了不少办法,最后才从国务院进口的有限车辆中拨了一辆。
我在写这段文字对。曾停下写作,就科学家有没有小汽车的问题。专门打电话向著名科学家王大珩老先生讨教。下面是1998年12月8日下午4点我和王老在电话中的一段对话:
我问:“王老,你自己现在有小汽车吗?”
王老(先笑了):“我自己哪儿有小汽车呀?”
我问:“像你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没有小车呢?”
王老:“这个国家有规定,要部长一级才能配专车。我们中国科学院只有院长、副院长才有专车,其他科学家都没有的。”
我问:“那你现在用车怎么办呢?”
王老:“科学院在原则上保证我用车。比如开会呀干什么的,我事先打电话,院里再做安排……不过,我现在用车还比较方便。”
我问:“为什么?”
王老:“因为我在空间中心兼职,他们给我安排了一辆车。”
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买一辆呢?”
王老(又笑了):“我哪儿买得起呀!”
王老只差两个月就满84岁,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英国留学10年,是中国第一批科学院院士(学都委员)、“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在科学技术上一生中创下了20多个“中国第一”,被人们誉为“中国光学界的泰斗”和“中国光学之父”。那么像王老这样的“中国光学之父”都没有自己的小汽车,其他科学家就可想而知了。
蒋新松也没小汽车。
蒋新松在沈阳当所长时,出门时基本可以保证有一辆小车,但也没有专车。他在北京时,不但没有自己的专车,而且连像王大珩那样在“原则上”保证用车都无法完全做到。因为他所在的“863计划”专家组根本就没有小车。他每次出门开会,有时是专家组办公室从清华大学帮他要车,有时就“打的”,有时就干脆自己骑自行车。应该说,蒋新松在世时,国家科委和清华大学对他相当不错,不仅想法先在清华大学给他借了一套住房,而且,国家科委的朱丽兰副主任等几位领导还积极争取给他解决一套房子,只可惜这套房子正办批准手续时,他却匆匆去了。至于小车,国家科委自然也就无能为力了。
几年前,我曾站在北京的一座立交桥上,卡着手表做过一次无聊的统计:1分钟内从我脚下来回驶过的小车,有88辆之多!我知道,用公款争相购买小汽车,是中国前些年最为“壮丽”最为“气派”的一大“景观”。有的单位买车,买了一辆再买一辆,全要名牌的,全要进口的,看谁的外汇花得多,看谁的牌子名气大,你追我赶“争上游”,谁也不甘落后当“下游”。我还知道,现在有的地区的一些小科长、小处长、小局长什么的,每人都有自己的小车(有的是占用公家的,有的不知是用什么钱买的),并随时都可以驾着小车带着老婆或者“小蜜”满街逛游。然而,在90年代的今天,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管大街小巷小车如潮、车满为患却就是没有一辆属于我们中国科学家的(个别科学家除外)!
这让我想起了明星。(明星已经被人们说得多了,不想再说了。)
还让我想起了足球。
先说一段新闻:伊朗足球明星马达唯基亚,参加完世界杯后由于按政府的规定不得不服两年兵役,因而只好被迫放弃了去欧洲一流俱乐部踢球的邀请。但正当他即将服役之时,伊朗政府鉴于他在世界杯赛期间对美国队的比赛中为伊朗队射进了制胜的一球,决定为他免除兵役,因而这位素有“德黑兰小公牛”之称的球星得以在1998年亚运会上大显身手!
在中国,球星的待遇同样不差。据说,某些场次一个球员只要能踢进一个球,便可得几万甚至10万人民币(我这里想说的,不是该不该拿和拿多拿少的问题,只是借此作个比较而已)。记得有那么一场球,比赛还没开始,小汽车已经放在球场边上了,谁能获得最佳射手,便可得到一辆小汽车。这辆车,运动员当然该拿,但同样为国家“踢进”了不少“好球”的科学家们,又该不该拿呢?
读完蒋新松的赦事,我们可以想想,科学家蒋新松“踢”了多少年的“球”了?他“射破”了多少旧体制、旧传统、旧观念牢牢,把守的“大门”?别说“踢进”了一个“球”,漂亮的“金球”恐怕也“踢进”了好几个!比如:
他为中国研制出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改写了中国没有机器人的历史,这算不算他为中国“踢进”的一个“好球”?
他打进苏联的国门,与俄罗新专家联手,为中国研制出了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这算不算他为中国“踢进”的一个“好球”?
他为中国创建了完全可以号称,“亚洲第一”的国家机器人示范研究中心,这算不算他为中国“踢进”的一个“好球”?
他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研究中心,并获得美国“大学领先奖”和“工业领先奖”,这算不算他为中国踢进的一个“好球”?
他身患多种疾病,仍坚持从科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出路,并写下了中国第一篇探索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的长达3万字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企业必须重组的重要理论,为国家贡献了一份极有份量的历史性文献,直到去地的最后时刻,也念念不忘此事,这又算不算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中国“妙传”了一个最关键的“好球”?
但我们的纪检部门可以派人去查一查,看蒋新松究竟得了多少人民币?看又有谁给过他多少马克或者美元?
也许有人会说,科学家有了发明创造和杰出贡献,不照样也有奖金吗?
不错。在我国,目前主要设立了四个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这四个奖项,是国内最高规格的科技大奖。那么它的奖金是多少呢?现在,就让我把以上四个大奖的奖金在此作个公布吧——
国家自然科学奖,1993年以前的奖金是:一等奖2万元,二等奖1万元,三等奖5000元,四等奖2000元;1993年之后的奖金是:一等奖6万元,二等奖3万元,三等奖1.5万元,四等奖6000元。
国家技术发明奖奖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奖相同。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以前的奖金是:一等奖1.5万元,二等奖1万元,三等奖5000元;1993年之后的奖金是:一等奖4.5万元,二等奖3万元,三等奖1.5万元。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3年以前的奖金是:3—6万元。1993年之后的奖金是:10—20万元。
显然,在这几个奖项中,奖金最高的是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但要想拿这个奖相当不易,即使有幸评上了,还须经国务院批准。而且能获得这个奖项的都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集体,比如像“长征3号”运载火箭研制工程什么的,少则几十人,多者数百人,所以等这份奖金分到每个人的手上时,最多者恐怕也不过就两三千块钱罢了。更何况上述四个奖项两年才评一次,一次就一个(有时最多两个),有时连一个也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奖1998年度就空缺)。再说,中国的科学家成千上万,鞠躬尽瘁、呕心沥血者大有人在,而一生中能有幸获得其中一个奖项的,又有几个呢?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足球,想起当今中国的足坛霸主“万达”。“万达”之所以能横扫全国,称霸足坛,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是遇上了一个好老板王健林!如果没有像王健林如此气派的老板的鼎力支持,“万达”?要想威风八面、连年不败,可能吗?
那么,好了,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大老板们能像王老板支持足球那样来支持我们的科学家,那中国的科技水平,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的科学家,又该是怎样一种气派呢?
毫无疑问,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像蒋新松这样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若是真要与我们的男足相比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一辆自己的小汽车呢?
然而问题是,应该,是一码事儿;有没有和能不能有,又是另一码事儿。如今健在的中国科学家们在不久的将来能不能有一辆自己的小汽车,我不敢断言;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蒋新松生前如果能有一辆小汽车的话,他绝对不会再花60元钱去买那辆破破烂栏的自行车!
活着的中国科学家们,你们什么时候才有一辆小汽车呢?第四个问题:蒋新松到底是人还是神?
蒋新松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这一点已是无可非议、不用争辩的事实。但蒋新松这个“典型”是不是就完美无缺呢?比如,作为一个人,他的人性有没有不完善的一面?他的性格有没有什么缺陷?作为一个所长和总经理,他会不会也变成了一个贪官?作为一个首席科学家,他有没有重大决策上的失误?有没有搞“科学造假”的行为?等等。
过去,像蒋新松这样的“典型”人物,我们是忌讳谈缺点的。但我想,如果我们对英雄和典型人物从另一方面也作点探讨,说不定同样也很有意义。因为英雄和典型也是人,不是神,而是人就会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缺点。邓小平不就说过吗?我最多是三七开!蒋新松自己也常常对同事们说:“有突出优点的人,常常伴随着突出的缺点。”蒋新松无疑是有“突出优点”的人,那么他的“突出的缺点”是什么呢?
我在采访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蒋新松是否实事求是?在科研活动中是否有弄虚作假的行为?
我得到的反映是:蒋新松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他最反对、最反感的就是弄虚作假。他对每一个科研项爵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他自己不搞弄虚作假,也决不允许别人以假代真、以假乱真。
我在采访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中国“863计划”自动化领域一个首席科学家,蒋新松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有没有失误?他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没有不足或者偏差的地方?尤其是一些重大工程项目,有没有过失败?有没有给国家造成过经济上的损失?
我得到的反映是:无论是蒋新松在担任所长和首席科学家期间,他所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侧重搞工程的,而工程项目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一旦立项,国家就要投资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人民币。蒋新松所搞的几个重大工程项目都取得了成功,没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我在采访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和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的总经理,蒋新松是否廉洁?会不会也是一个贪官?
我得到的反映是:尽管当今中国,贪官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一个话题;尽管蒋新松既是所长,又是首席科学家,还是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的总经理,手上曾经控制着几千万的人民币!而且,作为首席科学家,不少动辄几十万元的项目经费,批准的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上。如果他真要贪一把的话,可以说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但蒋新松确实很廉洁,绝对不是一个贪官。与他共事多年的机器人专家周国斌说:“老蒋不贪钱,不贪财,也不贪吃,也从不用职权谋私利。在社会交往中,他主张‘君子之交淡如水’,最反对的就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老蒋几乎没有因私事请别人吃过一顿饭,也没因私事吃过别人请的一顿饭。在我的记忆中,他只在科学院的饭堂里用饭票请我们吃过一顿饭。”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个别对蒋新松有些意见的人,也是承认的。
而我对此也颇有同感。蒋新松生前,我曾去过他在清华大学的“家”,“家”中非常俭朴。蒋新松去世后,我又多次去过他在沈阳的家,这个家依然朴实简单,连客厅里的沙发,也极为普通,看不出有一点奢侈的样子。而且我第一次去他家便发现了一个细节:地板上的每一道裂缝处,都粘贴了一块一块的胶布。蒋新松的妻子告诉我,“这是老蒋生前的‘杰作’,他每次发现地板坏了,就用剪刀剪下一块一快的胶布,然后很细心地贴在地板上。若是下次坏了,他再贴。家里的玻璃坏了,请人来换,六毛钱他都要照付6走廊里的灯泡坏了,每次都是他掏钱去买来安上。他常给我讲,公生明,廉生威,当领导的只有无私才能无畏。”
我在采访中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人,蒋新松在人格、品质、工作方式和性格上有什么缺点和不足?
我得到的反映是:蒋新松这人思想品质很好,很有人格魅力,很有工作魄力,不玩阴谋诡计,也从来不整人。但缺点是性子急,脾气大;不注意说话方式和工作方式;有傲气,瞧不起人;晚年不太听得进去意见;等。
谈论蒋新松缺点的人,都是蒋新松生前的好友,或者与他共事了多年、几十年的同事。他们态度诚恳,心底纯正,不带个人成见,而完全是出于对一种问题的探讨。现择录几段如下,以供参考:
说法之二:蒋新松性子急,脾气大,说话太直,批评人也从不讲方式方法,有时话一出口,让人无法接受,伤了所里的一批老同志。连朱丽兰主任都对蒋新松说过:“老蒋,你说话得注意点包装!”有的老同志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找他谈,谈着谈着他就急了,一急他就吼,甚至有时还拍桌子。他在工作上要求太高,总是用他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他的水平和标准。比如,他每次出差前,就给几位副所长布置工作,就像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一样。他一回来,就开始检查“作业”,一旦发现某项“作业”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训人,一点不给人面子。但每一次吵架或者训人,都是为了工作,等吵过训过之后,他什么事都没有了,第二天又给人道歉,从来不往心里去(关于这一点,也有人说,蒋新松脾气大是大,但他从来不对下面的技术人员或者他的学生发火;还有人说,因为他有甲亢这种病,所以容易发脾气)。
说法之二:蒋新松最能识别人,也最会用人,但他不会关心人,或者说他不关心人。他脑子里整天就想着要为国家干大事,一些老同志的命运不太好,他也不太过问。不少老同志跟他干,干到最后,生活方面有些困难,他也不太关心。他自己于活从来只讲奉献不讲索取,所以他要求别人干活也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在他看来,只要是为了工作,为了国家的事情,你即使累死了,也是应该的。
说法之三:蒋新松这人太傲气,一般的人他瞧不起。他在研究所上班下班,途中遇上谁,从不打招呼,就像不认识似的。有时你主动给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像没看见你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次机器人专家周国斌给蒋新松提意见说:“老蒋,你得注意一点,你太傲气了!”他说:“我承认我骄傲,目中无人,但我从小就骄傲,想改也改不了啊!”不过也有人替他辩解说,蒋新松当了20年的“右派”,20年没人理睬他,他也不理睬任何人,几十年如此,习惯了。另外,他从来就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加上眼睛不好,走路时常常考虑问题,所以给人造成了一些误会。我的观点是,蒋新松的骨子里确实有一股傲气,但这股傲气并非完全不好一不该有的傲气另当别论。清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大凡有本事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傲气的,而没有本事的人,是从无傲气可言的。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总是一副奴气,而外国人在中国人面前却尽是一副傲气!为什么?别人兜里有钱,屁股下有车,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能不傲气吗?你若没资本没本事,傲一下试试看?肯定没人说你傲气,而只能说你“傻气”或者“酸气”。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傲气比奴气好;人,应该有一种傲气。如果有一天12亿中国人都有了傲气,那该是一件多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啊!)
说法之四:蒋新松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对中国的自动化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出名后被围住了,后来就不太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了,离群众也越来越远了。蒋新松是人不是神,他也是个矛盾体,身上同样有封建文化色彩的东西。他开始很民主,后来就不怎么民主了,所以我们曾经给他开玩笑说:“老蒋,希望你不要做晚年的毛泽东!”
任何伟人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格的局限、知识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蒋新松‘自然’更不例外。由于探讨蒋新松的另一面并非本文的主旨,谨此打住,仅供读者参考、思索、批评。
1998年5月—11月写于北京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