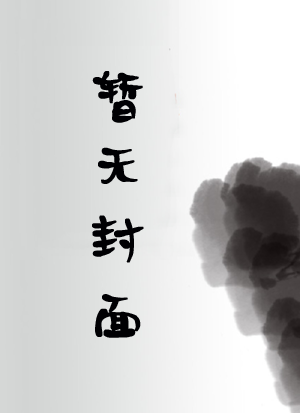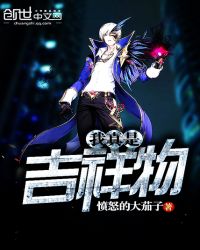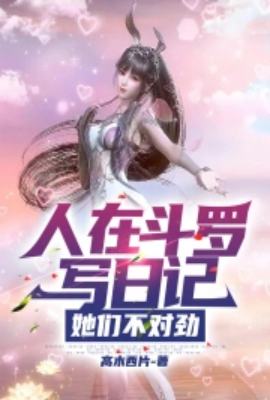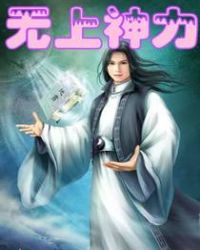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最后的年月》被停售前后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李致文存:我与出版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 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最后的年月》被停售前后
我有一个保存资料的习惯,但日积月累,资料一多,有些资料很难找到。年过八旬,丢三落四,更是如此。这一次,在子女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两份有关《最后的年月》一书的信件和文件。
就从此说起:
三十年前(即1980年),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因出版部队作家丁隆炎的《最后的年月》,发生一桩公案,直至惊动了中宣部和时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
1975年,丁隆炎在资阳县人武(人民武装)部认识了彭德怀元帅的警卫员景希珍。彭德怀是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在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59年,彭德怀为“大跃进”造成的灾害,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丁隆炎在得到景希珍的信任后,听景希珍讲述了许多有关彭德怀的故事。彭德怀的品质和遭遇,深深地打动了丁隆炎。丁隆炎冒着政治风险记下了景希珍的讲述。粉碎“四人帮”后,丁隆炎在他战友杨字心(时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等人的支持下,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全省只有这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记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一些感人事迹的《在彭总身边》。
《在彭总身边》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好评,有不少报刊转载和电台播放。我寄了一本书给胡耀邦同志。在其后一次中宣部的例会上,耀邦同志说:“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听到这个话,作者和出版社都深受鼓舞。
丁隆炎也因此调到中央军委的彭德怀传记写作组。在这段时间,他接触到更多有关彭德怀的材料,包括彭总侄女梅魁的很多叙述。他为彭德怀生前最后几年的遭遇感到心痛,也为彭德怀崇高的品质所感动,他满怀激情写出了《最后的年月》一书,他认为记录这些事实是他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本书很好,我和社长崔之富,先后在审稿时流了不少泪水。当时,中央正在全面否定“文革”,我们认为尽快出版这本书对全面否定“文革”会有很好的作用,决定打破先征订后印刷的惯例,首印四十万册。出版部也大开绿灯,其他图书统统让路。
由于人们敬重彭德怀,也因为有《在彭总身边》一书的影响,《最后的年月》发行前一天,成都市新华书店人民南路分店贴出通告,第二天一早书店开门前,买书的读者就排起了长队。出版社也寄出不少样书给北京、上海的有关单位和朋友。
天有不测风雨。出人意料,第三天省委宣传部传达中宣部指示:《最后的年月》一书停止发行。请示原因,说是彭总夫人有意见,与事实有出入;丁隆炎违反写作组纪律,泄密,等等。其内容详见彭总传记写作组5月15日的信件:
王任重同志并耿秘书长,韦、杨副秘书长:
你转给浦安修同志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报告,我们看过之后,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大不一样。当然这也难怪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因为在《最后的年月》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一直没有人找我们核对过材料。他们仅仅根据丁隆炎同志一个人的说法,也只能得出他们那样的判断。对于这一点,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有些问题,也还需要说明。
一、这本书直接违背当前中央宣传的精神。报告中提到“不少读过这本书的老同志极受感动”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总观全书,就会发现它与1980年2月29日的中央各部发电第二号文件,《关于五中全会后的宣传问题》中规定的“不要发单纯控诉性的文章”直接相违背。例如,写彭总在一次被批斗的情形时,“人们见他满面青红交错的伤痕,衣袴几处都被撕破了,脚上的鞋一棉一单,另两只鞋显然是在某处批斗时被拖掉了,他大病在身,重伤未愈,每走一步都使他十分吃力。正当他抱着一根柱头喘息不止时,一个穿绿衣的‘首长’从远处冲刺而来,大喝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他甩开大臂,向彭总那伤痕累累的脸打去,对方立刻摔倒在地。……然后用一只脚踏住彭总的胸口:‘你,还认识我吗?’”有的人曾来信说,他们看了这本书很激动,大家议论:“彭总这样悲惨的结果,难道都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吗?林彪、‘四人帮’没有人支持敢这样做吗……”又如,书中44页,引彭总的话说:“我敢立下一个军令状,只要三年,搞不好我自己再把右倾帽子戴起来。”接着,他更大声说:“这话,我到哪里都敢说!你说你那一套好,我觉得我的想法也不错,有什么呢?大家都试试嘛!给我一个公社,让我作三年主,先给我这点权力,先把我的右倾帽子放在一边。三年一到,我不行,把我的这点权力收了,把我的帽子戴上,那该叫人多么心服呵!”这种写法,我们认为是很不妥当的,有损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二、这本书中的许多事实有重要出入。例如,报告中说,彭总在进三〇一医院的报告是经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签署同意的,还说什么“有根有据”。可是,最近经我们再三查对彭总住进三〇一医院的档案,没有周、叶的签名,也没有“此报告经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签署同意”这样一句话,更没有张才千同志送呈周总理和叶帅的彭总住三〇一医院的报告书。丁在北京时,也没有人批准他去查阅过“彭总专案组”的档案。
报告中,把彭总的档案硬要说成是“遗嘱”,把篡改硬要说成是删节,这就不实事求是。彭总这样的人物,这样重要的谈话,丁隆炎同志有什么权利擅自抢先公布,又有什么权利篡改已存入档案里彭总的重要谈话记录?
书中写的浦安修同志在太行那些事情,报告中说:“这个材料来源于太原市退休老干部刘志兰同志。”据刘志兰同志最近来信说,她并没有谈过那些话。书中写的既然是浦安修同志的事,为什么不找浦本人核对?
除了上述一些问题外,还有不少失实或作者自编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中央宣传部决定停售《最后的年月》这本书,是正确的。
三、报告中说:“浦安修同志对《在彭总身边》一书,也曾如对《最后的年月》一样,要求停售和销毁”。这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1979年2月,在成都有丁隆炎、吴定贤 注释标题 吴定贤:应为吴正贤。 、杨字心三同志,送给浦安修同志一份回忆彭总的材料,浦看后,热情地和他们谈过三次,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3月份,在北京又和老丁谈过数次,对材料提出三、四十条修改意见,还专门派丁回成都修改小样。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根本没有说过“停售和销毁”。丁隆炎同志,如果对于宣传彭总事迹具有严肃态度的话,是决不会把这些好心的帮助反而当作是“阻挠”的。
为了更好地宣传彭总的革命事迹,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的宣传政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于5月3日曾向王任重部长当面表示过,愿意向四川人民出版社提供情况。现在我们再次诚恳表示,希望能同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的同志约到一起面谈。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
1980年5月23日
当时,我们并没看见这封信,但既然间接地知道这些观点,于是核对有关情況,梳理了我们的意见,在出版社党委的支持下,我和吴正贤(文艺编辑室主任)、杨字心到四川省军区找军区首长反映,除了说明情况,还表示《最后的年月》一书是出版社约丁隆炎写的,稿件经过出版社的三审,即使有问题,责任在出版社领导(在我这个总编辑)。幸好军区首长对丁隆炎也持保护态度。
在5月份之前,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一次出版工作座谈会议。我去了北京。我到中宣部出版局反映《最后的年月》一书的情況,表明不同意停售《最后的年月》。时任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副局长牛玉华都不赞成停售《最后的年月》。边春光为证实他的观点,拿出他的记事本给我看,表明他一贯反对停售。当时,有些中央部门,特别是中央党校不少学员看过《最后的年月》,对停售该书很不满。正在党校学习的、主管出版社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陈杰(1937年入党),一贯是非分明、心直口快,坚决支持出版社向中宣部申诉,力争解除禁令。
在开会期间,我向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写了信,请戴云转呈。戴云原为胡耀邦同志的秘书、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任中宣部办公厅副主任。我们在团中央共过事,又一起被关过“牛棚”。第二天,戴云高兴地告诉我,说任重同志表示该书可以解禁,令我十分高兴。我写了一封感谢任重同志的信,请戴云转呈。可是,第二天戴云告诉我,说任重同志的态度完全变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该书不能解禁。戴云还说看见一份文件,上有主管意识形态最高官员的批示,说应该开除丁隆炎的党籍!这个批示使我十分惊讶:开除党员党籍,必须经该党员所在支部大会讨论,本人在场并可申诉,作出决定后报上级党委审批。这位大首长居然忘记了党章的规定。
怎么办?
会议开完之后,我到耀邦同志家向他申诉。我据理力争地说,您鼓励我们出好书。现在我们出了好书却不许发售。不许发售又没有正当理由。耀邦同志听了以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两手左右摆动。他见我不懂其意,说了一句:你们自己发嘛!
耀邦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主持正义的党的领导人!
我用长途电话把在北京的过程向出版社党委报告。当我乘飞机回到成都双流机场时,社长崔之富、党委副书记聂运华到机场迎接我,以示出版社党委的团结和决心。
尽管耀邦表了态,因有中宣部的禁令,出版社仍不敢擅自发行。经出版社党委讨论,针对我们所知道对方的观点写信上诉。
以下是上诉信全文:
川社党[1980]第9号
耀邦、任重同志并中央书记处:
我社于4月26日上午,接到四川省委宣传部转中宣部4月25夜“立即停售”《最后的年月》一书的电话通知后,立即坚决执行了这个通知,并向省委宣传部作了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当天,新华书店就停止了该书的发行。但是对停售这本书,我们是不同意的。现将有关意见陈述于后:
一、《最后的年月》一书,系我社继出版《在彭总身边》一书之后,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约请该书整理者丁隆炎同志写的。它记录了彭德怀同志在世的最后八年(1966年12月至1974年11日)的一些生活片断,感人至深地表现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纯朴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在短暂的发行期中,我们便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反映。说明该书的社会效果是很好的。有的单位的党组织把此书作为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补充读物。不少读过这本书的老同志极受感动,有的认为读一遍“就好像上了一堂党课”。中央党校有一位老同志接到此书后,许多人闻讯赶来,排队借阅,一天就传阅了六位同志。有的青年同志反映,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从小立下的入党志愿产生动摇,现在从彭老总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品质,深深感到我们革命的老一辈好得很,我们的党好得很,做一个共产党员光荣得很,决心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一些团员和青年反映:过去思想上分不清林彪、“四人帮”和我们党的界限,分不清他们那套极左货色和毛泽东思想的界限,分不清党内不正之风和光荣传统的界限,读了《最后的年月》,这些糊涂思想都被彭总的一言一行澄清了,迄今为止,我们接触到的读者,都认为《最后的年月》,是继《在彭总身边》的又一本很好的书。
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完全明白停售《最后的年月》一书的原因,仅了解到主要是彭总夫人浦安修和彭总大事记写作组的某几位同志,对该书提出了一些意见。一是说,内容中有损害浦安修同志的地方。事实上,作者对浦安修同志一直是抱着尊重的态度的。例如,本书第31页写浦安修同志说过“我不理解他(指彭总),我们合不来。但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一点反党的言行”。这就反映了浦安修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界限是清楚的。很多看过此书的同志,也认为这是对浦安修同志的赞扬。
二是说,本书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或是“造谣”。我们同作者在一起查对了他的材料来源,就目前所提出的问题来看,事实并无重大出入。如说:彭总逝世前并无遗嘱,而书中却错误地列出一个叫作《遗嘱》的篇目。据了解,彭总生前的确没有正式立过遗嘱,文内也只说发现过一份《彭德怀临终前的谈话记录稿》(第48页)。一般来说,将死者逝世前说过的一些重要的话称作“遗嘱”是完全可以的。斯大林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这个发言是斯大林同志给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留下的遗嘱。至于说“篡改”了彭总临终前的谈话,我们不知道具体指什么,据作者查对,他仅删去彭总谈话稿的几个地方,主要是彭总当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否定刘少奇同志的一两句话。我们认为这种删节是符合当前中央的精神的。又如,还指责说批准彭总进三〇一医院是张才千同志,而书上说成是周总理和叶帅,这样歪曲事实,必将引起严重后果!其实,书中第38页提到的“一位部队领导送呈一份报告书”的“部队领导”就是指张才千同志。作者从“彭德怀专案组”的记录上曾查到:“此报告经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签署同意。”不但有根有据,而且歌颂了周总理和叶帅,有什么不好?作者如果不这样写,那倒真的成了对事实的歪曲。再如,还指责说作者把彭总给他侄儿、侄女的谈话,都写了给梅魁(彭总最大的侄女)一个人的谈话。这只要翻一翻该书第46~47页就清楚了,上面明明写着:“在这以前和以后,梅魁的弟妹们也多次来过医院探亲,伯伯对他们说过许多话。”紧接着便引了六段彭总对他的侄儿、侄女们的谈话。再如,书中写浦安修同志在太行山时,有一次要求彭总派人送她的事(第30页),说是无中生有。这个材料来源于太原市退休老干部刘志兰同志,她是左权同志的夫人。据称,当年左权同志夫妇与彭总夫妇住地相邻,亲如一家,很多生活片断她至今记忆犹新。再如说,浦安修同志在北师大斗批彭总的大会上并未说过话,而认为作者写她在大会上讲过“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指彭总)有过一点反党的言行”等话是蓄意捏造。据了解,浦安修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确实没有讲过话,但这样意思的话,她也确实向一些人(包括作者在内)讲过多次。在文学性的回忆录里,只要不违背本质的真实,在时间甚至情节上作些调整,是完全许可的。可以看出,以上指责,都欠妥当。退一步说,即使本书在某些细节上真有失实之处,我们欢迎提出,而且再版时应该修改。但绝不能因此否定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更不能成为停售的原因。
三、关于指责作者思想品质不好,沽名钓誉,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事关人的政治生命,我们特到作者所在单位(四川省军区政治部)作了了解。去年丁隆炎同志被军委办公厅借调去彭总大事记写作组帮助工作,半年期满返回原部时,写作组曾书面规定丁隆炎同志不准用他在写作组接触的材料写作除《彭总青少年时代》以外的文章。可是,军委办公厅未予以认可。而《最后的年月》的写作,则是作者在我社编辑部多次动员后才接受了写作任务的,同时也向四川省军区政治部领导作了报告,省军区有关领导表示完全支持。我们认为,这不存在违背组织纪律的问题;即便在这方面有何缺点、错误,主要责任也在出版社,我们愿意承担责任并作自我批评。至于指责作者沽名钓誉,我们觉得很不公道。丁隆炎同志早在党中央为彭总平反的一年之前,便冒着风险记录了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同志关于彭总的回忆,并开始同我社编辑部接触,初步提出了整理这部回忆录的设想,这足见他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都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沽什么名?钓什么誉?《在彭总身边》出版后,四川省军区非常重视,政治部给丁隆炎同志记了二等功,提前晋级。省军区这种是非分明、赏罚分明的态度,我们感到是完全正确的。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的年月》一书出版后,初步反映的社会效果是好的。如果没有重大的政治错误,轻易地将其停售,就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疑问和顾虑。就我们所知,浦安修同志对《在彭总身边》一书,也曾如对《最后的年月》一样,要求停售和销毁;在耀邦同志肯定以后,浦安修同志才改变了态度。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在彭总身边》一书,社会反映很好,而浦安修同志的阻挠是不正确的。这一次,浦安修同志仍如以往,一会儿提出《最后的年月》一书损害了她的形象;一会儿又强调事实有所不符;一会儿又指责作者思想品质不好。诸如此类,既要停书,又要批人。对于出版记述彭老总的这两本书,浦安修同志一次再次地进行阻挠,毫无支持同情的表示,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吗?这种做法,难道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相吻合吗?这难道与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历次讲话的精神相符合吗?因此,我们建议恢复《最后的年月》一书和它的作者丁隆炎同志的名誉;尽快批准该书继续发行,同时在普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再版,使这本书更好地发挥它鼓舞群众,教育青年的重要作用。
以上意见,我们曾委托我社总编辑李致同志趁最近去北京参加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机会,向中宣部和耀邦、任重同志反映。他所写的书面报告,我们党委看后也是完全同意的。
急切地等候你们的关注并指正。
此致
敬礼
中共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
1980年5月15日
此信发出后,没得任何回音。一年后,省委宣传部传达中宣部通知,《最后的年月》一书可以内部发行。当时,内部发行的书不能公开摆在书店出售,能买内部发行的书还得有规定的级别,能卖出多少?这样一本好书大部分化浆,并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实在可借,令人心痛!当时出版社与上海《收获》杂志相约,《最后的年月》一旦出书,《收获》即全文发表。该书被停售后,《收获》也不能刊登了。巴金老人时任《收获》主编,一直关心该书的命运。
到明年就事隔三十年,我找到这两封信,现把它公开出来。它说明什么,读者自可判明。
作为尾声:
作家丁隆炎没受到任何处分,以后还晋了级。
事过不久,耀邦同志有批示,要有关领导同志的夫人不干预传记写作组的工作。
2009年立冬
附记
此文先后在《四川文艺》《当代史资料》和《读者报》上发表。《四川文学》2013年第四期,以“特别推荐”栏目刊出,该刊名誉主编马识途眉批:“读完此稿,感慨不已。往事历历在目,至今犹觉悚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