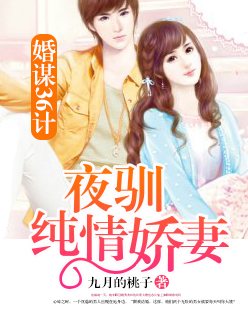出版家李致印象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李致文存:我与出版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 出版家李致印象
◎ 秦川 注释标题 秦川: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曾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
我与李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共事八年,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和善可亲、思想解放的领导。
1973年,李致由团中央调来四川人民出版社任革委会副主任,1982年底调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和他的同事们几年间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出版社提升到全国出版界前列,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报道,表扬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出版社工作中,我深感李致是一位视野开阔,眼光敏锐,敢为天下先的领导。他对下属,识才重才,和善可亲;用人不疑,大胆放手。在他手下工作,让你有一种知遇之感,只有全力以赴,否则无以为报。
抓重点,“扔石头”,这是李致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任总编辑时,亲聆胡耀邦同志关于做好出版工作的教导时体会出的精髓。回忆录首篇《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中回忆道,耀邦同志说,每期报纸刊物都要有一两篇重头文章。这些文章应该是青年最关心的问题,写得又好,群众才有兴趣。不要脱离实际,不要不抓重点,不要怕花大力气。一个季度,总要丢几个“石头”引起波澜。半年或一年,一定要丢几个大“石头”,引起轩然大波,才会有影响。四平八稳,平均使用力气,隔靴搔痒,谁会注意你这张报纸、这个刊物、这家出版社?李致将此奉为出版工作信条,短短数年间使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全国崛起,谱写了四川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
《周总理诗十七首》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国情民意,扔出的第一个大“石头”。这本书虽是一本小书,却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出版界一个大波澜,成为四川出版界改革开放的先声,地方出版社勇闯禁区第一炮。当时出版这本书是冒有风险的——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因人民群众清明节悼念总理引发的“天安门事件”,压在人们心上的阴云还未完全散去,心有余悸。按常规出书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央有规定,地方出版社只能出版地方性图书。出版中央领导人的著作想都不敢想。敢不敢打破这一禁区,这是对出版社领导素质和魄力的考验。除首先思想要解放,敢于打破禁区,敢为天下先,具体操作也是对出版家领导艺术的考量。
经过一番筹划、运作,《周总理诗十七首》在1977年国庆节通过邓颖超同志同意正式出版,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出版社连出两版,印刷三次,发行近百万册。许多人,包括领导、思想文化界名人、作家、评论家,纷纷向出版社要书。有的地方(省)还自行翻印了《周总理诗稿》等,实际发行数难以统计。著名诗词曲大家、书法家赵朴初先生发表书评《真能参透生死关——读周总理遗诗志感》,对总理诗给予极高评价,说:“周总理的遗诗,虽然只寥寥十七首,却为我们透露了总理青年时期内心世界的一些片断,从而使我们在总理的崇高形象上见到了过去不曾见到的另一个光辉方面。”“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们——认识总理,学习总理的典范人格,有很深的启发意义和教育意义。”总理诗有很高的艺术性,“五四”前的旧诗“风骨开张,才气横溢”,“五四”后的白话诗“卓有成就,不同凡响。”文末赋《调寄临江仙》词一首,赞曰:“不负澄清天下志,生平事迹般般,真能参透生死关,生为民尽瘁,死有重于山。持荐轩辕多少血,词华和梦都捐。岂期身后见遗篇?吉光片羽,芳泽满人间。”
1979年出版社又推出了《在彭总身边》一书,以彭总警卫参谋亲闻亲见,口述了彭总在庐山会议前后的感人事迹,在全国反响强烈。一天,李致对我说,写一篇书评给《四川日报》。我写了《铁骨雄风——读〈在彭总身边〉》发表在同年11月2日《四川日报》三版。文章特别赞扬了彭总敢于面对现实,“为人民鼓与呼”及“庐山上书”所表现出的“刚风劲骨”。当时正值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历史重大冤案之际,引起高层注意。李致得知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在中宣部一次讲话中对这本书的评价:“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也许与此相关,许多报纸转载,许多电台广播,好评如潮。
其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执笔的《最后的年月》。这本书忠实地记录了林彪、江青之流对彭总的残酷迫害,和彭总身处逆境时表现出的高贵品格,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铁证。李致回忆说,编辑流着泪审稿,工人流着泪排字,九天印四十万册。刚一发行,即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引起轰动。可是,却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作者,要开除作者党籍,以致暂停发行。对此,李致敢于承担责任,保护了作者,同时直接找耀邦同志申诉说:“您叫我们出好书,现在好书出来了,又不许发行,而不准发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脚。”耀邦同志开始有些犹豫,感到难办,最终表态:“你们可以——自己发嘛!”经过一年多申诉,主管部门最终准予内部发行。
“文革”十年,文化荒芜;人们渴望精神食粮,嗷嗷待哺。为解决书荒,为老作家恢复名誉,四川人民出版社在李致领导下,编辑出版“近作系列”和“选集系列”两套丛书。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1978年8月,“近作”丛书率先推出巴金的近作,收文十一篇,附录选译俄国作家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沉思》。1980年9月,又出版《巴金近作》第二集,收文六十篇,发行六万二千册。为巴金正名恢复名誉起到很好作用。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8月,出版社推出郭老有关四川的诗集《蜀道奇》,并影印了《蜀道奇》手迹。9月,又推出郭老近作《东风第一枝》,于立群作序,收诗二十五题二十九首,对联一副,文十篇,照片、手迹、题画等9幅。两书发行7万册,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郭老诚挚的怀念。
“近作”丛书内容丰富,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儿童文学等,又有如王朝闻《开心钥匙》美学欣赏评论集和艾青《归来的歌》诗集。正如唐弢在《唐弢近作·后记》中所言,近作是一种新创造的图书出版新样式,满足了特殊年代读者特殊的需求。近作还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丁玲在《丁玲近作·后记》中说:“这些文章,自然很能说明我的心情,也可以告慰于许多好心读者对我的关切和鼓励,同时可以减轻一点一年多来我没有给一些读者及时复信或竟然没有复信而引起的内疚。”再如《萧军近作》是他1979年的诗文选集,“可算做几十年得以公开发表文字以来,所获得的一点成绩。”(萧军语)萧军是上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一生坎坷,恢复名誉后勤奋写作,一年来写了四五十万字的作品,如《忆长春》《哈尔滨之歌三部曲》《我的文学生涯简述》等,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时代的一角。他在前言中有《忆成都》七律一首,以志与成都的一段鸿雪因缘:“当年漂泊忆蓉城,水碧山青尽有情。诸葛祠前千岁柏,薛涛井畔望江亭。”
《叶君健近作》《严文井近作》别开生面,是当时难得一见的翻译家和儿童文学作家近作,大受读者欢迎。《叶君健近作》收有三篇专给中国少年儿童改译的以欧洲民间文学为题材的童话故事,1979年6月出版,第一版印刷发行达30万册,创造了“近作”丛书的奇迹,填补了儿童文学严重短缺的空白。严文井在庐山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上,要求大家像战士一样在少年儿童读物这座宝山上为两亿儿童找宝,满足孩子们迫切的需求。
数年间,出版近作20余种,如《王西彦近作》《艾芜近作》《茅盾近作》《周立波黎明文稿》《罗荪近作》《夏衍近作》《康濯近作》《碧野近作》《吴强近作》等,都发挥了丛书短、平、快的较好作用。
同样,选集系列也获得可喜成绩,满足了广大读者特别是文学爱好者、教师、研究工作者的需要。1979年8~12月,出版社接连推出一套三卷五册的《郭沫若选集》,120多万字,以应当时需要,第一次印刷发行都在二万册以上。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出“立足四川,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接连出版了过世川籍作家何其芳、李劼人、周文、陈翔鹤、邵子南、林如稷、罗淑等的选集。接着又推出名作家选集,凡健在的全国著名作家多由作家自选或经作者同意专人编选,如《巴金选集》(十卷)、《沈从文选集》《冰心选集》《茅盾选集》《老舍选集》《陈白尘选集》《阳翰笙选集》《沙汀选集》《艾芜文集》等。而《鲁迅选集》是李致请曾彦修、戴文葆编选的。
李致和出版社编辑,诚心诚意与作家交朋友,为作家服务,受到他们夸奖。曾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刘杲说:“其作用绝不亚于组织部的红头文件。”有助老作家们迅速恢复了名誉。
“立足四川,面向全国”的方针,也得到了陈翰伯及边春光和许力以等的支持。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川版书有过一段辉煌时期,在全国颇有影响。1986年,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出版总社社长的李致,带队参加全国书展期间,在北京还举办了川版书展。老一辈革命家杨尚昆和张爱萍将军参观了书展和座谈会,充分肯定四川提出的“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的指导思想。“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原是诗人冯至赞美四川出版社的话,意在多出书,出好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社会效益放到第一位,最大限度地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那时候改革开放下的经济大潮开始席卷全国。有同行非议,认为四川保守,不敢言商。杨尚昆同志指出:书籍不同于一般商品,既有商品属性,在市场流通,又有意识形态属性,能影响人的思想,不能因单纯追求利润出不好的书和坏书。事实证明,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是对的。四川出版社的经济效益超过许多出版社,修了职工宿舍,建了十二层办公大楼,这在当时全国出版界少见。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执行统一核算,该赔就赔,该赚就赚,薄利多销。如前所述,“近作”丛书定价低廉,发行量大,受到读者热捧,一般都在一两万册以上。连成本高的大部头的选集,因出版及时,满足读者需要,发行也在两万册以上。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文化出版基本建设任务极重。1977年以来,民间也先后有业余编纂的《鲁迅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家辞典》。在李致领导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开拓进取,决定接手这两部辞书的组织和编纂出版工作,命我担任责编,并参加《鲁迅大辞典》编纂组。新中国成立以来,业余编纂大辞典尚属首次,在当时也是思想解放、突破禁区的一大举措。
《鲁迅大辞典》由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单位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与业余编纂,十分艰苦。出版社仅补助两千元印制专用稿笺,购置卡片、卡片盒。但编纂组一班人以找回被“文革”十年耽误的时间的精神相激励,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完成了阅读、搜词等基础工作,制作了十数万张卡片,完成了词目普查,并编辑出版了《鲁迅佚文集》,初显业余编纂的优势与灵活。
虽然《鲁迅大辞典》是业余编纂,拟由地方出版社出版,但一开始就受到全国关注。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等始终关心、指导辞典的编纂;中国社科院十分重视,在1979年初由陈荒煤主持的昆明全国文学规划会上,该书被列为全国重点项目之一。其后,在全国二次人大会议期间,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向大会提交了编纂《鲁迅大辞典》提案。由于1983年李致和我先后调离出版社等客观原因,后来辞典交由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纂,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中国文学家辞典》由北京语言学院业余编纂,分古代四个分册,现代四个分册,后扩展为现代六个分册,共收文学家三千七百七十五人,其中有大量文学新人和海外华文文学家。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学家辞书。长期受思想束缚,只有盖棺论定后的死人才能入典——“活人不入典”是首先要打破的思想和出版禁区,“活人入典”,是这部辞典的最大特色。其次内容翔实,材料多来自作家本人撰写或亲属提供。其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实事求是,不“以言废人,以人废言”。如现代一分册初编时,丁玲、艾青等著名作家尚未落实政策,仍然收录;陈独秀、胡适等历史人物,不因政治、见解不同,任意贬抑。其四,校正错误,补充新材料。如胡适原名胡洪骍,闻一多入清华读书是1912年,而非过去文学史、年谱上讲的1913年等。
《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辞典一开始就得到全国和地方文联、作协等单位或组织的支持帮助。郭沫若在病中表示关切,希望早日出版;茅盾题写辞书书名。巴金等先后写信鼓励、指导。巴金在信中说:我支持你们。我早就主张有人来从事这一工作,可是没有人去做这于今人、后人有益的工作。人们害怕活人,出版社更怕;你们的思想也要更解放一些。趁老作家们在世的时候,“抢到”第一手材料,这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义和宝贵的事。
1979年12月《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出版,第一次发行十八万五千册。接着第二、三、四分册出版,发行均在四万册以上。
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出版中外古今著名作家作品,繁荣了我国出版事业,受到读者欢迎,但也惹来一些出版社的不满。因为这些书过去都是由他们垄断出版,是“看家书”——利润的稳定来源。地方出版社的做法,无异于抢了他们的饭碗,动了人家的奶酪,岂有不反对的。果然一次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有人对地方出版社提出批评:乱出书!此言一出,引来地方出版社不满。李致在会上发言,大意是说,那比如四部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大家都可以出版。开会回来后,李致与我商量出版四部古典名著的事。我们认为直接翻印虽然省事,但毕竟是人家的版权,也有损四川出版社的名誉。不如另起炉灶,重新校注,搞四川版新校注本。四川人民出版社为此发了文件,由我负责组织、出版。
新校注本《红楼梦》早已由李希凡、冯其庸组织进行,为避免重复,四川只出另外三部。方案确定后,重要的在组织力量,谁来校注,谁来审订,很费了些思考。思想解放给了我们大胆尝试的勇气,确定请北大中文系56级我的同窗担任新校注,北大老师担任审订。《西游记》的校注最难,由安徽师大朱彤和安徽大学周中明担任,北大教授吴小如担任审订。《三国演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吴小林担任校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陈迩冬担任审订。《水浒传》由苏州大学李泉担任校注,北大教授王利器担任审订。他们都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堪称一流。新校注本注释条目均在两千条左右,而过去已出的书一般只有四五百条。新校注三部中国古典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后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新校注本时,还参考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版的校注。
三十年过去了,四川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早已翻过去,留下了更多的怀念。翻检记忆到此,出版家李致的印象在我心中更多鲜活,可亲,可敬。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