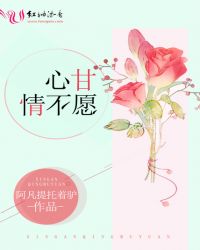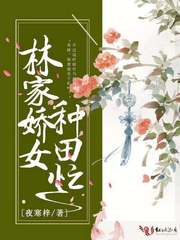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李致文存:我与出版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 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 注释标题 本文原载《中国出版》2016年第3期。
编者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走出的中国出版人顺应时势,锐意改革,开创了中国出版业的新辉煌。那是一个在中国出版史上值得铭记的时代。当时,四川出版人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率先突破“三化”方针的束缚,出版了一大批好书,为出版改革做出了贡献。本期,汪家明编委约请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张京,采访四川出版业的两位老出版人——李致和李正模,请他们回忆四川出版业当时的情况。此书仅收录对李致的采访。
整理者记录和整理口述人亲历、亲见或亲闻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更加鲜活的研究素材。但是,口述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口述人的观点、记忆准确性等,都可能对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在使用口述资料时需特别引起注意的。我们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进行口述出版史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更多有思想、有内容的口述史文章。
一、突破“三化”方针的束缚
四川出版在全国产生影响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和湖南、吉林等省的出版社一起,突破传统的束缚地方出版的“三化”方针,“三化”就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
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时,省新闻出版局收到中国版协邀请我出席纪念座谈会的信。座谈会强调,地方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针,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界最大的举措之一。
宋木文(曾任国家出版局办公室主任,后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在给湖南胡真(曾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所作《我的出版观》一书的序上,说湖南率先提出突破“三化”方针。我在你(指张京,时任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支持之下编的《我与出版》那本小册子(1988年编印)里,说是四川率先提出突破“三化”方针的。
宋木文后来在成都主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本)的首发式,邀我参加,我与他说到此事。他通过魏善和(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干部,后任副局长)找到邓星盈(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后任社长),看到陈翰伯(原国家出版局代局长)1980年2月15日给邓星盈的信。信上明白写着:“在长沙开会时我曾约四川代表详谈一次。我对你社出书面向全国这点,极为赞赏。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我们把这个方针推及到全国地方出版社去了。”宋木文曾写信给我,表示要改正他原来的说法;不过后来又说,说川、湘率先都无不妥。许力以(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后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非常支持我们“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他当时在抓《汉语大字典》。
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左)与李致在1986年全国书展
1979年“长沙会议”召开前,我和崔之富(时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商量,这次会上要低调,因为当时出版界对地方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针有很大分歧。
“长沙会议”上,代表们就要不要突破“三化”方针争论较大。会议最后一天,我跟袁明阮(时任四川省出版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商量,还是要发个言,用我们这两年多的实践来说明问题。当天上午,我报名最后一个发言,随即在会场上写发言提纲。我发言后,很多地方同行来跟我握手。许力以对我说:“我支持你们出《李劼人选集》。”
“长沙会议”之前,胡真同志带队到四川访问,看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样书展后,当着我的面,对他的同行者讲,四川出本省老作家选集,我们为什么不能出?说这说那,类似情况不少。
出版界有些人,老把四川出版与湖南出版相比,好像我们两家有矛盾,总在争什么。其实,我们两家相互学习,互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胡真是1935年入党的老同志,我和他关系很好,我至今保存他给我的多封信件。他有两个“台柱”,都曾想调到四川来。一位是通过刘令蒙(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提出来的,后来北京一家出版社借调他去帮助工作,此事就没再提了;另一位托萧乾跟我说,想到四川来。当时我有顾虑,这两位同志都是学者和骨干编辑,我当然欢迎,但是怕人说是挖湖南的墙脚。1986年全国首次书展,我在北京见到胡真说起此事,胡真说这是他支持的。其中一位骨干要来四川,是感到湖南的编辑力量虽比四川强些,但湖南省的个别领导思想解放不够,不如四川。“士为知己者死”,所以想来四川。我们为他安排了职务和住房,后因我调离出版总社,他才打消了来四川的念头。
二、四川出版的“书事”
为什么当年四川出版会异军突起?首先是书荒,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中除马列著作和毛著、语录及“样板戏”外,其他都被批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简称),不允许出。虽然中间也曾出过《红楼梦》等作品和鲁迅的书,但数量也不多。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新华书店曾出现“站一天一夜,买一本《一千零一夜》”的现象。北京印出书后分到四川很少,巴金在上海都曾托我给他买“四大名著”。四川当时近亿人口,靠北京几家出版社改变不了这种状况。这是大的形势。
再就是四川出版的小形势。这就要提到江明(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时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20世纪70年代末调京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他掌握政策很好,把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面缩到最小。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有两位编辑,跟着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田禾搞诗集《进攻的炮声》,而自贡也搞了个什么“炮声”,四川就查这两个“炮声”。社里召开批判其中一位编辑的会,他很害怕,手都在发抖,但当他把问题说清楚后就解脱了。我马上派他到北京去组《周总理诗十七首》的书稿,他从此放下思想包袱,全力工作。当时,北京、上海一些出版社正忙于清理,顾不上出书,存在一个空间,我们先走了一步。
四川最早抓的重点书是《周总理诗十七首》和毛主席圈阅过的《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周总理诗十七首》出版后,印发上百万册,很受欢迎。出书后,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胡耀邦(时任中宣部部长)在茶话会上讲了话。我向他敬酒时,他对我说:“我收到你寄来的书。你们注意,不要搞宫廷文学。”我不了解他指什么,会后到耀邦家去问他,耀邦说:“有关四川的古诗词,你们自己出版好了,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阅的?”我说:“出这本书时,古典诗词还属于‘封、资、修’,不许出版,我们是打着毛主席旗号冲破这个禁区的。出书前,我曾请示过杜心源同志(时任分管宣传工作的四川省委书记,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赵紫阳),心源同志没有表态支持,但并没有反对。”
李致与作家严文井(右)
“拨乱反正”后,四川出版的“第一炮”是《周总理诗十七首》。出版后,每天来买书的人很多,出版社成了“门市部”。《诗词若干首》也受欢迎,沙汀在北京,多次给我写信要买这本书。
这之后四川出版还做了几件“大事”。粉碎“四人帮”后,因广大人民群众怀念老一辈革命家,我们及时出版了李大钊、吴玉章、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集,《罗瑞卿诗选》印了五十万册。后来又出了陈毅元帅夫人张茜的诗集,以后又出了张爱萍的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了《陈独秀早期文选》,虽然当时影响不大,但说明我们出版社思想解放。
除《周总理诗十七首》外,影响很大的是《在彭总身边》。当时胡耀邦在中宣部,我寄了一本给他。他在中宣部的一次例会上讲:“昨晚我睡在床上,一口气看完《在彭总身边》,拿着就放不下来了,这本书写得很好,很生动,很感人。”这是在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
李致与作家王蒙(右)
柯岩的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影响也大。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安法孝让我们出四川作家的书,我们出了《四川十人短篇小说选》,实际上给这十位老作家平了反。
之后,曹礼尧(原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小说组编辑)提出多搞一些近作,应该从全国范围考虑出老作家的书,包括北京的唐弢、丁玲、叶君健,湖南的康濯,上海的吴强、王西彦等二十位作家的近作。这一炮打得很响。茅盾、冯至开始认为自己的作品需要经过时间检验,不愿出近作;唐弢认为近作不分体裁不好。我说出版近作,能使读者知道这些老作家在“十年浩劫”后,不但健在,而且还有新作。在我的再三劝说下,他们就都同意把近作交给我们出版了。老作家们的近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多数作家只出了一本近作,以后自己出专集。只有夏衍出了两本近作,巴金出了五本近作,其中“近作五”《讲真话的书》,收入巴金在“十年浩劫”后的全部著作,包括《随想录》和《再思录》。
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沙汀、艾芜、高缨与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室同志合影,前排左起:陈红、段传琛(高缨夫人)、艾芜、沙汀、高缨、李致、曹礼尧;后排左起:秦川、陈川、陈天笑、文甫、李定周、蒋牧丛、曾志明、杨莆(木斧)、金平
我找巴老商量,要求他把解放前文化生活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交四川出版。当时,广东花城出版社出了这批书中个别作家的单行本。
巴金跟我说,与其你把文化生活社的书拿来一本一本出,不如你们自己出“现代作家选集”丛书。这之前,我们出版了邵子南、周文、林如稷、何其芳、陈敬容、陈翔鹤(陈翔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当时还未平反)等六位川籍老作家选集。巴老一点明,我们就在全国组稿了。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丁玲、沈从文、沙汀、艾芜等四十多位老作家选集。这套丛书影响大,多次被选入国际书展。曾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刘杲说,在恢复作家的名誉上,其作用超过组织部的红头文件。
1980年秋,全国外国文学年会在成都举行,会后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副总编辑刘令蒙、文艺编室主任吴正贤与到社参观的全国著名翻译家合影
前排:左一戈宝权 左二朱雯 左三艾芜 左四冯至 左五罗大冈 右一吴正贤 右二黄源 右三石璞
后排:左一李致 左二刘令蒙 左三赵瑞蕻 左四王佐良 左六叶水夫 右二方敬 右三倪受禧 右四草婴 右五陈冰夷
这一期间,四川人民出版社各个编室都有好书推出。
如政治理论编室(一编室)。现在看来,盐道街三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所在地)影响最大的是“走向未来”丛书。这是张黎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上世纪50年代为《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后曾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给我写信说到编这套书的。他在信中讲,改革开放后,国外思潮是什么?先进观念和科学是什么?国人应该了解。我立即同意接受,把这封信拿给一编室,编室安排安庆国(时任编辑,后任“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室主任)、倪进云(时任编辑),带着我给张黎群的信去北京找主编组稿。书陆续出版后,有领导同志就这套书给我打招呼,说内容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要注意把关。我回来后没有传达。以后是杨忠学(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分管一编室的副总编辑)、安庆国他们坚持搞下来的,共出了七十六种,发行了八百多万册。回过头来看,这套书在全国都站得住,得到大家的肯定。
再看文艺编室(二编室)。四川是诗歌大省,而出诗集是赔钱的。但我们出版社既出“四川诗丛”,又出艾青的《归来的歌》,李瑛的《李瑛诗选》,公刘的《仙人掌》和臧克家的诗,这些诗人在全国都很有名气。四川古代诗人陈子昂、杨慎的诗集,是戴安常(时为二编室诗歌组编辑)抓的,共出了四五本。戏剧类图书,出版了曹禺单本的《王昭君》和多卷本的《曹禺戏剧集》,还有陈白尘的《大风歌》。曲艺类图书,出了很多川剧单行本。还有四川方言剧《抓壮丁》,“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点名批判,我们也出了。对振兴川剧,四川出版是做了贡献的。我们还出了《马季相声选》,为此马季还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来说过相声。
还有少儿编室(原是二编室少儿组):出了柯岩的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还有那三个小东西,即《七十二变》《猪八戒外传》和“小小连环画”(就是小开本的连环画)。还有“科学家的故事”丛书和陈伯吹、包蕾、鲁兵的书,再就是“小图书馆”丛书和“未来军官学校”丛书了。
美术编室是三编室,主任是王伟,思想也很解放。出了《张大千画页》(张长期在台湾)、《陈子庄画页》(陈子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有“历史问题”)。从《华君武画传》突破,出了“中国漫画家”丛书。年画《敬爱的元帅》质量高,发行量大。还出了《王朝闻文集》,可惜只出了一半。
其他如民族编室(四编室),出了《格萨尔王传》;科技编室(五编室),出了《李斯炽医案》和陈达夫《中医眼科六经法要》;辞典编室(六编室),主要就是和湖北协作编纂出版《汉语大字典》。
三、四川出版在困难中前进
那个时期,是先出书,不断遇到挑战和问题,又不断解决、突破。不是说我们四川出版开始就有什么大思考,而是从抓出好书开始突破的。1978年庐山全国少儿出版工作座谈会后,我带着四川出的几本书到北京找曹禺约《王昭君》稿,曹禺一看我们出的书就心动了。这本书一出来,就引起“轩然大波”。
陈翰伯找我说:听说你们开高价买稿子?我问崔之富(时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老崔说我们是在稿酬规定标准内付酬的。当时国家出版局另一位领导来成都时说:“四川怎么能够出曹禺的书呢?”巴金知晓后,叮嘱我们一定要把曹禺的书出好。所以我在“长沙会议”上说,我们决心以出好书回答别人的疑问和不理解。只有把书出好才站得住脚。
崔之富是老出版人,对“三化”方针的束缚是深有感触的。他曾说:过去好的小说、好的学术著作都流失出去了,书店卖的,只有本省出版的为配合中心工作租型的书和字大、图多、本薄、价廉的小册子。
从我个人来讲,有三个因素和“面向全国”相关。一是我读中学时,常去巴金担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玩耍,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书就是面向全国的。这应该说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二是我在《红领巾》杂志时,虽没有面向全国组稿,但《红领巾》杂志专刊《刘文学》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全文刊登其内容,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热潮(当然,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刘文学》一书显然受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我认识到,只要是好东西,就可能在全国产生影响。三是我调到北京办《辅导员》杂志,它就是面向全国的。可以说,我脑子里没有什么“三化”方针的束缚。
我在《李致与出版》“后记”中说道:我们在定规划、选题时,眼界就比较宽。周总理诗出好了,巴(金)、茅(盾)、曹(禺)、臧(克家)、艾(青)的书拿出来,其他都好组稿了,有的作家没有在四川出书还感到遗憾。以后才知道,这就是“名牌效应”。在抓质量上,除了订好选题计划,我每年还两次到北京、上海组稿。当时,我还分管总编室,重点是抓装帧设计和校对。对陈世伍设计的《王昭君》封面,曹禺极为满意,并广为宣传。戴卫(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为《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之三)设计的封面非常漂亮,巴金非常满意,萧乾说该得奖。
抓好这两条后,我去组稿时,绝大多数时候是带书组稿,用书说话。把书一摆,不用多费口舌,作家就心动了。我提倡编辑们用这个办法去组稿,后来形成全国作家“孔雀西南飞”的局面。“孔雀西南飞”,是作家形容的。
在装帧设计上,也有不少“斗争”呵。如出版科长李郁生开始怕成本高,不同意在书的封面、封底加“勒口”,但老崔(崔之富)支持加“勒口”。后来,李郁生说,四川的书出好了,普遍受到称赞,他们出去开会底气都壮些。由于书出好了,把他们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对重点书,我坚持掌握进度和材料工艺。我多次到印刷厂了解印制进度和质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了出好书,在老崔指挥下,社里曾派三路人马到全国各地找塑膜原料印制《巴金选集》封面,保证了十卷本的《巴金选集》在一年内按时出版(当时出版周期较长),得到了《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的表扬。“面向全国”,不只是把书发到全国,主要是提高书的质量,让读者愿意买你出的书。
我特别感谢当年的省新华书店副经理袁学林。那时只有新华书店这一个发行渠道,而原来省店的图书征订单只发给省、市、自治区一级新华书店和各大图书馆,最多发一两百份。我们面向全国以后,他们尝到甜头了,为适应面向全国,在我们的催促下,袁学林带领本版科的同志把省店的征订单发到了全国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两千多个县店,经常是搞个通宵。省店本版科也由过去的冷冷清清变得很有生气了。
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在四川省出版总社与总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谢临光、朱启瑜、李致、徐惟诚、冯国元、钱铃、关源博、李正模后排左二起:邓星盈、李陈、解伟、张再德
我觉得是这样一种进程:用出书来突破“三化”,到了书在全国有了影响,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进而才提出突破“三化”方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个方针提出后,又引起很大的争论,直到“长沙会议”时,才得到国家出版局的确认。以后就不是我们几家地方出版社面向全国了。所以在出版界纪念改革开放20年时,突破“三化”方针被认为是我国出版界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之一。
有意思的是,杨字心(时任文艺编室副主任)到北京出差,北京一家文学出版社的同志问他:“你们这样搞,我们还怎么吃饭呀?”老舍的女儿舒济告诉我,“长沙会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回社传达破除“三化”的会议精神,以激励该社的队伍。为了密切与同行的关系,我们出了人文社社长严文井的“近作”,出了韦君宜的小说《女人集》和《编辑手记》,还出了韦君宜丈夫的《杨述诗选》。韦君宜重病时,我两次去看望她。当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很注意我们,这个社的总编辑林纳愿把他的散文集交给我们出,结果没交稿他就去世了。
四川出版当时能取得一点成绩,得益于一个重要背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民主空气。胡耀邦同志在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召集团中央所属各出版社和报刊社总编辑开会,强调出版社和报刊都要抓重点。平时要丢“小石头”,一定的时候要丢“大石头”,要有重头文章,才会有大影响,引起“轩然大波”。只要是对的,就要坚持下去,就要奋斗。我们当时那样做,也受他的影响。
后来出的书中,整得最热闹的是出版记述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历史的《最后的年月》。这本书极为感人,编辑流着泪审稿,工人流着泪拣字和拼版,九天印了四十万册;但书刚出版即被暂停发行,作者和出版社都受到责难。向上申诉无结果,我去找耀邦同志反映。他开始没有表态,我就跟他争,说你让我们出好书,结果出了好书又不准发,不准发的理由又站不住脚。他考虑后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说完,他左一挥手,右一挥手。见我还不明白,他又说,你可以——自己发嘛!这本书最终被准予内部发行。
中国翻译家协会到成都开会,冯至、黄源等多人到会,我请他们来出版社看样书。代表们对川版书的选题、作者、装帧等称赞不已。中午,社里破天荒地请他们在芙蓉餐厅吃便饭。席间摆谈,冯至对我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官,也不是出版商。我认为,这绝不是说我个人,出版是个整体,他这句话是对全体四川出版的同志说的。
进入市场经济后,有人对我们提出的“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表示否定。有人主张“先做出版商,后做出版家”;也有人主张“既做出版家,又做出版商”。有一次,我和徐惟诚同志谈到这件事(他当时是北京市委副书记),他说他是支持我们的。我多次表明,不要玩文字游戏,我们从不否认经济效益,曾以盈补亏出了不少好书,不仅分三批盖了职工宿舍,还盖了出版大楼。我们总结的经营理念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是薄利多销,不是越多越好;赔是能不赔的就不赔,能少赔的就不多赔。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我们说要做出版家,就是邓小平说的“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现在看来,还是要当出版家。
还有就是要让所有的出版人都热爱出版工作,甘为他人做嫁衣,不要当“出版官”,对作者不可冷淡。巴老也说,一定不要当出版官。四川出版社提出,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应该是为作者服务。除了出好书,还要关心作者,与作者建立友谊。曹禺是我的长辈,先称我为“李致同志”,后改称“李致兄”。他与我们建立了深情厚谊,表示要和四川出版社“生死恋”。诗人公刘生病,我们派张扬(时为二编室诗歌组编辑)去广西探望他,他很感动,来信给我表示感谢。这类事例很多。
我离休以后开始写书。作为作者,对“出版官”的体会太深了:有些编辑接到稿子不跟你说一声,用不用也不跟你说一声。
对出版人来说,丢掉官气很重要。
2015年7月23日采访于成都金杏园李致寓所
采访手记
去年7月,家明兄(汪家明)还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任上,他到成都参加全国“美联体”订货会,会后约我一起去看望李致同志。他俩是头回见面,说起范用、萧祖石等共识的熟人,说起书来,一见如故,有说不尽的话。临别,李致送给家明两样书,一是他刚在天地出版社出的三卷本《往事随笔》,另一本是记述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事出版工作时所作所为、所见所闻的《李致与出版》(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
出门后,家明感叹:没想到老人家记忆力那么好!又说到即将创刊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委托他组稿,他希望我能写写李致,帮助人们了解那一代出版人是怎样把那个年代的出版做到那样一个高度的;他们那代人有着家国情怀,后来者很难逾越,应该把他们的作为真实地记载下来,毕竟那代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他一再叮嘱我:这个活儿必须你来做。
家明兄嘱托,我没法推辞。于是就有了7月23日对李致同志的访谈。
这些年,写李致出版生涯的文章不可谓少。我这次访谈当从何说起?
李致,原名李国辉,1929年生于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青年团重庆大学校委书记、共青团重庆市委大学部部长、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后期回到四川,先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总编辑,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四川省文联主席。
李致告诉我:他一生中有三件令自己满意之事:一是解放前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二是从事出版工作,出了一批好书;三是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为“振兴川剧”鼓与呼。
我是1976年9月15日从部队退役后分配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文艺编辑室)少儿组做编辑的,那时李致分管我们,是我顶头上司的上司。那年,我二十二岁,他四十七岁。李致中等个头,敦敦笃笃,推个平头,戴副墨镜(他患眼疾),没架子,待人随和。他爱书。那时书少,一次到他办公室谈事,我见桌上摆一摞从市书店“内部服务部”购来的未公开销售的书,忍不住动手去翻,被他一手拦住:“洗手去!”洗罢手又想翻,他还不放心:“小心点,别折页!”他对书的珍爱,可见一斑。
他懂书。常见他外出开会、组稿,每次回来,收获颇丰。他人缘通融,作家、名人以至年轻作者都买账,组回来的书多能打响。对编辑们,他一是带,二是帮,三是促。遇到好稿,眼睛发亮,绝不放过。
他好读书,亦好藏书,酷爱编书。
那年月当编辑,李致等领导带着我们做书像在打仗,总有说不完的选题,做不完的工作,还不觉得累。从那时起,我体会到了编书的无穷乐趣。那是一个充满朝气、使人鼓劲的时代,我所在的是一个齐心协力出好书的群体。随着一本一本好书的积累,四川出版开始崛起……
一晃,近四十年过去了。这段历史是值得留下的。于是,从这个话题说起,我开始了这次采访。采访时间近三个小时。
说起往事,李致如数家珍,口述一气呵成。当年我是个年轻编辑,知晓的为四川出版的枝节,李致是改革开放后出版“川军”的领军者之一,他的回忆展现了出版“川军”的整体情况。
记录稿拟出后,老人要看。为了定稿,后来我又如约登门,准时按响了李致家的门铃。他是个十分守时的人。随着一声响亮的“来啰”,李致同志开了门。先表扬我准时,接着就说这稿子害得他昨晚半夜睡不着觉,今晨5点就起来在电脑前审改:“好辛苦哟!”
他对文章一字一句地审,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最终,他敲定了这篇采访记录的标题:《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这篇口述史,由亲历者亲述,有点、有线、有面,原汁原味,有血有肉,不需采访者画蛇添足了。
临离开李致家时,我请老人家多保重。他说他昨天还曾去参加了一个学会的会,身体不错。对于自己的状况,他说:“今年已步入八十七岁,也算廉颇老矣!人们常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本人尚能吃饭,胃口也好;虽四肢无力,但中气十足。”说罢,他笑起来,眸子里闪出孩童般的得意。
这就是八十七岁的李致。衷心祝愿老人家活力永葆。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