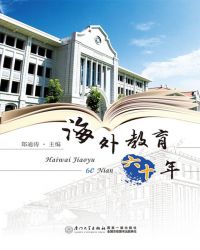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海外教育六十年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对外汉语教材词语英语译释研究概览
吴 琳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361102)
摘 要:教材建设与词汇教学有一个经纬交叉的结点,就是教材对于词汇的处理,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教材中词语译释的问题。本文拟从两方面对与本题相关的研究做以小结:一方面是理论性的研究,主要关注翻译理论研究和释义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是与第二语言教学实践相关的研究,包括教材词语英语译释专题研究,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和国内英语词汇教学研究。通过分析前人的相关成果,总结得失利弊,展望研究前景。
关键词:教材;词语;译释
所谓“译释”是指通过翻译的方式进行释义(作为行为本身);或者说是以翻译为手段的释义(作为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译”是手段,“释”是目的,“译释”是偏正关系,即对应的英语表达应为“translative explanation”。对外汉语实践证明教材中词语的英语译释的确有可能造成中介语中的偏误,这些问题已经对教学本身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
①你认识他的名字吗?(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②我姐姐结婚了她的男朋友。(我姐姐和她的男朋友结婚了。)
③公共汽车来了,你看了吗?(公共汽车来了,你看见了吗?)
④我喜欢吃汤。(我喜欢喝汤。)
⑤今天下午我有了一个睡觉。(今天下午我睡了一觉。)
表面看来,以上偏误的产生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是翻开这些学生所使用的汉语教材则不难发现,如果造出一个与上面的汉语句子表达相同意思而且具有相似结构的英语句子,那么在汉语错句中误用的词语往往有一项教材所提供的英语译释可以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进入这个英语句子:
①Do you know his name? 认识:to know;知道:to know
②My sister married her boyfriend. 结婚:to marry
③The bus is coming. Do you see it? 看:to see, to look, to have a look, to watch
④I like eating soup. 吃:to eat; 喝: to drink
⑤I had a sleep this afternoon. 睡觉:to sleep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材词语英语译释问题很有研究价值。本文拟从两方面对与本题相关的研究做以小结:一方面是理论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与第二语言教学实践相关的研究。
一、理论方面研究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译释”,那么与之相关的理论自然就分别来源于“译”的理论和“释”的理论。“译”的理论指的是翻译学理论,其研究的核心是“翻译标准”问题。“释”的理论指的是应用语言学中有关词语释义内容的理论,其主要成果集中在词典学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则是围绕“释义的要素”问题展开的。无论是“翻译标准”还是“释义的要素”它们之所以分别处在各自理论体系的一个中心地位上,是因为它们都属于最根本的原则性问题。下面就对这两方面理论进行基本的考察,特别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一)翻译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翻译”的定义不下百种。很难讲哪一种绝对正确,因为几乎每一种都有它的合理性,而且不同定义之间的差异往往是由观察角度或侧重点的不同带来的,因此也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例如,“尤金·奈达(Eugege Nida)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他把对等分为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和功能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后改为functional equivalence)”(邱懋如,1998)。这一定义含有“信息”和“对等”的概念,“蕴涵了翻译的‘等值标准’的意义”(黄锦炎,1998)。纽马克(Peter Newmark)定义翻译为“把一种语言承载的信息转换为另一种语义等价信息的手段”,则是“引入了信息语言学的概念”(黄锦炎,1998)。许均在探讨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时说,“翻译活动是翻译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这里又着重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以及影响翻译活动的“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许均,1998)。既然多种定义方式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那么我们不妨将它们的“公因数”提取出来,作为“翻译区别于其他语言活动的几个特征”:第一,“翻译是联系两种语言的语言活动”;第二,“翻译要求在语言转换时,原语的信息不变”(黄锦炎,1998)。
具有以上本质特征的翻译,其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是语言之间的可译性。“所谓可译性问题,关键在于译者用原语接收的信息是否都能用译语表达出来”(黄锦炎,1998)。在这里,首先是能不能译的问题,其次是能译多少的问题。“现代语言学告诉我们:任何语言都有其复杂的语音、语法和词汇体系,都有生成新话语的无限潜力,换句话说,任何语言都有对任何事物、事物的性质、事物的运动等进行描述的无限潜力。”(黄锦炎,1998)我们基本同意这个观点,但同时要强调两点。一是此处所谓“无限”应该是指“开放性”,它相对于“封闭性”而言,并非是没有任何限制,因为这种潜力无疑要受到来自客观世界、交际者的思维意识及语言自身规律等因素的制约。二是“信息”的外延很大,既包括实现“达意”的基本信息,也包括用以“移情”的附加信息。而对于原语某些形式意义的特定组合才具有的“移情”效果,译语再强大的“描述”能力也望尘莫及,因为那部分由语言的意义和形式共同承载的“信息”就不具备可“描述”性。也就是说,即使从“出发语”的角度看存在“可译性”,也并不能保证从“目的语”的角度看有“可接受性”。(潘文国,2002:44)故我们赞同这个观点——“翻译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绝对不能的,它是可行的,但有限度”(许均,1998),限度的具体情况要结合特定的翻译活动具体分析。
可译性为翻译的存在提供了基础,那么翻译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就涉及翻译目的的问题。“翻译的实质更重要地反映在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上”(黄锦炎,1998)。“翻译目的是指通过翻译意欲达到的效果。”而且,“翻译活动的目的对‘翻译什么’与‘为谁翻译’以及‘为什么翻译’有着直接的影响,对翻译立场、翻译方法也有制约”(许均,1998)。其中,“翻译立场”就关系到“翻译标准”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也很多,尽管各种主张各有侧重,但是都关系到“翻译对等”(或者说“等效”)这一核心。“对等”的参照点(如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等)和对等的层面(如“信、达、雅”分别所针对的层面)确定后,“翻译立场”也就基本确定了。而这两个重要问题都是由具体翻译活动的具体目的决定的,翻译这项实践活动“开始便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许均,1998)。“不同种类的翻译需要不同要求的翻译标准”(庄夫,1998),它们之间“既有共同的基本原则,又各有其特殊规律”,比如“法律要求特别严谨,电影需要字数和口形,广告强调吸引性”等等(金隄,1998)。因此可以说,具体的翻译目的决定具体的翻译原则,该原则又贯穿始终地指导整个翻译过程;不仅如此,我们还能通过对照翻译的结果和目的反观前面的可译性问题,因为这样“往往可揭示出在翻译活动中客观上存在着译者难以自主的一些因素”(许均,1998)。
关于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这里借鉴了金隄四大门类的划分结果(详见金隄,1998,《等效翻译探索》),同时类比语言学的相应分类情况对其层次和定位调整如下:第一刀先切分出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而后理论翻译学又包括普通翻译学(即“第二门类:翻译学本体理论”)和具体翻译学(即“第三门类:翻译学专项研究”),应用翻译学又包括狭义应用翻译学(翻译教学研究,即“第四门类:翻译学技巧研究”)和广义应用翻译学(即“第一门类:翻译学基础理论”)(金隄,1998:8-13)(见表1)。其中我们说的“广义应用语言学”与金著中的“翻译学理论基础”之间的对应关系似乎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翻译学理论基础”包括“一切与翻译有关的学科”,这方面的研究指的就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对这些“本身大多是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就其中某些学科的性质而言,的确可以称得上“翻译学基础理论”(如金著所举的“哲学”“信息传递学”等);但就翻译学在这种交叉性研究中的角色而言,又确实属于翻译学的应用性研究——二者便统一于此。
表1 翻译学及其分支学科
近年来国内立项的翻译研究课题所反映出的趋向“似乎证明实证型的、理论的研究较受重视”。这些课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史类研究”、“理论类研究”和“教学研究”(许均、王克非,1997)。这三个方面分别属于广义应用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包括普通和具体两个小领域)和狭义应用翻译学。可见,翻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虽然涉足翻译学的各个领域, 但极少专门关注翻译学与第二语言教材词语译释问题之间的交叉研究。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带有普遍性的翻译学理论——尤其是有关词层翻译、翻译同语境间的关系、翻译同语言对比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用于译释研究,从而发现并总结出这一特定范围中的“译”的特点及规律。
(二)释义理论研究
“释义”顾名思义,就是解释意义。这个“义”是广义的意义,包括词语的词汇和语法两方面意义。“释义的任务主要有三个,即:词典编纂;一般选文注释;语文教学。”与我们所研究的译释关系最紧密的释义当然是第三种(以语文教学为任务的释义),它的特殊性是由它特定的目的决定的:“一是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一是丰富学生词汇;不了解语词的具体义不能看懂课文,不了解语词的概括义就不能掌握、运用,也不能丰富词汇。”(孙良明,1982:80)但是就目前的释义理论研究状况来看,它主要是作为词典学的一个核心部分来研究的。这也不难理解,显然释义是关乎辞典编纂成败的核心问题,而对于选文阅读和语文教学来说释义只是一项辅助性因素,再重要也不是核心本身。释义理论也就因此在词典学中得到了较为深入的发展。于是在一般的语义学的释义理论之外,词典释义理论也就成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如同翻译的标准能使翻译活动有据可依一样,搞清释义的要素也就令释义活动有章可循了。选择释义要素无疑也是一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情,特殊的释义目的决定我们怎样选择释义要素,但是在选择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对选项的情况有个全局性的了解,也就是清楚有哪些内容要素可供选择。这里就涉及“释义应该处理的几种关系”:“字义与词义”,“字面义与用法”,“概括义与具体义”,“义场与义心”,“词汇义与语法义”,“本义与转义,古义与今义”等等(孙良明,1982:118-152)。只有弄清了与释义相关的一些基本关系,我们在确定释义要素的选项并做出选择时才会更加有的放矢。
与具体操作更为相关的是释义方法方面的理论。方法直接关系到释义活动的实现,因此几乎这方面的每本论著、每篇文章都会或多或少地谈及这一问题。比如,“描述式”“形容式”“发生式”“原因式”(黄建华,2000:113),“直接释义”“解述性释义”“复合释义”“功能性释义”(章宜华,P75),通过标明词的词汇义场、语法义以及感性义等进行释义的方法(孙良明,1982:17-52),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提法之间的差异不仅来自不同的角度,还来自不同的层面;共同点是都处于词条内部,没有超出单个词条释义方法的研究范围,故在此且统称为“狭义的释义方法”。与之相对的“广义的释义方法”即在此基础上还包括词条之间的统筹规划问题,通常就是体例方面的安排方法,规范词条结构等方法。黄著中的“微观结构应有稳定性”(黄建华,2000:68)就是着眼于广义的释义方法而提出的。教材词语译释研究是应用性研究,所以与实际操作密切相关的方法问题自然也是关注的对象,各种具体的方式最终都是服务于“释”的目标的。
本文的“释”是以“译”为实现手段的,因此词典学中关于双语词典及其释义方面的论述对我们的研究更有针对性。比如黄建华对双语词典的特殊性“两套符号的对应”的阐述,对适于双语词典的释义方法的总结(黄建华,2000:127-134),李明、周敬华对“主动型词典”和“被动型词典”的区分(李明、周敬华,P31)等等,都为我们的思考与分析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参照体系。
其实,无论是“译”的理论还是“释”的理论之中都蕴涵着来自语言学方面的更为基础的理论支持,这种支持以其根本性与普遍性对“译释”的研究发挥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理论语言学方面,主要有三个分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基础理论动力:语义学(特别是词汇语义学中的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语法学(尤其是语义语法学中的配价理论和格关系理论)和对比语言学(主要是汉英对比语言学);而“译释”又是以辅助教学为终极目标的,因此应用语言学中第二语言教学原理也是研究的基石。这一着眼教学应用的研究当然是以语言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为基础的,无须赘言。 海外教育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