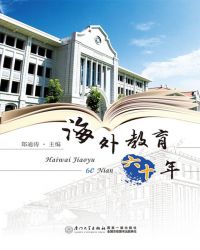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海外教育六十年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忠于原文”是否可能
——理雅各《论语》英译本发微
王 梅 曾振宇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361102)
摘 要:理雅各的《论语》译本已历经150多年。它在饱受来自中西两方各种毁誉的同时,也逐渐确立其经典译本的地位。在中国,对这一译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直译问题、误译问题和文化归化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些批评入手,考察分析这些批评产生的原因、可能存在的误解,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发掘理雅各《论语》译本的经典价值。
关键词:理雅各;《论语》;经典;直译;误译;文化归化
经典是时间的产物,“唯有时间才能将有意义的东西从无意义的东西中筛选出来”,因为时间可以“清除非本质的东西,而让隐藏在事情中的真正意义变得清晰可见”。数千年来流传的《论语》无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而对经典译介产生的经典译本也需要来自时间的考验。根据杨平博士的统计:第一部由外国人翻译的《论语》英译本(The Morals of Confucius)初版于康熙三十年(1691),可能由拉丁文转译而来;第一部由汉语直译而得的英译本为马歇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于1809年出版的《论语》英文节译本;第一部中国人翻译的英译本则是辜鸿铭(Ku Hungming)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译本(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目前,《论语》的英译本已达五六十种,其中经过150年时间洗礼的理雅各译本,无疑是影响最大的英译本之一。2011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理雅各的《中国经典》。2014年1月,上海三联书店重新出版理雅各的《中国汉籍经典英译名著:论语、大学、中庸》,在其封面上则印有“西方世界公认的标准译本”。在西方,理译《论语》仍在重印,如2006年9月密西根自由大学出版社的版本、2014年3月Createspace出版社的版本,以及数个Nabu press的版本。
在学术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对理雅各译本及其本人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仅对理雅各的《论语》译本,中国知网中收录的文章就有380篇。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论语》英译个案研究、《论语》英译对比研究、《论语》词汇英译研究。其中更以英译比较研究居多,特别是对理雅各与辜鸿铭的比较研究就占据多半。近年来,在数篇以《论语》英译本研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中,理雅各的译本也常常是必选项。就研究主体来看,大多研究者均为国内高校英语专业的学者。因此,他们多从翻译学角度入手,依据相应的翻译理论,分析译本在字词、句式处理时所采用的翻译技巧及方法,抑或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译文和译者的文化背景来进行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对理雅各本人的研究在国内主要有岳峰的博士论文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专著《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2004)。此外,2011年出版了周振鹤翻译的美国学者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2002年撰写的《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译书中同时收录了理雅各后代海伦·蔼蒂丝·理(Helen Edith Legge)2010年撰写的《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James Legge, Missinary and Scholar)。
翻译可以无限进行,因为没有所谓绝对的完美译本。但综合看来,从理雅各译本的存在时间、对其研究的力度和广度以及其对中西学术领域的影响来看,在《论语》的众多译本中,理雅各的译本无疑超越了自己形成的时代,并开始具备成为经典译本的气质。面对理雅各150年前的《论语》译本,作为处身于变化如此剧烈的新世纪的读者或研究者也许首先会遇到以下问题:理雅各的译本为何仍会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共鸣和关注?它又如何在此后丛生的众多译本中生存下来并确立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到译文本身。国内评判理雅各译文风格、特色的论文数量众多,它们多在肯定其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其不足之处。这类论文展开批评的方式多为选择另一译文,将其与理雅各的译文相比较,然后得出结论,比如在批评理雅各“译文冗长、笨重,不宜朗读”时,必选出另一译文精简、易于阅读的译本来比较。这样依据一个比较对象或选出几段译文范例的比较方式看似清晰明了,但其实在说服力上仍显欠缺。通过解读译文,发现不足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确实是翻译学界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最惯常的研究方法。本文则希望逆向而行,从众人的批评出发,来寻找、理解被批评者翻译时的状态和思量,正如从地面斑驳的树影中寻找阳光一样,我们希望从批评入手,重新理解和体会理雅各的译本,进而寻找其百年来流传并深具影响的原因所在。综合众多译文比较及分析的论文,我们可以将对理雅各译文的批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直译问题(主要关涉到译文的语言风格)、误译问题(译文的准确程度)、文化归化问题(译词的基督教化)。
一、译文的语言风格
直译和意译及其相关的归化与异化概念曾经是翻译界争论多年的话题。面对直译和意译这两种翻译策略,对其选择则需依据原文特色,以及更为重要的“翻译目的”来确定。正如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所认为的“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从翻译目的来看,我们可简要将《论语》译本分为侧重介绍型及侧重研究型两类。第一类译本通常将《论语》作为一种东方文化或人生智慧进行介绍,这包括一些语录体的译本及普及型的译本。这类译本的首要特点为简明扼要、易于阅读,在翻译方法上也倾向于意译,有些则只是摘取部分段落或片段进行翻译,如曾在西方畅销的林语堂的《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就是四书加《礼记》的摘译;第二类则是侧重研究型的译本,由于译者的研究需求不同,其侧重点也各异,如安乐哲与罗思文(1998,Roger T.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Jr. )的译本希望能突出《论语》中包含的中国哲学之异质性;白牧之、白妙子 (1998,A. Taeko Brooks, E. Bruce Brooks) 的译本《论语辨》(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则拆分、组装《论语》几千年来固定的章节,以形成自己对早期儒家流变史之梳理。这类译本一般强调直译,特别对核心词的处理更是颇费心思。
理雅各的译本无疑是属于研究型的译本,他在《中国经典》第一卷前言中指出自己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圣贤的思想,因为这是中国人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因此,追求“忠于原文”,而非“行文优美”是理雅各依据自己翻译目的所做的选择。这种以牺牲阅读快感为代价的策略从一开始就引来了诸多批评,正如辜鸿铭直言理雅各“大量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那些术语是深涩的、粗疏和不适当的,有的地方简直不符合语言习惯——理雅各的儒经翻译为普通的英文读者所呈现出的中国人的思想和道德观,就仿若普通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非常离奇怪诞”。对普通读者而言,理雅各的语言确实会带来阅读的障碍,但对研究者来说,与阅读快感相比,他们更关注译本的准确性及其传达的知识及思想信息。因此,当面对一个以直译为策略的研究型的译文,我们很难让它与以意译为策略的介绍型的译文比较简洁生动。如“君子食无求饱”(1.14)一句, 理雅各的“He who aims to be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in his food does not seek to gratify his appetite”的可读性自然无法和许渊冲“An intelligentleman eats to live, and not lives to eat”相比。但同时,他确实更加贯彻其直译的准确性标准:比如尽量让每一个汉字都得到翻译(君子—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食—food;无—does not;求—seek;饱gratify his appetite);在句式上,这句译文也基本依据汉字的顺序。这种将译文词语、句式与原文尽量对应的翻译策略虽然不能贯彻于每句中,但确实是理雅各译本的一大特色。
当我们获得直译带来的“忠实”时,不得不牺牲一下它同时带来的生涩。其实,在直译和意译问题上,任何译本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但每个优秀的译本必然是在有所侧重基础上的平衡。高度赞扬理雅各的吉瑞德甚至认为他的译本超越了直译和意译:“翻译的时候,不是按照字面意思的直译,或者以理解的意思的意译,而总是要像理雅各那样,努力通过一种‘同情的理解与阐释性的实践’的更为互惠的、比较的、隐喻和象征的方法,去直接面对学习处于敌对面的宗教、经典以及学术权威。”姑且不论这一评价是否过高,但吉瑞德提到了重要的一点,即译者对原文及其背后文化的“同情的理解”。这一情怀首先使译者在翻译中会尽量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以及面对译介作品时的积极态度,如果再加上卓越的学术能力和严谨的学术风格,所形成的译本一定会具备优秀的质量和学术价值,下文将通过一些例子及其他研究成果来详细说明理雅各的上述特点。 海外教育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