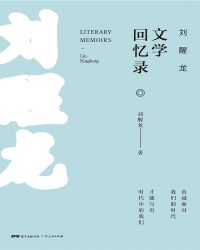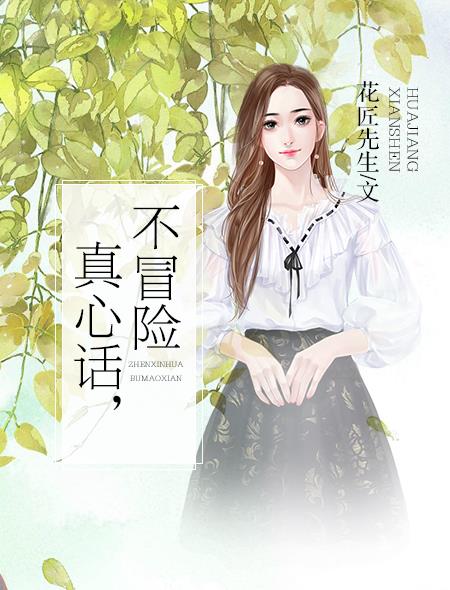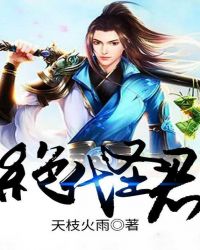第90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90节·
人的灵魂深处有个毛病,世界上的尖端问题研究得越多越热闹的时候,就越喜欢去想一些寂寞的问题,如生命怎样才算是自由的?在实用价值、实际价值越来越成为判别人人生价值的大众标准的时代,那些卑微人群的精神价值是否还有意义,他们在世界上的定位是否与别人平等?其实就生命本身来说,只要能跑、能走、能自由自在地活在世上,它们的历史地位就不该有什么不同。基于这一点,写作者最愿意做的事便是在文学中自由地表现自我的思索、自我的思想和自我的思念。虽然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尚不能有证据证明它是个人化的,但我认为只要它是个人的,就很好,何必非要统一地化成什么的呢。
文学是人的精神的一种表达方式。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精神必须是极其自由的。当一个人选择文学时,他其实就是在选择自由,所以任何人都不应以任何方式来干涉任何人的文学寻求及自我定位。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一直不大习惯北京。无论是从西客站进入,还是从首都机场进入,一沾它的边,就会感到盛气凌人。接触多了以后,慢慢地就觉察到在什么都敢说的气氛中,有一种被压抑得很深的歇斯底里。仿佛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自由,也从未有过平等。
在我从前的小说《凤凰琴》里,我曾深深地怀念多年前在山里听见的一种笛声。那是水库工地上受饥饿和劳累双重压迫下的民工用劣质的笛子吹出来的,旋律不流畅,音色也是疙疙瘩瘩的,然而它却是那个环境里唯一抽象出来的美。人随听觉跟上它,超越黄昏暮色寒霜冷月,一时间竟然也能进入心旷神怡的境界。我一直以为,那些将无可奈何、无所谓和无常说得极顺溜的人们,内心里响着的同样是只在山野间回荡的粗粝的笛声。那是一种真正属于个人的无所束缚、自由的心声,虽然内容包藏着苦涩艰辛,可那飞翔的空间足以容纳一切想象和神往。我无法不屈服于这些笛声,它那在晚风中飘扬、缥缈和漂泊的样子,实实在在是一个个真切的生命,是一个个灵魂重获自由以后的高贵写真!这种高贵来源于人的精神面对命运时的浪漫!
自由是每个人毕生的精神根基。失去精神根基后,人是何等的不足挂齿!一辈子斜眼看人昂然叫狗、一辈子竖着耳朵缩着脖子,鸡鸣狗盗地小有进项,那种日子到头来连自己都瞧不起。
我们不能放弃根基!这一点现在看来不成问题。问题来自另一方面。
1998年夏天从西藏归来,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神圣二字。这种收获完全来自身临青藏高原时,原始山野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以及缺氧条件下人对自身曾经面对自然自由地为所欲为方式的否定。它极端真实,让人无法矫情。所以它同人在用自己经验里的怀旧情绪逐步酝酿起来的那种神圣截然不同。前一种神圣是从灵魂中升华起来的,而后一种神圣则会妨碍灵魂归依到本真的位置。我越来越看重这一年自己的那篇《大树还小》。我们的世界有时挺让人悲哀,因为有了自我假定的神圣,一类人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忽略另一类人活着的意义和活着的质量,用一己的自由去置换他人的自由!
在自由的精神根基上,平等是人存在时的尊严。自由是平等的前夜,平等是自由的明天。今天实际是我们正处在二者之间。那么我们会不会永远只能在祈盼中等待明天哩?如果是这样,那些因为一些人神圣的需要而被理直气壮地忽略的另一类人,是不是就应理所当然地弃之世界的暗角!在《大树还小》里,“知青”只是相对这一类人的另一类人,是在不平等世界中两个对应符号中的一个。袭用哲学语言,只要是人,不管他是美国总统,还是非洲难民,都应该是相同的符号。要命的是,谁真正将自己当成过符号?符号“知青”和符号“当地人”在相同苦难面前的不同历史记录,正是用这样的心理现实书写的!世界上许多曾经的真实就是这样被人毫无羞耻地篡改的。
真实就是这样残酷,一个“符号”在事关自己时,就连多少分之一的机会也不肯给另一个“符号”。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应运而生,将人、人性以及思想的破损,毫不留情地镂刻在艺术的灵魂上。同时修补社会史和思想史里不可避免的缺陷,能够在后人对前人的诘问面前提供一个多维模型,使本不能重复的东西再现于多少年以后。
当下世界视角太多。从东南到西北,最时髦的同最原始的,最先进的同最落后的,犬牙交错混合在一起。特别是最公正的和最不平等的搁在一起时,简直让人心里翻江倒海不知该如何去用心想用眼看。人之间不可弥补的差异,几乎在精神上将一些人与另一些人完全撕裂开来。彼此间的漠视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解决不好走在前面的少数人进入自由王国,和走在后面的多数人渴望权利平等的关系。以至总是由落在后面的人发动起义,将一切砸个稀巴烂,耗尽一点可怜的社会积累以后,又不得不从头再来。如此周而复始,历史老在皇帝的家门前打转。
我们可以祈祷自由万岁,千万别以为自由万能。
写作者在很多时候对自由的把握要超乎常人,而不需要平等。
独立并不是自由,也不是平等。独立更多是由于利益的驱使,而自由平等才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在利益的驱使下,独立实现之日便又是另一类人深陷不自由不平等的开端。生活源头的一些复杂情节,对人类意志的作用,常常只是过去的一段故事。
文学这本该是故事的东西只能站出来,用艺术来做世界的良心。
《大树还小》也是用良心写的,是为了天下的“符号”不再有贵贱之分。
写作者首先应该是善于宽容的智者。文学的天国里不可以使谁像鲁戈瓦一样,抢一席之地,遇事只认自己的意志,只相信自己的意志才是不可能出错的,也只有自己的意志才是拯救与升华,并且为了这一点不惜将自己的言行夸张到极致。
不只是新老纳粹和新老霸权主义者,写作者同样也能发动对自由与平等的根本破坏。一旦写作的权利只被一部分人所占用,拥有它的人便会在思想上变得简单和单一。面对这样一个繁杂的世界,写作者更应站上山脉的分水岭,注视另一半空间,这样做也是对自己情操与素质的清点。
对于人格健全的写作者,一部作品的完整创作过程必须包括对自己心灵的完善。
上帝给我们天空,是为了让我们思想享有充分的自由。上帝同时给我们以大地,是为了让我们享有充分的平等。上帝显然预见到了人可能会犯的错误,所以它将无限的天空设计成虚的,而将有限的大地建造成实的。上帝的想法是人可以尽情地在空中自由地胡思乱想去,回到地上后就得面对现实,平等地使用有限的物质。本来自由是高贵的,是所有价格制定者和使用者都望尘莫及的。痛惜的是人在不知不觉中,将自由和平等揪到了一起,放在沾满泥泞的大地上,成了一种招揽生意占有份额的招牌。
回头来看,以北京的感受为典型,我们也许确实并不懂自由平等对人的真正意义。还有上海人看谁都是乡下人,广东人看谁都是穷光蛋等例子。无论如何,我不能认同《大树还小》里秦四爹那样的生活,活着人的模样,就要有人的意义,谁也无权剥夺他在上帝心中享受幸福的权利,谁也不能假借手中的便利,冒充合理合法地去漠视他们。秦四爹与所有的人一样有着健康的四肢五官,正常的七情六欲和符合人的道德规范的思想意识。不平等地给他以历史生活各个方面的人权,是对历史生活的肢解。我愿意看到《凤凰琴》里余校长他们那只有一些普通光辉的精神,虽然它被那“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新闻压在报纸的一角,但在报纸不能覆盖的崇山峻岭中,他们用最质朴的美感实现了自身的自由。
人只能平等地看待自由,而不能自由地看待平等。如此对照当下真实,不能不遗憾,自由平等这棵大树依旧还小。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