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月夜行路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辘轳井
早年,家乡父老们离不开辘轳井。他们的生计与命运都维系在悠长的井绳上;甚至连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惆怅尤怨也融进了粗哑的辘轳声里;以致寂寥而平淡、艰辛而困顿的岁月,还有殷切的盼望与美好的憧憬,一并随着迟缓而间歇摇滚的辘轳沉落和升腾……人们离不开辘轳井而深深依恋着,并把挚爱和怨恨统统施予了她,多少代人都没有摆脱她的缠绕。
那时候,村里人浇田灌园和饮用都依靠辘轳井。每逢仲春或清秋,田野里没日没夜地响着喑哑、苦痛般的辘轳声。父辈们起早摸黑,或披星戴月地站在井台上,俯身摇辘轳汲水浇灌着皱巴巴的几分水田。天色微亮就起来劳作,一直把太阳摇到东边的龙山顶上很久了,婆姨们碎娃们、大姑娘小媳妇、抑或老太太挎着篮儿,拎着黑釉瓦罐稀稀落落、三五成群地出现在田野里,转而送饭的人们像采蜜的蜂儿一般散落在自家的井台边。
女人的笑语与嘈闹的辘轳声,渐渐浸没在绿色中了。她们默然取出干粮、倾倒一碗清汤寡水,慎重地摆在井台上,才提醒家人该吃早饭了。男人则一声不吭地停下,惆怅似的凝视一瞬葱绿的田畦,然后情不自禁地喟叹一声,搓搓手就蹲下吃喝起来了。此时的田野里显得很静谧,也很怡然而温馨。
庄稼人渴望田禾长得旺势,秋后多打几斗粮食。倘若灶王爷情愿惠顾的话,那就顿顿让一家老小吃稠一些,即使清汤寡水也别断了顿。财神爷哩?您就高抬贵手赐几许散碎银子或铜子儿吧——积攒起来置两亩地弄一头牛,最好再制一挂大轱辘牛车?要么就给娃定亲娶媳妇。唉,狗日的光景过得太难肠了。
摇辘轳浇田灌园是一桩苦力活儿。一个强壮的汉子不分晨昏地摇整整一天,大概能浇六七分或一半亩吧?最苦的日子就是夏天——骄阳似火,烈日灼烤着疲惫的人和焦渴的禾苗,他们都竭力渴望清粼粼的水来润泽,然而摇辘轳浇田灌园的人们不能停歇。倘若稍稍怠慢了,那就有些前功尽弃的徒劳无益,只有一笆斗一笆斗的不间歇地摇啊摇,才能够浸透一小畦。
摇一天辘轳,自然是腰酸背疼、手臂僵硬的,躺下就像散架一样动弹不了。然而想到了收成,想起了生计,还有未来的憧憬,没等天亮就去重复那种枯燥、辛苦的简单动作。
辘轳的响动是衡定庄稼人勤劳与否的标准。朴实、勤劳的庄稼人凭着体魄和力气,从井里摇着丰收与喜悦。他们不断把梦想和希望投入井里,再拼命往出摇着残酷的现实。
辘轳声是判断庄稼人心境的准则。他们的喜怒哀乐、忧怨烦躁都寄予在粗粝喑哑的声响里了。喜则轻盈迅捷、悦耳动听;怒则疾促粗砺、惊心动魄;哀则迟缓低沉、如泣如诉;怨则嘈杂暴躁、节律紊乱;闷则悠长深暗、单调抑郁……
清晨的辘轳声清脆明快、午时沉觉烦躁;傍晚缓慢混沌。春天则清新而悠扬,似一首优美舒畅的抒情曲,悠悠荡漾在充满生气的田野上,蕴涵着“生”的期盼与“活”的渴望;夏日却艰涩而嘶哑,若一曲凄美忧伤的歌,惆怅诉说着曾经的往事,还有对未来的渺茫期待;秋天有点儿深沉而空茫,仿佛一段古老的民间传说,描述了曾经的悲壮与苍凉,时断时续地飘忽在苍茫的大地间,预示着一个辛酸故事的间歇,或者结束。
女人有时候坐在井台旁,一边做着针线活儿,一边陪着男人摇辘轳。面前是一条瘦弱的涓涓细流,是一片翠绿的田畦;还有蔚蓝的天空和宁静的白云;微茫的原野和蜿蜒的远山;痴呆孑立的孤树;漠漠的村落——身边则竖立着苍老而丑陋的辘轳架,赤膊裸背的男人正在俯首躬腰,一起一伏的摇着。
她们用细针密线把粗糙的井绳拧成一条温情的柔丝;在粗粝“咿呀”的辘轳声中,精心绣出了一幅豪壮与纤细、粗犷与温柔的风俗画。每个辘轳井旁都是一片希望、一首凄婉的歌、一幅恬静田园画、一段沧桑的故事、一个憧憬未来的梦。
辘轳井演绎着家乡人的简朴生活:女人们坐在旁做针线活儿拉家常;男人们蹲在一边谈论庄稼长势,年成的好赖;老人聚在一起回首往事;孩子们喜欢在井旁嬉戏……
那些相亲相爱的男女哩?一般都爱选择在辘轳井旁诉说衷肠。姑娘趁着给父兄送饭的间隙,特意绕到意中人的井旁,深情的一瞥或甜美的一笑,或者调笑一阵,抑或窃窃私语一番,随即像一股柔弱的微风似的,轻盈而匆促的旋进了绿野里。
小伙子痴痴望着飘摇离去的背影,情不自禁地松开绞了一半的笆斗。疾速倒转的辘轳把儿,猝不及防地一家伙把呆怔的小伙子击懵了,并带着深幽的艾怨不由分说地沉落了。姑娘闻声回首凝眉一瞥,禁不住“咯咯咯”的笑着跑开了。
这时挨了痛击的小伙子哩?往往呲牙咧嘴地忍着疼痛,不由自主搓摸着脑袋,瞅着姑娘的背影“嘿嘿嘿”的傻笑,直至那个颤动的身姿堙没在绿色里,才嘟哝着重新摇起了辘轳。
倘若他们相爱而遭到父母的反对与阻挠,俩人也会选择在辘轳旁相会。惨遭阻挠的爱情,以及失恋的痛苦折磨,酷似蚕食桑叶一般吞噬着两颗赤诚的心。姑娘依然在给家人送饭的时候,绕道经过意中人的井旁,然而俩人都失去了往日的喜悦。她惶惑而痛楚地默视良久,随即就默然低头而去了。
忧伤而悲痛的小伙子也无可奈何,呆呆地愣怔半晌,忽然咬牙切齿地摇起了辘轳。霎时间,一股脑儿地把全部的苦痛、忿怒、怨恨,还有烦躁与苦闷都缠绕在转动的辘轳上;并且发疯似的倾泻在持续不断呻吟的辘轳声里去了。
辘轳井是家乡人的希望:那喑哑、艰涩的吟诵声里,蕴涵着父辈们的艰辛与苦难;那幽深的井里隐藏着他们的梦景与幻想;那长长的井绳维系着他们“生”的期望与“活”的渴盼;还有苍茫岁月和惆怅的日子。古老的辘轳摇撼着那片苍凉的土地;旋转的辘轳摇出了一轮明月,也摇走了无尽的时光。
无数充溢着父辈希望、企盼、痛楚、忧愁与惆怅的春夏秋冬、日月星辰被摇没了。曾经依靠摇辘轳浇田灌园谋求生计的人们依然健在,但是辘轳井和辘轳架却荡然无存了。我时常怀着一种恋旧心态同他们谈起逝去的往事,情不自禁地提及曾经依靠辘轳井浇田和摇辘轳的经历。他们一听就默然伤神的沉思不语了,静默一阵,才淡淡地低语:如今好了,还提过去的事儿干什么?
久而久之,终于明白了家乡父老不愿谈及有关辘轳井的缘由。用他们的话说:那不是人干的活儿。我想不论怎样?辘轳井曾在慢慢岁月里养育了几代人;家乡父老在那种艰苦磨砺中,自然铸就了一种真诚、质朴、豁达的性格;还有那种吃苦耐劳、奋发向上的精神,否则怎么会有今天的幸福和欢乐哩?
话“奴”
家乡的方言很有意思:倘若形容小孩长得猪头猪脑般的憨实,或丑陋笨拙,即说“太奴了。”有时候,你若忸怩作态或呲牙咧嘴、蹙眉瞪眼的不愿去做某件事,人家也会用“看你那奴样”或“瞅你的奴相”来比喻。起初没有留意,也没有什么感悟,一次看电视节目,主持人让几位洋人即兴表演,便产生了诸般想法。
说实话,单纯的爆料、逗笑倒也罢了,而对洋人的那等卑躬屈膝的殷勤、毕恭毕敬的谄媚,总之那番亲昵与那般的讨好,真胜于待其亲爹亲妈了。毫不讳言:大约对其爹娘也没那等亲切、孝敬,由此就想到了“奴性”与类似的话题。
坦白的说,我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即使不说民族气节、尊严,那么做人的尊严与人格哩?毋庸置疑,社会公众人物的言行与形象,已经不单纯的代表个体了。倘若在相应的范围,或一定场合与场面,也许就代表阶层或集团,甚至国家、民族形象了。
我始终以为:无论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做考察,还是以社会形态做分析,汉民族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所谓的新旧石器时代,即母系与父系社会,也没有像欧洲历史那样,出现与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形态。那会儿的部落内部结构,大致有些等级区别,但是部落酋长与其成员的关系,绝对不是所谓奴隶主与奴隶奴的关系,而是属于带有血缘亲情的族群关系。即使部落之间发生了侵伐、征战,获胜者抓了一些俘虏,弄回去采取奴役的方式,迫使这伙战俘做些粗活脏活累活,也不能而此论定就是奴隶社会了。其实虐待战俘的现象,时至今日仍在不断地演绎。
类似的社会形态,大既可从《黄帝本纪》与《夏本纪》等典籍中得到佐证。据悉黄帝治世那会儿,则是“万国谐和”的景象,到了禹做主儿的时候,似乎也很温和的。否则老人家就不会一边治水,一边根据地形地貌教黎民植桑养蚕、栽种水稻了。大约到了殷商后期,确实有点儿乱道,可资借鉴的就是殷纣王那小子了。他让狐狸精妲己蛊惑的神魂颠倒,根本没把生命当回事儿。尽管如此,也只能判定政治者的残暴,而难以证实整个社会形态就是奴隶时代了。
不可否认:中国是一个讲究等级制度,类别划定很细微,也很森严的国度,这种分门别类的划定,究竟肇始于何年何月?真格无法做出确凿的考据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教九流,”即把整个社会结构层面自上而下,从人之等级到职业类别都悉数囊括、涵盖了。
由此谈及“奴”的产生与具体含义。原本属会意字,即女子抬手取物。后来不知怎么弄的?词义的外延扩大为役使,并因此而演化出了诸多相关的形容词。其实早先的“奴——”并非属于贬词,似乎还有些谦逊的意思。
古代女子对相公自称:“奴家”或“奴婢,”我想大概是那会儿很时兴的一种自我称谓的谦词,绝对不是包括千金小姐在内的那般小女子,自我作践而自取其辱吧?
倘若说“奴”的等级,抑或形态产生,真格的由来已久了,那么早就自觉不自觉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有意无意的坦露或溢于言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奴性”与“奴相”了。
毋庸置疑,每个人的性格里都蕴涵着“奴性”因子。倘若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行为学诸方面做一番考察,即可发现中国人的奴性,不仅十分的浓醇,而且表现也是淋漓尽致的。
国人的奴性,似乎有点儿与生俱来的内质。不仅从远古一直延续到了现如今、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窥见,抑或即时即景都能够淋漓尽致的演绎。无庸讳言,中华民族确实有许多优良的传统文化,可惜一直在时断时续的状态下承传、延续……
事实上,我们确有许多真格优秀的东西,却被有意无意的丢弃或遗失。但值得庆幸的是:唯独“奴性”这玩意儿,始终没有舍弃,并且从古到今都在薪火相传的继承、演绎着。
我以为:国人的这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承传式性格特质,不仅仅是一种人性内质的显形,而是一种文化浸渍、溢泄的表征。说实话,中国文化既有无与伦比的兼容性与十分浓郁的染色性。我们不可遑论:所谓的“奴性”完全缘于这等染色文化,无疑是其荼毒、浸淫的结果。
既然把人划分了那么多的等级,再不断地施加一番“礼”的教化、规范,那么别说那般“学而优则仕”者了,就是那帮一字不识的走卒贩夫和庄稼粗汉,也变得循规蹈矩起来了。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弄得国人很看重同类的等级,并且养成了一级害怕一级的习性。事实上,中国的百姓一直很怕官,同时也很信任官的。不论官说的正确与否?一般都会遵从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奴性”的表现。
早先县太爷升堂,按照程序需先拿起醒堂木猛击一下,意在显示大老爷的威仪与警示堂上的一干人犯,保持肃静而不得随意喧哗,结果没等大老爷开始审问,堂前那伙作奸犯科者本来见了大老爷就吓得浑身哆嗦,猝然听见这么一声巨响,以为大老爷发脾气动了怒,立刻不由自主的两腿发软,“咕咚”一下跪倒在地,一面磕头一面哀告:“青天大老爷哪——小的冤枉……”这番突如其来的动作,反倒弄得大老爷有点儿一惊一愣:“抬起头来回话。”
“哎哎哎、是,大老爷在上,小民确实很冤枉哪——”
普通百姓虽然怕官,然而对皇帝却很尊崇,始终以为皇帝就是天的儿子。倘若不信奉或不顺从皇帝,那就是违天抗命的大逆不道了。假设皇帝驾崩或“不坐龙庭”了,即会出现“如丧考妣”的哀伤恸哭景象。哪怕这个皇帝是个白痴、混蛋,大致也是类似的情形。一旦“真龙天子”现世,不论你是乳臭味干的小儿,还是草莽粗汉,只要登基坐了龙庭,一面是热情洋溢的拥戴,一面是群情激昂的谩骂。普通百姓哩?大致都陷入深深怀念之中了。
事实上,中国民众的心态很复杂:谁做皇帝,以及皇帝好与坏?他们并不甚操心,然而千万不能叫女流之辈执掌了生杀予夺的权柄。一旦如此,不仅朝野上下的骂声不绝于耳,而且永世要落骂名的。即使弄得再好也不行,大致武则天就是例证了。
此外,中国的百姓很爱念旧。时代更迭,即怀念旧朝,执意不与新政为伍。这种情形大致从伯夷、叔齐开始吧?后来这等精神不断发扬光大。最鲜活的例证就是明末清初,以及后来的清末民初,不仅普通百姓受不了,而且连许多文人学士也执意不从。唯有的疗治与自慰方式就是不知就里、稀里糊涂的乱骂。
动辄就骂,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传统。即使人家没招没惹,只要心里不舒服就骂,倘若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做判断的话,那就是“你他妈的”和“王八蛋,”以致从八辈子祖宗上溯到远古时代。曾有文人学士对此做过评判,称其为“人的劣根性”和“民族的劣根性,”然而我觉得这是一种“奴性”释放的形式。
从一般意义上讲:“奴性”的显形与流露,大致迫于强权、暴力或外力作用而处于无可奈何的情态,所做的一种屈从、臣服、以及自救避让的选择途径。人们习以为常的诸般不由自主、即情即景的肆意表现,那就确实需要另当别论了。
集体无意识的“奴性”演绎,大概非清帝国莫属了。当初的情形:不仅至上而下的见了皇帝,均需心甘情愿的自称:“奴才”了,而到了道光、光绪皇帝摆弄朝政那会儿,这种集体无意识,从上而下演绎到了洋鬼子面前。割地赔款、鉴定条约、划定租界——由此涌现了一大批洋奴。
事实证明:洋奴十分可恨也非常危险。不仅在洋人面前有意无意的失却了人格、尊严,而且丢掉了民族气节和国家尊严,最可怕最可恨的是出卖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奴性”本是人性内质使然。人的确应该有尊严活着,不要轻易失却了做人的根本。置身社会、政治、经济多元化的时下,我们确需广泛的交流、学习、借鉴。倘若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失却了人格、尊严,不仅丢失的是个体,而且损害公众、国家、民族利益,以致丧失了国家、民族气节与尊严。
现在的“奴性”演绎,似乎越演越烈而不以为然了。许多鲜活的例证,只能以家乡的描述形式,说“看你那奴样”或“瞅你那奴相。”除此还能怎么样哩?我又没有乱骂的能耐,也没学会骂人的本事。 月夜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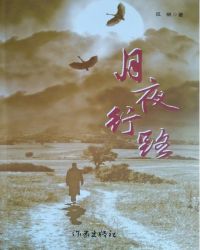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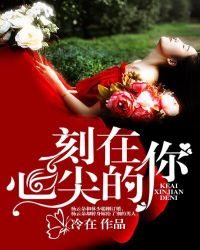
![[柯南]我在酒厂的那些年](/uploads/novel/20210405/2b761df75b9ebaf0b6f829d3a28a7c9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