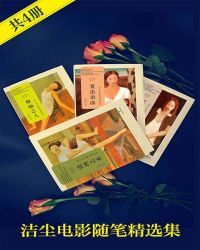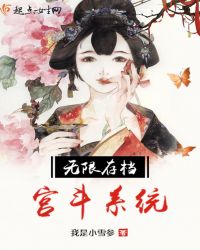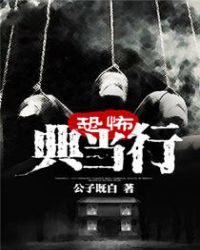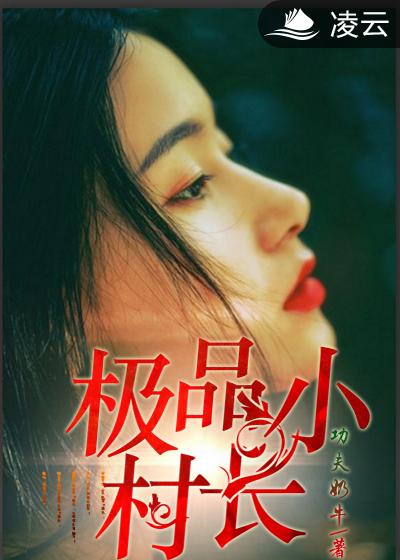当贝利遇到艾丽斯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洁尘电影随笔精选集(共4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当贝利遇到艾丽斯
最近很偶然在深圳的物质生活书吧买到一直想看的一本书,《当贝利遇到艾丽斯》。这是电影《艾丽斯》的原著。大概是五年前吧,刚看完电影,观感十分伤感且柔和,和一个朋友聊,他说,他刚看了英文版原著,很好,很感动。那时我就开始找这本书了。中文版《当贝利遇到艾丽斯》是2006年12月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当我从物质生活书吧的书架上取出仅剩的这一册时,多少有一种众里寻它千百度的感觉。
英文原版的《当贝利遇到艾丽斯》是在1999年艾丽斯·默多克去世之前出版的,当时,她已经进入阿兹海默氏症(老年痴呆症)的晚期了。电影《艾丽斯》拍摄于2001年,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辞世的结局。
书和电影都相当引人注目的首要原因在于,所涉及的两个人物都是当代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作者约翰·贝利是牛津大学文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布克奖委员会主席;传主是约翰·贝利的妻子,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布克文学奖得主艾丽斯·默多克。引人注目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打动人心,但贝利和艾丽斯的故事却把两者融为一体;一方面,两个杰出人物之间的心灵碰撞、生活琐事、个性差别所产生一系列的小插曲,让这个故事有一种清淡温和的英伦喜剧风格,另一方面,这又是一出凄伤动人的悲剧,在贝利和艾丽斯四十三年婚姻的后期,贝利一路扶持着患阿兹海默氏症的妻子,慢慢地走向她生命的终点。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相知、相爱、相濡以沫之后,两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是那么勇敢地对抗绝望和悲哀,实在令人动容。
在电影的开头,是凯特·温斯莱特饰演的年轻娇美的艾丽斯在湖中裸泳,她像一条白花花的大鱼一样在水草间穿梭,湖水有点昏暗,衬得她的白和丰腴格外刺目。这个时候的艾丽斯是牛津大学青年教师中的公主,被众人追捧;她思维敏捷,言辞犀利,生活放浪不羁。暮年的艾丽斯是由朱迪·丹奇扮演,她功成名就,作为一个著名的著有二十六部小说的文学家,她被奖励、访问、讲座、拜会所包围。但,此时的她已经是一个衰败的老女人,矮小、臃肿、满面风霜,那形象,仿佛是对她成就的一种恶意的报复。但这还不够,神可能是太嫉妒她的优秀了——终于,艾丽斯听不懂电视台主持人的提问,然后,她不能写作了;渐渐地,她发音开始出现错误,不会确切表达自己的想法,把dog认作god……终于有一天,她不能认字了,连人也不认识了——老年痴呆症控制了这个昔日视思考和写作为生命的女人。
改编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美化或歪曲。电影中前后两个艾丽斯在外貌上有一种很大的反差,形成了一种戏剧化的对比。其实,艾丽斯本人并没有这样的反差。约翰·贝利在原著中说,当他二十八岁时在牛津大学校园里刚刚遇到三十四岁的艾丽斯时,看到的她是这个模样:五官扁平,一只狮子鼻,一头蓬乱的短发,不修边幅,一条脏兮兮的长裙下面是乱糟糟裹在腿上的棉袜子,两条腿又粗又短。贝利说她“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点性吸引力”。但不知怎么回事,贝利一下子就爱上了艾丽斯,他撇开了艾丽斯的外貌,直接被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智性光芒给俘获了。为此,贝利还因为艾丽斯那“糟糕”的形象而窃喜不已,因为他觉得这样一来,别的男人就不会打艾丽斯的主意了。但事实上,艾丽斯身上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性吸引力,加之其本人在性方面的开放态度,她的风流韵事却是相当多的。这一点在电影中做了如实的反映,在原著中更是一个重点着墨的部分。贝利在这本书中一点不讳言夫妻二人早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扰和矛盾,两人之间的情感也就在这种特殊的磨砺之中,渐渐走向了一种更高层次的交融汇合。贝利在书中有一段话阐释了他和艾丽斯之间婚姻的质地,他说,“显然,我们的婚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奇异的、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阶段——借用澳洲诗人霍普兰的说法,那就是‘渐行渐近却也渐行渐远’。这种分离是亲近的一部分。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它是对亲密关系的一种确认:夫妻之间要想真正相互了解,必须保持心灵上的距离。”
但是,这对知识分子夫妻所保持的智性色彩的婚姻到了晚年终于瓦解了。阿兹海默氏症病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亲人无比强烈的依赖,几步到了寸步不离的地步。贝利和艾丽斯之间多年来分离却又融合的关系转变成了一个大人和幼儿之间的关系。贝利说:“以前,我活在她的心灵之外,就像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受她的生命和创作力影响。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我觉得我们夫妻俩已经融合成一体。有时这会让我感到害怕,但同时却也觉得心安、踏实、正常。”关于这一点,贝利有许多思考和感触,他开玩笑地说,一向“反婚姻”的他们,而今遭到了婚姻的反击。这个观点令人莞尔,也发人深省。
我们在电影《艾丽斯》的后半部看到了一个情景,这个情景原著里没有,是电影的虚构,但这个虚构情景相当出色:衰老不堪的艾丽斯走出了家门,然后像所有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一样迷路了。大雨中,她像一个婴儿一样懵懂无知地走在街上,在车流、人流中惊险万状地游走。她浑身透湿,脚步蹒跚,衣服肮脏凌乱,脸上的表情茫然无措。这个时候这个样子,她比世上无数的潦倒的女人都更让人心酸,她的渊博,她的成就,她那曾经的动人心魄的丰美的身体,她曾经的如花美貌,都被晚年这场凄惨的雨给冲走了。她没有什么可以搭救她自己的东西。
其实说来还是有的,她有爱情。她的丈夫贝利,一个古英语教授,从她年轻时就爱慕并崇拜她。在她还没有得病之前,艾丽斯每次出外演讲,贝利都随行在她身边,坐在听众席上,为她讲的每一句话微笑、迷醉,带头鼓掌。艾丽斯病了,约翰专心守在她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忍受着辛苦、孤寂和绝望。
但是,爱情到了这种地步,可能只对贝利有用,对艾丽斯本人来说,这一切,这伴随一生的爱情,没有任何作用了。她在死去的路途上,她的理智像一盏即将熄灭的灯,在不断加重的夜色里渐渐地暗淡下去。这像是一个昏迷的过程,一个坠落的过程,美好的留恋的一切一点点从手心挣脱而去,人毫无办法地一点点掉下去,掉下去……这样的人生悲剧是如此的巨大和缠绵,它像一大床浸满了水的被子一样覆盖上了观者的心。
好几年前,我是把2002年奥斯卡的两部入围影片《美丽心灵》和《艾丽斯》放在一起来看的。前者是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与精神分裂症,后者是文学家艾丽斯·默多克与老年痴呆症。同样题材同等强度的作品,且同样都是传记电影。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不分高下,只是味道不同,《美》更美国化,《艾》的英国味道很纯正。当然,奥斯卡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美》好过《艾》,所以前者获得了最佳影片。如果让我投票,我也会把那一票投给《美》,虽然我更喜欢《艾》,但是它容易让人蹈入虚无之境,这和社会主流的倡导不太适应吧。这两部电影的区别在于:从对心灵的功用角度看,《美》是上升的,而《爱》是下沉的;但它们的最后都归于一点:灵魂的安详和永恒。这一点也许就是两部作品都入围奥斯卡的基础吧。
艾丽斯的两个扮演者,朱迪·丹奇和凯特·温斯莱特的表演非常出色,她们双双获得了2002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奖,最后她们俩败给了《美丽心灵》中纳什妻子的扮演者詹妮弗·康纳莉。纳什妻子和艾丽斯的丈夫约翰·贝利一样,坚如磐石的爱和水滴石穿的付出;巧的是,扮演贝利的吉姆·布劳德本特因为这个角色获得了同一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两个献身的人得到了奥斯卡的褒奖。在《美丽心灵》中,妻子胜了,她帮助纳什反击了命运;在《艾丽斯》里,丈夫也胜了——在约翰的帮助下,艾丽斯在走进临终关怀医院的时候,已获得了最后的安详。她击退了狂躁和不甘,在理智之光熄灭的前一刻,她接受了命运。
很多时候我们不认命,这是对的。但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要认命,这更加正确。后者也许更需要智慧。电影里,在艾丽斯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她常常在医院洒满阳光的走廊上专注宁静地凝望着在空气中舞蹈的灰尘,她的脸看上去很美,一种放弃的美。我想起了也是因阿兹海默氏症去世的美国前总统里根,那个在彻底丧失理智前向全体美国人民告别的令人尊敬的老人。我相信他在黑暗彻底降临之前也获得了安详。
2007年8月12日 洁尘电影随笔精选集(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