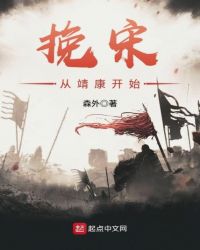内心与外界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泰戈尔精品集.散文卷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内心与外界
早晨,我在船舱中的床上醒来,透过窗户朝外面望去,只见海面上白浪滔滔,海风从西面吹来。侧耳谛听涛声,忽然觉得,有一种看不见的乐器在弹奏乐曲。那乐音不像雷鸣那么洪亮,而是那么舒缓,那么低沉。但是,如同在响亮的锣鼓声中,小提琴的一根弦丝弹出的乐调脱颖而出,在人们心里回响,那舒缓、低沉的乐音,充满天空之心,经久不息地回荡。后来,我试图哼出在心里听见的那种乐曲。可尝试无异于干扰,只会破坏那恢宏乐曲的安谧。所以,我只得保持缄默。
我觉得,晨曦中,大海操动我的心琴弹奏的乐曲,不是风啸和涛声的回声。我绝不能说,它是满天的风声、水声的翻版。它迥然不同,它是一首歌,它的乐音像花瓣,一片片,一层层,缓缓地展开。
可是我又觉得,它不是别的,它就是大海洪亮的心声。这首歌,好似寺庙里萦绕的香烟,向上升腾,充满了天空所有的缝隙。从大海的气息中扩散出来的,在它的外面,是声响,在它的心里,是歌曲。
这固然是内心与外界的联结,可这种联结不是同类之物的联结。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异类之物的联结。两者融为一体,但无从找到两者的相同之处。那是无法表述的相同,是不可观察的、不可证实的相同。
双眼感受到脉动的冲击,心里就看到光亮。身体触及物体,心里产生美感。外面发生的事件,在内心激起苦乐的波澜。前者有形体,可以剖析;后者没有形体,不可剖析。
我们对所谓“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外界,它通过众多声音、气味、接触,通过众多瞬间的思考和感觉,在整个自身中表现出来的东西,那就是我。它不是外在的形象的影子,而在外界的对立中显露出来。
艺术家和文人墨客,急切地想表现世界具象的内在之美。他们立足于模仿所进行的探索,是不可能成功的。许多时候,我们受习惯的制约,我们的感觉是死板的。那时,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当直接看见的表象声称自己就是极致,并对我们做自我介绍时,如果我们承认它的身份,那么,在那种死板的介绍的过程中,我们的心不会苏醒。那时,我们在世界上行走、奔忙、工作,但不能用我们的心接受世界。因为,世界的内在之美,是我们的心灵之物。揭掉习惯的罩布,展示那内在之美,是诗人和哲人的事业。
所以,他们不模仿习见的具象,而是让它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们不把一种具象引进另一种具象,不接受它终极的要求。他们把目睹的物体置于用耳朵倾听的位置,把耳朵听的东西转化为眼睛看的形象。
就这样,他们昭示:世界上的具象,不是永恒的东西,仅仅是形体,进入它的内心,才能从束缚中得到解脱,在快乐中得到拯救。
我们的艺术家谱写了维伊罗比和杜里调的曲子,说:“这是清晨的歌曲。”不过,歌曲中,能够看见对早晨刚刚苏醒的世界的各种声音的模仿吗?一点儿也没有。那么,称维伊罗比和杜里为清晨的曲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艺术家用他们的心谛听了早晨所有声响和静穆中内在的乐曲。如果以内在的乐曲去配早晨任何外在之物,那必然会失败。
我非常喜欢富有印度特色的歌曲。在孟加拉地区,创造了早晨、中午、下午、黄昏、午夜以及雨季和春天的曲调。我不知道,是不是人人认可这些曲调。至少我心里没有感受到,萨伦调是中午的曲调。尽管如此,在世界之主的隐秘的舞台上,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日子,演奏的新曲已飘入我们艺术家的内心。我国的杜里调和卡那拉调显示:表现外在之物的后面,同时也在表现深邃的内心。
欧洲的大作曲家,肯定从不同的角度,在他们的歌曲中,力图传达世界之心的信息。如果了解他们的作品,是可以展开讨论的。起码,在欧洲的音乐厅大门口聚集的听众中听到的零星乐章,在我的心里响起来了。
我们船上的几位旅客,在黄昏时分,弹唱歌曲。当举行这样的演唱会时,我也会坐在音乐厅的角落里。吸引我的缘故,并非我天生喜欢英国歌曲。可我知道,优秀作品总会努力让人喜欢。不经过努力就打动我们的,往往是假货;而积淀下来的那部分,才有真正的趣味。所以,我培养欣赏欧洲歌曲的习惯。当我不喜欢时,我也不会厌恶地将它拒之门外。
船上一个年轻人和两位女士,歌好像唱得不错。我看到,听众听了他们唱的歌,显出欢快的神情。有一天歌会的气氛相当热烈,他们一首接着一首唱了许多歌曲。有的歌表达英国的傲岸,有的歌叙述恋人分手的哀伤,有的歌则抒发情人的痴情。我注意到了演唱这些歌曲的一个特点:不时强化歌的曲调和歌手的嗓音的力度。这种力度,不是歌曲的内在力量,而好像是外在的努力。换言之,它试图通过强化音调和嗓音,更清晰地展露心中的澎湃激情。
这是很正常的。随着心中起伏的激情,我们的嗓音自然而然时而舒缓,时而激越。但歌曲不是对性情的机械模仿,因为,歌曲和表演,不是一回事。如果把歌曲和表演混为一谈,就必然抹杀歌曲的纯正力量。所以当我坐在客轮的大堂里听他们的歌曲时,我老觉得,他们似乎力图显示他们强化了的心绪。
然而,我们不想从外部审视歌曲。情人的感受究竟怎样,我们是无从知晓的。我们想在歌曲中领略的,是那种在内在的感觉中回响的心曲。外在的表现和内心的表现,截然不同。原因在于,外在的激情,在内心就是美。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如同“能媒(能媒,英文为“ether”。)”的脉动和阳光的显露,迥然不同。
我们流泪、哭泣、畅笑,表达心中的喜悦,是很正常的。但是唱悲歌,歌手就挥洒泪水,唱欢歌,就放声大笑,那么,歌坛上的文艺女神,无疑会受到羞辱。事实上,在不流“泪眼”里的泪水和不发出“欢笑”里的笑声的地方,音乐才有魅力。通过人的啼笑,“思绪”在无限中扩展的地方,我们才能懂得,我们苦乐的乐曲折射出所有树木、河流的心音,我们心绪的波澜,是世界的心海的嬉戏。
但是,强化曲调、嗓音,模仿心中的激情,势必妨碍音乐的庄重。犹如大海的涨潮、落潮,乐曲也有跌宕起伏,那是它自身的东西。像诗韵一样,歌曲也有美的舞步。它不是我们心中激情的木偶之舞。
就整体而言,表演较之其他艺术更注重模仿,可它并非纯粹模拟。它接受了通过极为自然的表情之幕的缝隙,展示心理活动的任务。过分注重外部表情,内心活动易被掩盖。舞台上常常可以看到,为了过分显示人物心中的激情,演员刻意强化声调和形体动作。这是因为,不展示真实而只想模仿真实的人,只能像做伪证的证人那样,滔滔不绝地诉说。他没有勇气保持克制。在印度的舞台上,经常可以看见做伪证那样的大汗淋漓的表演。
不过,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我是在英国看到的。我曾在那儿看过著名演员阿尔平主演的《哈姆雷特》和《拉马尔姆的新娘》。看着他矫揉造作的表演,我简直目瞪口呆。过度的夸张表演完全损害了戏剧内容的连贯性,它只有外部渲染,这种对进入内心世界的阻碍,是我前所未见的。
艺术的节制,至关重要。因为,节制是进入内心世界的门户。人生的探索,也是如此。那些想颖悟精神真理的人,必定舍弃一些外在因素,崇尚节制。关于精神世界的探索,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以付出获取享受。对无所不在的梵天的探索,也是艺术的终极探索。所以,以强大的冲击,给心灵以醉汉般的癫狂,不属于真正的艺术范畴。以含蓄的手法,把我们带进心灵深处,是它的真正目标。不要模仿我们看见的东西,也不要用粗笔在它上面涂抹,肆意把它夸大,像哄小孩那样哄骗我们。
以表演的强度冲击心灵,在欧洲艺术中是司空见惯的。总之,欧洲想以一成不变的目光观察现实景物。所以,我们看见的虔诚画面是这样的:双手合拢,昂首望着天空,翻动着眼珠,以外在动作夸张地表现虔诚。印度前往英国学习艺术的学生,对这种表演手法趋之若鹜。他们认为,注重现实,方能达到艺术目的。所以要画那罗特(那罗特,指印度神话中专门挑起争吵的神仙。),他们就画孟加拉剧团的演员演的那罗特。因为,他们的探索,不是以想象的目光进行观察。除了剧团的演员演的那罗特,在别处他们没有见过那罗特。
印度的佛教时代,希腊艺术家曾创作苦修的佛陀的塑像。那是饿得瘦骨嶙峋的佛陀的真实模样,前胸的肋骨可以数清楚。印度的艺术家也创作了苦修的佛陀的塑像,但在他身上没有挨饿的真实痕迹。表现苦修者心灵的塑像上,看不见肋骨的数目。进行艺术创作,不同于医生给一张诊断书,它不拘泥于实际情况,才得以表现真实。死板的艺术家是现实的证人,而高明的艺术家是真实的证人。实物要用眼观察,而真实要用心灵观察。用心灵观察,必须排除双眼看到的东西的干扰;对外部形体,要勇敢地说:“你不是终极,你不是极致,你不是目标,你只是表象而已。” 泰戈尔精品集.散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