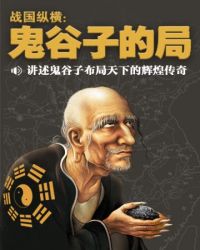“惊喜”的使者——斯普林佐先生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了不起的女孩系列(套装全7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献给马丁
感谢你做我的“同伙”、
冒险伙伴和此生唯一的真爱,
还要感谢你比任何人都更睿智。
·“惊喜”的使者·
斯普林佐先生
“先生,我给您读一下报纸吧?”
微弱的声音挣扎着透过轰鸣的雨声,穿越了过路骡子沉重的脚步声、喘息声以及浸透雨水的帆布在风中的啪嗒声,飘荡在无人回应的集市上。这时,最后几个被淋透的摊贩也放弃了与这阴郁天气做斗争。人们把托盘和篮子挡在头顶,四处奔逃。集市就像咖啡中的饼干一样分散瓦解了。
“喂!先生!我给你们读读报纸吧?”
两个疾行的农夫并没有因此停住脚步,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身边有一个娇小的身影。她所站的地方,虽然不能很好地遮风挡雨,但是至少可以让雨打在身上时不那样猛烈。法院、监狱和治安官的房子上层向外突出,就像三个皱着眉的额头一般。突出部分之下,这具小小的身躯弯着腰倚在墙上,遮挡住几份又湿又皱、似乎饱经风霜的《品卡斯特报》。也难怪这可怜的报纸无人问津,即使在城市里,阅读也是一项鲜有的才能,更何况是在格拉伯雷这座小小的牧羊城镇,这里根本没人识字。
雨水不断冲刷着从市集广场返回的人群、撤走的货摊儿和手推车,只剩下那个如同顽渍般的身影。雨滴顺着她尖尖的鼻头流下,边缘有些磨损的软帽耷拉在她脑袋上,盖住如暴风雨中被掀翻的乌鸫鸟巢般凌乱披散的头发。不合身的橄榄绿裙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腰间,膝盖以下都是厚厚的黄泥。几绺紧贴脸颊的湿发后,一双大眼睛像煤块一样闪闪发亮,凝视着这个集市,眼神中流露出煤的坚忍、幽邃,深处仿佛还燃烧着熊熊火焰。
这具倔强的身躯早已浑身湿透,她瑟瑟发抖,紧咬着牙关。她有名字,她的名字叫作莫丝卡·迈尔。“莫丝卡”的意思是苍蝇。在帕尔皮塔图(阻挡蚊蝇进入果酱和奶油搅拌机的神)掌管的夜晚出生的孩子,用家蝇来命名最合适不过了。而这个名字在她家乡的村庄有很高的知名度。那里的人们对磨坊失火、重犯被释放,以及一只凶暴的大野鹅被盗等事件仍心存疑惑。而在曼德里昂这个西部城市里,有几个消息灵通的人知道莫丝卡的名字,也知道那些闹得这个城市鸡犬不宁、天翻地覆的阴谋、凶杀案、江边之战和革命与这个名字有脱不开的关系。
莫丝卡已经离开曼德里昂三个月了。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冬天悄然而至,她的鞋底已磨薄,双颊变得粗糙,钱袋被掏空,最最重要的是,她对同行伙伴的最后一丝耐心也被磨光了。
“莫丝卡?”一个微弱、抱怨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就像出自一个垂死的老妇人之口,“如果不想让我饿死冻死,你就施点儿魔法吧。卖花的姑娘们叫卖时都尽可能让语调温柔、声音婉转——她们才不会像猎食的老鹰一样尖叫呢。”
这个声音是从监狱墙上一个窄小、装有铁栅栏的窗户里发出来的。莫丝卡向窗内窥视,只能看到一个穿着衬衣的臃肿身躯躺在稻草铺成的床上。这个喊她的男人肥胖的脸上写满了悲痛和委屈,仿佛是他而不是莫丝卡在忍受那样恶劣的天气。他的外套、假发和怀表链都已经卖掉了,只剩下一件打了好多补丁的马甲。他叫艾庞尼莫斯·科兰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曾获得过文学奖。他还是世界上所有吝啬鬼的大克星,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他绝不会自己付账。曾几何时,莫丝卡认为比起在曼德里昂定居,不如和他一起继续旅行。他们志同道合,都喜爱文字、热衷于冒险,并且都与村民们感到疑惑的种种事件的真相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但这些相似点也只能让两个人走到这么远了——似乎只能带他们到格拉伯雷,不能再远了。
“科兰特先生,你有没有可以给我们施的魔法啊?”莫丝卡没好气地厉声问道,“你为什么不施魔法把自己从牢房弄出来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变点晚餐什么的?”
“她嘲笑我,”科兰特嘟囔着,语气里有一种令人恼火的隐忍似的原谅,“这就是她的天性。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和浅陋的灵魂来说,每每碰到了真正的苦难,他们就会对平日里最好的朋友和保护者兵戎相见。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这是命运。”他叹了口气,“女士,你想一下,至少你还有自由。”
“是啊,外面真的好极了。”莫丝卡怒视着她自由世界中阴沉的天空,“如果再自由一点儿,我可能早就染上流感了吧。”
“或者,”科兰特接着说,语气里带有一丝幽怨,“你可以想一下我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毕竟当初是你坚持要带他来这座可恶的小镇。”莫丝卡做了个鬼脸,不过不幸的是,科兰特说的确实有道理。如果不是因为她,萨拉森就不会跟他们一起来了。在莫丝卡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里,萨拉森是身为孤儿的她唯一的伙伴,所以她也带他一起逃离了那又潮湿、又令人伤心的家乡。之后,莫丝卡还否决了科兰特要把萨拉森卖掉、丢掉,或引诱到装馅饼的盒子里等所有想法。一般情况下,莫丝卡会给萨拉森戴上口络、拴上皮带。可是在他们到达格拉伯雷的第一天,一个可笑的旅馆马夫犯了一个错误。按照他的逻辑,如果一个动物摇摇摆摆、走路看起来很滑稽,那么他肯定是无害的,如果他无害,那么即便摘掉口络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科兰特因无力偿还萨拉森对那个旅店造成的损失而被送进了监狱。那个马夫,不知怎么回事自己也受伤了,被带走的时候要求给萨拉森戴上枷锁(根本卡不住他的翅膀),并且要求当众鞭打他(似乎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当市民们鼓足了勇气,搜罗了一大堆又长又尖的武器时,萨拉森早逃到乡间去了。
自那时起,萨拉森就“声名鹊起”。然而那个“名”并不是“萨拉森”。的确,人们说起他时更多的是“那只地狱之鸟”,“你看见他对我的腿做了什么吗”,“杀了他杀了他,他往那边走了”,或是“那只鹅都做了些什么”之类。每次当莫丝卡通过乞讨、小偷小摸或给别人读东西赚足了可以赔付科兰特债务的钱后,又会有遍体鳞伤的农夫一瘸一拐地去城镇举报,或称房顶被毁或言骡子被惊,然后科兰特又要为萨拉森的所作所为承担一切罪责。最后他们发现,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如果我能赚钱我当然会去赚啊,”科兰特接着说,语气里还带着刚才那般的伤感,“但是现在文具店不买我写的诗了……我能怎么办呢?”
尽管没有人明说,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在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强大的行业协会,它们代表了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职业和手艺,把这个国家凝聚在一起。令人敬畏的文具店协会控制着这一带所有书籍的印刷,它们的人还会烧毁所有他们认为危险的书籍。大多数人都愿意把这个事情交给他们去做,因为人们相信读不好的书会使人变疯。两害相权取其轻,显然文具商是比较轻的那一害,尽管它有可能为了纠正你的语法而烧了你邻居的家。科兰特曾为文具店当间谍,就是在他们的命令下,科兰特才紧跟着莫丝卡一路奔波到曼德里昂。然而,文具店协会并没有命令他去帮忙推翻这个城市的政府,因此他们在知晓莫丝卡和科兰特参与了曼德里昂革命的事情之后勃然大怒。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他们拒绝买科兰特的任何作品,哪怕是打油诗,这充分表明了他们的愤怒。
“如果你们不让我的手写东西,为什么不砍掉它呢?”科兰特不停地抱怨,“如果你们不让我的脑袋做梦,为什么不砍掉它呢?”
“不要以为他们没这么想过,科兰特先生。”最终他得来如此简洁的一个回复。
莫丝卡的情绪在想起所有这些事情后并没有什么好转。眼下,莫丝卡拥有的最有销路的商品就是她的眼睛——格拉伯雷只有她和科兰特两个人识字这个事实。在格拉伯雷,报纸通常没有什么地位。而邻近城市要求把他们的告示和通缉令贴在这里法院的门上,当然上面写的是什么居民们都不认识。因此,在过去的两周,莫丝卡每天都会站在广场上为人们提供读报、读信、读通缉令和小册子的服务,每次只要一便士。大家都怕书,但莫丝卡却对书有一种近乎热切的渴望,不过目前她大部分清醒的思想都被一种更加寻常的、对食物的渴望所占据了。
当然,许多人都对《品卡斯特报》很感兴趣,想知道更多关于曼德里昂这个古怪的造反小镇的消息。在那里,一个改过自新的强盗率领人民推翻了当地的公爵,他们反抗的队伍在周边强烈的反对之下依然屹立不倒。不幸的是,在叛乱发生的一周后,小镇里没有一个人听到报纸上有关这件事的报道,于是莫丝卡就开始编造故事,现在她害怕人们已经对此有所察觉了。
“再喊一声试试,这次喊得稍微温柔一点儿……”
“这儿根本没人好吗!”莫丝卡爆发了,“这可恶的街上连个人影儿都看不着!没有人想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了!我这是在向讨厌的鸽子们卖消息!这儿没人——哦,等等……”
一个男仆从法院里走出来,他一脸疑惑地盯着手上的告示,然后把告示倒着贴在了门上。当官方告示和法令被送到格拉伯雷之后,当地的治安官就会让人把他们按规定贴在法院门外,尽管他对其中的内容一无所知。
“先生!先生!我把内容读给您听吧?先生!只要一便士!”
男仆看着她,撩开挡住眼睛的湿发。
“好吧。”他把一便士抛给莫丝卡,“只说大意,利索点儿。”莫丝卡倾斜了一下身子,这样她的脑袋几乎就倒转过来,她顺手抓紧头顶的帽子。
“这是个……”不同于莫丝卡身上的其他地方,她的嘴里突然变得很干,“这是……这是个关于桌腿税收的通知。”
“桌腿!”这个男人骂了一句,竖起衣领,“我就猜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一边朝街上走一边喃喃自语。
莫丝卡转身去看告示,她睁大了眼睛,脸色煞白。其实,上面的内容是这样:
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因涉及三十九桩案件被通缉,其罪行包括诈骗、造假、销售传播未获许可的下流文学、声称自己是公爵没有钱的儿子、假扮治安官、假扮兽医、毁约、四十七次未付债款潜逃、盗取神龛、在法庭审判前潜逃、从窗口偷馅饼、从旅店偷家具、为牟利制造帕尔斯洛浦特大马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演奏手风琴等。不建议大众将钱借给他、从他那里买任何东西、租给他屋子或相信他说的任何话。他不像他所从事的职业身份,等他付给你钱只会遥遥无期。
艾庞尼莫斯·科兰特在监狱里透露了他的真名。这是不可避免的。
没人会谎报自己的名字,尤其是怕惹恼了他们的布拉维德守护神。布拉维德是一些小小的神灵,每个人都相信是他们让世界运转、让云彩飘浮、让母鸡下蛋,并把小孩儿眼里的灰尘清除。因为有太多的布拉维德,如果让他们每一个都掌管一年中的一整天是绰绰有余的。因此每一个守护神都只能将就地掌管白天或黑夜中的一小段时间。如果你出生在某一个布拉维德掌管的时间段里,那么这个布拉维德就会成为你的守护神,你也会得到一个与守护神相关的名字。每个人都同意人如其名这个观点,名字显示了你注定的、神赐的天性。谎报名字就像扇你的守护神一巴掌或把一个新的灵魂粘到你的身体上一样,让人不敢想象。
科兰特的名字是“艾庞尼莫斯”,因为他生在方加沃特(捋平讲故事者的舌头和构建传奇事迹的神)掌管的时段。尽管科兰特能恬不知耻地假扮从高级警察到刺猬的各路角色,他也不敢对自己的名字撒谎。因此,早晚会有另一个识字的人出现在格拉伯雷,看到这个告示。他可能会把内容大声地读出来。
“哦,我的天,”莫丝卡嘟囔道,“我们完蛋了。”
然后,她突然想到,只有科兰特一个人会完蛋,船沉的时候她不一定要在船上啊,这个念头不断地出现在莫丝卡的脑海中。
她沿着墙根一路向东跑去,轰鸣的雨声淹没了她脚上木底鞋撞击鹅卵石的咔嗒声。城镇很小,没用多久她就跑到了头。一出城,道路便变得泥泞不堪。一座座房子向后退去,她气喘吁吁,不停打着喷嚏,目光望向前方那条光秃秃的土路,它像布条般穿过灰色的荒野。
路的两侧是一些格拉伯雷的布拉维德雕像,像夹道欢迎的不整齐的队伍似的。这些布拉维德雕像由木头砍削而成,被水打磨光滑,呈现出深红色。其中,格雷格罗里手里拿着剑,哈弗帕斯挥舞着六分仪,汤伯里斯打着鼓。
今天早上是安博里泽尔女士(防止肉变硬变质的神)掌管。而每年今天从中午到黄昏的这段时间,属于斯普林佐先生(把冰水滴进衣领里或把珍珠放进蚌贝中的神),他负责为人们带来“惊喜”,不论好坏。不知是谁把一个编得很粗糙的树叶环戴在了他的脖子上,以表明这是属于他的时间段。
像其他人一样,莫丝卡也从小信奉布拉维德神。她的内心习惯性地提醒她要表现出对这些小小神灵的尊敬,以避免或大或小的灾祸。但是,她天性暴躁、叛逆,做事讲求实际,总是想着:“如果我不尊敬他们,会发生什么呢?”
莫丝卡的妈妈在生她的时候死了,因此莫丝卡只记得她的爸爸,奎拉姆·迈尔,一个勤奋而坚定的人。他在莫丝卡八岁的时候也去世了,让她成了孤儿。在一些人的印象里,奎拉姆·迈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英雄。他曾和残暴的布尔德凯其尔斯(在他统治下的几年充满了血腥暴力)进行英勇的决斗。然而,他后来撰写的书中那些他对于“平等”疯狂而激进的观点中见证了他被流放异乡、在乔夫那个穷苦而偏僻的小镇度过余生的岁月。他的女儿也在那里出生长大。莫丝卡的童年生活一直充斥着村民对她父亲的种种猜忌。如果乔夫的村民们知道奎拉姆·迈尔的全部观点,那么他们可能在他踏进这个村子第一步时就把他烧死了……因为奎拉姆·迈尔一直是一名隐秘的无神论者。
自从莫丝卡发现父亲坚持无神论以来,就开始谨慎地停止对布拉维德雕像点头哈腰,不再背诵祷告词安抚它们或在它们袖珍的神龛里供奉祭品。尽管这样做了,但她似乎并没有被雨水淋得更湿,她的牛奶也没有加速变质,她遇上狼群袭击的概率也没有增大。
因此,当她坐在斯普林佐先生雕像上那又宽又平的脑袋上来思考她的境遇时,没有感到一丝不安。她掏出一个木制烟斗,不往里面放烟草也不点燃,只是气愤地嚼着烟杆。这是她很久以前就形成的习惯,每当她需要整理思绪的时候,就会这样做。
我和科兰特没什么关系了——这次彻彻底底地没关系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找到萨拉森,然后让那个没有一句真话还不知感恩的老家伙自食其果。
但是她能跑到哪儿去呢?到西边,回到曼德里昂?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她在那里倒是有朋友……但是在那场革命之后,一伙有权有势又异常危险的人已经明明白白地警告过她、科兰特和萨拉森,让他们必须离开曼德里昂,终生不能再回来。除此之外,即使她现在赶往那座城市,她也有可能永远无法到达那里。据说那座城市的周边已经变成了战区。
一个月前,所有和曼德里昂毗邻的大城市都急匆匆地下达了新法令,禁止任何人和那个造反的城市进行贸易。他们的想法是把那里的人都饿死,但是事实上,这意味着所有像格拉伯雷这样需要通过与曼德里昂进行贸易来维持生计的小城镇的市场上卖的东西大幅减少,粮仓也日渐空虚。因此一些人心想,在曼德里昂本地也许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地从自己的镇上逃离,加入造反的队伍。现在,许多城镇都派遣了差役和其他执法人员,去荒野中搜寻那些想要逃去曼德里昂的人,时刻准备把他们抓进比关科兰特的牢房还要恶劣千百倍的地方。
她能在附近北边或南边的哪个城镇里度过这个冬天吗?不太可能。很快树上就没有苹果可摘了,人们的好脾气和慷慨也会因寒冷而消失殆尽,这样也就没有人会付钱让她读报纸了。通晓消息不会比吃饱肚子更重要。苍蝇们一般都去哪儿过冬呢?
“它们不过冬,”莫丝卡嘟囔着,眼眶盈满泪水,“它们到那时候就死了。嗯,先不管那么多了。”
她要向东走,要穿过那条“不可跨越”的河流——朗斐泽尔河,它波涛汹涌,穿过峡谷,从高山奔流入海。她将跋涉至衫德琳,或者威梅勘姆,人人都说在那里生活相对容易一些。可她要怎么穿过朗斐泽尔河呢?唯一横跨它的桥梁由托尔小镇控制,可是没有人能不交钱就过桥,当然这个钱她是交不起的。
……不过也许她可以再从陌生人身上赚点钱。
莫丝卡回头向城镇的边缘眺望,她看到一个在破旧牲口棚里躲雨的身影,晶柱般的雨水从浸湿的茅草屋顶倾泻而下,半掩住那个身影。他很高,肩膀微微耸起,好像外套勒得太紧似的。他正招手示意莫丝卡过去。
莫丝卡犹豫了一下,收起她的烟斗,一口气冲进牲口棚,然后连忙把打湿的头发从眼前拨开,仔细打量她的新“朋友”。
他面如刀削,鼻子略长,给人一种异常安静的感觉,这让莫丝卡想到了池塘边的鹭,静静地等待时机,只要脚下的鱼稍微迟钝一下,就立刻变身长满羽毛的标枪,朝鱼刺去。
“你认字?”这一问题深沉而严肃。
“嗯,您想让我读报纸吗?我这里有……”莫丝卡勇敢地挥了挥手里早已湿透的报纸糨糊。
“不,不是读报纸。跟我来,我想让你和我的朋友们谈谈。”
莫丝卡跟着他进了旁边一个棚子,眼睛扫了一遍这个陌生人的穿着打扮:发霉一样颜色的外套、精致的靴子、饱经风霜的帽子。她的心开始激动地打起了小算盘。当然,她可以跟这个男人和他的朋友多要些钱,但是要多少钱才不会让他们感觉要得太多呢?要多少钱才不至于让他们满心厌恶地离开而是跟她讨价还价呢?
后一个棚子里有四个男人坐在稻草堆上,其中一个正拿块湿方巾擦他的领子,另一个正用力拧干他的帽子。当莫丝卡和她的“向导”进来的时候,这几个人全都望向他们。
“这就是那个女孩儿,斯凯罗先生?”一个语气刻薄的男人问道。
“就是她,”带她进来的男人回答,“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莫丝卡。”好了,现在他们都会像盯苍蝇一样看着她,觉得她吃残羹剩饭,或是能在天花板上走。这是没办法的事。没人能谎报自己的名字。
“在我看来她可不像是一个学者,”那个刻薄的家伙说,“这是个骗局。她认识的字可能还没我们多。”
“我能证明给你们看!”莫丝卡怒气冲冲地喊道,“找几个单词来,我读给你们听!或者我可以给你们写几个!”
“过来,格莱普。你认识几个字母对吧?”
那是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戴了一顶无檐帽,看起来鬼鬼祟祟的。“我只认识我的名字。”他冲着自己的衣服领子自言自语道。
“把字写在地上,我们来看看她会不会读。”
留络腮胡的男人跪下,用食指在土和稻草碎末上写了几笔。
“你叫本,”当他写完字,莫丝卡脱口而出,“但是你的字母B写反了。”
几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她确实认字。”斯凯罗说。
“下雨天得付我更多的钱,”莫丝卡哆哆嗦嗦地补充道,“你知道的,因为这是比较特殊的服务,我得冒着被洪水淹死、弄坏衣服,和……和得胸膜炎的风险。”她乐于看到自己说出的生僻词带来的效果。
是的,我得要更多钱,尤其是对这种穿着好靴子,藏在镇子边上的牲口棚里而没有跑去住旅馆的人,哪怕他们现在淋得比鲱鱼还湿。尽管你遮遮掩掩地,但是我还是知道你有个很重要的东西需要别人给你读,斯凯罗先生,你给我钱,我就给你读。
“要多付多少钱?”斯凯罗问。
莫丝卡张开嘴,犹豫了一下,她估计了一下自己能赚到钱的概率,不由得加快了呼吸。然后她的眼睛对上了斯凯罗的目光,不自觉地说出了能付清科兰特债款的金额,她稍微加了一点儿价,以防他会讨价还价。
一阵让人心惊胆寒的沉默过后,其中一个男人咳出一声冷笑,但是没人动手把她扔出去。
“你肯定,”斯凯罗冷冰冰地说,“非常,非常害怕得胸膜炎。”
“我一家人都得了。”莫丝卡马上回答。斯凯罗盯着她看了很长时间。
“好吧。”他说。
莫丝卡的眼睛变得又大又亮,为了不让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她努力克制,弄得脸颊生疼。她成功了,她唬住他们了,她感觉所有的难题好像手铐咔嗒一声解开又哗啦一声落在地上一样,全都解决了。
斯凯罗把手伸向别在腰带上的钱包,犹豫了一下:“我只是付你的钱,对吗?别等我给了你钱,然后发现你还有,哦,一个主人,或是挨饿的父母,又或者是染上胸膜炎的兄弟姐妹,然后又要给钱?”
莫丝卡突然想到了科兰特,她对自己把科兰特当作“主人”的这个想法愤怒不已。
“没有,”她恶狠狠地叫道,“没有别人了,只有我,我没有其他人需要担心了。”
“很好。”斯凯罗说。他边说边微笑着,尾音发得就跟用石头在窗玻璃上刻字似的。他的嘴角高高扬起,在两颊各处形成条条沟壑般的皱纹,露出窄窄的一排牙齿。这是一张不经常展露笑容的脸,因为笑得并不熟练。
然后,一块布猛地蒙在了莫丝卡脑袋上,把她淹没在黑暗中,几乎让她窒息。那个微笑是她在这之前眼前的最后一个画面。 了不起的女孩系列(套装全7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