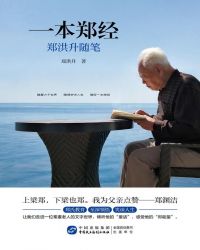法然院随想一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一入再入之红:日本文学行走随笔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法然院随想一
故居
二十多年前,我在我的第一本书《艳与寂》里,有一篇随笔叫做《谷崎润一郎,独自开放》。在那篇文章里,我说,谷崎的作品于我“是一种刺痛”,“疼痛瞬间袭来,又在瞬间逃遁得无影无踪”,按他自己的意象描述是“无人之境中悄然开放的樱花,使人油然感到一股妖气”。
在二十多年的写作中,我曾经多次在文字中感谢过谷崎润一郎对于我的影响和作用。他的阴翳美学不仅成为我美学立场的出发点,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构成了我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和角度。
多次到京都。但对于谷崎润一郎墓地的探访,2017年11月底才一了夙愿。
1965年,一代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逝于神奈川县汤河原吉滨的湘碧山房,享年七十九岁。葬于京都法然院。
三岛由纪夫在悼文中感叹,日本文学的一个时代因之而结束,后世若将谷崎润一郎迄今为止这六十年的文学概括为“谷崎朝文学”,倒也不足为奇。
我在查阅谷崎润一郎故居这个主题时,着实被弄得眼花缭乱,一头雾水。这位被称作“搬家狂人”的大作家,一生著作颇丰,但究其根底竟然也是因其为过于丰富的私人生活所逼迫,多次离婚,多次搬家,且家居要求考究,于是乎狂写不止,所获的丰厚的稿费收入,也就紧随其生活要求,彼此求个扯平而已。
这里扯白两句。对于某些作家来说,自主的动力毕竟是有限的,若没有一些旁逸斜出的刺激,很难保持一种持续的创作动力。若无个人生活的鸡飞狗跳乃至焦头烂额,比如谷崎润一郎和女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债务、卡佛与酒精……也许我们很难看到好些伟大的作品呈现出来。
谷崎润一郎的生活高调且奢侈,其宅邸曾经因为无法缴纳税金而被没收。他的每一处豪宅似乎都处在一种财务危机中,这也是他经常搬家的一个原因。让人钦佩的是,他真能过一天享受一天,并悠闲淡定地礼赞着阴翳。
现在我能查到的著名的谷崎故居,有位于神户市东滩区住吉东町的倚松庵和位于京都市左京区下鸭泉川町的潺湲亭(后被称为石村亭)。
谷崎在倚松庵的居住时间为1936年至1943年,宅名灵感来自其第三位夫人松子。在这里,谷崎开始了长篇小说《细雪》的写作,四姐妹所在的大阪落魄豪门莳冈家的场景描写,其素材几乎均来自倚松庵。
1949年至1956年,谷崎搬迁至潺湲亭,其晚年作品《少将滋干之母》中,有对潺湲亭庭院和居住环境的借用性描述。
谷崎最后居住的湘碧山房,不太清楚其形貌,但估计也不会降低多少标准。
墓之空与寂
我没有探访过谷崎润一郎的故居。我去过好几次京都,也没有打算去探访潺湲亭,这座宅邸现在是日新电机公司的产业,好像除了特定的时间不对外开放的。
但我很早就知道谷崎润一郎葬在了京都的法然院。
在其最后的小说《疯癫老人日记》中,男主人公,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从东京到京都,为自己选择墓地,最后选中了法然院。“法然院现在在市中心,市营电车就从旁边经过,疏水樱花盛开的时候尤其热闹。但是只要一进寺院,便异常肃穆,使人心情自然而然平静下来,这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
在小说中,老人说不喜欢用常用的花岗岩做墓碑,想采用松香石。说到墓碑的式样,他说不喜欢千篇一律的长方形,在石头上刻上法名或俗名,下面垫上底座,底座上面凿出放香和洒水器皿的圆洞,这个模样太俗气了。他想要的是五轮塔式的,或者带观音像的,观音的模样就做成跟他所迷恋的儿媳妇飒子的模样有点类似,别人看不出来,但睡在墓地下面的色老头儿自己知道,且美滋滋的。
空与寂。法然院的谷崎墓地。
2017年11月29日,我来到了法然院。
同行友人朱艳宁每天都要在其公号上发布日志,她在这一天的日志上写道:
藏在银阁寺后面的法然院安静朴素,在夏日,穿过密不见光的树荫,我来过,一个人在院子转了半天,喜欢得不得了。没想到,安排这次行程时,洁尘说我们去法然院吧,谷崎润一郎的墓在那儿。于是,这个秋天,阴天微雨中又来到法然院,依然朴素安静,连浓烈的金秋在这儿都变得清淡雅致了,只有鹅黄的树叶和绿色的树叶穿插呈现,和这个微雨的天气甚是和谐。我稍微能明白了为什么谷崎润一郎要把自己的墓地选在这儿。
我和洁尘在寺院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墓碑。当然,不会甘心,正好遇上一位妇人,洁尘用手机写了谷崎润一郎的名字前去询问,妇人秒懂,告诉了我们墓地的所在。
站在法然院公共墓地入口,远远望去,墓地规模不算小。洁尘冲在前面,埋头找着。我说,分头找吧,看缘分谁先找到。于是大家散开来,我和洁尘向上走,凭感觉转向山坡旁,稍微偏僻的地方,远远看到两块天然形状的石头,稍微走近能看到上面的字“空”和“寂”。就是这儿了,我大声对洁尘说。洁尘不说话,静静地看着墓地,神情端肃。我对她说,你简直就是一个迷妹嘛。她沉吟一会儿说:对,我是他的迷妹,他是我的大偶,迷了他二十多年了。
我要补充描述一下谷崎墓地的形貌。
一块长方形的平整的墓地,分立着由两块天然的石头做成的墓碑。(不知道这种石头是不是就是谷崎在《疯癫老人日记》中心仪的松香石?)面对墓碑,右边的石头上刻着“空”,左边的石头上刻着“寂”。“空”和“寂”,都是根据谷崎的手书铭刻的,都有“润一郎”的落款。“空”墓是谷崎夫人的妹妹重子夫妇的合葬墓,“寂”墓则是谷崎润一郎和夫人松子的合葬墓。两块墓碑之间是一棵垂樱,初冬时节,枝条萧索但舒展有致,可以想见这棵樱花在春天开花的时候那柔美多姿的形貌。围绕着整个墓地的,是用一种秋冬时叶色呈浅金红色的小灌木做成的矮墙,或者说是小隔离带,与石头的质地和颜色相比对,这些小巧的红叶显得相当的娇俏。我不太清楚这种灌木叫什么,有机会的话,我得向人请教一下。
查了一下资料,说是谷崎墓背靠大文字山,面向京都大学旁边的哲学之道,左边邻近银阁寺,右边邻近南禅寺。这块墓地如此这般被四周优美有品的风物所包围,跟谷崎润一郎先生一辈子讲究的派头相得益彰。
艳宁在日志里说我“静静地看着墓地”“神情端肃”。那时,我其实什么都没想,心境安静柔和,但又相当空茫,似乎只有一种幸运感充溢心间。藉由文字这个媒介,读者和作者之间被冥冥之神选中彼此达成了一种缘分,这种缘分超越了世间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的阻碍,非常深入,非常亲切。对于谷崎先生来说,我只是他的一个读者,而且还是异国读者,但我相信,我的存在和他的存在之间,也有一种微茫的联系。对于我来说,茫茫书海,与这个作家相遇对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多年来一直积蓄的感谢之情,如今在他的墓前有了一个仪式化的交代。
这种仪式化,没有任何外显的表达。一切都在心里,足够了。
夜宴夺美
谷崎润一郎在旅途中不写作。他经常在上午写作,而且必须穿戴整齐。对他来说,包括阅读也是正襟危坐的效果更好。日本的稿纸和中国的稿纸一样,四百字一页。一天写三四页,算下来也就是一千多字。
我也是这样的写作者:在家时上午写作,旅途中不写作。写作和阅读时穿戴整齐、正襟危坐,平均下来每天差不多写一千字。
写作的辛苦往往只有同业者才深有体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看到同业者的写作习惯跟自己近似时,就会有一种特别会心的感觉。
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于东京。其中文译者之一吴树文说,“谷崎润一郎出生于东京的日本桥区,父系、母系都是所谓的‘老东京’,日本桥一带又是三百年来江户文化的中心基地,遂使这位纯粹的‘江户儿’文学上显现出都市性固有的唯美色彩。”
谷崎润一郎幼年养尊处优,因父亲不善管理祖业,优裕的家境在其小学二年级破产衰落,但自出生开始习染的考究习气伴随了谷崎一辈子。1908年,谷崎润一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开始发表作品,后被永井荷风发现并赏识,大力提携,由此登上文坛。关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有一段著名的评论,“(谷崎润一郎)是开拓了明治以来无人染指、也无法染指之艺术领域的成功者”,其表现有三大特点:肉体性恐怖导致的神秘幽玄,悉为都市性情趣,文字无懈可击。
在我看来,肉体性恐怖导致的神秘幽玄,特别体现在其代表作品《春琴抄》和《少将滋干之母》中,前者有春琴毁容后,佐助自刺双眼让春琴安心的情节,后者有国经为忘却被藤原时平夺走的娇妻,夜赴郊外坟地修不净观的描述。二者都是十分骇人的篇章,但在谷崎的笔下,却在骇人之中呈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神秘幽玄之气。
要说谷崎之神秘幽玄之气,于我来说最深刻的阅读体验,是《少将滋干之母》中“国经佯醉献妻,时平顺势掠美”(这个章回名是我自己拟的)那一幕:
酒宴上,七十九岁的国经大纳言假装烂醉如泥,当着满座公卿的面,把年轻的妻子当礼物送给了左大臣藤原时平。夫人在幕帘后面,“国经将手伸进帘中,帘子的中部便凸起来,露出了一个和服袖口,紫色、深红色、桃红色,在灯光下显得五彩缤纷,那是夫人身穿衣服的一部分,那样从帘中的空隙露出的光景,宛若万花筒里耀眼的色彩,变化得叫人眼花缭乱;又像一大朵罂粟或牡丹花瓣在摇曳。接着,一朵真人大的锦簇花团终于露出了半身……”
时平如梦初醒,一把抓过女人,拖拽出来,半拖半抱,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中,径直朝外走去,“她左臂搭在左大臣右肩上,面部深深地俯在左大臣的后背上,软不拉塌,不象个活人,但又是用自己的脚在走路。刚才从帘内露出的五彩缤纷的衣袖和衣襟与那拖地的长发纠缠在一起,在地板上拖着行走,左大臣的衣服和她那五颜六色的衣服连成一团,刷刷地响着走下台阶。……”
这段描写的最后,时平将大纳言夫人拖抱至车内,车子行将启动,纷乱之中,有一个人把夫人拖到地上的外袍的一角给塞进了车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就是时平的情敌平中。跟时平一样,平中也是平安早期著名的风流贵公子,有才有貌,女人缘丰沛,留下了很多花花草草的逸闻,这个人物后来在《源氏物语》里还被光源氏在与紫姬的闲聊中拿来打趣。这是另外的故事了。
我设想《少将滋干之母》中的那一幕,黑夜中,一个忧伤的男人将一团艳丽的锦缎衣角塞进车门,该是怎样的一种凄清艳丽的心境?拍成电影的话,前面那个帘中扯出和服袖口和后面这个往车内塞衣角的细节,想必都相当出彩。
以女人彩衣的一个局部来呈现美艳残酷的恋情之争,谷崎润一郎的手法实在是高妙。
香气袭人的一方深涧
最近重读《少将滋干之母》时惊奇地发现,这完全就是一部从没读过的小说啊。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那一次的阅读留下的唯一记忆就是“无人之境中悄然开放的樱花,使人油然感到一股妖气”这个意象了。
当然,我还是得说第一次对这部小说的阅读非常有效,而且是特别有效。无人之境的樱花与妖气之间的那种神秘的牵绊和联系,这种独特的审美意境,对于我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这句出自《少将滋干之母》的结尾,滋干少将在音羽川无意间寻访到母亲的那段。樱花的上空是雪白的月光,这种月光仿佛雪光一样,土地是湿漉漉的,空气是凉丝丝的,天上有一点淡淡的云影。那是“香气袭人的一方深涧”。
这次的阅读,我又发现了一个相当厉害的情节:在《少将滋干之母》中,左大臣酒宴上抢夺大纳言之妻的故事相当惊人,人物心理重峦叠嶂。女主角是在原业平之女,身份高贵。两个男主角平中和时平(左大臣)之间的情场角力也很精彩。平中对在原夫人重燃恋情的那一幕描述,会让人联想到三岛由纪夫的《春雪》,清显少爷对聪子的恋情也是在聪子即将嫁入皇室时重新点燃的。
谷崎润一郎是一个色情受虐狂,终生喜爱坏女人,迷恋各种伤害带来的痛楚。关于谷崎的情爱故事,有很多文章加以梳理和阐释,对谷崎润一郎其人其文有所了解的读者,想必耳熟能详。行文至此,我就大概地八卦一下。
谷崎润一郎从二十多岁开始就有一种奇异的爱好,要找一个娼妇型的女子做妻子。他迷上了一个艺伎,名叫初子。但初子已经有人包养,于是就把自己的二妹介绍给了谷崎,这就是谷崎的第一任妻子石川千代。千代生下了谷崎唯一的孩子,女儿鲇子。千代夫人十分贤良,让谷崎大失所望,他看上了初子和千代十五岁的三妹圣子,于是把千代打发回老家,自己在东京和圣子半公开同居,这段培养少女的经历,被他写成前期的代表作《痴人之爱》。想知道圣子是如何把谷崎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可以读一读这部小说。
谷崎对温顺的千代十分厌恶,多次在小说中臆想杀妻的情节。他想甩掉千代,同时又觉察自己负有责任,得确定好她今后的生活,于是撮合他的好朋友、著名诗人佐藤春夫与千代相恋。三个人之间纠葛不断,分分合合长达数年,最后三人达成协议,谷崎对外声明:“千代和谷崎离婚,与佐藤结婚。谷崎家的住房让给佐藤和千代,女儿鲇子由千代抚养。”当时谷崎住在神奈川县的小田原,这件事被称为“小田原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被当作文学家道德败坏的例证。
在和千代夫人关系冷淡期间,谷崎一直出游在外,一次在别人招待芥川龙之介的宴会上,他认识了慕名前来拜会芥川龙之介的根津松子夫人。根津夫人出生于大阪的富豪之家,但是当时已经结婚并生儿育女。谷崎对根津夫人十分仰慕,随即追随迁居京都,与根津夫人做了邻居。谷崎的长篇代表作《细雪》里面提到的大阪富豪之家的四姐妹,原型就是根津家族。
在渴慕根津夫人而不得的几年中,谷崎在1930年与千代离婚,第二年与一位二十岁出头的文学女青年古川丁未子结婚。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之后松子离婚,谷崎在四十九岁那年与三十二岁的松子结婚,从此有了终身的伴侣。
谷崎创作风格的转变,跟根津松子有很大的关系。在此之前,作为东京人的谷崎,家境优裕,就读东大外文系,十分崇尚西洋文化。追随根津松子搬迁至京都之后,谷崎反过头来对日本文化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形成了自己关于日本美学独特的阐释。
阴翳礼赞
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是我的案头书。常常翻阅。
在《阴翳礼赞》中,他主张文学语言的暗示性、抽象性,“在文学领域里,唤回渐渐失去的阴翳世界,把文学殿堂的屋檐加深,使墙壁幽暗,将过于显眼的器具放置暗处,取下室内无用的装饰……”
《阴翳礼赞》是谷崎后期的作品,是其端详的对象和审美的视角发生重大转变之后写作的内容。作为昭和早期文人,年轻时的谷崎,在欧美文明的强光照耀下相当亢奋,艳羡之意的表达,生猛且喜剧。他在中年之后回头凝望自己所属的文化,发现了阴翳世界的趣味和美感。这个转身,这个回头,这种在强光的映照下才能显现的幽暗,让谷崎的美学呈现有了层次,有了景深,有了路径,有了跋涉的艰难和顿悟的欣悦,因此特别动人。
在很多年前,感悟谷崎之阴翳的同时,他所赞同的斋藤绿雨的一句话对我也深有触动,“风雅就是寒”。这句也译作“风雅就是清冷”。于我来说,这个意象直接触到了我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本质,我对和缓、淡漠、回避、寡言的迷恋也有了温度这个层面的美学支持。
记得在二十五年前,读了《阴翳礼赞》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漆器的文章,那是我面对当时收藏的一堆彝族漆器的有感而发。我说,“那些在阳光下花哨刺目,让人心绪不安的漆器,一旦到了昏暗闪烁的油灯或蜡烛底下,就会缓缓地韵动出黑夜的脉搏,诱人想入非非。……西昌的漆器体现着彝族的审美观,用色一律是彝族图腾的三种颜色:红、黑、黄。以黑作底,红和黄的线条四处游走,交织出铺陈烂漫的效果。黑是正黑,红是正红,黄则近乎是金色,把这样一个什物放在幽光逶迤之处,有庄重,有热烈,也有几分俗艳动人的挑逗。看久了,心却静了,说得玄点,此时的感觉仿佛是迎了红尘又破了红尘,身后的那一片空间竟坐出了几分禅意。”
现在看这篇收在我第一本书《艳与寂》中的文字,那句“迎了红尘又破了红尘”和“禅意”,把自己给窘笑了。年少轻狂真敢写啊,留下如此的笑柄,也没有办法。但这篇文章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是某种延续至今且逐渐夯实的美学理念的开启。有意思的是,这种开启,经由谷崎润一郎这个点进入,逐渐地在另外好些境外之域与之相遇,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芝加哥的雨雾里,在华沙深秋凌晨四点的街头,在内罗毕郊外的咖啡种植园……每一次的触点都特别有意味。现在,我反复地行走日本,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是,我感觉我的背后似乎也有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影子,在异国文化之光的映照下,这个影子随着我的行走愈发贴近,它有重量,有温度,有情感,还有DNA的力量。这个影子来自中国文化的深处……我知道它在,但我还看得不太清楚。屋檐很深啊,阴翳中的内容还有待慢慢浮现。 一入再入之红:日本文学行走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