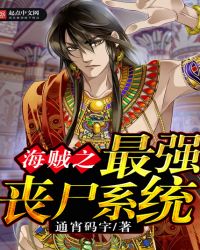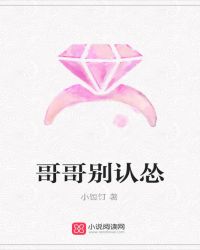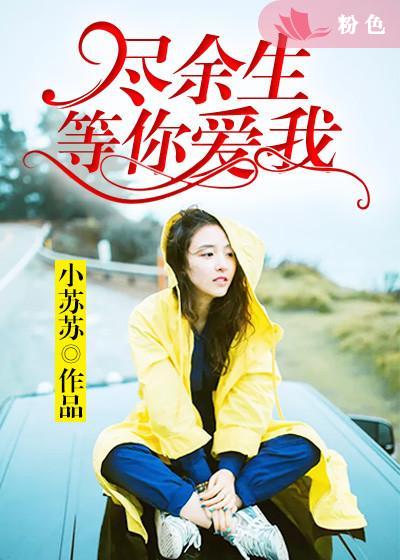第二章 自然状况下的变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凤凰联动文库:论文学涵养细节(套装共15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章 自然状况下的变异
在器官、形态、颜色、习性等方面,个体间都有相当的差异,完全相同的个体绝对没有。 一棵树,能长出各不相同的幼苗;同一头猪,产下了有明显区别的幼崽。
自然界里,越是普通、数量越多的物种,和其竞争对手比较,它们越具有生存优势,比如水葫芦以空前的速度在各地繁衍,所到之处,当地水草纷纷灭亡。这样的物种也更容易变异,比如能适应新环境的变种——不列颠的红松鸡,有的鸟类学家认为是挪威红松鸡的变种,而有的则认为是土生的独特物种。根据分布的距离、习性等,不能把生物是物种还是变种区分开来,物种和变种,二者没有确切的区分标准。
野生东北虎
野生东北虎被称为“丛林之王”,爆发力和攻击力都十分惊人,它们以野猪和豹子为食。为了猎取这两种本身就非常危险的动物,野生东北虎的爪子和犬齿进化得利如钢刀。
变异
在将前章所得到的各项原理应用到自然状态下的生物之前,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简短的讨论,即是否自然状态下的生物更容易发生变异。要处理这一问题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就必须列举一长串枯燥的事实,这些事实将会在我今后的著作中发表出来。在这里,我也不讨论那些已经加在“物种”这个术语上的诸多定义。没有一个定义能让所有的博物学者都满意,但当博物学者彼此之间谈论物种时,他们却都含糊地知道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在通常情况下,“物种”这一术语都包含着未知的具有特殊创造作用的因素。几乎同样难以给出定义的还有“变种”这个术语,虽然它很少能够被证明,但它几乎普遍地暗示着相同的血统。还有就是被我们称为“畸形”的这一术语,它也很难解释,但它正逐渐向变种这个方向发展。在我看来,畸形就是指在体质上的某一部分存在着明显的偏差,而且这种差异在一般情况下对于物种是有害的,或者是无益的;在通常情况下,畸形是不会传播的。
有些作者在使用“变异”这一术语时,是有着专门的技术含义的,即变异是一种直接由物理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变化。在这个定义中,“变异”被认为是不能遗传的,但是谁又能解释为什么波罗的海咸水区域内贝类的矮化病、阿尔卑斯山顶峰的那些矮化植物,或极北地区的动物长有较厚毛皮,在某些情形下它们都至少遗传了几代?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类型是可以称为变种的。
埃塞俄比亚狼
埃塞俄比亚狼,因其发现于埃塞俄比亚西门山而得名“西门豹”,它们是非洲唯一的野生狼,只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几个非常狭窄的区域里,目前仅有500只。埃塞俄比亚狼保留了狼家族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精神,通常会在黎明和中午聚集在一起,对领地进行巡视,其余时间则觅食。
鬃狼
鬃狼又名巴西狼、南美狼,分布于巴西东北部到秘鲁南部区域,包括巴拉圭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主要栖息在干燥的草原、灌木丛和河流附近,成对或单独居住。鬃狼生性胆小,主食是各种水果,也会在夜间偶尔捕食兔子、昆虫等小动物,这也使得它们的犬齿退化,不如其他狼锐利。
在我们的家养生物里,特别是在植物里,我们偶尔看到的那些突发的和显著的构造偏差是否能在自然状况下永久传下去,这还是一个疑问。几乎每种生物的每个器官都与它的复杂生活条件有着美妙的联系,尤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任何器官都会突然地、完善地生长出来,正如人类完善地发明出一台复杂的机器一样。在家养状态下,有时会发生畸形,这些畸形与一些和本物种大不相同的物种的正常结构类似。比如,猪有时一生下来就具有一种长吻,如果同属的其他野生物种天生也具有这种长吻,那么或许可以说它是一种畸形,但在我的长期努力探索下,我发现任何一个拥有正常身体结构的具有长吻的物种同猪的正常身体结构都不类似,同时也只有猪的这种畸形才和这个问题有关。如果这种畸形类型的确曾出现在自然状态中,而且能够繁殖(事实并非永远如此),那是因为它们的发生概率太过稀少而且特殊,所以必须依靠异常有利的条件才能把它们保存下来。不仅如此,如果将这些畸形的第一代或以后的几代同普通类型相杂交,它们的畸形性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消失。至于对具有单独性的或偶然性的变异体的保存以及延续,我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个体间的不同
在双亲相同的后代个体中所出现的大量细微差异,或者在同一局限区域内生活的同属物种的不同个体中所观察到的,而且可以被假设为也是在同一父母的后代中所出现的大量细微差异,都可以称为个体差异。没有人会作出同属物种的所有个体都是由一个相同的“模具”“铸造”出来的假设。这些个体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有极高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变异为自然选择的积累提供了原料,正如人类能利用家养物种中的那些具有指向性的个体差异对家养物种进行选择积累一样。
桫椤
在达尔文看来,变种是由于环境的挑战而产生的,然而内部模式的不变性不允许变异超越某种限度。与恐龙同时代的蕨类植物桫椤是物种中最稳定的,经过一亿多年的时间,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博物学者看来,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差异都出现在不太重要的部位,但是我却可以用一连串的事实来证明,无论从生理学还是分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差异都必须称为重要部位。有时在同属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也会发生变异。我相信,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博物学者,在如此众多的变异事实面前也会感到惊奇。只要他能在这方面花上许多年的时间,他就能如同我一样,在许多权威著作中搜集到大量有关变异的事例,甚至还搜集到许多关于结构中的重要部位的变异事例。应该牢记,分类学家对在重要性状中发现变异会感到非常不高兴,而且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花费大力气去检查内部的重要器官,并在同属物种的许多个体间去比较它们。我从来没有预期到,昆虫的靠近大中央神经节的主干神经分支在同一个物种里会发生变异,我曾以为这种自然状态下的变异只能缓慢地进行。然而卢伯克爵士的解释却指出介壳虫的主干神经的变异程度,几乎可以比得上树干的不规则程度。在此我要补充一下,这位具有哲理的博物学者曾在最近指出,某些虫的幼虫在肌肉方面存在着高度的不统一性。当一些作者陈述生物的重要器官不可能发生变异时,他们时常采用一种循环辩论的方法,事实上,他们正是这样,将不变异的部位列为了重要的器官(正如少数博物学者曾公开承认的那样)。在这种观点下,当然就永远无法找到有关重要器官发生变异的事例。但在任何其他观点下,许多事例就能被确确实实地列举出来。
长颈鹿
达尔文认为绝大多数变异是非遗传性的,是由环境引起的。长颈鹿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动物。其实,它们祖先的颈和腿原本并不长,后来在取食过程中才慢慢形成了长脖子。
在个体差异上,有一个问题让人感到非常迷惑,我指的是所谓变形的或多形的那些属,在这些属中,个体物种之间表现出了惊人的变异。在到底该将这些个体归为物种还是变种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两个博物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以植物中的悬钩属、蔷薇属、 山柳菊属以及昆虫类和腕足类的几个属作为例子。在大多数多形的属里,有一部分物种有着稳定的性状。除了一些例外之外,在某地属于多形的属的物种,在其他地方也似乎是多形的,而且通过对腕足类的判定,早期的腕足类也是如此。由于这些事实似乎是在证明这种变异是独立于生活条件之外的,因此它们使人感到极度的困惑。我假设至少在一些多形的属里,我们所看到的变异对物种是无用或无害的,因此,自然选择就会因为不能对它们产生任何作用,而无法使它们被确定下来,这一点在以后还要进行说明。
众所周知,同种的个体在构造上常常呈现出与变异无关的巨大差异。比如在动物的两性之间,昆虫中无生育能力的雌虫即工虫的二、三职级间,以及在许多低等动物的发育不完全状态和幼虫状态之间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再比如,在动物和植物里,还存在着二形性和三形性的例子。在最近,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华莱士先生曾指出,马来群岛的某种蝴蝶中的雌性,有规则地表现出了两个甚至三个极为明显的不同类型,而其中并不存在中间变种。弗里茨·米勒描述了某些巴西甲壳类的雄性也存在类似的但却更为异常的情形,比如异足水虱的雄性有规则地表现了两个不同的类型,即一个类型有着强壮且形状不同的钳爪,而另一类型则有着非常多的嗅毛触角。尽管在大多数的例子中,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在两个或三个类型之间并不存在中间类型,但它们却可能曾经存在过中间类型。比如华莱士先生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同一岛上的某种蝴蝶,它们有着一系列的变种,这些变种之间是由一条中间锁链相连接的,在这条锁链的两个极端上的物种,与马来群岛其他部分的一个相似的二形物种的两个类型极为相似。蚁类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不同职级的工蚁也很不同,但在我们随后将要讲到的某些例子中,这些职级被那些分得很细的级进的变种连接在了一起。正如我所观察的一样,一些二形性植物与动物是一样的。同一类型的雌蝶具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产生三个不同的雌性类型和一个雄性类型;一株雌雄同体的植物能在同一种子中产生出三种雌雄同体的但类型却大不相同的植物,而这三种雌雄同体的不同类型还包含着三种不同的雌性和三种甚至六种不同的雄性。这些事实似乎的确非常奇特,但这些例子只不过是将下面所说的一种普通事实进行夸大罢了,这一事实就是雌性所产生的雌雄后代的彼此差异有时会达到惊人的地步。
蝴 蝶 摄影
蝴蝶为鳞翅目,分布于南极洲之外的各洲,蝴蝶翅展长1~29厘米。蝴蝶的生命会经历四个非常明显的阶段:卵期、幼虫期、蛹期、成虫期。每经历一个化蛹阶段,它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因此也就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
可疑的物种
有些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物种的性状,但它们又同其他类型非常密切亲近而且相似,又或者它们通过中间级进与其他类型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导致博物学者们不愿意把它们列为不同的物种,而这些类型的某些方面却对我们的讨论至关重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可疑且极度相似的类型中,有许多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地保存着它们的性状,因为据我们所知,它们和良好的真种一样,长久地保持了它们的性状。事实上,当一位博物学者用中间锁链把任何两个类型连接在一起时,他就会把一个类型当做另一个类型的变种,他把最普通但常常是最初记载的一个类型作为物种,而把另一个类型作为变种。
可是,当决定是否能把一个类型作为另一个类型的变种时,就算这两个类型被“中间锁链”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也存在着重重困难,我并不想在这里列举这些困难,即使中间类型具有一般性的假定杂种性质,也常常无法解决这种困难。但在很多情况下,把一个类型列为另一类型的变种,并非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已经找到了中间锁链,而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类推法,我们假设中间类型的确生活在现在的某个地方,或者它们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如此一来,就为疑惑或臆测打开了大门。
困扰达尔文的“中间锁链” 水彩画 20世纪
中间锁链,也就是指中间类型,它们常常把生物的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比如鸭嘴兽,这种唯一的卵生哺乳动物,由于同时具有水栖动物和陆栖动物的特征,它就属于中间类型。这种情况同样会出现在同属的物种当中,比如人和猿人之间的智人,它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一级,也属于中间类型。然而在具体区分某些生物的种属时,由于缺乏中间类型,往往让分类学者们无所适从,这也是长期困扰达尔文的一个关键问题。
鹅掌楸 摄影
鹅掌楸为木兰科,鹅掌楸属。曾生活在侏罗纪时代,是著名的孑遗植物。鹅掌楸多生于溪畔和湿润地区,但耐寒性也极强,它这种冷暖不惧的品性,或许是其成为孑遗植物的重要原因。现存的鹅掌楸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北美鹅掌楸,另一种生长在我国亚热带地区。
当决定一个类型到底该归为物种还是归为变种时,有准确判断和丰富经验的博物学者的意见,似乎成了理应遵循的唯一标准。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大多数博物学者的意见来作决定,因为有一些特征显著而且众所周知的变种,曾经被几位有资格的鉴定者列为了物种。
有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到处都存在着具有可疑性质的变种。把植物学者们所著的大不列颠的、法兰西的、美国的植物志进行一番比较后,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变异类型的数量是多么庞大惊人,而且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被某一位植物学者列为良好物种的,却被另一个植物学者列为变种。我要感谢沃森先生,他在许多方面都帮助了我,是他告诉我,在现在,有182种不列颠的植物被认为是变种,但是所有这些植物在过去却曾被植物学者列为物种。当制作这张表格时,他排除了许多细小的变种,然而这些变种也曾被植物学者们列为物种;另外他还把几个高度多形的属完全排除掉了。在含有最多形的类型的属之下,巴宾顿先生举出了251个物种,而本瑟姆先生却只举出了112个物种,这就是说,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139个可疑类型之差!在每次生育都是通过交配完成、具有高度移动能力的动物里,存在着一些可疑类型,这些可疑类型被某位动物学者列为物种,但却被另一位动物学者列为变种;这些可疑类型在同一地区是非常少见的,但在互不相邻的两个地区却很普遍。北美洲和欧洲的许多鸟和昆虫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它们曾被某一位优秀的博物学者列为毋庸置疑的物种,但却又被别的博物学者列为变种,或将它们称为“地理族”。对于栖息在大马来群岛上的动物,特别是鳞翅类动物,华莱士先生写过几篇有价值的论文,在这些论文里,他指出该地区的动物可以分为四类:变异类型、地方类型、地理族以及真正的、具有代表性的物种。变异类型在同一个岛上就存在着极多的变化。地方类型则比较稳定,只是在各个彼此不相邻的岛上存在着区别,虽然同时在极端类型之间有着充分的区别,但当把几个岛的一切类型放在一起作比较时,却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差异十分细微,以至于我们无法区别和描述它们。正是因为这样,地理族是完全固定的、孤立的地方类型,但由于它们彼此之间在最显著和最主要的性状上没有差异,因此“没有标准的区别方法,只能靠个人的意见去决定哪种应该是物种,哪种应该是变种”。最后,在各个岛的自然结构中,具有代表性的物种与地方类型和亚种有着同等的地位,但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量比地方类型或亚种之间的要大得多,因此博物学者们几乎普遍地将它们列为真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提出一个可以被用来辨认变异类型、地方类型、亚种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物种的确切标准。
许多年前,我曾自己亲自作过并看到别人作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各个邻近岛屿上鸟类的对比,以及这些鸟类与美洲大陆上鸟类的对比,通过对比,我深感物种和变种之间的区别是多么的暧昧和武断。在沃拉斯顿先生的那篇令人赞叹的著作中,他把小马得拉群岛的小岛上的许多昆虫列为变种,但一定有许多昆虫学者会把它们列为不同的物种。甚至在爱尔兰,也存在着少数的动物,这些动物曾被某些动物学者列为物种,但现在一般却把它们列为变种。一些有经验的鸟类学者认为不列颠的红松鸡属于挪威种,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特性显著的族而已,但大多数学者却把它列为大不列颠所特有的物种。两个可疑类型的原产地如果距离太遥远,就会被许多博物学者列为不同的物种。曾经有这样一个很好的问题:“多少距离才算足够?”如果美洲和欧洲间的距离算得上足够,那欧洲与亚速尔群岛、马得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之间的距离是否足够?小群岛的几个小岛间的距离又是否足够?
松鸡起舞 斯蒂芬·盖特尔 摄影
松鸡,脊椎动物,鸟纲。多分布在北方的亚寒带针叶林中,为适应气候寒冷的特点,它们的鼻孔和脚上都长有羽毛以御寒,此鸟通常在冰雪尚未融化时开始配对,雄鸟常立于荒地高处或高树上发出“克克、克克”的叫声,吸引雌鸟。在争雌时,雄鸟常在平地或空中用喙相互击刺。
杰出的美国昆虫学者沃尔什先生,曾经描述过他称之为的植物食性昆虫变种和植物食性昆虫物种。大多数的植物食性昆虫只以某一种类或某一群类的植物为食,而还有一些则以多种植物为食,但它们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异。然而,在几个例子中,沃尔什先生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以多种植物为生的昆虫,在它们的幼虫或成虫时期,或在这两个时期中间,它们的颜色、个体大小、分泌物的属性都存在着轻微且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在某些例子中,只有雄性才存在细微的差异;在另一些例子中,两性都存在细微的差异。如果差异变得非常显著,且两性在幼虫和成虫时期都受到了影响,那么所有的昆虫学者就会把这些类型列为良好物种而不是变种了。就算一个观察者可以为自己决定哪几种植物食性的昆虫是物种,哪几种又是变种,但他却不能为别人作决定。沃尔什先生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可以自由杂交的昆虫类型是变种,而那些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的昆虫类型则是物种。由于这些差异是因为昆虫长期吃不同的植物而产生的,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再找到那些连接在几种类型之间的中间锁链的希望了。其实,博物学者在把可疑类型归为变种或物种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指导。生活在不同大陆、不同岛屿上的同属生物也必然有相同的情况。另外,当一种动物或植物分布在同一大陆或同一群岛的各个岛屿上,且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不同类型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有机会去发现连接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类型,这些类型被降成了变种的一级,而不是物种。
食肉动物猎豹 摄影
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极限时速可达120公里,不过耐力不佳,无法长时间追逐猎物。为了适应高速的奔跑,它的身体变得修长,爪子也不能随意伸缩。另外,猎豹不能长时间奔跑是因为肉食性的猎豹没有草食性动物的蹄。
有少数博物学者坚持认为动物是不会有变种的,他们认为极细微的差异也具有物种的价值。如果偶然在两个区域或两个地层中发现了两个相同的类型,那么他们则会认为这是包裹在同一外套下的两种不同物种。于是物种就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名词,它表示或假定了分别创造的作用。诚然,性状上如此完全类似的物种,被很多的优秀鉴定者判定为变种类型,而又被另外一些优秀的鉴定者判定为物种,但在物种和变种这两个名词的定义还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之前,就来讨论是将它们归为物种还是将它们归为变种,是徒劳的。
有许多关于特征显著的变种或可疑物种的例子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在试图决定它们的等级时,从地理分布、相似变异、杂交等方面已经展开了几条有趣的讨论路线,但是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将不能对它们进行讨论。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精密的研究可以使博物学者们在可疑类型的分类上达成共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点,那就是在研究得最透彻的地区,我们碰到的可疑类型的数目也最多。下列事实就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即如果在自然状况下,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有着较高的利用价值,或因为任何原因,导致了人们的强烈关注,那么它的变种几乎就会被普遍地记录下来,而这些变种则经常被某些作者归为物种。比如普通的橡树,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是多么的精细,但一位德国作者却从那些被植物学者们所普遍认为是变种的类型中确定出了12个以上的物种;在英国,我可以列举出一些植物学方面的权威人士以及一些实践者,他们中有的认为无梗的栎树和有梗的栎树是良好而独特的物种,而有的则认为它们只是变种而已。
北美红橡树 摄影
北美红橡树,全日照乔木,耐瘠薄,喜光照,比绝大多数树种都容易移植成活。并且,它们对城镇环境的适应力也惊人的强大。北美红橡树现已成为非常优良的观赏树种。
虾虎鱼 摄影 现代
虾虎鱼是世界上寿命最短的脊椎动物,它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腹鳍愈合成吸盘状。该吸盘的功能与鲫鱼的背鳍吸盘和圆鳍鱼科的腹鳍吸盘类似,因此是趋同进化的结果。
在这里,我要谈一下最近由得康多尔所发表的对全球栎树进行讨论的著名报告。在物种的区别上,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材料能像他的那样丰富,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栎树的研究能像他那样热心、敏锐。首先,他大量且详细地列举了物种在构造上的变异情况,并用数字计算出了变异的相对频率。他甚至列举出了发生在同一枝条上的变异,这些变异的性状达到了12种以上,有的变异是因为年龄和发育的原因,有的则是因为毫无原因的理由。当然,这些性状并不具有物种的价值,但却正如阿萨·格雷在评论这篇报告时讲的那样,这些性状一般都带有物种的定义。然后,得康多尔继续论述说,那几种类型之所以被他归为物种,是因为在同一株树上,性状绝不可能出现变异的地方,这几种类型出现了变异,而且这些类型彼此间不出现任何的中间锁链。经过这个讨论——这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以后,他强调:“有些人反复地告诉我们,绝大部分的物种都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且可疑物种也就那么几种,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要一个属,还没有完全被认知,而且它的物种只存在于少数的几个标本上时,也就是说,当它们是被假定的时候,那种说法才可能是正确的。当我们对它们有了更好的认知后,中间类型就会不断出现,那么对物种界限的怀疑就会相应地增大。”他又补充说:“只有那些被我们所熟知的物种,才具有最大数目的自发变种和亚变种。比如夏栎,它拥有28个变种,除了其中的6个变种以外,其他的变种都围绕在有梗栎、无梗栎及毛栎这3个亚种的周围。正如阿萨·格雷所说的那样,目前,这些中间类型已经很稀少了,如果完全灭绝的话,那么这3个亚种的相互关系,就完全和那些环绕在典型夏栎周围的四五个假定物种的关系一样了。最后,得康多尔还承认,在其“绪论”中所列举的300种栎科物种中,至少有2/3的栎科物种是假定物种,换句话说,他并不能严格地知道它们是否能适合上述的诸种定义。还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得康多尔已经不再相信物种是不变的创造物,而坚信“转生学说”才是最符合自然的学说,他说:“该学说是与古生物学、植物地理学、 动物地理学、解剖学以及分类学的已知事实最为相符的学说。”
栎树
栎树,壳斗科,栎属,也称橡树或柞树。其变种繁多,现在已知的栎树有600多种,其中450种来自栎亚属,另外150种是青刚亚属。
当一个青年博物学者对一个十分陌生的生物群类进行研究时,一开始,最让他感到困惑的就是决定什么才是物种的差异,什么才是变种的差异。他之所以困惑,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生物群类所发生的变异量和变异种类,至少,这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生物发生变异是一种多么普遍的情况。但如果他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地区里的某一类生物上时,他就能很快地决定如何去对大部分的可疑类型进行分类。他一般会倾向于列举出许多物种,之所以这样,是正如以前所谈到的养鸽爱好者和养鸡爱好者那样,他不断研究的那些类型的变异量给他造成了深刻印象。与此同时,他非常缺乏其他地区、其他生物群类相似变异的一般知识,以致这些一般知识无法被用来校正他的最初印象。当他的观察范围扩大之后,他就会遇到更多困难,因为他将遇到数目更多的相似类型。但是,如果再将他的观察范围扩大,那么他将能作出最后的决定。他如果想要在这方面获得成就,就必须敢于承认大量的变异,但承认这项真理常常会引发他与其他博物学者的争辩。今天,如果从已不再连续的地区找来近似类型,并加以研究,他就不可能从其中找到中间类型,因此,他不得不完全依靠类推法,但这种方法会使他面临极端的困难。
有些博物学者认为亚种已经非常接近物种了,但还没有完全达到物种的级别。诚然,在物种和亚种之间,还不曾有过一条明确的界线,而且在亚种和显著的变种之间,在不大显著的变种和个体差异之间,也不曾有过一条明确的界线。这些差异被一条难以发现的系列混淆在了一起,而该系列则被人们认定成了演变的真实途径。
朱 鹮 摄影
朱鹮,鸟纲,鹳形目, 科,朱 属,体态典雅,性格温顺,有“东方宝石”之称。朱 喜欢栖息在高大乔木的顶端,在水田、沼泽、山区溪流附近觅食。过去在西伯利亚、朝鲜、日本等地均有分布,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环境变化,朱 进化滞后不能适应新的环境。野外已难觅朱 踪迹。朱已被列为濒危鸟类,世界上仅存的朱 种群在陕西洋县。
因此,我认为分类学家虽然对个体差异不大感兴趣,但它却对我们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差异是轻微变种的最初步骤,而这些轻微变种在博物学著作中仅仅是勉强值得记录下来的。同时我还认为,任何程度上的较为显著且较为永久的变种都是走向更显著且更永久的变种的步骤,而且变种是走向亚种,并最终走向物种的步骤。在许多情况下,从一个阶段的差异到另一个阶段的差异,可能是因为生物的本质和生物长久居于不同物理条件之下的简单结果,但对于那些更重要且更能适应的性状而言,从一个阶段的差异到另一个阶段的差异,则应被归为将在后面文章中所提到的自然选择的累积作用,以及器官的增强使用和不使用的效果。因此,一个显著的变种可以被称为初期物种,但是这种观点是否合理,必须根据本书所列举出的各种事实和论点的价值加以判断。
不要认为所有变种或初期物种都可以达到物种级别。也许它们会灭绝,也许它们会长期停留在变种阶段,这正如沃拉斯顿先生指出的马得拉的某些陆地贝类变种、得沙巴达所指出的植物变种一样。如果某个变种数量很多,甚至超过了真种的数目,那么它就会被列为物种,而真种则会成为变种;它还有可能将真种彻底消灭掉,进而取而代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者并存,被分别归为独立的物种。我们将在以后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物种”这一名词是为了便于区分一群彼此之间非常密切亲近而且类似的个体才被使用的,它和“变种”这一名词的本质是一样的。变种指的是差异较少且相似之处较多的类型。另外,所谓的变种与个体差异的对比,也是为了便于区分才被使用的。
范围广、分散大的和普通的物种变异最多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按照理论的指导,如果将几种编著得比较好的植物志中的所有变种列成一个表格,那么我们在对变化最多的物种的性质和关系的研究上就可能会取得一些有趣的结果。一开始,我以为这似乎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沃森先生就让我意识到了其中的大量难点。在此,我要深深地感激他,他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了我宝贵的忠告和帮助,之后,胡克博士也有这样的说法,甚至还对该说法进行了强调。至于所有的难点和各变异物种的比例数目表格,我将在以后的其他著作中进行讨论。当胡克博士仔细阅读了我的原稿,并审查了各种表格之后,他允许我进行补充说明,他认为下面的论述成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这里,虽然必须把整个问题讲得非常简单,但其真实情况却格外复杂,并且还不得不涉及到一些将在后面讨论的问题,如“生存斗争”“性状的分歧”等。
栽培甘蓝 摄影 当代
甘蓝为十字花科,两年生植物,最先只有一个品种,通过改变DNA、杂交等方法,现已有上百个品种。从外形上看,它们有着明显的差别。甘蓝可以分为结球甘蓝(俗称莲花白菜)、孢子甘蓝、花椰菜(菜花,又分绿色花和白色花)、球茎甘蓝、散叶甘蓝、彩色甘蓝等。
得康多尔和别的一些人都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般情况下,分布很广的植物都会出现变种。这一观点是可以被预料到的,因为它们生活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之下,而且它们必须和各类不同的生物进行斗争(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中看到,这是同样真实且更为重要的条件)。但我的表格却作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即在任何一个受限制的地区里,最普通的物种,即个体最繁多的物种,以及在它们自己的区域内分布最广的物种(这里的分布广与之前所说的分布广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它和“普通”也存在着略微的差异),发生变种的情况最为频繁。这些变种有着足够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会使植物学者认为它有被记载的价值。因此,最繁盛的物种,或者说最有优势的物种——它们分布最广,在自己的区域内分布最大,个体也最多——也是最为频繁地产生显著的变种,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它们是初期的物种。也许这一点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因为如果变种要在所有层次上都变为永久,那么它就必须和该区域内的其他生物进行斗争,而已经取得优势的物种,将最适合于产生后代,尽管这些后代的变异程度不如其亲代,但它还是遗传了其亲代的胜于同地生物的那些优点。这里所讲的优势,只是指那些互相进行斗争的类型,尤其是指同属或同纲的具有极度相似的生活习性的成员,至于个体的数目,或物种的普通性,则只是指同一群类的成员。如将一种高等植物和生活在类似相同条件下的其他植物进行比较,前者的个体数目更多,分布也更广,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获得了优势。这样的植物并不会因为本地水里的水绵或一些寄生菌的个体数目更多、分布更广而减少它的优势。但如果某种水绵和寄生菌在上述各点上都胜过了它们的同类,那么它们就会在自己的这一纲中获得优势。
大属物种的变异多于小属物种
如果把记载在任何一部植物志上的某地的植物分为对等的两个群,即将大属(即含有许多物种的属)的植物作为一个群,将小属的植物作为另外一个群,我们就会发现,大属里那些最为普通且分布极广的物种或优势物种的数目会比较多。也许这一点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仅仅需要看看栖居在任何地区中的同属物种所存在的事实,就可以知道了。任何地区的有机和无机条件必然会在某些方面有利于这个属。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大属里,我们会发现比例数目较多的优势物种。但是如此多的原因却能让结果变得模糊不清,以致我感到奇怪,我的表指出的大属这一边的优势物种只是稍稍占多数。在这里,我只想解释一下两个模糊不清的原因。一般情况下,淡水产的和喜盐的植物的分布都很广,而且极为分散,这种情况似乎和它们居住地方的性质有一定的关系,而和该物种所归属的大小有很小的关系或者没有关系。另外,低级植物的分布一般比高级植物广,而且这也和属的大小没有关系。低级植物分布广的原因将会在“地理分布”那一章中进行讨论。
同属不同种的动物 摄影
虎和狮子同属世界珍稀动物,是著名的野生动物。这两种猫科动物同属于美洲豹属,但不同种。它们遗传了祖先凶猛的本性,是最强有力的捕食者。
由于我认为物种只是特性显著且界限分明的变种,所以在我的假设中,各地大属物种出现变种的频率会高于小属物种,这是因为,按照通常的规律,在那些已经形成了密切亲近且相似的物种(即同属的物种)的地区,也许有大量的变种即初期的物种正在形成。在许多大树生长的地方,我们有找到幼树的希望。在一些地方,如果同一属的大量物种都发生了变异,这就说明各种条件都有利于变异。因此,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些条件还会继续有利于变异。相反地,如果我们认为各个物种是被分别创造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没有明显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含有多数物种的群类出现变种的频率会高于含有少数物种的群类。
美丽的仙人掌 佚名 摄影 当代
在常见的栽培植物中,某些植物的茎、叶或花苞,由于外界因素的刺激,会发生颜色、形态等的异常变化,形成比原植物更加奇特和美丽的品系。甘蓝、仙人掌就是这样的植物。育种专家和园艺师们正是根据这一特点,培育出了很多蔬菜新品种和观赏植物。
为了证实我的这一假设的真实性,我把12个地区的植物以及两个地区的鞘翅类昆虫分成了两个比较相等的群,大属的物种在一边,小属的物种在另一边。事实证明,大属产生变种的物种的比例比小属的多。另外,在变种的平均数上,大属物种也永远比小属物种产生得多。即使采用另一种分群方法,即把只有一到四个物种的最小属都不列入表格内,我们也得到了与上述情况同样的两种结果。这些事实对于物种,即对只是显著而永久的变种而言,有着明显的意义。因为在曾经形成过同属的许多物种的地方,换句话说,曾经是物种制造厂的地方,我们一般都还可以看到这些工厂依旧还在活动,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物种的制造过程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如果把变种当做初期的物种,那么上述这点肯定是正确的,因为我的表格作为一般规律清楚地对此进行了解释。在曾经形成一个属的许多物种的任何地方,该属的物种所产生的变种(即初期的物种)的数目就会在平均数之上。这并非是说,在今天,由于一切大属的变异都很大,因此它们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也不是说小属都不变异,而且其物种数量也不再增加。要真是这样,我的学说就必然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因为地质学清楚地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变迁,小属常常会增加,而大属则常常会因达到顶点而衰落,甚至灭亡。我们要说明的是,通常情况下,在曾经形成了一个属的许多物种的地方,有着许多物种正在形成,这才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大属物种之间的关系受地域限定
大属物种与有记载的大属变种之间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其他关系。我们已经论述过,物种与显著变种之间的区别并没有绝对正确的标准,当两种可疑类型之间没有任何中间形态存在时,博物学者必须根据其彼此间的差异量来决定,并用类推法来对这些差异量进行判定,以决定是否能把一方或双方升到物种的级别。因此,差异量就成了决定两种类型到底应该是物种还是变种的至关重要的标准。弗瑞斯曾对植物、威斯特伍得曾对昆虫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这样的诠释,即大属物种之间的差异量常常很少,我曾用平均数的方法来竭力证明这一点,所得到的结果表明他们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我又询问过几位卓越而且经验丰富的观察者,在经过详细的考虑后,他们也赞同了这一观点。因此,在这一方面大属物种与小属物种相比,就显得更像是变种了。也许这种情况还能用另一种方法来进行诠释,即在大属中(目前,在这些属里,有超过平均数的变种即初期物种正处于制造中),由于物种间的差异还没有普通的差异量多,因此,许多已经制造完成的物种在某种范围内仍然与变种相似。
现代象 摄影
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它们的祖籍在非洲,距今已有3600万~5500万年历史了。最早的象叫始祖象,与现在的猪差不多大,很可能生活在水中。它们有像河马一样的眼睛和耳朵,眼和耳长在头部很高的地方,即使在沼泽里打滚,也可以露出水面观察周围的情况。始祖象随后分化成恐象、乳齿象、剑齿象等,最后才进化成现代的象。
另外,大属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任何一个物种的变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似的。没有一个博物学者敢说,在区别上,同一属的一切物种是相等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亚属、级或更小的群类。弗瑞斯曾清楚地论述过,小群物种在一般情况下就如卫星一样,环绕在其他物种的周围。所谓的变种只不过是一种类型,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等的,它们环绕在某些类型——即环绕在它们的亲种的周围。毫无疑问,变种和物种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点,即变种之间的差异量,或变种与亲种之间的差异量,比同属的物种之间的差异量少得多。但当我们讨论被我称为“性状的分歧”的原理时,各位就会看到我是如何对此加以说明的,并是如何说明变种间的小差异是怎么增大成物种之间的大差异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变种的分布范围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确,这一点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因为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变种比它的假定亲种的分布范围更广阔,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们的称谓颠倒过来,即它是物种而它的假定亲种则是变种。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与其他物种极为亲近且类似的变种的物种,其分布范围常常是受到了极大限制的。比如,沃森先生曾把精选的《伦敦植物名录》(第四版)中的63种植物拿来给我看,该名录将这些植物全部归为不同的物种,但沃森先生却认为,由于它们同其他物种极其相似,因此它们的价值非常值得怀疑。按照沃森先生所作的大不列颠区划,这63个可疑物种平均分布在6.9个区中。而在同一个名录里还记载了53个公认的变种,它们的分布范围为7.7个区,而这些变种所属的物种的分布范围也达到了14.3个区。因此,公认的变种和密切亲近的类型在平均分布范围上几乎都受到了相同的限制,这些密切亲近的类型正是沃森先生所谓的可疑物种,但这些可疑物种却几乎被绝大多数的大不列颠植物学者们归为良好、真实的物种了。
争夺交配权 刘亦 摄影
大象的求爱方式比较复杂,每当繁殖期到来,雌象便开始寻找僻静之处,用鼻子挖坑,建筑新房,然后摆上礼品。雄象四处漫步,用长鼻子在雌象身上来回抚摸,接着用鼻子互相纠缠,有时把鼻尖塞到对方的嘴里。当然,有时会出现照片中描绘的情况,两头雄象为了争夺一头雌象的交配权而进行搏斗。
本章重点
综上所述,除非满足这样几点,否则变种与物种是无法进行区别的。第一,有中间类型被发现。第二,两者间有一些不确定的差异量,因为如果两个类型的差异量很少,那么一般来说,就算它们并没有密切的关系,也会被归为变种;但到底要多大的差异量才能把任何两个类型都分别归为物种,却无法确定。在任何地方,如果一个属所含的物种超过了平均数,那么它们的物种也可能有超过平均数的变种。在大属中,物种密切地但不均等地相互近似,形成了一个个的小群类,这些小群类环绕在其他物种的周围。显然,与其他物种密切亲近的物种在其分布范围上是受到了限制的。从上述这些论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属物种与变种非常相似。如果某一物种曾经作为变种生存过,而且是由于变种而形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相似性;但如果说物种是被独立创造的,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对相似性作出任何说明了。
在各个纲里,我们也曾发现,大属中的极其繁盛的物种即优势的物种,都能产生出最大数量的变种,同时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变种具有变成新的且明确的物种的倾向。因此,大属将变得更大;而且,在现在的自然界中,由于那些占优势的生物类型留下了许多发生了变异和优化的后代,因此它们将会更加占有优势。但这些情形尚需作出解释。大属也有分裂为小属的倾向。于是,全世界的生物类型就由一个群类分为了多个群类。
地 球 摄影
地球形成于50亿至46亿年前。当时大地上火山遍地,岩浆横流,根本不适合生命生存。现在已经知道的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出现在34亿年前,是以像现在的细菌一样的形式出现的,叫做蓝菌。 凤凰联动文库:论文学涵养细节(套装共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