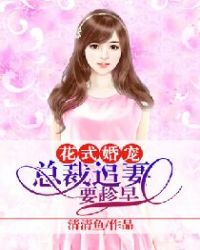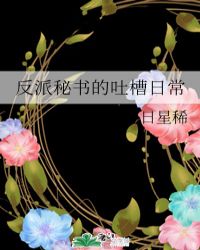府河上的桥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成都街巷志.上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桥
万里桥木质桥基/1988年/李绪成摄影
成都多河,也就多桥,从李冰治水时期所造的“七桥”到今天雄伟的立交桥,数目众多,单是清代的文献记载中就有大小桥梁180多座。而在这众多桥梁之中,最负盛名的则是今天的南门大桥,亦即当年诸葛亮送别费祎之处的万里桥。因为古老的万里桥不再适应如今城市交通的巨大压力,已在1995年被拆除之后重建。这里是维修之时在河道之中发现的十分罕见的清代建造的木质桥基。
府河上的桥
在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地图上,府河进入市区之后只有万福桥、北门大桥、东门大桥三座桥。发展至今,府河在三环路之内已经有了大大小小19座桥梁。其中有些架在府河上面的桥极为平坦,以致人们已经没有觉得是在过桥了,二环路府河市场西侧的府河桥就是相当典型的一例。
西北桥
府河进入成都市中心的第一座桥就是西北桥,位于今天的一环路北二段。由于是在通衢大街之上而且没有一点坡度,人们无数次从它上面通过,却往往会忽略了这是一座桥梁。
西北桥原址叫封家碾渡口,过去长期是依靠渡船摆渡过河。1938年建造了一座木桥,就因为是位于成都城的西北而被命名为西北桥。1956年木桥被冲毁,1958年结合修建一环路而建成了今天的钢筋混凝土大桥,1986年又进行了扩建。
西北桥河边 20世纪50年代 王华提供
西北桥以北,新中国成立之初建有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中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694个“限额以上”的大型重点项目之一(这一批大型重点项目成都总共有11个,包括成都人所熟知的量具刃具厂、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机车车辆厂、电讯工程学院等)。加工厂将通过府河河水日夜漂流而下的大量从岷山上砍伐的原木加工为各种板材与其他制品,一度是我国西部最大的木材综合加工厂,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由于近年来我国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岷山上的原始森林停止砍伐,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不再有大量的漂木原料,故而生产规模已经大大缩小,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之中消失。
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堆料场 20世纪60年代 张蜀华摄影
五丁桥附五丁路
五丁桥是在新开的五丁路(即在原来的皂角巷和白马后巷的基础上开辟出的新街)上建在府河上的一座大桥,北通火车北站,南通宁夏街。这里在1936年建过简易的木桥,当时叫王爷庙桥。1960年改建为砖砌拱桥,现在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是近年来新开东城根街北延线时新建的。
五丁路和五丁桥都以五丁为名。这“五丁”二字源于成都古代一个十分美丽而悲壮的神话传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汉代著名成都籍学者扬雄所写的《蜀王本纪》和西晋著名成都籍学者常璩所写的《华阳国志·蜀志》等书中,记载了这样的神话传说:古蜀开明帝时期,大力士五丁手举万钧,力能移山。北方的秦王有五头石牛,拉出来的粪便都是黄金。蜀王请秦王将石牛送给自己,并派五丁去迎接。三头石牛来到成都就成了金牛,石牛所经之处的道路就叫石牛道或金牛道。秦王又要将五个美女嫁给蜀王,蜀王还是派五丁去迎接。在返回的路上遇到大蛇挡路,在与大蛇的搏斗中,五丁拉垮了大山,虽然五丁与秦女都被压死了,但是大山分开了,从此以后蜀中与北方的秦国之间就有了一条叫作石牛道或金牛道的通道。
《五丁开山》雕塑谭云作
明月峡川北栈道 1993年 陈锦摄影
神话是历史现实的折射。五丁开山与石牛便金的神话,反映了古代的蜀中先民为了走出盆地而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终于开辟了通往北方的通道,变“蜀道难”为“蜀道通”的历史真实。所谓“五丁”就是经过编伍的劳动群体(因为人手有五指,所以古代习惯以五人作为编组。“五五制式”是军队编制的基础,“队伍”一词至今使用。中国象棋中兵卒定为五个正是古制的遗存,至今在民间仍然还有“一五一十”的俗语),所谓“石牛便金”和“美女入蜀”就是通过努力从北方传入的中原文化的成果,而那条金牛道就是以千里栈道为代表的秦蜀通道。这条通道已经使用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的宝成铁路和108国道,仍然是以古老的金牛道为基础线路建成的。正因为如此,五丁一直受到蜀人的高度评价与崇敬,如唐代诗人李同甫在《蜀避寓怀》一诗中写道:“千里烟霞锦水头,五丁开得也风流。”宋代诗人杨亿在《成都》一诗中写道:“五丁力尽蜀山通,千古成都绿酎浓(按:绿酎即醇酒)。”
五丁桥头的城墙 2005年 朱林摄影
今天成都的金牛坝、金牛区的得名,五丁路和五丁桥的得名,还有原来建在二环路上的五丁开山的雕塑(2007年被移至北新大道),都是来源于古老的五丁开山与石牛便金的神话传说。
万福桥
位于人民北路与人民中路之间的万福桥,俗称人民北路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打通火车北站与市中心的通道而新建人民北路与人民中路时修建的。所以名为万福桥,是因为原来在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古老的万福桥。古老的万福桥的得名,又是因为在距此不远的府河畔有一座著名的万福寺(唐代称净众寺,宋代称净因寺,明代称万佛寺、万福寺,毁于明代正德年间,旧址在今通锦路)。
万福桥是府河上一道重要的桥梁,位置在不同时期有过上下移动。最早建桥时间不详,最早的记载是在清代同治年间的《成都县志》,清代最后一次重修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位置在今天的万福桥的下游,连接着金华街和上河坝,是一座“长五丈,宽丈余”的石墩木桥。桥上有木栏画廊覆盖,两端有亭,是一座廊桥(四川民间叫风雨桥),桥上经常有小贩摆摊贩卖。最有特色的是在桥中段的一侧还修有一个很小的小庙,桥的两端还有寺庙,桥北有东岳庙,桥南有水神寺,是成都西北方向入城的重要通道,又是当时的木材市场,是城西北相当热闹的地方。这座古老的木桥在1947年被洪水冲毁,当时未能按原样修复,只修了一个一般的木桥,1954年再次被洪水冲毁之后,也是只恢复了普通的木桥。1959年在古老的万福桥的上游修建了今天的人民北路大桥,先建快车道,后建慢车道,一直到1964年才全部建成,原来的老桥自然也就废弃了。新桥最初叫人民北路大桥,1981年正式定名为万福桥。
20世纪70年代的万福桥 陈德龙摄影
成都万福桥 1935年 杨显峰提供
1947年冲毁万福桥的洪灾是成都有水文资料以来最大的洪灾。从6月30日开始的连续7天特大暴雨,单是7月4日一天的降雨量就高达233毫米,锦江望江楼段岸上水深80厘米,城中大小桥梁被冲毁60多座。特别不幸的是安顺桥被冲毁时,桥上还有若干观看涨水的群众同时落水。市内受灾街道多达80多条,有的街道上积水盈尺,府河和南河两岸很多房屋受灾,甚至被冲光,万福桥头的陈麻婆豆腐店也被冲走一半。全市因洪灾而死亡者86人,伤残者198人,财产损失难以估量。
原来的万福桥桥头是牌坊式的建筑,上面有一道贴金匾额,写有“万福来朝”四个大字,万福桥由此而得名(十多年前在二环路的人民南路立交桥下塑造了著名的“老成都民俗公园”,里面就有微型的万福桥,只是在匾额上把“万福来朝”误写作了“万福来潮”)。过去的成都人都把这道贴金大匾视为招祥祈福的吉祥物,新人结婚时,不少人家都要把花轿抬到这里来过一次桥,叫作“踩桥”,用以祈求安康吉祥,是当时成都民俗文化中的一个很热闹的内容,就好比今天成都结婚的新人好多都要到合江亭去拍一张婚纱照,用以祈求百年好合一样。除了新婚夫妻,正月十五之前的新春佳节期间,也有不少人来到万福桥“踩桥”,以求吉祥。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1947年万福桥被洪水冲毁才结束。
过去的府河水量远比今天的大,从上游夹带而下的沙石也比今天的多。府河进入成都城区后,在今天的西北桥拐了个弯,又在今天的五丁桥前分出了饮马河,水势明显减缓,于是在万福桥一带沉下大量河沙,万福桥也就成了过去成都人在河中捞沙的主要地段,常年有两三只打沙船在河中用类似大钳子一样的“打沙夹”在河底捞沙,故而有些文人还把这里的“夕阳沙船”作为了成都一景。也因为这一河段水流平缓,河底多沙,河岸边还有沙滩,这一河段就成了成都人游泳的好地方。1966年成都市第一个正式开放的天然游泳场就设在这里,名为万福桥天然游泳场。只可惜就在这一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所以这个万福桥天然游泳场只存在了一个夏天。
早已名闻中外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万福桥头。
暑假在河里戏水的儿童1962年 杨永琼提供
20世纪70年代开在西玉龙街的陈麻婆豆腐店陈志强提供
陈麻婆是一个麻面妇人,娘家姓刘,生于清嘉庆九年(1804),于道光四年(1824)与其夫陈春富在万福桥头开设乡村饭店“陈兴盛”,为进出北门的平民顾客服务,因为擅长做以“麻、辣、脆、嫩、烫、鲜、浑”为特色而又物美价廉的红烧豆腐而日渐闻名。因为来往的顾客都称她为陈麻婆,她烧的豆腐也被人们称之为陈麻婆豆腐。陈麻婆病逝于清咸丰八年(1858),因为夫妇无子,由女儿鲁陈氏与女婿鲁希智继承家业。鲁陈氏病逝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由其子鲁世权继承家业。此时的小饭馆已被《成都通览》列名于成都的22家“成都著名食品店”中。冯家吉于1924年刊印的《竹枝词》中也曾经写道:“麻婆陈氏尚传名,豆腐烘来味最精。万福桥边帘影动,合沽春酒醉先生。”几十年来,这家著名的小餐馆一直都没有挂出过陈麻婆豆腐店的招牌,陈麻婆豆腐也不是一道正式的菜肴名称,只是人们口中流传的一道菜名。一直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万福桥畔又有人家开了一家饭馆,店名叫“江头归”,对外宣传时也说是自己最擅长做红烧豆腐。为了与“江头归”相抗衡,陈家后人才正式打出了“麻婆豆腐”的菜肴名。麻婆豆腐不仅正式命名的时间较晚,制作店招更晚。现在大家所见到的店招是1966年由著名书法家余中英书写之后制作的。
直到现在,麻婆豆腐仍然是川菜中最有名的代表菜之一,1952年由川籍厨师陈建民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人民最喜爱的菜肴之一。正因为麻婆豆腐最初是诞生在万福桥头,今天成都市饮食公司所开设的麻婆豆腐餐厅的总店仍然设在当年的万福桥头之西、今天的人民北路大桥之南。
万福桥桥头北看人民北路 20世纪60年代 王文相摄影
星辉桥
这是一座新桥,是在府河与南河综合整治时,城建部门为了方便花圃路与城隍庙市场的大量行人与车流,在星辉西路与大安西路之间的府河上修的一座桥,形状颇像南河上俗称的“彩虹桥”(“彩虹桥”的正式名称是南门桥)。当城建部门还没有为这座桥正式命名时,人们就把这座桥称为北门彩虹桥或小彩虹桥,一直使用到现在(包括大多数地图),而星辉桥这个正式的名字反而很少有人使用。
在本书修改定稿的时候,在星辉东路与大安东路之间的府河之上又修建了一座大桥,施工部门公布的名称叫星辉东路桥。
北门桥(北门大桥)
从北大街向北的北门桥是一座古桥,虽然曾经有过多次改建,但其位置基本未变,所以无论是老成都人还是新成都人一般都把它叫作北门大桥。清代重建的北门大桥是一座三洞石拱桥,长54米,1952年改为缓坡,1966年扩建为较为宽阔而平缓的五孔石墩桥,一直使用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改建为一座钢筋混凝土平桥,很多老成都人至今都还记得当年拱桥上面的那些石栏杆。
今天的北门大桥是清代的北门外的大桥,清代的成都北门名叫大安门,又叫迎恩门,所以北门大桥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大安桥”或“迎恩桥”,但是成都人一般都将其叫作北门大桥。
几十年前,北门大桥一带还有一些船码头,而在一百年以前,从这一带一直到合江亭、九眼桥一线则长期有着十分繁荣的水运业,是成都地区与金堂、新津并列的三大港口之一。当时从彭山、眉山等地上行的中小型木船,从灌县、郫县漂流而下的木材、竹子以及运货的小船与筏子都云集于此,来自四面八方的各路客商一年四季在此奔忙。码头有柴草码头、煤炭码头、百货码头、盐码头、粪水码头、砖瓦码头、石灰码头等专业分工,其景象就有如今天八里庄的火车站。在各种运来成都的货物中,又以家家户户一日三餐所大量使用的木柴的数量最大(成都人做饭的燃料长期是以木柴占绝大多数,只有极少数的团体伙食团和餐馆才用煤炭,后来家家户户使用的蜂窝煤是1955年由廖新祈工程师发明的)。只是由于河道在近代不断加剧的严重淤塞失修,同时,因抗日战争时期公路的修建而出现了更为快捷的汽车运输,锦江的水运业才逐渐衰退,锦江中船只往来、江岸边码头林立的景象也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北门大桥 1993年 周筱华摄影
北门大桥侧的府河石梯1994年 陈维摄影
在北门大桥之下,还有在老成都人心中印象深刻的“十八梯”,即用红砂石砌成的18级台阶,附近的人们就是经这18级台阶上下挑水,包括不少茶馆中冲泡“河水香茶”的用水。在没有水文测量的年代,这个“十八梯”也正好作为人们观察水位涨落的标志。每到夏天,人们担忧是否会有洪水到来,总会有不少人不时询问:“十八梯的水涨到好多梯了?”
府河北门桥段,左岸街道是金华街。 1994年 周孟棋摄影
如今在成都开了无数家的小吃肥肠粉在改革开放以前并不多见,民国时期就更少(笔者在清代文献中还没有见到相关记载),而民国时成都最著名的肥肠粉小摊就摆在北门大桥北边曹家巷口,人们都喊为肠肠粉。《锦城旧事竹枝词》是这样描述的:“天色微明炉火熊,桥头贾客过匆匆。肠耙汤滚加椒水,一碗银丝暖融融。”现在老一辈成都人仍然称之为肠肠粉,而年轻一代才称之为肥肠粉。
太升桥
位于太升北路与马鞍南路之间的太升桥也称太升北路大桥,是新建太升北路时新建的大桥,也因为太升北路而得名。
太升桥头卖鞋垫的老人 2009年 苟世建摄影
太升北路和相连的太升南路,是1989年在市中心新建的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这条大街从提督街向北,再通过马鞍南路和马鞍北路直通北一环路,沿途经过了很多条小街。所以命名为太升路,并不是如有的介绍所说是取自于“东方红,太阳升”,而是因为这条大街是先修太升南路,后修太升北路,都是在原有若干条小街拓宽取直的基础上修成的。在太升南路这一段原有5条小街,最南端的是从提督街到兴隆街的太平街,最北端的是从童子街到玉沙路的升平街,所以就取了太平街与升平街的头一个字,名为太升南路,向北的一段就叫太升北路,太升北路北端新建的跨于府河上的新桥,就叫太升桥。
太升桥向北越过马鞍南路、马鞍北路可上一环路北段,车辆行人不少,这座桥是城区重要的通道之一。
红星桥(一号桥)
红星桥也称红星路大桥,是市中心连接北郊工业区和八里庄火车货站的十分重要的一座大桥,也是几乎所有的成都人都走过的大桥,可是几乎所有的成都人都把它叫作一号桥。这是怎么回事呢?
红星桥附近河道两岸 1984年 王晓庄摄影
原因是这样的:1954年新辟红星路的时候,这条大街和架于府河上的这座桥都没有命名。市政工程在设计施工时,要在府河上修建三座木桥,因为这座桥最先施工,就编号为一号桥,这是一个工程的代号(大约同时上马的还有二号桥也就是后来的新华桥,还有三号桥也就是后来的万福桥,即人民北路桥,最初的设计都是木桥,以后才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大桥)。1959年改建时仍然沿用了一号桥这个名字,当大桥完全建成并正式命名为红星桥之后,大家已经很难改口,就一直叫一号桥。就这样,除了正式的地图之外,一号桥的名字就一直使用到今天。
红星桥 2009年 林立摄影
成都市的行政区划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到今天曾经有过六次调整。目前的行政区划是在1990年9月确定的,市区共分为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锦江5个区,从此就以“五城区”来称呼成都市的城区(也叫主城区,除城区以外还有原来属于郊区的14个区、市、县,共为9区、4市、6县)。可能很多成都市民都不知道,成都城区唯一的一个四区交点,就在红星桥。如果我们向北站在桥上,左前方是金牛区,右前方是成华区,左后方是青羊区,右后方是锦江区。关于这一点,相关四区在1997年进行了勘界确定之后曾经签订有边界协议书,其中有这样的约定:“四区交汇点位于成都市红星桥(一号桥)府河北岸桥头西北角”。
新华桥(二号桥)
新华桥也称新华路大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修新华路时新建的大桥,是市中心连接东郊工业区最重要的一座大桥,成都人一般都叫二号桥,其原因与上述把红星桥叫作一号桥完全一样。
新华桥一带的河道 1989年 王晓庄摄影
红星桥和新华桥是姐妹桥,都是在1954年建成木桥,1960年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新桥。它们的长度都是82.8米,只是宽度有所不同而已。
成都城区最大的儿童游乐场和最大的游泳场——猛追湾游泳场就在新华桥桥头,近年新建的四川电视塔也在新华桥桥头。
新华桥 2009年 林立摄影
武成门桥(新东门大桥)
武成门桥是新东门之外的一座桥,所以成都人一般都把它叫作新东门大桥,连一些地图上也写为新东门大桥。我们在前面介绍新东门时已经谈到,武成门是1914年在东边城墙上新开的一道城门。当时的市政当局于1915年开工在武成门外修建一座砖石拱桥,但是在工程进行中因为工程款被侵吞而停工,直到1927年这座五孔砖石拱桥才建成,是民国时期在府河上修建的唯一的一座砖石拱桥。当时还有过“顺江桥”和“东安桥”等不同名字,桥在1947年的洪水之中被冲毁,1949年修复。现在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是在1970年扩建的。1997年,成都市地名委员会正式命名其为武成门桥。
新东门大桥在修建中因为缺钱而停工时,是川剧泰斗杨素兰慷慨解囊,捐助了大部分工程款,方得以建成。但是杨素兰未能见到大桥通车就饮恨辞世了。
新东门大桥 20世纪50年代 陈德龙摄影
20世纪80年代的武成门桥 杨显峰提供
杨素兰(1878—1926),遂宁人,清末川剧艺人的杰出代表,主攻青衣,兼演其他旦角,在世时就被称为“旦角泰斗”。他德艺双馨,无论在业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有极好的口碑。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高潮中,他捐出60亩水田用作修建川汉铁路的资金,在当时曾经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1912年他和其他川剧艺人共同组建了著名的川剧团体“三庆会”,并出任第一任会长,还和大家提出了“同辛亥革命同休咎”的口号。在他的主持下,“三庆会”为川剧艺术的改革,为近代川剧的形成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东风桥
东风桥又称东风路大桥,是蜀都大道上横跨府河的重要大桥。
东风路是1958年新建的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在修建东风路的同时,新修了这座三孔砖石拱桥,1981年扩建蜀都大道时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大桥。
东门桥(东门大桥)
20世纪40年代的东门大桥杨显峰提供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东门大桥 陈德龙摄影
20世纪60年代的东门大桥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成都人今天所称的东门大桥的东门,就是老成都城的老东门迎晖门,门内就是古老的东大街。老东门外的大桥是一座古桥(清末补修时曾经发现宋碑,可知至迟在宋代已经建桥),所以老成都人都把这座桥叫作老东门大桥或东门大桥。宋人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称此桥叫濯锦桥,明代也叫濯锦桥,清代改名长春桥。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和光绪十二年(1886)经过两次重修,是三洞的石拱桥,两边有石栏杆。从宋代就有濯锦桥的名字和明《天启府志》中有关“濯锦桥,府城东门外,其下有坊,江合二水,濯锦鲜明”的记载来看,古人是既在南河中濯锦,也在府河中濯锦,还在两河合流之后的府河中濯锦。所以,无论是南河和府河,在过去都是美丽清冽的,古人把它们都称为锦江,我们今天当然也应当把它们都称为锦江。
老东门大桥桥基 1995年 韩国庆摄影
东门大桥一带在民国时期是全城有名的乞丐集中区,桥下的桥洞就是乞丐们晚上的栖身之所,被时人戏称为“王爷庙”。
1950年、1952年和1965年,东门大桥曾经有过三次维修扩建,前些年在府河的综合整治中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扩建。
合江桥
南河与府河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成都的游览胜地。早在唐代,就建有著名的合江亭与芳华楼,与南河上游河畔的另外两个著名的楼阁张仪楼和散花楼组成了一条河畔的景观带。在合江亭旁,建有一大片掩映在绿树翠竹与花卉之中的楼阁台榭,号为合江园,当时就被称为“成都园亭胜迹之最”,同时也是锦江上的重要船运码头和行者往来之所。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中写道:“蜀人入吴者,皆自此登舟。”宋人吕大防在《合江园记》中对这里有一段描述:“合江故亭,唐人宴饯之地,名士题诗往往在焉。俯而观水,沧波修阔,渺然数里之远……”在宋末的战乱中,合江亭与合江园全部被毁,一直未能重建,明清时期这里仅仅是官家收取船税的地方,到了民国时期就完全成了一片荒地,只剩下一个合江亭的地名。
汇入南河前的府河两岸 20世纪70年代王文相摄影
刚建成的合江亭与合江桥 1989年 王学成摄影
这里长期无桥,只是在府河出口处有渡船摆渡。1970年建过木桥,1987年才在这里修建了今天的合江桥。1989年,又在这里重建了合江亭,江边高台之上双亭连体的八角亭净高12米,亭下还建有与之配套的一楼一底的听涛舫。1991年,成都评选新的蓉城八景,合江亭景点入选,并被命名为“解玉双流”,因为合江亭是目前唯一能够观赏左思《蜀都赋》中“带二江之双流”这一名句所描绘的二江双流胜景的地方。
就在新建合江亭之后不久,成都开始了府河与南河的综合整治工程,这一工程完成之后,合江亭下、合江桥畔就成了一处极为漂亮的水景小游园思蜀园。一对对结婚的新人们既欣赏这里的美景,更喜爱“合江”二字所包含的二江合一、永不分离、和和美美、江流不息的寓意,纷纷在大喜的日子到这里拍摄婚纱照,而且一年比一年人多。每逢吉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来此拍摄婚纱照的新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超过200对。为此交通部门不得不集中大量警力到现场疏理交通,还应群众的要求在街道上画上了一条醒目的“爱情斑马线”以供新人过街。从2004年起,成都交警三分局正式打造了“合江亭婚庆保障服务模式”,合江亭下的天仙桥南路也逐渐形成了以婚庆服务业为特色的“婚庆一条街”。笔者认为,如果要寻找改革开放之后成都出现的新民俗,“合江亭下结鸳鸯”应当排名第一。
合江亭“爱情斑马线”上的新人与亲友 2009年 李杨摄影
安顺廊桥
府河和南河汇合之后,向东流去,一直到下河心村汇入分出的沙河,仍然叫作府河。这以下直到彭山的江口与岷江相汇,过去也可以叫作府河,按现在的规范化名称,是应当叫作锦江。在与沙河汇合之前,府河上还有几座重要的桥梁。
我们到了合江亭附近,就可以见到合江亭下游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很漂亮的双层廊桥,桥上还有一家陈设很讲究的川菜酒楼,这就是2003年才新建成的安顺廊桥。安顺廊桥借用了上游的老安顺桥的名字,并仿老安顺桥廊桥的风格,为打造水井坊旅游区而修建的。其主要作用是用于观光旅游和餐饮服务,而不是为了行人过河的方便,虽然行人也可以从桥上通过。
如今到安顺廊桥上游赏,可以看到廊桥上的元代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雕刻。马可·波罗是第一个向世界介绍成都的外国旅行家,在他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第113章“成都府”中这样写道:
“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深,广半哩,长延至于海洋,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其名曰江水。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于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城内川上有一大桥,用石建筑,宽八步,长半哩。桥上两旁,列有大理石柱,上承桥顶。盖自此端达彼端,有一木制桥顶,甚坚,绘画颜色鲜明。桥上有房屋不少,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
新建的安顺廊桥 2005年 严永聪摄影
锦江河畔交相辉映的安顺廊桥与香格里拉大酒店 2009年 顾求实摄影
这是最早向海外具体描绘成都锦江中的水运盛况和廊桥上商业活动的外国作家的文字。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可·波罗行纪》中所描绘的桥就是元代的安顺桥,所以安顺廊桥的设计者才会在安顺廊桥上安排了有关马可·波罗的雕塑。无论上述说法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真实,我们今天对这类描述都可能会“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因为成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九眼桥附新九眼桥
九眼桥是成都东南角最重要的、也是近代成都市区内保存年代最古老、规模最宏大的桥梁,长期有成都“东南形胜”之誉。
清代九眼桥 [法]杜满希提供
九眼桥这个位置的锦江河段,是古代成都最重要的水运码头,载客载货的船只与上船下船的车辆、行人不少,所以很可能自唐宋以来就应当有桥,只是今天已经见不到有关的记载。根据明代天启年间的《成都府志》记载,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起,在四川布政使余一龙的主持下,花了五年时间在这里建成了一座宏伟的石拱桥,因为地处两河汇流之下游,江面宽阔,所以名为洪济桥。“桥成,为洞者九,纵四十丈,横四十尺。远而望之,虹舒电驰,霞结云构,若跨碧落而太空为门;俯而瞰之,飙涌涛舂,鲸飞鲵走,若驾溟渤而巨浪为溜。”明天启年间改名为锁江桥。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四川总督李世杰的主持下又做了一次补修。因为桥下有九个桥洞,民间一直称为九眼桥,但是以洪济桥得名的街名至今仍保留着,就是桥北的宏济路。
这座古老的石拱桥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长度是90米,宽度是10米),行人往来不绝,而且通行汽车。1953年进行了一次大修,加修引桥并将拱背的坡度减小,铺了沥青。1959年和1966年又进行了两次维修,在两侧加宽了人行道。随着成都经济的迅速发展,古老的九眼桥实在不堪重负,1986年在老桥上游14米处新建了半立交的新九眼桥。新桥的主桥长88.41米,引桥长26.21米,桥宽40米。由于建了新桥之后,老桥已经失去了交通的功能,多个桥墩又不利于泄洪,遂在1992年被拆除。
20世纪80年代初的九眼桥 成都市府南河管委办资料 周筱华提供
古老的九眼桥被拆除之后,成都不少人就此事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九眼桥是成都名胜,应当作为历史文物而在新建的大桥旁边被保护下来(这种新旧并存的格局曾经存在了6年),而规划部门则认为新旧两桥并存对防洪不利。为了对两种方案进行一个合理的折中,2000年就在需要建桥的河滨印象小区的府河上新建了一座与九眼桥相似的桥,用以保留九眼桥在人们心中的记忆,而且就命名为新九眼桥。
九眼桥南岸一带长期都是锦江中的重要水码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然还有若干船只停泊着,船中的主要货物是家家需要的木柴。
九眼桥因为邻近郊县,所以这里曾经是成都最有名的“人市”之一,过去不知有多少贫苦人家在走投无路之时被迫在这里卖儿卖女。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人市”都被取缔。改革开放之后,成都最早的自发的劳务市场也是出现在九眼桥上游的北岸,由政府进行了规范化管理之后,就正式命名为九眼桥劳务市场。为了有更大的空间和更有效地管理,这个劳务市场后来被迁往东二环之外的郭家桥地区。由于九眼桥劳务市场这个名称实在是影响太大,新的劳务市场虽然已经远离了九眼桥,人们仍然把它称为“九眼桥劳务市场”。
九眼桥劳务市场 1995年 杨永琼提供
成都人一提到九眼桥,就会与四川大学联系起来,因为位于九眼桥侧的四川大学已经在这里办学60多年了。
四川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地址在总府街以南的三圣祠街。1902年,四川中西学堂与著名的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完成了四川高等教育的古今交替,成为四川省的最高学府,学校校址为南较场原来的尊经书院旧址。在经过与其他几所学校的几次合并之后,发展为1931年成立的国立四川大学,设4院11系,还有两个专修科,是当时我国13所国立大学之一,也是西部唯一的国立大学,校长是王兆荣。国立四川大学的校本部在原来的贡院(即成都人所称的“皇城”),还有一部分设在南较场。抗战爆发之后,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学校于1939年9月迁到峨眉山继续办学,校本部和文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设在伏虎寺,理学院设在保宁寺和万行庄,教职员宿舍设在报国寺,新生院设在鞠槽将军府。1943年初开始迁回成都九眼桥侧的新校区。
刚建成的四川大学新校园 1943年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四川大学新校区始建于1937年6月6日。新校区的选址是对狮子山、南台寺、白塔寺等几处地方考察比较之后确定的,新校区的建设是在当时的校长任鸿隽的主持之下进行的。任鸿隽仿武汉大学在城外建校的成功先例,将难于发展的城内贡院的土地向四川省政府换来了锦江边的2270亩农田(川大原来的农学院就设在这里),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筹得4150万元经费,聘请著名建筑师奚福全与吴颂声主持设计。从第一批建筑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开始修建,一直到1947年,修建和接收旧房的改建才基本结束,从九眼桥到三瓦窑,连绵十余里。任鸿隽不仅是四川大学新校区的奠基人,也是从成都走出去的我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
任鸿隽
任鸿隽(1886—1961) 成都人(生于垫江),1908年赴日本留学,一边学习化工,一边参加民主革命,曾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他在日本写出了著名的《川人告哀书》和《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并立即回国。回国后,与吴玉章、杨杏佛同任孙中山先生秘书。辛亥革命后他因受袁世凯的迫害而远走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15年,他与杨杏佛、赵元任、秉志、周仁等人创办中国科学社并出任社长,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先后出任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专任秘书和干事长,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他与胡适等共同筹建了北京图书馆,与蔡元培等共同筹建了中央研究院。1935年,四川省聘他出任四川大学校长,他立即回到了家乡就职,并对长期基本上处于盆地内封闭状态的老川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向全国礼聘名师,从全国招收优秀学生。选址征地2270亩修建锦江畔的新校区,是他对四川大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因为他的夫人、著名世界史学者、中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作家与诗人,笔名莎菲)撰写了《川行琐记》《四川印象记》等文批评了四川社会生活的若干弊端,引起四川守旧派人物的忌恨并迁怒于他,使他难以继续施展抱负,乃于1937年6月主持了新校区的奠基典礼之后辞去川大校长职务(继任校长是他的好友张颐,他的一系列建校方针由张颐继续完成),应蔡元培之邀去中央研究院任干事长。1949年,他应邀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晚年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联主任委员、上海图书馆馆长。
任鸿隽、陈衡哲夫妇
四川大学(包括其前身)作为四川省最早和最重要的大学,多年来既有很多名师在此执教,也有很多著名人士在此学习。1906年至1908年,朱德(当时名朱建德)在四川高等学堂体育科甲班读书。1912年,郭沫若是四川高等学堂正科二部的学生。1922年至1924年,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担任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1926年至1931年,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以后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曾经担任成都大学校长,上述几个学校都曾是四川大学的前身。著名学者朱光潜、钱穆、周太玄、吴大猷、张奚若、肖公权、潘重规、刘大杰、向楚、林思进、庞石帚、赵少咸、谢无量、蒙文通、刘鉴泉、卢冀野、钱崇澍、吴君毅、魏时珍、李珩、徐中舒、丁山、闻在宥、冯汉骥、缪钺、罗念生、熊佛西、卞之琳、桂质柏、张文裕、彭迪先、杨东莼、陶大镛、张怡荪、柯召、杨允奎、杨开渠、方文培、吕子方、刘承钊、袁翰青、侯光炯等都曾经在学校任教。
四川大学正门 1958年 杨永琼提供
1944年四川大学校园内出土的唐代印刷品《陀罗尼经咒》
1944年4月,四川大学在邻近锦江的校园内修建道路时,发现了一座唐墓与三座宋墓。在唐墓的死者骨架臂上的空心银镯内发现了一个用蚕茧、桑皮、麻、檀木浆混合制作的纸卷,纸上是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右边首题汉字一行“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家□印卖咒本”。主持发掘的冯汉骥老师(当时正在川大教授考古学)经研究后确定这件印刷品的刻印时间应当在公元757年到907年之间,是目前保存在我国国内唯一的一件唐代印刷品实物,也是全世界可以明确刻印时间与地点的两件最早的印刷品实物之一(目前全世界发现的唐代印刷品还有几件,但是都无刻印地点的明确记载,有记载的两件都是刻印于成都,这是成都作为全世界最早的印刷术中心的铁证),是极为珍贵的国宝。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院系调整,原来的四川大学分出了部分院系,与其他学校部分院系新开办了成都工学院、四川农学院和四川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于1954年的成都工学院在1978年改名为成都科技大学。1994年,四川大学又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为四川联合大学。1998年,四川联合大学又与华西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四川大学。新的四川大学现在有望江校区、华西校区和江安校区三个校区,占地面积7000多亩,现有本科生近4万人,硕士博士生近2万人,此外还有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和网络教育学生。
望江桥(玉津桥)
1980年,在望江楼公园与府河对岸的龙舟路之间,曾经架有一座只供行人通过的古色古香的砖石结构的双曲拱桥。因为这里曾经是过去的玉女津,因而取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玉津桥,但是没有流行和使用,大家都把它叫作望江桥。1999年防洪部门预报该年可能有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为了不阻塞河道,遂将该桥撤去,这座桥只使用了18年。
20世纪80年代望江公园鸟瞰 杨显峰提供
清末雷神庙中的阁楼 杨显峰提供
锦江岸边望江楼公园地区原来是江边一处重要的水码头,本名叫玉女津,既有少数的房舍与店铺,也有一些林木,还有一座清嘉庆十九年(1814)由四川总督常明修建的雷祖庙(也称雷神庙,旧址就在今天望江公园中薛涛纪念馆)。在雷祖庙侧有一口水井,水质清冽,在明代以前也被称为玉女津。自唐宋以来,成都造纸业的主要地区都在今天的浣花溪至百花潭一带,著名的薛涛笺就是用浣花溪水制成的。到了明代,百花潭淤积,水质不佳,蜀王府就在玉女津设立了一个制作笺纸的作坊,用清冽的井水仿制闻名已久的薛涛笺。过去曾有《竹枝词》记其事:“一泓秋水色澄鲜,十样翻新出井边。绝似美人颜色好,诗成争擘浣花笺。”由于受一些诗人墨客所写的怀念薛涛的诗作影响,时间一长,这口水井在明代就被误称为薛涛井。清康熙三年(1664)成都知府冀应熊在此立了一个刻有“薛涛井”三个大字的石碑,周围的一些建筑也逐渐被附会为薛涛故居。不过这种误解在一些了解薛涛史事的学者们心中是很清楚的,清代著名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他的《薛涛井》一诗中就是这样写的:“不见薛笺惟见井,琅玕万个绿阴阴。何人刻竹留题满?我欲编诗入笑林。”
薛涛井水的知名度在成都一直保持了几百年,明代以制笺闻名,清代以制酒闻名(清代曾有作坊在这里取井水酿酒,而且名字就叫薛涛酒,今天的全国名酒全兴大曲的初创期也曾专门取这口井中的水酿酒,所以有《竹枝词》说:“枇杷深巷旧藏春,井水留香不染尘。到底美人颜色好,造成佳酿最醺人。”)。一直到清末,薛涛井水仍然是官府招待外来重要官员的专门饮用水,是总督府泡茶的必用水。清末的《成都通览》说它“井水甘洌,为成都第一泉”;“城外之井水,以望江楼之薛涛井为第一,上年秋闱(指全省的科举考试)之试官及委员,均饮此水”。据前辈回忆,民国时期成都的著名茶馆,如少城公园的鹤鸣、东大街的华华、春熙路的饮涛,都是雇专人从薛涛井中挑水或用板车运水以供泡茶之用。
1908年的望江楼 [英]威尔逊摄影 杨显峰提供
1926年的望江楼 [日]岛崎役治摄影 杨显峰提供
望江楼前的玉津桥 20世纪80年代 陈道洋摄影
薛涛是唐代诗坛上最负盛名的女诗人,虽然出生在长安,但是自幼便随父亲薛郧来到成都。她在成都长大成人,作诗制笺,交友成名,卒于成都,葬于成都,所以在文学史上都称她为成都女诗人。她在成都的故居本是在今百花潭一带,但因为她利用当时成都在全国最为高超的造纸技术,亲手制作了一种远近闻名的彩色诗笺,被后人称为薛涛笺,而明代的蜀王府又在玉女津仿制薛涛笺,于是玉女津地区就与薛涛发生了愈来愈多的联系,不仅有了薛涛井,在与望江公园一墙之隔的四川大学校园内,原来还有一座薛涛墓。笔者在川大生活时曾经多次在墓前流连(薛涛墓在宋代就有记载,川大校园中的薛涛墓虽然已被证明不是真墓,但是在1883年还有“浙西沈寿榕”主持的重修,立有石碑,仍然是一处纪念地。此墓在1970年初毁,2006年全毁)。由于几百年来有愈来愈多的薛涛崇拜者来此凭吊,这里与薛涛有关的各种纪念性建筑愈来愈多,就作为纪念薛涛的文化活动中心。直到今天,望江楼公园仍然是全国唯一的薛涛纪念地,全国性的薛涛研究会就设在这里。1984年,望江楼公园内塑造了薛涛的汉白玉雕像,设计者是温昌绪。
薛涛井 1934年 庄学本摄影
清人绘制的薛涛像
成都诗婢家仿制的薛涛笺
玉女津原本有一些接待旅客的休闲性的建筑,在明代时就已经有了一座临江之楼,明代著名的成都籍文学家杨升庵就曾经在《江楼曲》中写过“江上楼,高枕锦江流”。此楼在明末毁于战火。清嘉庆年间,成都的地方官在这里修建了一些纪念薛涛的楼阁。清光绪十二年(1886),由马长卿发起并主持事务,由一批成都士绅募款,经各府州县推荐遴选,由崇宁县唐昌镇的木工杨前生、杨燕如叔侄二人设计并充任正副掌墨师,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崇丽阁。其得名来自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崇丽阁于光绪十五年(1889)建成,共有4层,通高27.25米,全木穿斗式结构,没有一颗钉子,是清代成都城区最高的建筑,也是多年来成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由于杨前生为此楼的修建立下了赫赫功劳,当时的四川总督刘秉璋破例特赐他以“木秀才”的顶戴殊荣。2009年10月23日,望江楼公园举办了首届望江楼古典文化艺术节,以庆祝望江楼建成120周年。
谈到崇丽阁等建筑的修建,我们不应当忘记马长卿。
马长卿 华阳人,出身富商,光绪五年(1879)举人,曾官至直隶州知州。但是他对仕途兴趣不大,而是回到家中经营实业,成为当时成都最著名的商人,织机帮(即织锦业)巨头,并开有大型绸缎与百货铺,在宜昌、汉口、上海等地都有商号,时人誉之为“成都之卓、郑”(按:指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蜀中巨富卓王孙、程郑)。他一生热爱公益事业,特别热爱园林景观的修建。他不仅倡议并主持修建了崇丽阁,捐款数他第一,以后又继续捐款主持重建了望江楼公园之中的濯锦楼、浣笺亭、吟诗楼,新建了五云仙馆,还凿有流杯池。在修建崇丽阁的同时,他还修缮过万里桥。民国《华阳县志》卷二十八在《万里桥》中记载说:“光绪中,县人马长卿复加营缮,虽制无更变,而坚固逾昔,于今利赖也。”在他的晚年,还在遇仙桥畔修建有当时成都西郊最著名的园林名胜马家花园。
崇丽阁自建成以来,已经进行过四次全面维修(最大规模的一次在1993年,解决了因为地基下沉引起的楼体倾斜问题),1928年正式辟为“成都郊外公园”。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3年更名为望江楼公园(成都人一直简称为望江公园,但是它的正式名称只能是望江楼公园),并设立了“薛涛资料陈列室”。经过了多次的扩大与补建,现在的望江楼公园不仅是纪念薛涛的胜地,还是全国竹类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公园,栽培有各种竹子两百多种,终年浓荫蔽日,摇曳多姿,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
崇丽阁(望江楼) 1959年 牟航远摄影
自从崇丽阁建成以来,成都人几乎从来不把它叫作崇丽阁,而是叫作望江楼。这种俗称之所以广为流行,是因为有一种见诸记载而且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崇丽阁建成之时,四川总督刘秉璋在此大宴宾客,以资庆祝。酒酣耳热之际,刘秉璋出了一个上联求对,即“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这个上联当时无人对出下联,但是很多人都想对出有水平的下联,于是望江楼的名字也就随着这个上联而广为流传,从而代替了崇丽阁的本名(顺便在此说明的是,这个上联至今仍然没有人能够对出可以与上联匹配的下联)。在没有汽车与火车的时候,成都人要走出盆地、走向世界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锦江中的木船,无数成都人背井离乡与亲人告别的地方就是锦江上的水码头,无数成都人在崇丽阁上望过顺江而去的船只,盼过远在天际的帆影。所以笔者认为,崇丽阁在大多数成都人的心中不是用来吟诗的,而是用来望江的,用来望江上的亲人的。因此,望江楼的名字肯定会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象,望江楼这个名字的流传,应当是人们内心的种种深情的自然流露。关于这一点,清人冯骧在他的《江楼竹枝词序》中说得很好:“望江楼,胜境也。西接岷江,东通夔万,揽益州之胜景,据长江之上游。楼阁高标,云山环绕,水波浩瀚,沙鸟纷飞。每当春和景明,天清气爽,骚人墨客,因选胜而遥临,绿女红男,共寻芳而缓步。此凭栏而载酒,彼破浪而乘风,其胜概豪情,盖与登楚之黄鹤楼、湘之岳阳楼,无以异也。”
1912年,著名学者吴虞应邀去乐山,他曾经记下了行船的途程:第一天中午在安顺桥登船,到薛涛井登岸,望江楼下喝茶宴饮。第二天一早登船,到苏码头上岸用餐,然后继续航行,水上有点逆风,当晚在张家坎夜泊。第三天仍是一早开船,在刘家场用餐,午后三点即到乐山。从他的行程看,水上行程不到两天,每天用的是两餐。
稍为年长一些的成都人都会记得,过去成都每年端午节时,有热闹的赛龙舟、抢鸭子民俗盛会,也都是在望江楼公园外面的锦江上举行的。直到在九眼桥下新建了橡皮坝之后,这一活动才向上游迁移,改在今天的安顺廊桥上游举行。
自古以来,锦江就是成都人餐桌之上各种鱼类源源不断的供应者。笔者从老一辈成都人的回忆中所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妇女在河边洗衣,衣服里能裹到鱼;男人在河里游泳,脚板能踩到鱼;小孩在河边玩耍,青苔里能捡到鱼;挑夫在河边挑水,桶里能装进鱼……有一次在望江楼下,两个游泳的小伙子从河堤石缝里一次捉了三四十条一尺多长的鲢巴郎。另一次是在蓥华寺(旧址在原来的十九中、今天的田家炳中学)的河边发现了一条卡在下水道中不能游动的大鲤鱼,当地居民用锄头把大鲤鱼挖死以后才取了出来,然后抬到猪肉案桌(即肉铺),就像杀了大肥猪一样肢解瓜分,一人分到十几斤鱼肉。
由于锦江水量愈来愈少,望江楼下已多年未见船影了。成都市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想法恢复沿锦江东下的航运,哪怕是船只不再载货,形成一条旅游航线也好。
望江楼下的渡船 1948年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