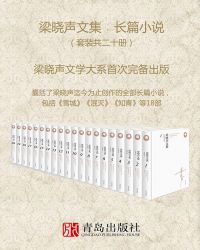第十八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八章
雪!……
从车窗望见大地上的雪,我才认为我是真正回到了我的北方。
我这个北方的儿子对雪有着一种对母亲般的亲情。一见雪,我是格外地想家了。离家不过两个月的时间,我却觉得像两年那么长。
哈尔滨——北京——成都——北京——哈尔滨,两个月内,竟没往家里写过一封信。不知母亲是怎样地日日夜夜为我的安危提心吊胆呢!大串联是我的第一次远足旅行。它使我亲眼目睹,全中国确是“天下大乱”了。据说乱是好事,可以暴露阶级敌人,锻炼革命“左”派。我想,十七岁的我,无疑是受到了一次锻炼的。起码我懂得了,鲍红卫之类,是应谨慎提防的。“张珊”和“姚舞”之类,是应不与之交往的。对于乱,哪怕是因自己而引起的乱,也不怎么惊慌了。这一点,差不多是当过红卫兵或虽未当过红卫兵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的共性。
“就凭这个阵势还想吓倒人啊?老子‘文化大革命’中领教过!”
在以后的一些小小的乱的场面,我常听到我的同龄人们这么说。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味。
“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是对我们共和国的一代人的彻底放任的“集训”。形成了他们与八十年代的青年风骨上气质上截然不同的区别。有人将一代红卫兵贬为“狼人”。这观点挺解恨,但并不完全正确。归根结底,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许许多多罪恶,倘全栽在他们身上,则无论怎么解释也不能够自圆其说,顺理成章。而他们正是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向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在全中国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反思的人们之中,一代红卫兵的反思尤为独特。他们的反思具有最属于他们的头脑的深刻。我在一本什么刊物上曾见到过罗丹那著名的雕塑——思想者的摄影,我欣赏了很久。思想者——这才更是一代红卫兵中仍未背弃对我们共和国的深厚感情的一批人的象征。倘剖开他们的胸膛,定会捧出一颗滚烫的心。这心内凝聚着一种使命——制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
当列车驶上松花江大桥,我不由将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那一年松花江封得迟。江心岛沙滩被雪覆盖得洁白无瑕。江水一点儿波浪也没有,像快要凝固了的岩浆一样缓缓地流。絮团似的雪花一接触水面,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江畔人迹寥寥,显得那么冷清。
我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就问借给我大衣穿的那个同校的红卫兵:“你看江畔是不是缺少了些什么?”
他便也将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也说:“真的,是缺少了些什么啊!”
于是好多人都将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
“咦?青年宫前的天鹅雕塑咋没啦?”
“江畔的雕塑怎么都没啦?”
原来缺少了的是一尊尊很美好的雕塑。
在我们这些哈尔滨市的红卫兵们离开它两个月的时间内,江畔的雕塑统统被砸毁了,扔到江里去了。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发议论:
“他妈的,准是外地红卫兵干的!”
“未见得,很可能正是我们哈尔滨红卫兵干的!”
“哈尔滨红卫兵可以到外地去砸。为什么外地的红卫兵不能到哈尔滨来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四旧’可以砸,别见什么砸什么呀!天鹅雕塑算‘四旧’吗?”
“那广州的‘五羊’算‘四旧’吗?不是也砸了个稀巴烂吗?”
“妈的!几个湖北红卫兵,分手时嘱咐我一定在天鹅雕塑前照张相寄给他们,砸了我还照个屁!”
“这就叫‘不破不立’嘛!”
列车已经开过江桥了,大家仍七言八语。仿佛只要这些人当时在哈尔滨,是断断不会允许那些很美好的雕塑被砸毁扔到松花江里似的。我想,这些人当时在哈尔滨,那些很美好的雕塑也注定了难逃厄运。说不定他们还亲自动手砸。砸,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可以谓之“革命”情绪罢。不砸,或者阻止他人砸,倒是会显得“别有用心”了。而任何的东西,只要是美的东西,当年大抵与“革命”格格不入。总能找出极正确的“革命”的理由砸它个稀巴烂!包括花鸟虫鱼。
“哈尔滨站”四个字是早已被“东方红城”取代了。列车在“东方红”乐曲中抵达“东方红城”,令人心格外引起一种波动。于我那冲动的原因却很单纯——管它叫“哈尔滨”还是叫“东方红城”,总归是到家了!
站台上两面旗帜迎风招展。一面旗帜上写着“八八团”,一面旗帜上写着“红色造反团”。两团的仪仗队肃立在站台两侧,之间有一段暂时“和平共处”的神圣距离。列车刚一停稳,两团仪仗队同奏两团团歌。
我们大为诧异,想不明白势不两立的这两大派组织,究竟为何抬举我们这些大串联归来的杂牌军,如此隆重地迎接我们。一个个从车窗探出脑袋,受宠若惊。
却白白浪费了一阵感情。迎接的并非我们,而是两团各自的赴京谈判代表。我们这些杂牌军,与名扬全国的两大派组织的赴京谈判代表同车归来,也够使我们很感到荣幸的了!
两团的谈判代表们当然没跟我们这些杂牌军混在一起。
各包了一节车厢,而且都享受着卧铺的舒适。在北京主持谈判的是周总理。据说两天内谈判了三次。据说他们当着总理的面互相大拍桌子,激怒了总理。总理后来也拍起了桌子。毛远新当时是“八八团”的大头目。而“红色造反团”的头目之一也是他们的赴京谈判代表之一的冯昭逢,则是烈士遗孤。据说还是总理的“义子”。名扬全国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头目们和赴京谈判代表们非等闲之辈,也就难怪总理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为他们主持谈判了。
两团赴京谈判代表踏下他们各自包的车厢,走向两团的仪仗队员们,纷纷与之握手。纷纷说: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敬爱的周总理支持的是我们!”
“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肯定了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说的差不多都是同样的话。也就无从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究竟肯定了他们哪一派?谈判的结果究竟圆满不圆满?倘说圆满吧,看他们那种相互敌对的态度丝毫未减,一如从前,分明在北京的谈判桌上并没有达成什么今后团结一致的协议,更没有当着周总理的面握手言和;倘说谈判破裂吧,听他们那些话,又仿佛对谈判的结果都感到十分兴奋。
从车站大楼内拥出了他们各自的团报记者,围向他们各自的代表,一手拿本儿,一手拿笔,提出一串串的问题,飞快地记录着。
“你对今后的斗争形势怎么看?”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你认为中央‘文革’内部存不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无可奉告。”
“我们‘红色造反团’有同‘八八团’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可能性吗?”
“这个问题应该向他们提出才对!我们‘红色造反团’决不同坚持‘保皇’派立场的组织实行什么所谓大联合!这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的斗争原则!如果他们重新选择他们的立场,我们举双手欢迎他们回到真正革命‘左’派的阵营中来!”
这一边儿在答记者问,那一边儿则在发表演说:
“我们‘八八团’绝不会重新选择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的立场,乃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立场。除了这唯一的立场,我们别无选择!谁诬蔑我们是‘保皇’派,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充当铁杆‘保皇’派!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不是我们‘八八团’的耻辱,而是我们‘八八团’的莫大光荣!……”
这一边有人以十足的外交家风度含沙射影。那一边有人以杰出的演说家风度慷慨陈词。两边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耀。情形使我们这些车上的杂牌军叹为观止。对两边都打心眼儿里肃然起敬。造反造到坐包厢车进北京,由周总理亲自出面从中调解谈判的份儿上,才算不枉“造反有理”了一次啊!
除了两派赴京谈判代表的两节车厢,其他车厢都没开门。乘务员们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手攥着钥匙把守车厢门口,等两派前来迎接的仪仗队员、记者簇拥着他们各自的代表,热热闹闹地离开站台,才打开车门。
杂牌军们争先恐后往车下跳,往出站口跑,都想要看到两派在站外继续什么名堂,什么热闹。
我也跟着人流跑,挤。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他拍摄的一部影片中,运用了一个情节形象地揭示了人的这种爱凑热闹的心理:年轻的男主人公本是为着追踪一个凶手才进入游乐场的——台上现代派歌手们在如痴如狂地演唱摇滚歌曲。其中一名歌手将电吉他连摔带踏弄得四分五裂,抛向观众,于是观众发了疯似的去夺去抢,人压人,脚踩手,抢夺得乌烟瘴气。于是主人公在那样一种氛围之下也一时忘了去寻找杀人凶手,也扑上前去夺去抢,抢到了电吉他的上半部,冲出重围撒腿就跑,身后许许多多人拼命追。终于他甩下了追他的人,气喘吁吁地站住了,看着手中那半截电吉他弦把,滴里当啷乱绕着弦,弦上还挂着些碎木片,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发了疯似的与别人去夺去抢这半点儿用处也没有的破烂东西,他甩手就把它扔了。穷追不舍追到他跟前的一个人立刻弯腰如获至宝地捡起来,可看了看同样觉得真是半点儿用处也没有,也甩手就把它扔了。它绊了一个行人的脚,那行人一脚将它踢到阴沟里去了……
而游乐场中,仍乌烟瘴气,观众仍在发了疯似的抢夺那把电吉他的碎片……
他们只有离开了那游乐场,摆脱了那氛围,才会明白他们是何等可笑何等荒唐……
安东尼奥尼所揭示的这种人的心理,也正是当时我和许多杂牌军们的心理。
我们像股洪水似的一拥出检票口,便一片片地滑倒了。检票口外的车站广场,简直成了溜冰场。无论穿着花样刀鞋还是穿着冰球刀鞋、速滑刀鞋在上面滑冰是绝对没问题的。站前广场冰冻着一条条大标语——这是“东方红城”的红卫兵们的“发明创造”。冬天“闹革命”自有冬天“闹革命”的便利,夹着一卷大字报或大标语,拎着一只水桶满市逛,见哪里适合,找个水龙头接桶水,哗地泼在地上或泼在墙上,将大字报或大标语一贴,一两分钟后就冻住了。而且有着一层冰保护,晶莹透明,仿佛塑料贴面。不到春暖花开季节,谁想去掉是很困难的。除非水管子接在锅炉上,用开水先浇化了冰。
车站广场方砖铺就,纵横开阔,是冰冻大字报或大标语的理想之地。也不知有多少人来冰冻过多少层大字报或大标语了。冰上加雪,雪上加冰,白雪衬黑字,分外醒目。变成了地平面“专栏”。
那一天冰冻在站前广场的大字报的巨幅标题是——看刘汉玉自我暴露的反革命嘴脸何其猖狂!
刘汉玉?
男性?女性?官?民?哪个单位的?没谁知道。那年月反革命多如牛毛。大概也没谁感兴趣知道。在那年月,一个人的名字,哪怕是一个庸常之辈的名字,也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黑”遍全市,家喻户晓,妇幼皆知——那是“革命”和“反革命”都极容易大出其名的年月。
“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的赴京谈判代表们已经上了两辆大客车,朝两个相反的方向缓缓开去。大客车前是各自的仪仗队开路。他们站在卡车上,继续吹奏各自的团歌。大客车后是两派前来迎接的战友,各自来了上千人,浩浩荡荡地进行声势游行。叫做“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
拥出检票口的杂牌军,有的分别跟随两支游行队伍瞧热闹去了,有的滑倒了爬起来后没走,站在广场上垂头看大字报。那冰冻在广场上的大字报很长很长,少说两万余字,三四百平方米的面积。
那样一种看大字报的情形在南方城市可见不到,人人都垂着头,边看边往后退。要想从头看起的,就从人墙后绕到前面来。
“对不起,请抬一下脚!”——脚下踩着字呢。
不知道是看大字报的,还会以为人们都在那里默哀呢。
“谁鞋底儿干净?尽个义务!”——有些地方的冰踩脏了,看不见字了。于是就有鞋底儿干净的用鞋底儿擦冰面。于是那些地方的冰面被鞋底儿擦得愈发晶莹透明,字迹看上去如同写在玉石板中。更有热心尽义务的,捧来几大块雪,摔散在地上。冰面经鞋底儿用雪一擦,不但晶莹透明,而且闪闪发光。
那样看大字报,真可以说也是种乐趣。
矗立在广场上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被用布从上至下严严密密地罩起来了。像黄山的“梦笔生花”,见“笔”不见“花”。
我脚穿解放胶鞋,下了车没过五分钟脚趾就冻僵了。我思忖我若穿着这样一双单鞋等公共汽车,非把十个脚指头全冻掉不可。
我撒腿往家跑。头上没有棉帽子,西北风像小刀子似的,割我的耳朵割我的脸。捂着耳朵跑一会儿,双手冻疼了,便顾不得两只耳朵,又袖起双手跑一阵。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却不敢停下来走。并且也不会走了。双脚由僵而木,冻得完全没了知觉,像凭着一双假脚在跑。
紧跑慢跑,跑了近一个小时,抱头鼠窜地跑到了家。
闯入家门,母亲正蹲灶口吹火,见我那样子,以为后边有什么人追赶,陡地变了脸色,一把将我拽在怀中,死死搂抱着,眼盯着家门,防范地预备跟接着闯入家门捉拿我的任何人拼命。
我急忙说:“妈,没人追我。”
母亲这才缓缓将我从怀中推开,突然劈面打了我一耳光,打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母亲打我之后,就转过身去哭了。
我呆呆地站在母亲跟前,一声不吭。
两个月我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哪怕是一封告诉母亲我身在何地的短信都没写过。我知罪。
脚开始疼,像针扎,像火烧。
我讷讷地说:“妈,我的脚……”
母亲朝我转过身来,发现我脚上穿着一双单胶鞋,大吃一惊:“活该!活该!冻掉你的脚才好!”母亲慌慌地将我推进里屋,推坐到炕沿上,慌慌地从我脚上扒下鞋、袜子,慌慌地解开自己的衣襟,将我的脚贴胸搂在她那温暖的怀里。
这时我获得了一种彻底的安全感。
我流泪了。
我无声地哭了。
中国再大,哪儿也不如家好。谁也不如妈亲。
我深深地理解了“儿女是娘身上的肉”这句话。
母亲在从我脚上往下扒鞋时,由于鞋冻在脚上了,由于过分心急,劈了自己的指甲,手指尖不断流血。母亲顾不上包扎,只是将手指尖放在口中吮。
我太困了。双脚被母亲搂在怀里,身子歪倒在炕上,竟那么睡着了。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