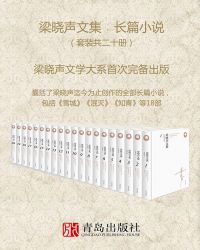第十二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二章
大串联开始了!
这一运动中之运动的“先驱”者们,也许应首推某海运学院的一批红卫兵。他们高举“长征队”的旗帜,从城市徒步出发,历时近百日,风餐露宿,沿途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们抵达北京后,受到首都人民和红卫兵的热情欢迎。受到中央“文革”成员和毛主席的接见。
两报一刊发表联合社论,高度评价红卫兵小将们的“长征精神”。指出这一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起到“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长征队”尤其是红卫兵的“宣言”方式——如果历史需要,我们也可以创立前人创立过的一切丰功伟绩——其实并不是精神继承,而更是初萌于一代人潜意识的精神挑战。更是红卫兵革命理想主义涅槃中升华了的自我证明和自我检阅的激情。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人,只要是处在温饱线以上的,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是平凡。他们总希望自己应该是为了惊天地、泣鬼神而生存的。并且总相信自己完全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他们是不甘于仅仅做前人的辉煌历史的阅读者和英雄纪念碑的瞻仰者的。这是全人类的普遍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煽起青年的一切超历史的欲望。减少他们面对某页伟大的历史感到无所作为的痛苦。
一代红卫兵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英雄主义的梦想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梦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被饥饿破坏过。那无疑是很可悲很严重的破坏。而一旦苞谷和高粱又可以填饱胃了,英雄意识也便又开始在他们的头脑中活跃了。何况红军所进行的长征就像是昨天的事。那一页历史太新了。创造那一页历史的伟人和英雄们也不算太老。文学、电影、话剧、歌曲、回忆录、陈列馆、纪念碑……一切可能的手段,一切可能的方式,一切可能的途径,都被调动起来,运用起来,目的是那么明确,缩短再缩短这太新的一页历史与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要永远永远使他们在它面前高唱颂歌,膜拜顶礼,做它那光荣的精神奴隶。
于是在他们预见可能会得到赞扬而非压制的情况下,他们便满怀豪情地进行自己的“长征”。希望自己的“长征”也被载入史册,也使后人同样对之高唱颂歌,膜拜顶礼。事实上,我们今天称之为一代人的“逆反”心理,完全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年代。不过这种“精神挑战”被肤浅地误解为“精神继承”罢了。倘若当年有人指出一代红卫兵心理上的“逆反”和“挑战”意向,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是诽谤因而愤怒起来的。
前不久,我从一本杂志看到一则实事报道:在苏联的某座城市,有一条街道,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保卫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命名。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才知道,他仍活着,并且就在这一座城市,每天无数次地经过那一条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常常看到青年人在街头他的半身塑像前致敬,默哀,献花圈。然而五十年来,他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那塑像就是我。后来在要把他的某些“遗物”陈列到英雄纪念馆时,他才不得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记者问他:“那是莫大的光荣,不是耻辱,你却为什么不愿代替你的塑像当之无愧地接受呢?”
已成老耄之人的他回答:“在非常岁月,每一代人都能创造光荣,产生英雄。这是很寻常的事。”
杜鲁门的外孙,直至上小学一年级,才在课堂上知道,自己的外祖父原来当过美国总统。回到家里,他问母亲,为什么从没告诉过他?
母亲回答:“这也值得你骄傲吗?美国人中能当总统的人很多很多呀!”
一位苏联老红军战士和一位美国总统的女儿也是美国儿童的母亲的话,提供了人类在心理素质方面已经进步的参照例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共和国对它的儿女们所进行的一切的,包括愿望最良好方式最有效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炫耀丰功伟绩,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味。历史一旦拿它来作精神统治的教科书,它的伟大和庄严实际上便开始丧失了。所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正中一代红卫兵下怀。所以下一代人的挑战——以“长征队”的升华了的行动体现的和以“造反有理”的彻底走向反面的行动体现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物极必反。
而林彪妄图篡改历史,取代“井冈山会师”中的朱总司令,其愚昧恰在于竟以为能够靠了一页光辉的历史来巩固自己在当代的地位。这是人类在心理素质方面没落的参照例证。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布,红军是英雄好汉。
“长征队”也是宣言书,它向全中国宣布,红卫兵也是“英雄好汉”。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英雄好汉”们,纷纷开始了他们自己的长征。他们擎举起自己的旗帜,高唱着对自己的颂歌,满怀英雄主义的豪情,大踏步地走向延安、韶山、遵义、北京。沿途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进行革命大串联,播下一堆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种,以为如此等等的作为,也算是“丰功伟绩”了。以为自己也肯定将会彪炳史册了。以为自己在使全中国人民“免受二遍苦,二茬罪”的历史的严峻关头,也都不愧是一场大革命的弄潮儿,人民将来可能也会称他们为“大救星”,像感谢上帝一样感谢他们。当然,绝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长征队”队员都作如是想。目的也根本不在于投机,仅只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证明,一种潜意识的“精神”挑战而已。如果历史客观地公平地发言,那么它应该承认也应该证明,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切行为,一切行动,都只不过是自我表现,自我证明而已,掺杂着压抑长久的充分的发泄,走向极端的英雄主义,对历史的变态的挑战意识,扭曲到妄想地步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还根本没有考虑到有什么投机的必要性,也还根本没有学会投机。
两报一刊又发表社论,敏锐地指出,红卫兵“长征队”的不断涌现告诉一切革命“左”派,进行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是革命“左”派们的一项任务,势在必行。
中央“文革”的首长们发表讲话:红卫兵和一切革命“左”派,全国各地都去去,欣赏欣赏大好河山也是理所应该的嘛!
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革命大串联好得很。
百万千万份传单,将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及毛主席对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红卫兵小将和一切革命“左”派的想念之情公告向全国。
毛主席想念我们,我们更想念毛主席!
以徒步长征的速度去到北京,去到毛主席身边,使毛主席他老人家感到,红卫兵小将和一切革命“左”派与他老人家是心心相连,息息相通的,显然太迟太迟太迟了!
于是他们在东西南北各条铁路线的各个车站拦截列车,强行登乘,都怀着十万火急的心情奔赴北京。“长征”在半途中的,也卷起了“长征队”的旗帜,改乘列车抵达北京后,再重新招展他们的旗帜,精神抖擞,飒爽英姿地行进在北京的大街上。反正也没人盘问他们究竟是走来的还是坐火车来的。
于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频频高呼:“红卫兵万岁!”“人民万岁!”
如今,已很难考证那些中央“文革”的首长们的讲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真伪。但我为了写这篇“自白”,从各种各样的人们那里借到的,求索到的当年的传单或小报上,白纸黑字、的的确确印着以上那些讲话,那些“最新指示”。而伟大领袖口中呼出的“红卫兵万岁”“人民万岁”两句话,则是我亲耳听到的。
一次次长久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还不断地从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那一端走到这一端;还频频挥手;还时时以自己的声音回应千百万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涛。还要乘敞篷车(当然也是站着)来到千百万人中间。白天检阅过了,夜晚还要满足千百万人“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强烈愿望。仅白天的检阅,往往就延长至四小时。这对于七十多岁的老人家的身体,不能不承认是危害健康的。
中央“文革”开始替毛主席的身体忧虑和不安了。
先后八次声势浩大的检阅中,有幸陪同者几乎次次更换。某些人第一次检阅时还手持红宝书,第二次检阅时便不知“君今何往”了。要么上了“百丑图”,要么被报纸宣布为又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红卫兵和一切革命“左”派的政治嗅觉变得异常敏感。今天一份“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图表式传单刚刚散发出去,明天又一份在紧紧急急地赶刻赶印。党中央两个司令部大分化大改组的动荡局面,似乎永远都处在变更之中。
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告——全国各地涌向北京的红卫兵人数日益增多,虽然连街道委员会的居民也动员起来了,首都的接待工作仍力不胜任。希望红卫兵谅解首都的难处,心疼毛主席的身体,顾全大局,暂缓赴京。
紧急通告并未起到作用。
实际上,大串联已经演变成免费的旅游。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大串联是一次获得大功利的机会。吃、住、行一文不花的旅游,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美事。当年的中国人能到过一次北京,比今天的中国人能到过一次纽约或巴黎还倍感荣幸,觉得是天赐良机。“开开眼界,见见世面。”这是今天出国的人们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当年的红卫兵绝不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存在的。甚至是压倒抽象的革命目的之目的。至于新闻电影中保留下的那些热泪横流的特写镜头,那些口呼万岁抬头仰望的动人场面,仅是大串联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面。何况眼泪和狂热情绪是具有感染性的。倘若当年也像如今一样,记者可以持着话筒现场采访,许多热泪未干的人很可能会如此回答:“别人哭,我也哭,眼泪是不由自主流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从总体来说,汉民族恰恰是很缺乏信仰的民族。所以,仅仅认为大串联是崇拜心理和热爱之情的必然结果,实在是过于理想化过于浪漫化的评价。倘吃、住、行需自己破费,当年到北京去的人可能连大会堂还坐不满。
我们那一派红卫兵组织解散不久,我很快又参加了另一派组织。我总得参加某一派红卫兵组织。我总得是一个红卫兵。这对我大大的有利。
那一天我们组织起来,到火车站拦截开往北京方向的每一次列车。我们在火车站各处,包括列车上刷标语。标语写的不外乎是——“听从中央‘文革’的话,心疼毛主席他老人家!”“见到毛主席是莫大的幸福,毛主席的健康是我们更大的幸福!”等等。
已经登上了列车的各校各派红卫兵,任我们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没有一个下来的。但也不与我们辩论。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方。他们与我们进行“战略对峙”。
于是我们便纷纷卧轨,在铁路上一趴下去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起来。那一天细雨蒙蒙。趴在湿漉漉的枕木和冰凉的铁轨上并不是件舒服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那也完全是凭着自我证明自我表现心理支撑的执拗行为。起码我自己是这样。心疼毛主席——是很值得自我证明自我表现一下的。证明自己表现自己热爱毛主席的机会很多,证明自己表现自己心疼毛主席的机会却难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今天,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否定时,一般都将“个人崇拜”的恶果过分夸大了。中国人的崇拜心理,尤其是汉民族的崇拜心理,其实有一定的虚伪性。
我和我的伙伴们在绵绵秋雨中卧于湿漉漉的枕木冰森森的铁轨上,我心中知道我那天的行动绝不会没有意义。我预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一行动肯定是我的政治鉴定上很“革命”的一笔。我认为值得。证明自己表现自己的强烈欲望在我心中一小块酸碱性土壤上,悄悄生长出投机的芽叶,嬗变为更加不可告人之目的。大家的衣服全湿透了。一个个冷得瑟瑟发抖,又都饿了,有人就爬起来要回家。
“不能走哇!”我大喊,“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谁想走就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大不忠!”
爬起来的纷纷又卧下了。
我们的一个伙伴,举着手提话筒,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对列车上的红卫兵们动员:“下来吧!真正听从中央‘文革’首长的话,真正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战友,请你们下来吧!毛主席能活一百五十岁,我们总会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最后两句话的意思,分明是只要毛主席健康长寿,还怕今后没有见到毛主席的时机吗?
列车上的部分红卫兵,正一字一顿、极有节奏地喊着:“我们想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车厢内还传出几个女红卫兵缠绵悱恻的“小合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们也只有以这种方式向我们表示令人怜悯的抗议。
但是我们那个伙伴的话,却使他们抓住了把柄。他们正没什么把柄可抓呢,终于抓住了,岂肯错过?千不该万不该,我们那个伙伴不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犯了造句修辞的严重错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
“他妈的,你们听这小子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比作什么啦?”
“比作木柴,揍他!”
“你们诽谤,我是将毛主席比作青山!”我们那个伙伴大声替自己辩护。
“比作木柴!”
“比作木柴!”
一张张愤怒的脸从车窗探出来。
“比作青山!”
“比作青山!”
问题太严重了!比作青山还是比作木柴,这可属于大是大非,政治性质!卧着的我们,纷纷爬起,帮我们的伙伴辩护。
“比作青山也不行!只能比作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就算比作青山,山上的一草一木是什么?是毛主席的头发!不怕没柴烧又意味着什么?”
“简直反动透顶!”
“谁敢动毛主席一根毫毛,谁就是我们的死敌!”
局面急转直下。他们处于优势,我们处于劣势了!
“揍他!揍他!”
“他们拦截列车,阻碍铁路交通,罪该万死!”
“揍他们呀!揍他们呀!”
于是许许多多男红卫兵纷纷从窗口跳下列车,由“战略对峙”而“战略反击”,对我们施展老拳狠腿。
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几个十几个围住我们一个,大打出手。
我们有的被打得抱头鼠窜,有的被打得呼爹叫娘;有的英勇无畏些,面对强暴,大义凛然,一味挨揍,不抱头鼠窜,也不呼爹叫娘,只是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为了毛主席粉身碎骨也心甘!”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概。
在他们纷纷从列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我情知不妙,灵机一动,一头钻入车厢底,钻到车厢那边去了。我躲藏在车厢那边,耳听伙伴们的哀嚎,鄙视自己的胆怯也庆幸自己逃得快,用“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句至理名言自己宽恕自己。
伙伴们被打散了。那些“抬头望见北斗星”的红卫兵大获全胜。仿佛“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似的,一个个趾高气扬地又登上了列车。
列车长鸣一声,喷出一阵白雾,缓缓开动了。
又一批红卫兵到北京去了……
我在铁道旁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觉得我所参与的这很神圣的行动,有点滑稽可笑。像一幕正剧,又像一幕闹剧,更像一幕以英雄们的失败而告终的悲剧。当年我还没听说过什么“黑色幽默”或“荒诞派”。如今想来,那一行动更具有此类色彩。
可我毕竟没挨揍,没额青唇肿,没掉牙,没流鼻血。半点伤也没有,与我们那些一个个都挨了揍的伙伴相比,我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临阵脱逃者,也不知是否被我的哪一个伙伴发现了。倘真的被发现了,我他妈的就完了!我将在男红卫兵中无地自容了!我将在女红卫兵中难以保持起码的自尊和人格了。而今后我无论再表现得如何如何“革命”,也难以重新获得红卫兵伙伴们的信任了!这太严重了!我心中不安到极点。不堪设想的后果比刚才拳舞脚飞的打斗场面更使我害怕。
我灵机一动——又是灵机一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自己变得聪明了许多),决定自己在自己身上制造个伤口,弄出点血来。我必须有个伤,我必须流点血,否则我说不清楚,向我的红卫兵战友们也向“革命”交代不过去!
地上正巧有截一尺来长的带钉子的木条,我捡起了它。
我曾看过一本小人书——《打严嵩》。内中有个情节,就是严嵩为向皇帝诬告别人打了自己,手持方砖,以袖裹之,自己向自己面门连砍三下,砍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兵法书上,叫“苦肉计”。周瑜打黄盖,也是此计,所谓“真打真挨”。可那奸相严嵩,是被寇准老儿捉弄,想以“苦肉计”诬陷别人而又上了别人“苦肉计”的当。兵法书上,叫“计中计”“连环计”。周瑜打黄盖,打得狠,四十军棍,两股皮开肉绽,那才真叫“苦肉计”。还有《岳飞传》里的那个“苦人儿”,为了到金营去对双枪小将陆文龙进行劝降,竟断臂。严嵩也罢,黄盖也罢,“苦人儿”王佐也罢,为了诬陷的目的,为了军事上的胜利,为了大宋抗金,苦一下“肉”都是值得的。而我呢,似乎也很值得又似乎他妈的一点儿也不值得。不苦还明摆着是不行的!
罢,罢,罢!该流血的时候就得流血!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
“苦肉计”不是高明的计。我左手拿着那木条,举起了几次,想朝自己右臂来一下,却来不成。
我闭上眼睛,咬咬牙,狠狠心,终于打了下去。
我感觉到钉子扎进了皮肉,倒不怎么疼。睁开眼睛,臂上却没伤。我以为是打下去了,还是他妈的没有打下去!
那时我才认清了我自己,那么缺少勇气!我想我恐怕永远做不出英勇的行为了。我很替自己悲哀。
又闭上眼睛,又咬咬牙,又狠狠心……
嘿!
低低地吼出了一声。
这下成功了。因为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疼。
我并未立刻睁开眼睛——手臂上只弄出个钉子孔儿算什么伤?也淌不出几滴血呀!
再咬咬牙,再狠狠心,钉子本没拔出,事倍功半。“一不做,二不休”吧!使劲一拽木条,疼得我哆嗦了一下。
臂上划出一个大口子,二寸余长,皮肤豁开着,鲜血如注。尽管疼,很满意。伤口像个伤口的样子,血也淌得够刺激的。
想了想,撕掉半截袖子,裸出血淋淋的左臂,为了使我的红卫兵伙伴们一眼可见,触目惊心。
我任凭血流不止,心说他妈的流得越多越好。
右手托着左臂,像个挂了彩的战士似的,蹒蹒跚跚、孑然一身地走出了火车站。
伙伴们正聚在站外。以为我肯定是在混战中被绑架到列车上了。那可就生死未卜了。一个个都忐忑不安。几个女红卫兵伙伴还哭了。
他们一见我,顿时大喜。围住我,七言八语:
“哎呀,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一个女红卫兵伙伴立刻掏出条洁白的手绢替我包扎。
我淡淡一笑,无所谓地回答:“没事没事,不过被他们用小刀划了一下。”
手绢马上被血染透。
那女红卫兵伙伴柔声问:“很疼吗?”她深情地望着我的眼睛。那是一种倾慕英雄的目光。我猜如果只有我俩在一起,她也许会亲我,可惜人太多了。
我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还动刀啦?我们要把全团的人拉来就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
“那也肯定吃亏,哪一节车厢都挤得像豆芽罐头似的,这一列车起码三四千人!我们不过才是小股游击队,他们是大兵团!”
“你没看清动刀那小子的袖标是哪个学校哪派组织的吗?”
“今天这仇一定得找机会报!”
我的伙伴们,包括女红卫兵伙伴,也都轻重不同受了各种伤。
我说:“算啦,今天的事儿过去了就过去吧!他们想念毛主席的感情也挺值得理解的。”
我这句话使伙伴们都生气了:
“那我们呢?我们心疼毛主席的感情为什么就不被理解?反而挨揍?”
“他妈的他们想念毛主席是假,一分钱不花去逛北京是真!”
“毛主席他老人家又不得不接见他们啦!他们一去倒是捞到了光荣的政治资本,我们为心疼毛主席挨揍,中央‘文革’的首长们知道吗?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吗?”
“就是!两报一刊还会大登特登,又一批日夜想念毛主席的红卫兵,幸福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伙伴们的话语中,流露着极大的愤愤不平、极大的委屈、极大的“太不上算”的意味。
我说:“我们心疼毛主席,是出于对他老人家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对毛主席最具体的最大的忠,挨顿揍、流点血算什么?大家的怨言是不应该的!”
伙伴们便都不言语了。看得出来,他们都被我的政治觉悟所折服。
几个用纸团塞进鼻孔止血的男红卫兵伙伴纷纷附和我的话:
“对,对,心疼毛主席是应该的,中央‘文革’的首长和毛主席虽然不会知道,但我们今天的行动将要写入红卫兵史!”
“谁来写?”
“我们自己呗!留取丹心照汗青!”
于是大家也就似乎因为挨了一顿揍,受了些个伤,流了血,荣耀起来,自豪起来,感觉自己的形象都高大光彩起来了……
回到家里,母亲捧着我那受伤的胳膊,心疼得要哭,这家找“二百二”,那家讨消炎粉,生怕我得破伤风。
她叨叨着:“谁想念毛主席就让谁到北京呗!毛主席都非常乐意让他们到北京,你们又何苦拦火车不让人家去呢!”
我说:“妈,你这话就不对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一次次检阅,身体还不被折腾垮了呀?他老人家的身体要是真被折腾垮了,中国的革命航船靠谁来指引方向?全中国人民靠谁领导着走向共产主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毛主席也是他们的大救星啊!”
母亲听我说了这番话,点头道:“可也是的,家家户户都贴着毛主席像,角儿八分地就能买一张,想念毛主席的时候,对着毛主席像看上一阵子,连他老人家下巴颏上那颗长寿痣都看得一清二楚,不强过千里迢迢地到北京去,只能远远地看到他老人家站在天安门上的那个身架?一次次检阅,一次次辛劳他老人家,不是天大的罪过吗?”
母亲言罢,转脸朝我家正墙上那张毛主席像瞥了一眼。那目光分明带着几分讨好的意味。仿佛那不是毛主席的像,是毛主席本人,也仿佛她的话不是说给我——她的儿子听的,而是说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听的。
像上的毛主席对我们永恒地微笑着。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