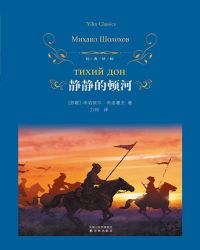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二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章
八月底,米佳·柯尔叔诺夫在顿河边无意中遇见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女儿丽莎。他刚从顿河对岸回来,正要把船往树桩上拴的时候,看到一只油漆过的小船轻飘飘地在水上滑行着。小船顺流而下,向码头驶来,划船的是包亚雷什金。他的光脑袋上的汗亮闪闪的,额头和两边鬓角上的筋都鼓了起来。
米佳一下子没有认出丽莎。草帽的灰色阴影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用晒得黑黑的双手将一束黄色的睡莲紧紧抱在胸前。
“柯尔叔诺夫!”她看到米佳,摇了摇头。“为什么你说话不算话?”
“怎么不算话?”
“记不记得,你答应跟我一块儿去逮鱼?”
包亚雷什金把桨放下,把腰挺了挺。小船的船头凭着惯性的力量爬到岸上,压得岸边的砂石咯吱咯吱直响。
“记得吗?”丽莎笑着,从船上跳下来。
“没工夫呀,太忙啦。”米佳解释说,一面屏住气注视着朝他走来的姑娘。
“不行啦!没劲儿啦!……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 ,我划不动啦!您另请高手吧,我不能给您效劳啦!真不得了,咱们在这该死的水上划了多久啦。手上都磨出血泡啦。真不是玩的。”
包亚雷什金那老长的光脚板重重地踏在有尖有棱的碎石子上,用皱巴巴的学生帽帽顶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丽莎没有回答他,只管走到米佳跟前。米佳笨拙地握了握她伸给他的手。
“咱们什么时候去逮鱼?”她仰着头,眯缝着眼睛问道。
“要是去的话,明天也行。已经打完了场,这会儿有工夫啦。”
“又是骗我吧?”
“哪儿话,不骗你!”
“你一早就来吧?”
“天不亮就去。”
“我等着你。”
“我去,真的,一定去!”
“没有忘记敲哪一扇窗户吧?”
“找得到的。”米佳笑着说。
“我恐怕不久就要走了,很想逮一回鱼。”
米佳一声不响地在手里摆弄着生了锈的船锁的钥匙,看着她的嘴唇。
“话说完了吗?”包亚雷什金望着手上一个带花纹的贝壳,问道。
“马上就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不知为什么笑了笑,问道:
“你家办过喜事,不是吗?”
“是我妹妹出嫁。”
“嫁给谁啊?”她没等回答,就诡秘而亲热地笑了笑。“你来吧!”又像第一次在莫霍夫家的阳台上那样,她的笑使米佳像碰着了荨麻似的,浑身痒酥酥的。
他用眼睛一直把姑娘送到小船边。包亚雷什金叉开两腿,把小船推下水去;丽莎含着笑,从他的头顶上望着玩弄着钥匙的米佳,朝米佳点了点头。
小船划出五六俄丈远以后,包亚雷什金小声问道:
“这小子是谁?”
“熟人。”
“心上人吗?”
听到他们谈话的米佳却因为桨架的吱嘎声没有听清后面的回答。他看到包亚雷什金把身子向桨上一压,又向后一仰,笑了起来,但是看不到丽莎的脸,因为她是背朝他坐着的。帽子上一条紫色的缎带滑到她那斜斜的光肩膀上,被微风吹得轻轻抖动着,越来越模糊,吸引着他的迷离的视线。
很少去钓鱼的米佳,从来没有像这天晚上这样热心地准备过。他劈了些干柴,在菜园里煮起小米饭,很快就重新拴好滑脱的钓绳。
米海伊看着他在准备,向他要求说:
“带我去吧,德米特里 ,你一个人很不方便。”
“我一个人能行。”
米海伊叹了口气。
“咱们很久没有一块儿去钓鱼啦。这会儿准能钓到十几斤重的大鲤鱼。”
米佳被饭锅里冲出来的像热气柱一样的蒸汽熏得皱起眉头,没有答话。他准备停当,便朝正房走去。
格里沙加爷爷坐在窗前,将一副铜边的圆眼镜架在鼻子上,正在读福音书。
“爷爷!”米佳肩膀靠在门框上,唤了一声。
格里沙加爷爷从眼镜上面朝他瞪了瞪眼睛。
“什么事?”
“头遍鸡叫以后,你把我叫醒。”
“这么早你上哪儿去?”
“去钓鱼。”
很喜欢吃鱼的爷爷,装做不赞成的样子:
“你爹说,明天要打大麻子。你倒想自在。哼,还钓鱼呢!”
米佳离开门框,使了个点子:
“我反正没什么。本来想钓条鱼给爷爷吃,既然要打大麻子,那我就不去啦。”
“等一等,你要上哪儿去?”格里沙加爷爷吓了一跳,摘下眼镜。“我跟你爹说一声,没事儿,你去好啦。钓些鱼腌腌吃倒是不坏,明天恰好是星期三。我叫醒你,去吧,去吧,浑账小子!你龇什么牙?”
半夜里,格里沙加爷爷一只手提着粗麻布裤子,另一只手握着拐杖探索着道路,走出门来。他像一个摇摇晃晃的白影子一样穿过院子,来到仓房里,直到拐杖头碰到在车毯上打呼噜的米佳。仓房里充满了刚打出的粮食气味、老鼠屎气味和无人住的地方那种又酸又陈腐的蜘蛛气味。
米佳睡在粮囤边一张车毯上。他没有一下子醒过来。格里沙加爷爷先是用拐杖轻轻地捅了捅他,小声喊道:
“米佳!米琪卡!……喂,坏小子,米琪卡!”
米佳重重地打了几声呼噜,把腿蜷了蜷。老人家狠了狠心,把拐杖的粗头儿抵到米佳的肚子上,像钻子一样钻了起来。米佳哎呀一声,抓住拐杖,醒了过来。
“睡成糊涂虫啦!像你这样睡法,真不像话!”爷爷骂道。
“别做声,别做声,轻点儿。”米佳一面在地上摸索着靴子,带着睡意小声说。
他来到广场上。村子里的鸡已经在叫二遍了。他在街上走着,经过维萨里昂神甫家门前时,听到鸡窝里有一只公鸡拍打了几下翅膀,用主祭神甫那样的粗喉咙叫了几声,几只母鸡也惊惶地小声咕哒咕哒叫了起来。
更夫正在商店门前台阶的最下一级上打盹,鼻子埋在暖暖和和的羊皮袄领子里。米佳走到莫霍夫家的栅栏跟前,把钓竿和装鱼食儿的小袋子放下,为了不叫狗听见,轻轻地踮着脚上了台阶。他拉了拉门把手——门是闩着的。他爬过栏杆,走到窗户跟前。窗子半开着。从黑洞洞的屋子里传出睡得暖烘烘的姑娘身体的香甜气息和又神秘又香甜的香水气味。
“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
米佳觉得自己喊得很响。他等了等,没有声音。“要是敲错了窗户,那可怎么办?万一老头子睡在这儿呢?那我就倒霉啦!……他会开枪的。”米佳心里想着,用手紧紧抓住窗上的把手。
“伊丽莎白·谢尔盖耶芙娜,起来钓鱼去。”
“要是敲错了窗户,那我就上钩啦!……”他又想道。
“起来,还不快起来!”他发急地说,并且把头探进屋子。
“啊?谁呀?”黑暗中有人惊恐地小声答话了。
“去不去钓鱼啦?是我,柯尔叔诺夫。”
“啊——啊,我马上就起来。”
屋子里窸窣响了起来。她的犹带睡意的、温柔的声音好像散发着薄荷香味。米佳看到一个窸窣响着的白影子在房里活动着。
“唉,要是跟她睡一觉才美呢……却要去钓鱼……坐在那里,还要冻僵呢……”他闻着卧房里的气味,迷迷糊糊地想。
窗口出现了裹着白色头巾的、笑盈盈的脸。
“我从窗户里爬出去。把手给我。”
“爬过来吧。”米佳用手搀着她。
她挽住他的手,面对面地看着他。
“我动作快吧?”
“不慢。咱们准有希望。”
他们朝顿河走去。她用粉红色的手掌揉了揉微微有些肿胀的眼睛,说道:
“我睡得正香呢。应当再睡一会儿。咱们去得太早啦。”
“正是时候。”
他们顺着紧靠广场的一条小胡同来到顿河边。夜里不知从哪里来了大水,拴在昨天还歪倒在陆地上的树桩上的小船,正在摇晃着,周围都是水了。
“要脱鞋啦。”丽莎用眼睛测量着到小船的距离,叹了一口气。
“我来把你抱过去好吗?”米佳提议说。
“不合适吧……我还是脱鞋吧。”
“合适,要舒服些。”
“不要。”她不好意思地推却说。
米佳用左胳膊搂住她的大腿,轻轻抱了起来,哗啦哗啦地蹚着水朝小船走去。她不由自主地搂住他那黑黑的、硬邦邦的脖子,轻轻地、格格地笑了起来。
米佳在村子里妇女们捶衣裳的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短吻。她哎呀一声,把嘴紧紧贴到米佳那干裂的嘴唇上,米佳在离灰色的船帮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水灌进了靴筒,冰得两脚够戗。
他解开小船,用劲将小船推离了树桩,顺势跳上船来。他站着划,每一下都划得很短。河水在船尾咕咕响着,像哭一样。小船翘着船头,从容地划破急流,向对岸驶去。钓竿乒乒乓乓跳动着。
“你往哪儿划呀?”她回头望了望,问道。
“上对岸去。”
小船在砂石陡岸边停了下来。米佳连问都不问,就用手将她抱起,抱进了岸边的山楂丛里。她咬他的脸,乱抓了一阵,闷声闷气地叫了两声,觉得浑身渐渐没有力气,就恼恨地哭了起来,不过没有眼泪……
九点钟左右他们才返回。橙色的雾气笼罩住天空。风在顿河上漫舞,吹起层层波浪。小船跳荡着,爬过一道道波浪,从水深处翻上来的带泡沫的冷水珠儿溅在丽莎那煞白的脸上,有些往下流,有些就挂在睫毛上和露在头巾外面的一绺绺头发上。
她疲倦地眯着失神的眼睛,用手指掰着带到船上来的花枝儿。米佳划着船,没有看她,他的脚下有不大的一条鲤鱼和一条鳊鱼,鱼嘴还保持着临死时抽搐的样子,带黄圈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米佳的脸上露着负疚的表情,还有满足中夹杂着惶恐的表情……
“我把你送到谢苗诺夫码头。你从那儿回家要近些。”他一面说,一面顺水掉转船头。
“好。”她小声答应说。
岸上一个人没有。落满灰尘的菜园篱笆闷闷地立在顿河岸上,热风一吹,空气中到处是晒热的篱笆枝条气味。被麻雀啄得不成样子的沉甸甸的葵花头儿熟透了,垂得低低的,毛茸茸的葵花籽不住地往下掉。滩地上重新长出的嫩草绿油油的。远处有几匹马在撒欢儿,马脖子上的铃铛悠扬、愉快地响着,热烘烘的南风一阵阵向顿河吹来。
米佳拎起鱼,递给正要下船的丽莎。
“你把这鱼带回去吧。拿着!”
她惶恐地扬了扬睫毛,把鱼接过去。
“好,我走啦。”
“好吧……”
她抬着手,拎着用柳条穿着的鱼,朝前走去。她露出可怜巴巴的样子,不久前的骄矜和快乐都丢失在山楂丛里了。
“伊丽莎白!”
她回过头来,那眉毛弯曲处隐隐露出气恼和疑惑的神情。
“回来一下子。”
等她走到跟前,他歉疚地说:
“刚才咱们没看到……哎,裙子后面……有一小片……红红的……”
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一直红到肩膀。
米佳沉默了一会儿,出主意说:
“你从后院走。”
“不管怎么样,反正都要经过广场。都怪你,叫我穿这脏裙子。”她带着懊恼和忽然涌来的痛恨心情望着米佳的脸,小声说。
“是不是让我来用树叶染成绿的?”米佳提出了简单易行的办法,他看到她眼里涌出的泪水,感到惊讶……
……一阵新闻像风吹树叶一样,簌簌地在村里传了开来:“柯尔叔诺夫家的米佳把莫霍夫老头子的女儿搞上啦!”妇女们在晨牧时间往外赶牛的时候,站在狭窄的、在灰色尘雾中慢慢移动的提水吊杆的阴影下,从桶里往外倒水的时候,在顿河边石板上捶衣裳的时候,都在议论这件事。
“这都是因为没有亲娘啊。”
“老子只顾忙自己的事,后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天,打更的‘断指头’达维德卡说:‘半夜里,我看见有一个人往边上那个窗户里爬。我心想,哎呀,莫霍夫家来贼啦。所以,我就跑过去,正要喊:什么人?警察,快来!可是,我一看,却是他,米佳。’”
“如今的姑娘们,一搂她们的脖子,就会跟着走……”
“米佳对我家的米基什卡夸口说:‘我要去求亲啦。’”
“让他先把鼻涕揩揩干净吧!”
“听说,起初她还不愿意呢,是他硬干的……”
“算了吧,大嫂!……”
流言飞语在大街小巷传播着,首先玷污了姑娘的清名,就像一扇新门被涂上了浓浓的焦油。
流言落到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那谢了顶的头上,打得他抬不起头来。一连两天他没有去商店,也没有去磨坊。住在下层的女仆,只有在开饭的时候才请他出来吃饭。
第三天,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吩咐将带花斑的灰马套到跑车上,他坐上车,对见到的人矜持而威严地点点头,跑车就朝镇上驶去。一辆漆得锃亮的维也纳式轿车紧跟着刷刷地驶出院子。赶车的叶麦里扬唾沫直冒地抽着粘在花白胡子上的弯烟斗,理好蓝色的丝缰,一对大青马就撒着欢,嘚嘚地拉着车子在大街上跑了起来。在像一堵墙一样的叶麦里扬的脊背后面,便是脸色苍白的丽莎。她将一只小小的提箱抱在怀里,很不开心地笑着;她向站在大门口的符拉季米尔和继母挥了挥手套。从店里一瘸一拐走出来的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向莫霍夫家的男仆尼基塔问道:
“小姐上哪儿去?”
尼基塔因为对十分平常的人类弱点抱着宽容的态度,就回答说:
“上莫斯科念书去,要上大学啦。”
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人们在顿河边,在提水吊杆的阴影下,在往外赶牛的时候,翻来覆去议论了很久……这天天黑以前(放牧的牲口群已经回来了),米佳来到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家里(他是有意去晚一点,为的是不叫别人看到)。他不是随便来走走,是来向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女儿伊丽莎白求亲的。
在这以前,他跟她一共相会过四次。在最后一次相会的时候,他们之间有过这样一番谈话:
“嫁给我吧,丽莎,好吗?”
“胡扯!”
“我会心疼你、怜惜你的……我们家里有人干活儿,你可以坐在窗前看书。”
“你好糊涂。”
米佳很生气,没有再说话。这天夜里他回家很早。第二天早晨,他就对万分惊愕的米伦·格里高力耶维奇说:
“爹,给我娶亲吧。”
“等等吧。”
“真的,我不是说着玩儿的。”
“着急啦?”
“就算这样吧……”
“你迷上哪一家的姑娘啦?是傻丫头玛尔芙什卡吧?”
“你请媒人到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家去。”
米伦·格里高力耶维奇把皮匠用的家伙仔细地放到板凳上(他正在修理皮套),哈哈大笑起来。
“孩子,我看,你今天太高兴啦。”
米佳硬是坚持自己的意思,就像公牛牴墙那样,于是父亲大发雷霆。
“浑账!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有十几万家产;他是大老板,你呢?……你给我滚,不要发昏,要不然我用皮套先把你这个新郎官抽一顿!”
“咱们家有十四对牛,有这样一大片家产,再说,他是个庄稼佬,咱们可是哥萨克。”
“滚吧!”不喜欢多说话的米伦·格里高力耶维奇十分干脆地下命令说。
米佳只得到了格里沙加爷爷的同情。格里沙加爷爷用拐杖哒哒地捣着地面,颤颤巍巍地走到儿子面前。
“米伦!”
“啥事?”
“你为什么拆台?……既然姑娘跟小伙子般配……”
“爹,说实话,您简直是个孩子!米佳已经够糊涂啦,您更是少有……”
“住嘴!”格里沙加爷爷用拐杖在地上捣了捣。“难道咱们配不上他们?能有一位哥萨克的儿子向他的女儿求亲,他该认为是荣耀的事。把女儿嫁给咱们,他还巴不得呢。咱们在全州是出名的人家。不是穷光蛋,是有家业的!……这可不含糊!……去吧,米佳,没什么好说的!叫他拿磨坊做陪嫁。去求亲吧!”
米伦·格里高力耶维奇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到院子里去了。米佳决定等到傍晚,亲自前去。因为他知道,父亲的犟劲儿就像长在地上的榆树:你折一下,它就弯一下;你要折断——休想。
他吹着口哨走到莫霍夫家大门口,可是到了大门口就胆怯了。他踌躇了一会儿,就进了院子。他在台阶上向穿着沙沙响的新浆过的围裙的女仆问道:
“东家在家吗?”
“在喝茶呢。等一等吧。”
他坐下,等着,抽完一支烟卷儿,用指头蘸了点唾沫,把烟卷儿熄灭,把烟头儿在地板上捻碎。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一面掸着背心上的面包屑,走了出来;一看到米佳,就皱起了眉头。
“请进吧。”
米佳迈步走进充满烟草和书卷气味的书房,觉得在家里积攒的勇气,只够走到书房门口用的。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走到桌子跟前,皮靴后跟咯吱一响,他转过身来。
“有什么事?”他的手指头在背后不住地划着写字台的台板。
“我是来问问……”米佳遇到他那逼视的眼睛的冷光,打了个寒噤,“您能不能把伊丽莎白嫁给我?”
米佳又失望,又恼恨,又胆怯,脸上不禁冒出了汗珠儿,汗珠儿不多,就像干旱时候的露水。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左眉毛打着哆嗦,上嘴唇往上直翻,露出白牙和红红的上腭。他伸着脖子,身子向前探着。
“什么?……什——么?……坏蛋!……滚出去!……我把你送到村长那里去!哼,你这个狗崽子!下——流——货!……”
米佳听到这气急败坏的喊叫,反而有了胆量,他对直地看着红中透青的血涌上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脸。
“请不要见怪……我是想补救我的过失。”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翻滚着因为充血和含泪肿胀起来的眼睛,抓起十分沉重的铁烟灰缸,摔到米佳的脚底下。烟灰缸一蹦,打在米佳左腿的膝盖骨上,但是他顽强地忍住疼,猛地将门拉开,因为又恼又疼,所以发着狠,龇着牙,大声叫道:
“随您的便吧,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您要怎样就怎样好啦,我可是实心实意……她这样的姑娘谁还会要呢?所以我想保全她的名声……要不然,嚼烂了的东西谁还吃呢?连狗都不理。”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用一块皱巴巴的手帕捂着嘴,追了出来。他拦住通往大门口的道路,于是米佳就在院子里跑了起来。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便朝站在院子里的车夫叶麦里扬挤了挤眼睛。米佳正在抽便门上闩得很紧的门闩,放出来的四条恶狗就从棚子角落里冲了出来,一看到生人,就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摆开了阵势。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一九一〇年从尼日尼的市场上带回了一对小狗:一公一母。这两条狗都是黑颜色,卷毛,大嘴巴。一年以后,都长得跟一岁的牛犊一样高,起初撕扯路过莫霍夫家门口的娘们儿的裙子,后来学会把娘儿们扑倒在地,咬她们的大腿,直到咬死潘克拉季教长的一头牛犊和阿杰平的两只阉猪,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才下令将狗锁了起来。每到夜里把狗放开,另外,每年春天还有一次放开狗,让狗进行交配。
米佳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脸来,最前面的一条名叫巴洋的狗就把前爪搭到他的肩上,用牙紧紧咬住他的棉袄,嘴巴闭得死死的。几条狗又撕又扯,像黑球一样团团乱转。米佳用两手拼命抵挡,竭力撑持着,免得跌倒在地上。他无意中看到叶麦里扬叼着直冒火星的烟斗溜进厨房,砰的一声关上新油漆的厨房门。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站在台阶的角上,背靠着下水管,紧紧攥着长满油亮的硬毛的白白的拳头。米佳摇摇晃晃地抽开门闩,可是他那血糊糊的两腿后面,还紧紧跟着汪汪直叫、发出热烘烘的狗臭味的狗群。他掐住巴洋的喉咙,掐死了;另外三条狗是几个过路的哥萨克好不容易帮他打退的。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