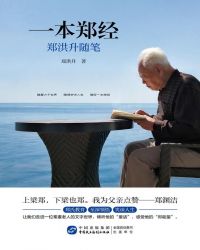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锦绣的城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9章
这一次遇到,他看向她的目光里就有了质问,充满疑虑。牛丽一派若无其事,看看窗外,继续剪手指甲。她像是忘了今天的正事,定下那套公寓房。每天都有正事,眼前这男人不过是最没谱的一件事,她连他姓什么都没掌握。假如不马上下车,换乘一辆的士,就赶不上那个楼盘的售楼会。牛丽脑子里糨糊一片,既没有最初的喜悦,也没有后期的愤怒,甚至夜半那种崩溃前的窒息,也化为乌有。一旦看到这个男人,她就变得噤若寒蝉。她的所有委屈、热望、忧虑化作了涓涓细流,脉脉流向了大海。
中途牛丽下了车,经过他座位时将右手上扬。他瞪着玻璃外的她,确切地说瞪着那两张卡,吊线虫丢失的卡。他看着她走远,目光一定恼怒、屈辱而又无法声张,牛丽就仿佛报了仇。
他也下车了,跟在她身后。牛丽的背马上变直了,脖子有点硬,因为她想回头。心是暖的,又冲,几乎要冲破胸膛到她前面去了。她扫一眼自己的百褶裙,不是那件最爱的橙色。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一早忙忙乱乱,她也没挑一件。这件是大红色,套了一个黑皮夹克,还是挺显肤色的。走了一阵,换作她掉到了后头,他抢在了前面。经过她时,他没有问她要那两张卡,甚至没对她正眼看一眼。
牛丽跟在他身后,一边抬头看头顶的乌云。不知为什么,她很盼望突然来一场暴雨,她和他被雨浇得透湿,喘不过气来,看不清前面的路。同时她又想不断同他走下去。巷子终归是巷子,能够围绕这个小城无限循环下去的只有巴士。
这天是有些征兆的,事事指向他们这次会合。一早天空就压着厚厚的云层。到了半上午,大朵的云团愠怒地翻滚,偶尔从生铁色的云体射出一丝金光。牛丽出门时就觉得今天不寻常,这些古怪的云给她带来了运气。就像是做梦一样,他们下了巴士,一前一后,拐进这条偏僻巷子。他的背影清瘦,很孤单,巷子里有几棵樱树,开花了,边开边落。他的步子踩在松软的落满樱花瓣的地面,不紧不慢,不犹豫,仿佛只是周末的一次野炊,没有目的地,没有时间限制,只是即兴下车,信步前行。他对这条巷子似乎不是很有把握,走了一刻钟,天也走灰了。
事情陡然有了转机,天空像是一个巨大的鬼脸。人生偶尔这样,一桩仿佛没有尽头的烦恼,迎刃而解。事实上,半空的云,地面的樱花,无人的巷子,这些在都城不易察觉的事物,造成了牛丽在这个早春傍晚的阵阵眩晕。她心里是情愿随他一直走下去的,脚下是他踏过的花瓣,那样一种脆弱的质地;阳光偶尔出现,把他的浅灰色影子直拉到她面前,她的鞋底便发起软来。这一回,他没有把她领向派出所。巷子是安全的,一段短短的路程。他很快在宾馆前停下步子,带着冷淡的神色抬头望望闪闪发光的店名。
如归。
一家四星级酒店,名字挺逗的。牛丽在大堂沙发上等的时候,脑子里想,来这里的莫非一个个像龟孙子呢。后来,她一个人在走廊里笑了出来。本来她以为他会带她去某个朋友的房子,但他抬脚就走,领她进了这家连锁酒店。走廊铺着厚地毯,她的笑声被地毯和墙纸吸去,短促、脆弱得像两声鸟叫。上了级别的宾馆这样静,像太平间。她在房间等男人的那会儿,笑意荡漾在心头,怎么也平息不下去。牛丽读过几年书,知道“宾至如归”这个词。但她没有对哪个词这样敏感过,没有什么词能引她发笑,正是因为对书上的字无感,她早早混上社会,在人堆里打滚儿。假如这是她开的店,店名就叫回家,一看就明白,不用咬文嚼字费脑子。不过,她如有开店的资本,可能先买上一栋大房子,一层租人开店,一层自己住,再把老家的父亲、小童、小赖接来住一层。这个时候想那些有点奇怪,一个人住那么一大层,难道她住得惯吗?牛丽看着雾气蒙蒙的镜子,伸手抹了几圈,笑了起来。
还真是缩头乌龟啊。
水放好了,她泡了一会儿,男人进来了。他在门边站了一站,打量着浴缸里露出半个胸脯的她。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告诉她自己的。他和她没有交谈过。但她大略知道他一点情况。某天他接电话时,她听到话筒里传来的一声称呼,春上老师。他是位老师再好不过,有稳定的收入和素质,她不会受到脏病的困扰。另外,牛丽能睡一个老师,也算是对多年前屈辱学生时代的一个交代。他们认识四个月了,每月能见几面。但他们没有面对面、背靠背,或前或后,一躺一站,这样相处过。说起来牛丽都不相信,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现在她也不打算先开口。他把衬衫领口的纽扣捏开,薄薄的嘴唇翕动一下,仿佛浴室的水汽让他呼吸不畅。她不失时机地伸出了一条腿,不,大半条。从轻盈丰富的奶白色泡泡里斜斜地递出来,面带着港台片里三级艳星的笑模样,一串细碎的水花从脖颈上滑落。有人说她长得像叶倩文,也有人说叶玉卿,早年间她在电影院里看过她们,也看过叶子楣。她没觉得这些姓叶的跟自己哪儿像。
她知道自己的腿不是很白,但是饱满紧实,走路、踢人都有力。当年三中出了一个姐妹帮,她算是副帮主的位分,因为迷上《射雕英雄传》里翁美玲演的黄蓉,她成天打打杀杀,挥舞打狗棒将一干男生治得服服帖帖。那时她的威信由班到年级直辐射到整个初中部,三中师生没有不知道初二的丐帮。
牛丽在老家有个外号叫黄鹂。街坊们都说这个女崽俚长大了要做歌星的,说的就是牛丽有把好嗓子。父亲听到了很不高兴,截断他们的话头说,老牛不姓黄!为此他得了个外号,牛黄。他是个挡车工,眼里瞧不上电视里莺莺燕燕的女子。他一辈子活得很有尊严,无论是在厂里终日轰鸣的机器中间,还是退休后打门球的队伍里,他都以出色的技术和好人缘受到普遍的尊重。顶让他为难的是,在被人喊一声牛黄师傅时,他是答应下来,还是装作听不到。好在耳朵逐渐聋掉一只,他不用左右为难了,同时这个称呼也就落实下来。牛丽对别人叫她什么,向来不以为意。别人对她的期望、好意、歹意,她全不放心上。从小脾气里带男性,没留意过洋娃娃、花朵、蕾丝,没玩过皮筋、过家家。她是上树下河、翻墙越窗,要不是生得人高马大,便要练习飞檐走壁的功夫。在课余时段,她通常带领一帮同学玩斗鸡,或是骑着一个瘦小男生的背脊去追杀强盗。她兴奋、嘹亮的嗓音布满了操场或是回家路上的角角落落,方圆一里都能听到。每当她扯起嗓子来,街坊们就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帮崽俚从学堂回来了。他们一下把菜倒进油锅里。有的早早做好了,便从橱窗里一盘一盘端上桌。人就闲闲靠在门上,等他们一脸油汗地经过,喊住她说,来,黄鹂给姨唱一个。牛丽当然不唱。姨手里有一把蚕豆或一只柿饼,她也不唱。她不想冒着给牛黄师傅暴打一顿的风险,吃她们手里那一点吃食。牛黄师傅并不常常打她,他的眉毛长得煞气,动气时眉毛就能杀死她。他在外面的好人缘不知是怎么来的,在家里总是阴沉着脸,没有一句好话,默默地给娘俩施展他各种技术,修煤气灶,清理排气扇,疏通下水道,甚至做出一台三叶电扇。他总在干重活、大活,日常的小活计从不沾手。做饭、买菜、洗衣、打扫都是母亲的事,这也使得母亲更容易拿到扫帚,无论当时手里抓着锅铲、撑衣杆、拖把,顺手就是一下。牛丽的脑袋被敲得发木发麻,功课越发不行。有一个时期头顶秃了一块,榆钱大小的头皮,雪白。后来扩大到半个巴掌大,母亲才慌了。她单位有个人的岳母是退休的音乐教师,一天路遇看看牛丽说,跟我一段试试。每天五点钟,牛丽就被叫起来爬南山,爬到亭子里,跟着退休教师吊嗓子。牛丽对爬山还算喜欢,但不喜欢那么早起床。天黑着,她从床上爬起来,心里对这个多事的退休教师咒骂不止。有时上到山腰,天渐白了,她眼窝里的眼屎才慢慢现形。那是个腊月天,山上风大,湿气重,迷糊中手脚并用爬上了山,身上才有一点热气。嗓子几番吊下来,背上就要出一层薄汗。到后来,天在自己的鬼哭狼嚎里大亮,看得见山脚下的鄱阳湖、楼房,甚至分辨得出哪一块是三中。她的情绪就会发生变化,嗓子越吊越清亮,心情越来越明朗,整个人像朝阳下那薄纱般的云一样透明、轻盈了。说也奇怪,两个月后,牛丽的头发就长出了寸把长,一根根透着亮,直到浓密的乌发布满肩头。
在牛丽完全秃顶前,母亲领她去半仙那里算了一命。一个神神道道的瘪腮帮老头,捏住牛丽的手心,左看右看,翻来覆去,啧啧称奇。母亲脸上透出喜色,那时牛丽的弟妹们还没有生出来,她对这个独女寄托着什么期望,平日并不透露。牛丽如今寻思下来,无非是考学做工嫁人条件优越些吧。瘪腮老头咂着嘴巴,用一根枯长的手指画着她手心,连叹,好命,好命哇。母亲赶紧把两张钞票插进他胸前的口袋里,切切地望着他的嘴。老头这才摇着头,将话抖搂了出来,发达,发达哇。今后你家靠她光耀门楣了。长了一副好手,杨贵妃的手。牛丽插嘴说她不姓杨,叫母亲打了一下。本来母亲想打在她手上,念头一转,杵在了她腰上。这不能算打,只是表明母亲的态度,让半仙不要见怪。半仙毫不见怪,听了牛丽的话沉吟起来。母亲小声说,既是贵妃命,头发还能长的?半仙寻思一下,不姓杨?这也怪了。头发不要紧,不要紧。母亲赔笑说,姓牛。半仙点头,露出一口黑洞洞的牙口,释然说,牛羊不分家,果然是贵妃投胎!当年杨贵妃曾进庙里修行,一头青丝虽未剃度,却也不见天日。如此韬光养晦,保全了一世荣华!
从此母亲不让她洗碗了。就这一点来说,牛丽觉得半仙不讨厌,她的手从此不用拿抹布、浸油水里,而是干干爽爽,很是清闲。有时父亲让她打打下手,母亲就会杀过来,一把将她扯走。母亲心性躁,一言不合发起脾气,让一家人不自在。何况事关女儿和家族的福分,母亲是当仁不让。母亲再也没借助任何工具敲过牛丽的头,不只是头、手,她好像怕了牛丽,简直不敢碰她一下。因为半仙说牛丽长了一对光宗耀祖的手,她的功课不及格,仿佛也不多么严重了。牛丽有了更多时间用于建立丐帮,整顿男生,当然,挥舞打狗棒时是戴着一副白色手套的。帮主助理说她这范儿是黄蓉、小龙女的合体,相当于校服外面披皮草,断非一般人可以驾驭。这时的牛丽不是黄鹂了,都叫她黄帮主。仿佛她姓黄一样,牛丽顾不着她父亲了,每次都胡乱地答应。牛丽被勒令退学的导火索,是她们修理到了政教处主任的独生子头上,据说生殖系统那块给她踢伤了。为着这个“害群之马”,她父母赔了不少笑脸和医药费。母亲挥舞着扫把赶她去主任家赔罪,不惜“做牛做马”,以换得“重新做人”的机会。随着牛丽对政教处主任儿子的再教育,生生将人生的节奏打乱,就此导致母亲梦想的流产。当晚,在抵挡母亲手里那把扫帚时,牛丽的手背被划出一些细小伤痕,破了相。母亲捧着她的手泪流不止,牛丽却没有什么感觉,既不感动,也不烦恼。也是这样一个傍晚,她拢拢被扫帚刮毛的短发,在脖子上贴个创可贴,背包一搭,跳上一辆长途大巴。
这样到了都城。
说起来,她的地位一落千丈。都城人不算欺生,但总归不如在家乡得意。社会终究比学堂复杂些,世道艰难,大事小情让牛丽逐渐丧失了耐性,很少引发她行侠仗义的冲动。打狗棒不知丢在哪儿了,但也不至于做牛做马,牛丽在街面上混生活就得了两字,快活。 锦绣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