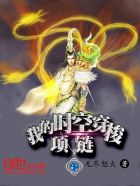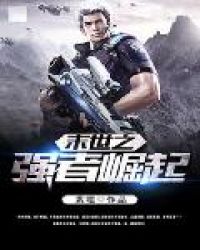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淡淡的乡愁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丁艳作品
作者简介:丁艳,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杂文学会会员。在《星星》诗刊等省市国家级报刊有多篇诗文发表并入选多种选本。个人文集《生命如莲》2011年12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公开出版。
我的小村庄
故乡是县域腹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子,基本就这一个姓。大都沾亲带故。四周没有山,除了田,就是溪沟。父亲常说,什么最难,上山砍柴。年幼的父亲在爷爷的带领下,往西北要整整走上20公里,才能砍上一小捆要烧的木柴。两个叔叔大一点后,就是父亲带着他们去。装上铁水壶,带上饭盒。顶着星星出门,迎着月亮回来,到了秋天,几乎要这样披星戴月砍上一个月,一整个冬天的木柴才够了。
木柴也只是冬天里弄年饭,客人饭,炖煮东西,蒸酒,做豆腐才用,平时吃饭烧的是稻草和茅草。小的时候,放假了,如果没有去抚州城里的外婆家,父亲就送我去村里。夏天,在村里是快乐的。我和那些一脸鼻涕的孩子们下溪沟里摸螺蛳和小鱼。身上脏了,就在溪水里打个滚就是了。这样混的结果是没有三天,我就和他们一样,一脸的鼻涕污泥,全身晒得乌黑。冬天是荒凉的。没有地方去,只好站在晒谷场和老人家一起晒太阳。跟着爷爷端一碗粥,拿一块霉豆腐干,从村头走到村尾,一圈下来,粥就光了。乡下的狗欺生,看见我总汪汪地叫。主人家就会呵斥自家的狗,说:狗眼不识人,小燕子啊,你莫怕,下次它看到你不会叫了。
那时候,村里没有商店,买什么要跑到几里路外的大队去,不过有货郎担会挑着担子来,有针头线脑的卖。最好的是卖豆豉的。货郎用纸包包成尖尖的一包,5分钱1包,每家人只许买一包。奶奶排队买上一包后,会叫上我,拿了钱再去买一包。村子里的人喜欢我,看到我再去她们也不说啥。最喜欢的是用油渣炒,这样饭也要多吃一碗。没有油渣,就用一块肉皮蒸了后洒点盐,就是我最好的美味。小叔叔只比我大五岁,看着馋嘴,多夹了几筷子,被大叔叔狠狠地骂了一句,小叔叔就把碗摔了出门斗气不吃饭。我吓得大哭,爷爷说,莫理他,不懂事的东西。
最喜欢的是坐在灶前烧火。学着姑姑的样子,将稻草挽成一个结,丢进灶膛,然后用一根棍子塞进去,把稻草结挑高点,里面的余热就将稻草烧着了。要么就是用铁叉子将散乱的稻草一股脑捅进去。饭熟了以后,在灰里放一个红薯或者是芋头,然后饭吃到一半了,红薯也烤得香香的。有一个夏天,我烧完火,要吃饭了,却发现自己凉鞋不见了。之前我明明脱了放在烧火凳子边的。到处找不着的时候,我灵光一闪,赶紧用叉子往灶膛里扒,果真扒出两只鞋子,已经烧得黑乎乎的了。没有鞋子了只好穿着姑姑的布鞋,长长的,一走路就掉,我又学不来那些打惯了赤脚的孩子,于是就在晒谷坪站着看别人玩。那天也巧。母亲正好从城里进修回家了,给我买了新凉鞋,父亲赶紧走了十多里山路来接我,我就穿着新凉鞋回了自己的家。
过年前夕有爆米花的人挑了工具到处喊:爆米花哦爆米花。我们就从米缸里抓一把米去爆米花。看那人把米装进黑糊糊的铁罐子里,然后在炭火上慢慢地转。差不多的时候,用布袋子套住铁罐子的口,打开,砰的巨响,袋子里就都是白花花的米花了。最好是糯米,爆出来的又大又香,如果加了糖精的话,那真是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了。我们爆米花是吃零食。大人爆米花,是为了储存做的灌心糖。
村子里年货都是自己做的,有灌心糖,里面灌了芝麻或者是黄豆粉,有点像大人抽的香烟。还有芝麻片,用芝麻、米花和麦芽糖一起做的。花生都是自己种了自己炒的。我喜欢吃姨奶奶家的炒豆子,是用洗干净的河沙炒熟的黄豆,酥脆可口。
书读得越来越多,离村庄就越来越远了。过了十岁,母亲放假也不让我回的。因为每到一家除了年礼,父亲还要给那家孩子压岁钱,如果我不去,那家就不用回压岁钱,这样我们家就要多给了,我去了,临走的时候,那家人家要把父亲给的钱回给我。到每一家拜年吃饭前笃定都要先吃水煮荷包蛋,一个人三个。不知道是怎么沿袭下来的。往往吃完蛋我也就饱了。很多的小孩子会站在门口来看我的稀奇。在他们的眼里,我这个来拜年的孩子和他们有太多的不同,我的衣着要比他们好看,我的鞋子干净得看不到一点污浊,特别是我不像他们脸上总是干裂得有一丝丝的裂痕。
拜年走的时候,很多的亲戚都会跟过来,这个塞几个鸡蛋,那个塞一袋自己做的麻片,还有的就干脆塞一块钱,其中有很多人家我们都没有去拜年的。
后来才知道,我们家的辈分在村子里也算高的。排起来,爷爷住的那个厅堂里,另外三家人家的户主甚至得叫我姑姑。
几个叔叔都迁到城里后,村子里最亲的是姨奶奶家了。姨奶奶是父亲的小姨,也嫁到了我们这个村子,就在爷爷家后面一点点。父亲十岁就丧母,姨奶奶对父亲格外疼爱。后来,因为姨奶奶多年未育,爷爷再娶后,生了两个叔叔,两个姑姑,大姑姑就送给了姨奶奶做女儿,所以这个姑姑实际上就是两家的孩子。大姑姑送给姨奶奶后两年,姨奶奶真就生下了一个女孩子,我也叫她姑姑。
那里孩子叫父亲不叫爸爸,叫“叔”,叫母亲不叫娘,叫“yi(四声)”。我初始不明白,父亲和叔叔姑姑怎么总是叫爷爷“叔”,还以为爷爷真的是他们的叔叔,后来才知道,方言就是这样。
现在回去,很多人家都从老屋迁出来了。那些大大的有神龛的厅堂变得破败荒凉,但是四周墙壁上人家办喜事贴的密密麻麻的喜联都还可见。细细地看,还有“恭祝叔公大人七十大寿志喜”,落款是“愚外甥谁谁叩拜”。
新村紧邻老村,一水地都是三层的楼房,虽然参差不齐,倒也有点规模。村边那条溪沟,在浑浊淤塞了好几年后,因为新村建设改造,现在恢复了往昔的清澈,小媳妇们又开始出来洗衣服洗菜洗家什,而她们,我却一个都不认识了。 淡淡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