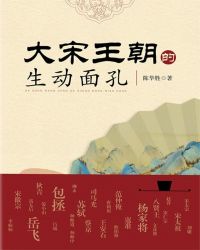第17章 司马光:一辈子都在砸缸却总也砸不破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大宋王朝的生动面孔【富媒体版】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王安石死后,他的死对头司马光被召回朝廷拜了宰相。在讨论对王安石的追悼仪式和身后评价时,司马光说了一句公道话:“王安石这个人还是一位正人君子,只不过固执了一点。”然而,这个“固执”的评价,其实也正是司马光的自我评价,他的固执劲头一点儿都不比王安石逊色,为此,苏东坡还给他取了一个“司马牛”的绰号,意思是像牛一样顽固。
今天我们知道司马光的大名恐怕得益于“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几乎所有的童蒙读物里都收录了这个著名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在司马光所处的年代就已经流传开了,当时的开封、洛阳一带有人把这个故事画成了图画,所以,司马光在他年少的时候就当了一回网红明星,成了宋朝小朋友们的学习榜样。
由于有这么好的童星基础,司马光20岁就中了进士。在庆祝的宴会上,朝廷照例把一盘盘的簪花赐给新科进士们,进士们纷纷将一朵朵的花戴在头上,这在当时是一种进士的荣耀。而司马光却不肯戴,他觉得这些珠光宝气的簪花太过奢华,直到有人提醒他:这是皇帝的赏赐,不可以不接受的,他才不情愿地取了一枝勉强戴上。
司马光的家人们是最能体会他的这种固执脾气的。在宋朝,元宵节是最热闹的节日,称为上元节,与端午、中秋并列为法定的三大节日。元宵的传统习俗就是赏灯,宋朝的上元灯会甚至比今天的还热闹,而在这天晚上,男女老少往往倾城出动去看灯展。偏偏司马光不喜欢这样的热闹,他的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却板着脸说:“家里有灯,何必出去看?”夫人只好说:“外面热闹,还想看一看游人。”没想到司马光的脸绷得更紧了:“想去看人?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是鬼吗?”
这个故事收录在宋朝吕本中的《轩渠录》里,听起来确实有些不近人情了,而司马光在官场上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人情。在《宋史》的记载里,他给皇帝进言,每回都是直言不讳:某某人是奸臣、某某人是小人,指名道姓,一点都不委婉,当然也不怕别人打击报复。
固执的劲头上来,他甚至敢跟皇帝“死磕”:皇帝亲信的一名宦官死了,皇帝想给宦官的追悼会提升规格,摆放一些宫廷的仪仗,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说宫廷的皇家仪仗就连孔夫子都担当不起,怎么能给一个太监用呢?后来,皇帝的妃子死了,皇帝又想动用这些仪仗,司马光还是上书反对:只有皇后可以享受的待遇怎么可以给妃子用呢?——在司马光看来,礼制的规矩可不像那只缸,说打破就可以打破。
宋仁宗身体不太好,但又没有亲生儿子,所以也就没有立太子。别的大臣心里担心却都不敢说。司马光可管不了那么多,他毫无顾忌地上书,请仁宗皇帝早立太子。同朝的大臣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他却对大家说:“我们今天都不发表意见,等到某一天皇帝不行了,半夜里从宫中传递出一张小纸条,说是某某将继承皇位,这样就靠得住吗?”司马光当然也知道,他这样会得罪仁宗皇帝,但为了国家大事他已经置生死于度外。所幸,仁宗皇帝并没有怪罪他,反而是虚心地接纳了他的意见。
仁宗死后,英宗即位。英宗是仁宗的侄子,他的父亲被封为濮王,而从名义上说,他是过继给仁宗当儿子,从而继承皇位的。两个父亲,一个是亲生父亲,一个是名分上的父亲,那么在礼制上应该怎么称呼呢?要是在今天,一定是倾向于血缘上的亲生关系,但在古代,正统的观念可不这么认为。英宗当然有些不甘心遵守正统的观念,于是,他把这个问题抛给大臣们,让大家讨论决定。本来是没什么好讨论的,既然要讨论,那就说明可以有另外的意见了: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观念更新得比较快,他们真诚地认为人伦亲情不能被替代,父亲总不得以DNA鉴定的为准;但司马光却保持着他一贯的固执,坚持认为既然英宗是继承仁宗的大统,那就应该称仁宗为父亲。大臣们喋喋不休地争论着谁是父亲的问题,分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最后,皇太后,也就是仁宗的皇后出来说话了,当然是捍卫仁宗的利益,于是,这场“濮议”之争最终是司马光一派获胜了。但胜利归胜利,司马光不讨英宗皇帝的欢心却也是明摆着的,很快,他就被赶出了朝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洛阳酝酿创作一部给皇帝治国当教辅书的巨著《资治通鉴》。
英宗又很快去世了,神宗皇帝即位。司马光对这位新皇帝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向皇帝献上了《资治通鉴》的十几篇样稿。神宗一方面是觉得司马光的这些样稿写得很好,这件工作确实值得去做;另一方面,他正想要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也不愿意司马光这个老顽固在身旁碍手碍脚,于是就顺水推舟,替司马光成立了一个创作班子,组成《资治通鉴》的编辑部,让司马光去洛阳当他的主编了。
司马光跟王安石其实很早就认识,两个人的关系也不错,互相赏识,但在治国理念上,他们的观点就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了。拿今天的话说,王安石秉承的是国家主义理念,他要改革创新,替国家积累财富,做到富国强兵;而司马光奉行的是儒家传统的思想,甚至带一点西汉初年文、景之治时“与民生息”的无为理念,强调国家应该首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让老百姓富起来,小河有水大河自然满,而不能以国家利益至上,让国家与老百姓争利。两个人为此在朝堂上进行过公开的辩论,宋神宗表面上说,他认为司马光说的对,但心底里他是支持王安石的。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另一个指责是王安石不会用人,他所用的都是一些奸佞小人。王安石所倡导的新法,到了具体执行的时候,由于这帮奸佞小人掺杂了各自的私利,不仅变形、走样,甚至成了老百姓巨大的灾难。司马光是敢说的,在仁宗、英宗朝,他就指名道姓地论说忠臣奸臣,到了这个时候,更是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他也因此受到了章惇、蔡京等新党的切齿痛恨,以致司马光死后,章惇甚至建议朝廷对他进行开棺曝尸,幸亏皇帝没有答应这个残酷而荒谬的请求。
司马光的意见在朝廷得不到响应,他也就退居洛阳安心去搞他的创作了。为了编纂这部《资治通鉴》,司马光也是蛮拼的,他特意用滚圆的木头做了一个枕头,取名叫“警枕”,意图在于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贪睡。因为头枕在这样一块圆木头上,进入梦乡后,身子只要稍微一动,“警枕”就会滚动,将自己惊醒。惊醒后的司马光也就立即起床,继续握笔写书。到了后来,他已经牙齿松掉、头发脱落、眼睛高度模糊。但他却无怨无悔,总想着尽心尽力地为后世的帝王们编好这本治国的教科书。
司马光人被赶出了朝廷,但他那些以民为本、为民生做主的思想和言论却在民间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当时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人选。神宗死后,司马光从洛阳赶回京城悼念,老百姓听说他回来了,蜂拥而至将他的车驾围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哭着对他说:“司马相公这一趟就不要再回洛阳了,留在朝中替我们老百姓做主,救救我们老百姓吧!”
当政的太皇太后也真的听取了民意,把司马光留了下来,让他代替王安石做了宰相。这个时候,离司马光生命结束已经只有短短五个月时间了,但司马光的固执劲儿却一刻都不消停,他上台后立马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所有的王安石新法一律推翻,重新来过。为此,原本也反对变法的苏轼与他发生了争执,在苏轼看来,王安石的有些新法还是可行的,不能全盘否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司马光对扰民的新法已经深恶痛绝,一点儿也听不进苏轼的意见,为此苏轼也恼火地将他称为了“司马牛”。
这头倔强的老牛想要打破一只名为“国家主义”的缸,这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政治学来看,显然都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甚至连王安石留下的那只旧缸也无法打破。司马光尽管在他拜相的短短五个月里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但等到他死后,新党人物又相继上台,新法也相继出台,北宋就在新旧两党的“翻烧饼”政治中走向了覆灭。
司马光地下有灵,也会痛心疾首:这可不是他想要砸破的那只缸! 大宋王朝的生动面孔【富媒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