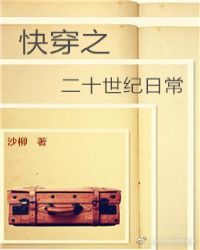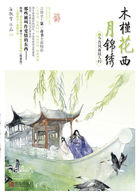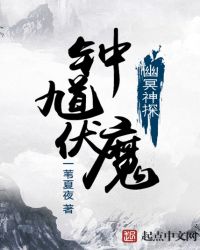第四章 谢绝宗教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当西方文明的“五月花号”从雅典启航,途经罗马、君士坦丁堡、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终于抵达费城时,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文明都怎么样了?
大多都不辞而别,比如奥尔梅克(Olmec)。
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中美洲的奥尔梅克也属于第一代文明,创造者则是种植玉米,吃南瓜、辣椒和西红柿的农业民族。他们崇拜美洲虎或者美洲豹,城市里有金字塔形状的神庙,但最具标志性的还是巨石头像。
这是一个至今无人破译的谜团。的确,这些石像是那样地怪异,无一例外地都只有头颅没有身躯,却个性张扬形象逼真。同时,它们又是那样地巨大,全部都由整块的玄武岩雕刻而成,最高的一尊竟重达三四十吨。
圣洛伦佐第八号大头像,高2.2米。
圣洛伦佐第六号大头像,高1.67米。
如此之重的石像,如何运到不产玄武岩的奥尔梅克祭祀中心呢?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这些石像最后被掩埋,不受打扰地静静躺在一个隆起的山丘下,上面长满灌木丛。直到火山运动把其中几个震落到草地上,它们才重见天日,并迎来另外一些人类敬畏、惊诧和疑惑的目光。
此刻,奥尔梅克文明早已陨落,连同它的创造者都莫名其妙地消失在热带丛林,不知去向。 注释标题 关于奥尔梅克文明,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学术界也说法不一。此处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3册、丁朝阳《玛雅文明》、王晶波《失落的文明》。
这座金字塔是墨西哥特奥蒂瓦坎遗迹中最大的建筑,特奥蒂瓦坎人有高超的建筑技术。
其他兄弟姐妹呢?
有的也不见了,比如哈拉巴(Harappa)。
哈拉巴诞生在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流域,因此也叫印度河文明,但与印度文明不是一回事,标志则是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巴这两座城市。它们分别在印度河的上下游,相距644公里,哈拉巴文明便由此得名。
两座城市几乎是孪生的,面积和人口大致相同,也都有卫城和谷仓,就连卫城的朝向和用砖都是一样的,不免让人猜测这两个独立的城邦很可能出自同一设计师的手笔。
没错,它们的卫城都面向西方。
与奥尔梅克的神秘和神奇不同,世俗的哈拉巴文明是平易近人的。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竟然是发明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奢侈品,这就是包括抽水马桶在内的卫生间。于是,哈拉巴人可以很方便地每天洗澡,而不用担心污水的处理。
据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
这其实是程度很高的文明。因为不但浴室的设计需要聪明才智,为城市建立排污系统更不是简单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证明哈拉巴文明有一个或一群智慧的领导者,可惜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两座城市都没有宫殿和神庙,那么是谁在高效率和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它们呢?不知。 注释标题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
但我们知道,这大不同于克里特(Crete)。
克里特文明是被历史学家以公元前1700年为界,分为早王宫和后王宫两个时代的,可见其显著特征是宫殿。其中最负盛名的米诺斯(Minoans)迷宫已经被考古学家完整地发掘出来,确实规模宏伟结构复杂,只不过里面没有怪兽。
怪兽是米诺斯王后与一头漂亮公牛的私生子,因此半人半牛。他或它就住在迷宫里,战败的雅典则被米诺斯国王勒令每年或每隔九年送来一船或七对少男少女,供那家伙消遣或者食用。这种残忍而悲惨的游戏持续了很久,直到寄养在外公家的雅典王子忒修斯(Theseus)横空出世。
忒修斯宣布,他愿意去做牺牲品。
毫无疑问,忒修斯是要为民除害。幸运的是,这位少年英雄刚一出现在克里特岛众人面前,米诺斯公主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公主给了他线团和一柄魔剑,忒修斯则用魔剑杀了怪兽,然后沿着一头拴在门口边走边放的线,按照公主从设计师那里获得的办法走出了迷宫。
可惜乐极生悲。忒修斯返回雅典时,忘了依照事先的约定将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误以为儿子已死的雅典国王悲痛欲绝跳海自尽,那片体现了父爱的海域则被以他的名字埃勾斯(Aegeus)命名为爱琴海(Aegean Sea)。 注释标题 以上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美国)依迪斯·汉密尔顿《神话》。忒修斯的故事也有各种版本,这里不争论。
这当然是神话传说,却也一语成谶,只不过挂上黑帆的是克里特文明。它被后来的征服者迈锡尼人(Mycenaeans)打扫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就像哈拉巴文明人间蒸发,两河文明掩埋在黄沙和土丘之中,全都了无陈迹。
至于今天的埃及,沃土还是那片沃土,河流也还是那条河流,但民族已不是那个民族,文明也不再是那个文明。作为运气最好的一家,古埃及也只留下了西风残照,以及并非汉家的陵阙——金字塔,还有躺在里面的木乃伊。
文明的陨落,几乎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
唯一的例外在我们这里。的确,创造中华文明的始终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一直在发展壮大,不断有新鲜血液增加进来。同样,我们创造的也只有一个文明,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三千七百年不曾中断,没有断层和空白,也没有陨落和衰亡,西方人总结的规律未必符合中国国情。 注释标题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争议,这里不展开。
但,以其他文明为参照系,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比如印度。
翻过喜马拉雅
公元1025年,也就是中国北宋的仁宗年间,有个名叫马穆德(Mahmud)的阿富汗突厥人,攻陷了印度西海岸的苏姆拉特(Somnath)城。马穆德对此地觊觎已久。在过去那些年份里,他每年冬天都要离开寒冷的加兹尼(Ghazni),率军到旁遮普平原(Punjab Plain)展示威武雄壮。他把这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所到之处是什么样子也就不难想象。
印度人却毫无戒心。
淡定和泰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苏姆拉特有印度最崇高的圣殿和神庙,里面供奉着湿婆(Shiva)。湿婆与梵天(Brahma)和毗湿奴(Vishnu)同为印度教的三大主神,其中梵天是创造神,毗湿奴是保护神,湿婆是破坏神。但湿婆只是在世界行将就木时才实施毁灭,而且毁灭之后将再造新生。
在大多数描绘中,湿婆有四只手,其中三只分别握着敲响生命节奏的鼓,举着能够毁灭和再生的火,拿着保证胜利的棕榈叶,另一只手则呈现出漫不经心的雄辩姿势。那高高抛起的头发表明他在以惊人的速度飞快旋转,脸上却依然是平静的微笑,表示世界在痛苦与欢乐中无限循环。
体现了再生力量的是名叫林伽(Lingam)的圣物。它是镶嵌着珠宝的直立柱子,象征着湿婆的生殖器。每天,人们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打水来清洗它,还有三百多名舞女在它面前不停地表演,从而确保信徒的虔诚和神的永恒。
这样的圣城,怎么会被攻陷呢?
印度朱罗王朝时期雕像,美国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藏。
因此,当马穆德到来时,那些印度教徒只是安静地冷眼旁观,并等待神的赐福。结果可想而知,马穆德以胜利者的姿态傲然站立在破碎的神像前,神庙里一片狼藉。 注释标题 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10册、(美国)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这段历史的人名地名有各种译法,马穆德又译马默德、马茂德、马哈茂德、麦哈茂德,苏姆拉又译索梅纳斯、斯谟那特,此处译名从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外文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
当然,马穆德的政权还是被另一帮突厥人推翻了,后者的领袖则在德里(Delhi)自称苏丹(Sultan),即伊斯兰世界世俗的君主。这个政权史称德里苏丹国家,北部印度也变成了突厥人的天下。只不过这时的中国已是南宋,德里苏丹的建国时间则在蒙古草原的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那年。
但,这种事情在印度却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成为这片土地君主的外国人,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之前统治时间较长的除突厥的德里苏丹,还有建立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的蒙古人。至于入侵者,则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公元前518年,波斯人;
公元前325年,马其顿人;
公元前304年,条支(伊拉克)人;
公元前180年,大夏(塞种或斯基泰人);
公元1世纪中,大月氏人;
公元5世纪中,白匈奴人;
公元712年,阿拉伯人。
此后,是突厥、蒙古、荷兰、法国和英国人。
这可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的确,在外人眼里,那片土地确实神奇,居然有长羊毛的灌木和产蜂蜜的芦苇。看来,仅仅棉花和甘蔗便足以让西方蛮族大惊小怪,真不知道他们看见骑在大象上的印度王公是何感觉。难怪就连唐太宗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管他只能从玄奘法师那里得到一些需要靠想象来补充的印象。
但,比较一下两大文明,却或许是有意思的。
表面上看,印度与中国不乏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只不过我们是黄河与长江,他们是印度河与恒河。然而喜马拉雅一山之隔,中华与印度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甚至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
最直观的区别在于对待历史的态度。近现代以前,印度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通史、编年史或者断代史,以至于历史学家想要弄清楚其来龙去脉,除了借助中国、西方和阿拉伯人的只言片语,便只能指望出土文物。
印度人自己却满不在乎。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从甘婆王朝(Kanva Dynasty)到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那一片空白的三百多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介意,如果历史出现了断层,将怎样体现它的连续性。 注释标题 比如哈拉巴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便有几百年的空白,从甘婆王朝到笈多王朝之间也有三百多年史实不清。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
这未免怪异。要知道,印度人对于时间的理解,可是连刹那(0.018秒)和瞬间(0.36秒)都有区别的,却不在乎几百年记录的空白或模糊。难道千年不过弹指,瞬间和刹那反倒永恒?或者过去并不重要,当下才是历史?
也许吧,也许。
实际上,印度文明本身就是难解之谜。它的时间线索断断续续,空间范围变动不居,中心漂移而结构复杂,宽厚兼容又固步自封。印度几乎从未侵略过别人,自己的历史却往往被外族改写。同样,在英国人之前,也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将众多的族群和林立的土邦真正整合在一起。他们是各自为政和自行其是的,却又同属于一种文明。
这真是咄咄怪事。
那么,在印度半岛,永恒不变的是什么呢?
有一件事情或许能够说明问题。
公元1000年,一座巨大的神庙在朱罗(Chola)王国的首都坦贾武尔(Thanjavur)竣工。这座花岗岩砌成的圣殿是那样宏伟壮观,仅顶部的圆形拱顶就重达80吨,上面还有金色的标志性装饰物。这是罗阇罗阇(Rajaraja,阇读如都)国王慷慨解囊和其他豪门奉献的结果,他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在底座刻上花体字的碑文,并在神龛前竖起林伽。 注释标题 坦贾武尔又译坦焦尔,此处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译文。本段描述亦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9册。
这时,只比马穆德攻陷苏姆拉特早25年。
苏姆拉特与坦贾武尔却是天南地北。后者在印度半岛东南部,与斯里兰卡(Sri Lanka,旧称锡兰)隔海相望,前者却因为在西北而受到来自阿富汗的打击。然而他们都有美轮美奂的神庙,而且供奉的也都是湿婆。
支持着印度文明的是什么,现在清楚了吧?
没错,那就是宗教。
宗教之邦
宗教是印度人的生命线。
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印度人这样痴迷于宗教。他们可以没有国家,也可以没有民族,甚至可以改变信仰,哪怕那信仰是外来的,但什么宗教都没有却绝对不行。因此,他们不仅宗教品种繁多,信徒到处都是,还为人类贡献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佛教,尽管它在本土反倒走向了衰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可能是地理、历史和文化多方面的。
的确,有着喜马拉雅这座庄严肃穆之圣山,恒河这条奔流不息之圣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的神秘和不可思议,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caste system)。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有着高低贵贱的等级。等级起先有四个,依次是:
婆罗门(Brahmin),祭司和僧侣;
刹帝利(Kshatriya),国王和武士;
吠舍(Vaishya),平民,包括商人;
首陀罗(Sudra),奴隶和被征服者。
后来,又出现了第五种姓(Panchamas),被称为旃荼罗或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意思是贱民。
种姓是与生俱来和世袭不变的,不同的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禁止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注释标题 以上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其实,这种制度也让所有人都活得担惊受怕。最低级的贱民固然时时都有性命之忧,高贵者也得小心翼翼,比如在晾晒被单和衣服时,必须确保不会有卑贱者偶然路过,因为那很有可能会使自己的贴身之物被后者的影子玷污。
于是就有了不同的声音。
为种姓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Brahmanism)。他们以创造之神梵天为最高信仰,古代文献吠陀(Veda)为宗教经典,奉行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按照他们的说法,四大种姓是梵天用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创造出来的:嘴创造婆罗门,手创造刹帝利,腿创造吠舍,脚创造首陀罗,当然贵贱有别。 注释标题 见婆罗门教经典《摩奴法典》。
这并不奇怪,毕竟,婆罗门是雅利安人的宗教,而雅利安人是次大陆的入侵者和新文明的创造者。哈拉巴文明湮灭之后,让印度半岛文明之花梅开二度的便主要是他们。与被征服的土著相比,雅利安人的肤色要浅得多,他们也当然要提出种姓的概念。要知道,种姓一词源于梵语瓦尔那,而瓦尔那( varna)的意思是颜色,同时也意味着品质。 注释标题 请参看(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龙昌黄《印度文明》。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征服者当中也有了婆罗门和刹帝利,白皮肤的征服者反倒有些人社会地位降低。重新洗牌不可避免,要求平等也呼声甚高,需要的只是说法。 注释标题 请参看(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应运而生。
两种新宗教对所有人都是敞开大门的,诞生于16世纪的锡克教(Sikhism)也如此。事实上,佛的本义是觉悟者,耆那的本义是胜利者,锡克的本义是学习者,所以,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每个人的血都是红色的,为什么要分等级?值得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学习和胜利,而不是出身。这样的说法,显然比繁琐的仪式和刻板的教义更能让人欣然接受,广为传播。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国王们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例如,比秦始皇略早一些的孔雀王朝阿育王(Asoka)就是佛教的信奉者。他放下屠刀皈依佛门以后,派到邻国的就不再是军队而是弘扬佛法的高僧。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Hinduism),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至于突厥人的德里苏丹国家、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当然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印度,岂能不是宗教之邦?
事实上,文明的嬗变,文化的传播,政权的更迭,王朝的兴衰,在印度都与宗教息息相关,也与王朝的宗教政策关系密切。笈多王朝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宽容,便让印度文化在其治下达到鼎盛;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Akbar)大帝娶印度教首领的女儿为妻,结果是政权稳固天下归心。
显然,阿克巴这个突厥化蒙古人的波斯混血儿是非常聪明的,尽管他不认识字,只是一介武夫。阿克巴甚至有这样一句名言:一切宗教都有光,有光就或多或少会有阴影。只不过,他不知道这光来自哪里,那影子又有多长。 注释标题 以上请参看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龙昌黄《印度文明》。
也许,这得去问犹太人。
没有国界的国家
迦勒底(Chaldea)王国的首都新巴比伦(Neo-Babylonian)美轮美奂。这座建造在巴格达(Baghdad)以南数十公里的城市有三道城墙,每道城墙每隔44米就有一座塔楼。墙上的大道可容四匹马并行,城外则是又深又宽的护城河。城中金碧辉煌的王宫内,还有一座高达25米的空中花园。那是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为他那娶自米底的美丽王后修建的,后来被希腊人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注释标题 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希腊人说的空中花园不在新巴比伦,而在亚述首都尼尼微(Nineveh),建造者则是亚述国王辛拉赫里布(Sennacherib)。
但在犹太人看来,这里不是花园,而是监狱。
建都耶路撒冷(Jerusalem)的犹太王国,是由于在大国争霸时倒向埃及,而被尼布甲尼撒列入黑名单的。中国春秋时期的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攻进耶路撒冷,把这个弱小的国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他当着犹太国王的面杀死了犹太王子,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然后挖去了那亡国之君的双眼。国王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同行的贵族、祭司和工匠多达上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 注释标题 以上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赵彦、于至堂《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
此一去差不多半个世纪,直到公元前539年,他们才被灭亡了迦勒底王国的波斯皇帝居鲁士释放回国,以“自治神庙城市”的形式在耶路撒冷重建家园。 注释标题 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据John Clark Ridpath《世界史》。
可惜,犹太人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此后,他们的国家又多次被征服,人民也多次被流放,最后在中国的东汉时期被罗马人赶尽杀绝,从此成为一个没有祖国、迁徙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可以说,几乎没有谁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又坚忍不拔。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那座哭墙(Wailing Wall),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 注释标题 哭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
但,一个文明史上的奇迹也被创造出来。
事实上,几千年来被征服的小国不可胜数。而且,只要国破家亡人员流散,就再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失去祖国一千八百年,流散世界十万八千里,而民族犹存。甚至可以说,他们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立于世界之林。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宗教。
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我们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要讲到的,犹太人是历史上最早建立信仰的族群。这种信仰的真正确立,则正好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旧约》的前五篇《摩西五书》,便是在巴比伦之囚那会儿,由犹太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们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唯其如此,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注释标题 见《圣经·旧约·诗篇137:1》。
啊,耶路撒冷城南的锡安(Zion)山呀!
这当然远远不够,尽管可能意味着复国。 注释标题 在犹太教的圣典里,锡安是雅赫维居住之地,也是雅赫维立大卫为王的地方,后来的锡安主义(Zionism)更被译为犹太复国主义。
于是,苦难的犹太囚徒被告知,只有他们的战神雅赫维(Jahweh或 Yahveh)才是唯一的神。可惜,此前的犹太人却忘记了这一点,反倒崇拜多神和偶像。显然,受难是因为背叛,新生则要靠虔诚,最早的一神教就此诞生。 注释标题 以上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英国)亚历克斯·沃尔夫《世界简史》、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没错,这就是犹太教(Judaism)。
从此,失去祖国背井离乡的犹太人有了主心骨,有了凝聚力,有了核心价值,也有了认同感。事实上,只要坚信唯一的神和先知的教诲,恪守教规,严守禁忌,那么,无论他身处何地,也无论贵贱贫富、肤色黑白,他就是犹太人。 注释标题 根据犹太教律法《哈拉卡》的定义,从宗教意义上讲,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从民族意义上讲,所有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都广义地属于犹太人。
国籍,反倒是无所谓的。
实际上,犹太人比许多有祖国的民族更团结,甚至更有文化优越感。因为按照他们的教义,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这种观念和感觉使他们保持了民族特质,并能够不间断地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输送人才,尽管犹太教也因此而无法像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具有世界性。 注释标题 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呵呵,此时无国胜有国。
其实,宗教之于人,意义和作用与城市和国家不乏相似之处。比如一个人说“我是佛教徒”时,就跟他说“我是曼谷人”或者“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效果都无非是身份的辨识或认同。你是北京人,我是上海人,是辨识;你是穆斯林,我也是穆斯林,则是认同。宗教甚至也像城市和国家一样能够提供安全感和自由感:来自神的保佑和庇护体现了前者,发自内心的真正信仰体现了后者。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然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们民族是没有宗教的,之后也不纯粹和虔诚。孔子的说法是“祭神如神在”,民间的观念是“不灵则不信”。说到底,是似信非信,若有若无。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还得先弄清楚宗教从哪里来。
巫术之子
后羿射日之前,女丑死了。
女丑不知是晒死的,还是烧死的。可以推测的是,她死前扮演了旱魃(读如拔)。旱魃就是旱魔。古人认为,旱灾是旱魃作祟的结果,对策则是让人装扮成旱魃,然后站在太阳底下暴晒。旱魃受不了,就会逃走,灾难也就解除。
当然,烧死这人,效果也一样。 注释标题 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及其所引《山海经》等资料。
无疑,这是一种巫术(Witchcraft)。
巫术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模式之一。在时间表上,只有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排在它的前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工具或者技术,目的则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只不过巫术的思维方式比较特别。比方说,它认为一个事物的样子,跟这个事物是同一的。因此,扮演旱魃的女丑死了,旱魃也就会死。
同样,天不下雨,就往天上泼水;人不生娃,就搞生殖崇拜;病治不好,就请道士画符。这些都是巫术,是几乎所有民族在原始时代都会有的救命稻草。它甚至需要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即巫师和巫婆,女丑则是其中之一。
难怪女丑非死不可。
遗憾的是,女丑虽然死了,旱情却依然如故,天帝或尧也只好让后羿出手射下那九个多余的太阳。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难怪就连古代神话也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也难怪许多人要批评巫术,或者把巫术称为“伪科学”。
但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即便是科学也要试错,巫术则是人类的“集体试错”。没有巫术的千万次试错,我们就学不会天气预报,也学不会人工降雨,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
据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正是巫术,把人类领进科学之门。
实际上,科学与巫术一脉相承。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掌握的。人类一旦掌握规律,就可以控制事态,改变现实。只不过,科学掌握的规律是现实的,巫术却很可能误入歧途,因为巫术的主张多半想当然。
所以,科学必然诞生。
巫术也不是“伪科学”,而是“前科学”。
没错,科学前的科学。
科学,是巫术的长子。
然而人类却不能过河拆桥,有了儿子就忘了老子。要知道,相对于科学已经掌握的部分,未知领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失去好奇心和敏锐度,甚至不能不想入非非。好奇害死猫,不好奇却可能害死人。
巫术,恰恰代表着人类那根敏感的神经。
也许,巫术探索世界的方法是错误的,也许而已。但科学的方法即便是正确的,也未必就是唯一的。至少,在科学诞生之前,巫术深刻地安慰了人类对不可知的恐惧,抚平了人类遭受飞来横祸和无妄之灾的创伤,使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变得温柔和向往,正如我们在女娲那里看到的。
巫术,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医生。
因此,它还会有两个儿子:宗教和哲学。
人类需要这两种精神文明,是因为科学并不万能。比方说,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都是人类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科学却回答不了也不该由它回答,只能拜托宗教和哲学。
宗教和哲学延续着巫术对未知世界的触摸,只不过方式不同。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需要幻想和直觉。巫术,就是直觉、幻想,再加操作。
所以,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艺术与巫术的血缘关系,在美学界早已不是秘密。简单地说,就是当某种形式或仪式的目的,由解决问题变成了传达情感,它也就由巫术变成了艺术。换句话说,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就是从工具到巫术,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 注释标题 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提出,人类的智慧、意识和精神生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巫术—宗教—科学”。起先人们以为,往天上泼水,就会下雨。这就是巫术。后来发现不管用,便叩拜神灵,乞求赐雨。这就是宗教。等到连这也不管用时,人类才真正踏进科学之门,学会了天气预报,也学会了人工降雨。所以,巫术是“前宗教”,也是“伪科学”。本书不同意这个观点。
所有的胎盘都会功成身退,巫术也一样。
功成身退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只不过,希腊是从科学到哲学,印度是从宗教到哲学,中国则有另一条路要走。
那就先看看希腊。
天上人间
阿多尼斯(Adonis)刚刚出世,爱神就一见倾心。
这里说的爱神当然就是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Venus)。没错,她还是美神。不难想象,能让爱和美之女神动心的,又该是怎样的男子!
那一定是人见人爱。
所以,当阿芙洛狄忒将这坨小鲜肉托付给冥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抚养时,后者也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两位女神互不相让,只好由众神之王来做包公。宙斯(Zeus)的判决则是:阿多尼斯秋冬归冥后,春夏归爱神。
哈哈,好一个平分秋色!
于是,每年那两个温暖的季节,阿芙洛狄忒都要放下神界的事务,万千宠爱地来陪伴那花样少年。可惜这男孩实在太贪玩了,竟然不打招呼一个人跑出去狩猎,结果死在野猪的牙齿下。等到爱神闻讯赶来时,已是回天无力。
阿芙洛狄忒也只能这样歌唱:
我的爱,就像梦,
顷刻间无影无踪。
你是人,我是神,
今生再也不能同行,
唯有长吻,在你嘴唇。
哭完,爱神俯下身子,在那美少年的唇间吻了又吻。
鲜血从阿多尼斯的伤口慢慢流淌出来,每一滴血渗过的土地上都开出了鲜红的花。此后,每当这鲜花盛开时,希腊的姑娘们都会举行哀悼的仪式,并为之癫狂。 注释标题 请参看(美国)依迪丝·汉密尔顿《神话》,阿芙洛狄忒的歌词有改动。
这实在是只有古希腊人才编得出的故事。
的确,正如埃及的神半人半兽,希腊的神半人半神。或者说,除了更加漂亮和永远不死,他们与人无异。人身上的七情六欲,甚至所有毛病和弱点,希腊的神都有。从争权夺利到争风吃醋,从胡言乱语到胡作非为,包括偷情、使坏和恶作剧,以及相互欺骗,奥林匹斯山(Olympus Mons)上的诸神哪一样没干过?能够想到的,他们都做了。
而且,从不忏悔。
这样的神,当然不可能承担宗教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希腊神话也只是他们的《西游记》,不是《金刚经》,更不是《古兰经》。说白了,他们干脆就没有宗教经典,当然也没有教主教义和教会教规,甚至不知信仰为何物。 注释标题 请参看(美国)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该书十分强调希腊宗教与希腊神话的区别。
那么,希腊人也有宗教吗?
有,但至少一半是用来玩的,另一半则交由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去自由创造。没有绝对权威和清规戒律,只有“将人向上提升的巨大力量”,以及关于理想境界的朦胧认识和模糊界定。如果一定要下定义,或许可以叫“完美”。 注释标题 亦请参看前书,所引为叔本华语。
完美即神。也许,这就是希腊人的宗教观。但是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这种完美主要是智力和审美意义上的,与道德无关。比如阿芙洛狄忒,便拥有无可挑剔的美。成为一个美女需要具备的条件她都有,却唯独没有贞洁。
所以,从道德的意义看,神也是不完美的。然而这却让神变得亲切。结果,神的所有错误和坏事,都被编成悲剧或喜剧隆重上演,以至于每次祭典也都是人的狂欢。
希腊人,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其实就连哲学家,也是嘲讽的对象。在阿里斯托芬的某部喜剧中,苏格拉底(Socrates)被装进吊篮高高挂起,让那参观“思想学校”校园的学生家长大开眼界。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台词:
学生家长:苏格拉底?真是好心肠的苏格拉底吗?
苏格拉底(居高临下地):凡人,你为什么叫我?
学生家长:请问,你在那筐里干什么呢?
苏格拉底:我在空中行走,逼视太阳。只有这样,思想的精华才不会像芹菜吸水一样,被土地吸走。
学生家长:你说什么?思想、精华、太阳和水芹菜? 注释标题 见阿里斯托芬《云》。便于读者理解,台词有改动。
希腊人,把哲学变成了艺术。
与此同时,或者更早,他们也把巫术变成了科学,甚至变成对纯粹真理的思考,而且是为科学而科学,为思考而思考。因此,他们又从科学走向了哲学。事实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那里就叫“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中文翻译为“形而上学”——超越具体事物的学问。
这就跟印度人不太一样。
印度人是先把巫术变成宗教,再把宗教变成哲学的。因此他们的宗教极具哲学意味,哲学也极具宗教意味。印度似乎是一个灵魂不灭的国度,一座建在人间的神殿,一条永远洁净的圣河。在那里,你能听见那些来自天国的声音,就像犹太先知、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能够直接得到神启。
犹太人和印度人在天上,希腊人和中国人在人间。
一直生活在人间的中国人甚至部分地保留了巫术。民间喜欢的口彩,皇家喜欢的祥瑞,便都是巫术的遗风。毫无疑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巫术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它也要变。只不过,既没变成科学,也没变成宗教。
那又变成了什么?
礼乐。
巫术变成礼乐,其实就是变成道德和审美,或伦理与艺术。因此,其他民族依靠宗教去实现的功能,在中国就靠礼乐来完成。礼的任务是维持秩序,给我们安全感;乐的作用是保证和谐,给我们自由感;而巫术变成礼乐,则不但帮我们实现身份认同,也是中华文明不曾湮灭的秘密所在。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实际上,从巫术到礼乐,在中国就像从部落到国家一样自然,只不过时间要晚得多。准确地说,那是周人智慧的体现。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讨论礼乐。因为历史舞台上还有一些明星没有退场,必须交代它们的去向。
比如图腾。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