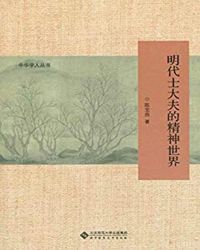四、士大夫的崇雅意识及其精致生活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四、士大夫的崇雅意识及其精致生活
明代士大夫的雅俗之辨,必然导致他们的生活观念发生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崇雅意识的崛起,进而导致他们的生活内容上,世俗与雅致并存。
(一)生活观念的转变
明代士大夫生活观念的转变,显然导源于儒释道三教合流。士大夫代表了儒学正宗,但在明代,已经深受老庄、佛教的影响。江盈科在《自述》诗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老庄生活观的认同,即吃亏是福、知足常乐。诗云:“人情譬如马,吃亏乃知福”, “善哉老氏书,知足常是乐。”在《忆昔》诗中,亦云:“达哉庄生言,三旌等羊肆。”受老庄生活观念的影响,这些士大夫大多抱有一种对官场厌倦的情绪。如江盈科,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选任苏州府长洲县知县。五年秩满,迁吏部考功司主事,因为考察他在长洲任上时征赋不及格,于是改任大理寺正。所以,他对自己在长洲做官的生活,一直体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在诗中称“六年苦海长洲令”,甚至将名场视为戏场:“看破名场是戏场,悲来喜去为谁忙?”“无心更与时贤竞,散发聊便卧上皇。”正因为此,江盈科在很多诗歌中,表达了对做官的厌烦,不愿再做宰官之身,如诗云:“解绶便安逸,抽簪得隐沦。为偿牛马债,一见宰官身。笑面人前假,攒眉背后真。从今登觉路,无喜亦无嗔。”将做官视为偿还做牛做马之债,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情绪。
当然,对官场厌倦情绪的产生,除了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做官之贫,如江盈科有诗说他做官三年之贫,其中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似母,宦囊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癯。乡书不敢寄,猨鹤恐嘲予。”二是政拙,江盈科有诗云:“直以肝肠合,宁论臭味同?世情欺政拙,吾党负诗工。”作为一个文人,他们在政治上确实缺乏治理的干才,但对自己的诗才还是相当自负的。
在厌倦了官场生活之后,这些士大夫所羡慕乃至最后的归路,往往就是逃禅。江盈科在给月空长老的诗中云:“逃禅余有意,欲撇进贤冠。”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袁宏道的身上。当袁宏道移病南归时,江盈科赠予他一诗,明确指出袁宏道原具佛性,不是一般的官场失意之后的“逃禅”。诗有句云:“宰官原佛性,不是学逃禅。”逃禅之后,他们的生活不外乎学佛、吃斋、读经。江盈科有《学佛》《崇国寺吃斋》《念经》三诗,所咏就是逃禅以后的生活。此外,在明代的士大夫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与僧人相交的风气。从江盈科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交往的僧人不少,分别有月空长老、怀旭长老、虎丘僧明觉、僧人愚庵、僧人朗目、娄门寺老僧、百花庵僧,等等。士大夫与这些僧人平常相聚在一起,其交往内容也相当丰富,或是士人聚集在僧寺一起品茗,或是替僧人之画题上一些诗句。
崇信老庄,皈依禅释,导致士大夫生活观念发生两大转变:一是信命思想的风行。如刘荣嗣云:“人生顺逆,命定之矣,踌躇计较为用也。所谓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二是“人生贵适志”思想的出现。明代的士大夫,始终抱有一种“人生贵适志”的人生态度,在生活中追求一种闲适之趣。他们最为无奈却又不得不应酬的是下面两件事:一是做官时的“簿书期会”,二是在故乡时的“酒食征逐”。这些应酬,无不使他们感到心累。所以,他们有时所向往的是山童野叟之乐。
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士大夫中风行起来。如洪应明云:“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明代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理应是社会各阶层无不忙于逐利,缺少一定的闲暇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亦即明代士大夫的生活已如“舞蝶游蜂”一般,是“忙中之闲,闲中之忙”, 由此确立了忙与闲的互动之势,甚而“忙中偷闲”。
正是这种“忙里偷闲”的观念,才最终确立了士大夫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追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理应提到晋代陶渊明的《闲情赋》,赋中铺陈,缠绵婉娈,无不寄其闲情。至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一书出,取情多而用物闳,更是成为天下雅人韵士家传户诵之书。然若论悠闲的生活方式,明代的士大夫堪称典型。
这种生活方式,奠基于士大夫对“逸态闲情”的追求,亦即在生活上追求一种闲居之趣。就逸态闲情而言,无论是昼闲人寂,只听数声鸟语悠扬,还是夜静天高,仅看一片云光舒卷,无不会使他们感到耳根尽彻、眼界俱空。在他们眼中,好书良友是千载奇逢,碗茗炉烟是一生清福。闲暇之时,烹山茗,听瓶声,一炉之内,即可识得阴阳之理;即使是自己与人弈棋,或者在旁观看,亦可悟得生杀之机。毫无疑问,这既是一种逸态闲情,只需自尚,不必外修边幅;又独具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加以掩饰。就闲居之趣而言,他们从内心已经深切体会到闲居可以带来以下五种快乐:一是不与人交接,可以免却拜送之礼的烦恼;二是闲暇增多,可以终日观书、鼓琴;三是无论睡起,无不随意,没有拘碍;四是与尘世相隔,可以不闻炎凉嚣杂;五是心无旁骛,可以一心课子耕读。这种闲居生活,即使只有茅屋三间,木榻一枕,但还是明窗净几,烧上一炉清香,啜上几盅苦茗,有时读数行书,有时与高僧谈禅,或者当暖日和风之时,在豆棚菜圃之中,无事时听友人说说鬼话,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书代益友,以著述代功业,无不是一种赏心乐事。
(二)崇雅意识
明代士大夫群体中“偷闲”观念的盛行,闲情逸致的心境,无不来源于他们崇尚雅致的意识。明代的士大夫,一语一事,无不讲求“韵”字。语韵则美于听,事韵则美于传。然在士大夫看来,韵亦有夙根,不然的话,即使再吞灰百斛,洗胃涤肠,也很难做到一语一事达到韵的境界。宋人黄庭坚曾嘲讽一个村叟云:“浊气扑不散,清风倒射回。”此犹写貌,未尽传神。说到韵人伎俩,简直可以令造化小儿羞涩,何止风伯避尘而已。即使是人所时有的“谑浪”,士大夫亦追求一种“雅谑”。究其原因,正如冯梦龙所言:“雅行不惊俗,雅言不骇耳,雅谑不伤心。”除了语韵、事韵、雅谑之外,士大夫尚追求一种“幽致”的生活境界。袁宗道诗云:“高枕非逃世,幽栖自寡营。”又云:“寂寞非逃世,幽栖自寡营。”可见,所谓的“幽栖”“幽致”,并非逃世,而是“寡营”,就是内心减少功利的念头。陈玉辉亦坦承,士大夫即使极其高雅,一旦进入公门,替人说事,便觉带几分俗气;即使极其鄙俗,一入佛寺看经啜茶,便觉有几分“幽致”。
明代士大夫的清高脱俗,显然建立在对物体的寄托之上,此即所谓的托物寄志。袁宏道曾说,陶渊明之爱菊,林逋之爱梅,米芾之爱石,并非真的喜爱菊花、梅花、石头,而是“皆吾爱吾也”。所谓的“吾爱吾”,其实就是通过这些与自己相似的外在物体,自己欣赏自己的清高脱俗。
揆诸明代士大夫的托物寄志,大抵以竹木、花草、动物三类为主。下面依次加以阐述。
古人以竹为用,至后世才开始以竹为玩物。自黄帝命伶伦于嶰谷取竹,制为律吕,唐虞之廷,诸如韶、笙、箫一类的乐器,均与竹子有关。至周,则竹之用处更加完备,或以为简,或以为笾,无不都是求其实用。汉、魏以来犹然。至晋,始以风流相尚,不事实用,于是有了竹林之游。然究之当时史实,尚未闻有爱竹之人。真正爱竹之人,应该说始于王子猷。自此以后,骚人达士,闻风相尚,取以为号,用以比德,慕其虚者有之,尚其节者有之。爱竹之人,更趋繁多。
明初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与吏部尚书詹同等谈论一些物理,兼及于竹。根据詹同所论可知,竹之种类实繁,仅晋人戴凯之所谱,就达50余种,或根如蟠轮,或节若束针,或细则胜剑,或巨可为舟,不可历举。无论何种竹子,其色皆青,其体皆圆。唯有吴、越山中,有一种方竹,其形最为诡异,四稜直上,弗偏弗颇,若有廉隅不可侵犯之色。所以士大夫大多爱此方竹,采而为筇。
在明代士大夫群体中,爱竹之人甚多。如明初裴日英,浙江天台人,大体生活在洪武年间。其性好竹,所居种竹数百,扁其室说“竹坞幽居”。后因荐至南京,居住在逆旅中,屋仅可俯仰,无从得竹,但还是揭其故名不废。有人怀疑此称名实不副,他却有自己的一番理论,认为有竹之竹,不若无竹之竹更美。有竹之竹,其舒适仅在耳目。无竹之竹,则舒适在人的内心。所居虽无竹,耳目不能见竹,但内心常有竹子存在。思竹之声,以为有《虞韶》之遗音;思竹之挺拔特立,以为有壮夫伟士之节;思竹之历寒暑而不变,以为类乎有道者。当然,裴日英之爱竹,仍是出于“取而比德”的目的。换言之,竹之虚中不窒似仁,竹之直遂似义,竹之周于用似才,竹之高自骞举、不屈侪类之下似智。明代大儒王阳明也以竹自况、自道。他建一亭子,周围种植许多竹子,称之为“君子亭”,究其原因,就是考虑到竹子有“君子之道”。他认为,竹子中虚而静,通而有间,有“君子之德”;外节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有“君子之操”;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有“君子之时”;清风时至,玉声珊然,中采齐而协肆夏,揖逊俯仰,若洙、泗群贤之交集,风止籁静,挺然特立,不挠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侧,有“君子之容”。还有一位张锡,曾在老家有一个竹园,他在上面建了一座亭子,借用苏东坡之言,称为“医俗亭”,希望通过竹子之节,以医世俗。他认为,坐在这座亭子里,竹子所发之声,清声戛玉,可以医治耳之喧嚣;竹子之幽香细细,可以医治鼻之铜臭;竹子之柯叶如翠,可以医治目之蜃楼;竹笋供茶馔,可以医治口之垂涎;竹子之虚心劲节,又可以医治自满而失守之人。
明代士人之尚物,所取者不是耳目之娱,意趣之适,而在于其德。竹子之德,为君子所尚,究其原因,明人刘基、杨士奇、徐枋均有讨论。如刘基认为,竹子柔体而虚中,婉婉焉而不为风雨所摧折,均是因为有“节”。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色苍苍而不变,更是如同临大节而不可夺之君子。杨士奇亦言,竹子中虚外直,刚而自遂,柔而不挠,有萧散静幽之意,无华丽奇诡之观,“凌夏日以犹寒,傲严冬而愈劲”。所取者,亦是竹子之节。鉴于此,正如徐枋所论,竹之后凋,与松柏相同,而其孤标风致,则似乎超越松柏。所以古人“具迈俗之韵者”,往往寄托流连,或者图写竹子的形状,以自娱悦。古人种植卉木,大多皆有取义,并非徒为玩好而已。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松有“大夫”之号。明人曹学佺坦然承认,很多士人以“松柏”命名自己的书斋,其实就是借物喻志。就松柏而言,其中包含着三层含意:一是松柏能傲岁寒而荣,这是自喻其“节”;二是松柏冠群木而长,这是自喻其“孝”;三是松柏又为女萝、葛藟所缠绵而栖托,这是自喻其“义”。一物之中,三善备具。
明代士大夫对松柏亦有特殊的爱好。如宋濂在谈到松树时,直言植物之中,禀贞刚之气,“唯松为独多”。他认为,若论能凌岁寒而不易行改度者,唯有松树。所以,昔之君子,每每“托之以自厉”。刘基亦说松树,“干挺而枝樛,叶细而条长,离奇而巃嵷,潇洒而扶疏”。当风起之时,松树不壅不激,疏通畅达,有自然之音。听松涛之声,可以解烦黩,涤昏秽,旷神怡情,恬淡寂漻,逍遥太空,与造化游。正因为此,适意山林之士,无不“乐之而不能违也”。倪岳将柏树比作士君子之节。他认为,士君子依仗大节而立于穹壤之间,不因穷达而移,势利而屈,祸福而动,“大试之而大成,小试之而小效”,就好像深山中的古柏,“冰霜摧之而不加瘁,雨露濡之而不加荣”,而其“梁栋榱桷之材,随所施而宜焉”。这是因为,柏树的刚大之气,“敛之则周于身,达之则周于用,大塞乎天地,而小入于细微,无时无处而不存也”。
尽管古人喜欢将忠臣志士比喻成“松柏”,但明末清初人魏禧则更注重在深冬时仍能保持“春荣”的“杂木”。他有诗云:“严霜无强叶,松柏特青亭。周庭多杂木,深冬如春荣。琐细不相识,但知天所生。物各抱真性,岂希松柏名?”可见,魏禧所重之杂木,名虽不如松柏,但同样抱有“真性”。至于其中的原因,他的好友林确斋有较为深入的剖析,认为松柏犹如知名于世的忠臣志士,而杂木则如无位无名、抱道守节、老死穷僻之乡之人。他们或赴难急公,或相从而死,其天植之性,正如琐细之木,堪称力敌雪霜。
花是草木精气上发以后的一种英华。天有四时,而四时之花各有不同,如春之桃花,夏之莲花,秋之菊花,冬之梅花。四时之花,臭色高下不齐,因而各配其人。所以,传统的士大夫认为,潘岳似桃,陶渊明似菊,周敦颐似莲,林逋似梅。换言之,菊代表隐逸,所谓隐者为高;牡丹代表富贵,所谓仕者为通;莲代表君子,其中所蕴含之义,就不仅仅是君子出淤泥而不染,而是另有一层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之意。正因为有了这种花品与人格的相似,于是后世的士大夫亦纷纷崇尚花草,从中寄寓自己之志。即使在当时读书人心目中具有至高地位的翰林院,别称“玉堂”,能够忝列中间的读书人应该说是士人的表率,但他们在闲暇之时,也喜欢结成“赏花会”之类的团体,并且一同赏花作诗。
桃李芳艳,普遍受到大众百姓的喜好,但在士大夫看来,恰好比小人邪媚之态,不过是“尘污”之物。他们更为看重的是菊。如丘濬认为,菊花芳香清冽,禀天地之正气;纯粹不杂,得天地之正色;高洁闲雅,全天地之正性。菊花不但有幽人逸士之操,而且有忠臣贞士之节,绝非其他草木可以比拟。陈献章《和罗服周对菊见寄》诗云:“春来苦不早,春去常愿迟。嗟哉造化机,万物安得知?岁晏菊始吐,鲜鲜在东篱。不污桃李尘,永续徵君诗。”细玩此诗之意,无非是说人之常情多爱春芳,而造化之机则有非万物所能测,如桃李生于春,却反而被尘俗所污,而鲜鲜之菊则生于秋,则不被尘俗所污。高濂更是坦言,菊花是花之隐者,只有“隐君子”“山人家”喜欢种植,所以并不多见,见亦难于丰美。屈原愤世嫉俗,称荃蕙为茅,兰芷善变,而唯独欲“餐秋菊之英”。究其原因,正如明末清初人徐枋所言,还是因为菊花具有凌霜之节。所以,逸人高士,往往寄托于菊花,并称之为“端友”。可见,与民间大众之喜好桃李芬芳不同,士大夫则喜菊之清雅。于是,随之出现了秋菊为隐者之良的说法,亦即菊花总是与隐士为伴。
莲是士大夫时常寄托之物。莲之为物,或以气味而爱之,或以芳泽而爱之,唯独遗忘了莲之德。自宋儒周敦颐专作《爱莲说》一文,以此寄托士人之德以后,莲德备受儒家士人称道。其实,莲同样可以象征士人之才。鉴于此,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重作《后爱莲说》一篇,加以阐发。他认为,就其大者而言,莲之用,实可与根一同以供笾豆之用,且可作为百姓之食,甚或治疗疾疢;就小处而言,莲之叶、须、茎、节,无一不可资人采择。在群卉之中,往往根之美者,叶或被弃;落其实者,干又有遗,很少求得兼善。而莲不然。当“阳煦已盛,厥荣渐敷,阴节未凝,蜇藏早固”,完全合乎君子进退出处之义。换言之,从莲德才兼备之质,借此说明士人亦应德才合一。这是张履祥《后爱莲说》新的发明处。
梅作为一种卉木,有岁寒之操,凌霜雪而独秀,守洁白而不污。梅花通常也是传统士大夫自我意志的寄托之物。如刘基认为梅有“君子之象”,亦为“君子所宜”。他仿屈原颂橘之体,作有一篇《梅颂》,对梅花的品格,多所比喻,如说梅花“章而贞”, “清以直”, “不挠其节”,有“玉之洁”, “美而完”, “丽而不淫”。尤其是梅花“文质彬彬”之姿,更是象征了一个君子的品德。在植物中,梅花可称“至清”,大多产于山溪林谷之间,于是,那些栖迹乎荒寒旷漠之滨的“逸人韵士”,就借助梅花“以适其幽独闲静之趣”。按照常理,万卉在经历了冰霜冱寒之后,无不摧败,唯有梅花,皎然孤芳,一尘不滓。鉴于此,杨士奇将梅花比喻为拔出乎流俗的“贞洁独行之士”,从而与君子之心相契。丘濬则从梅花中看到了从实到华的转变,重新倡导“敛华就实”。在丘濬看来,真正的有志之士,理应是“人皆务其华,我独敛其实;人皆骛于文,我独笃以行。不混俗以同,不随世以趣。”从这段记载中,不难发现丘濬的实学思想。换言之,通常士大夫认为,自己之心与物趣相契合,自己就取而法之,以花木比拟自己。但丘濬却持一种反对意见。他说:“冷蕊疏枝,何有于吾之性情?淡香疏影,何预于吾之身心?折枝以赠,何似乎简书?踏雪以寻,何资乎日用?”
明代灵修幽求之士,无不借助梅花而托迹寓意。何以取类于梅花?明人聂豹经过仔细的考察,认为主要还是基于梅花有“五美”:姿凌冰雪,是说梅花“贞之固”;几先品汇,是说梅花“神之征”;暗香疏影,是说梅花“幽而光”;林下水边,是说梅花“静而逸”;巡檐之索,是说梅花“调晢之需,臭味之相宜”。有此五种品德,所以凡是寓意梅花之士,“利贞”之人,则是为了显示“一其德”; “知几”之人,则是为了“尚其神”; “含章”之人,则是为了“致其幽”; “避地”之人,则是为了“适其静”; “臭味相求”之人,则是为了“崇其实”。进而言之,“实则用斯精,静则心斯休,贞则行斯峻,幽则暗斯章,神则风斯远”。所以,君子从梅花的品格中,悟出了“尚隐德”的道理。
梅既代表了士人的高洁,又是隐士的象征,于是也就有了所生之地的一种选择。若是梅生世俗扰攘之地,尤其是被植于衙门,或许就是对梅花的一种亵渎,令人惋惜。明代江南才子唐寅有一篇《惜梅赋》,基本表示了这样一种惋惜之情。他认为,梅花种植于县衙门庭院之中,显是“生不得其地”,从而使“俗物”与梅花的“幽姿”相混,如“前胥吏之纷拏,后囚系之嘤咿”,尽管可以说“物性之自适”,然揆诸人意,终究非宜。换言之,梅花理应“托孤根于竹间,遂野性于水涯”。根植于衙门庭院,顿使梅花丧失了“清绝”的姿态。可见,梅花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平常花卉,当交易之时,均可以称买或卖,唯有梅花,李日华认为不得直接称之买卖,而是应该称为“聘梅”或“嫁梅”。否则,就是对梅花高洁之性的一种亵渎。
宋人论牡丹之说甚多,如周敦颐称牡丹为花之富贵,欧阳修称牡丹为“花妖”。可见,对于安贫乐道的儒者来说,多不喜以牡丹自况,甚至欣赏牡丹。从这一角度来说,明末清初人归庄之四处寻探牡丹,甚至达到一种狂且癖的程度,显然有他自己更深一层的理解。有人问归庄:“牡丹属于富贵之花,而你却是贫贱之身,与你并不相宜。”归庄的回答很有意思:“吾贫则无儋石矣,而性慷慨;喜豪放,无贫之气;贱为韦布矣,而轻世肆志,不事王侯,无贱之骨。安在与花不宜?”狂者所为,一反士人常态,寄寓牡丹,别有新论。
自古以来,就将兰花比作“特立独行之士”。孔子就说过这样的话:“幽兰生于空谷,不以无人而不芳。”明代士人大多喜兰,如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作有《兰言》,其中所记,除了自己收集兰花的经历外,还包括他因兰花与人结交的故事。其中一人是他的小姬扣扣,因为家中盆兰盛放,就寄他一小笺,中云:“见兰之受露,感人之离思。”当冒襄回到家中之后,戏问道:“那得次好句,生笔下如许姿制耶?”扣扣答道:“《选赋》‘见红兰之受露’,我仅剪却一 ‘红’字耳。”另一人是竟陵派的著名文人谭元春,曾寄给冒襄一首《雪兰辞》,题中有“兰产石中,一茎一花,花开如雪”之语。冒襄和之,有云:“楚人竞赏兰,古有殷红,今有白雪。”这是以兰而成为“同心”之人。
隐者采芝以疗饥,神仙饵芝以长生。古来真隐,确乎去仙不远。无论是商山之芝,还是《离骚》香草,无不都是幽人贞士之所寄托。黄绮遁世无闷,则采芝以疗饥;屈原愤世嫉俗,则托香草以怀君子。芝草有兰蕙之芳,而同松柏之后凋;比蓂轶之瑞,而同醴泉之无源。芝草之德,可谓尚矣。清初士大夫遗民徐枋,不与清廷合作,避世灵岩山间,堪称真正的隐者。所以,他尤其喜画墨芝,非唯比德君子,而且借此寄寓自己隐居之意。康熙二年(1663),徐枋曾画香草十帧,赠送给友人,其起因就是因为友人“栖心尘外,翛然高寄”,而自己亦是“绝俗”长达20年,两人心期,同此芳洁。尤堪注意者,徐枋画芝,自比于郑所南画兰。然两者亦稍有别:所南画兰,多不着地;而徐枋画芝,则必画坡石。所南的本意,在于不踏新朝之土;而徐枋则坚信,自己所居之处,就是干净之土,入画有何不可。两相比较,所南心思,相对狭隘。
最为值得重视的是,在明代士大夫群体中,开始有人比德于“白菜”与“菜根”。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吕坤之《白菜图说》与洪应明之《菜根谈》。
物有八珍、十齐、十二和、百羞,当数菜为淡。菜分五味,又数白菜为淡。作为平凡之物的白菜,确实入目不华,入鼻不香,入口不爽,生长在樊圃之中,与“凡菜”为伍,却能做到秽恶无染,清素自如,不与名芳争斗妍媸。白菜的种类不一:丛生而环附者,称为“莲花”,好比“韫藉”之人;下广上狭,裒然内附者,称为“杓”,好比“虚受”之人;峭然玉立,若削若束,称为“箭杆”,好比“正直”之人。一颗普通的白菜,却是内含五常之性:叶属木,为“仁”;茎属金,为“义”;体质属水,为“智”;根坚结而中涵,为“信”;亭亭翼翼,不靡不披,为“礼”。白菜虽具五德,但究其根本,还是以“淡”为宗。故吕坤对白菜所具之“淡”性,更是深有体味。这从人性对于欲望的追求可以得到证实。在吕坤看来,人对于私欲,心有艳羡,故其追求,无不恣睢,不到餍足,绝不停止。荣门利孔,竞进奔趋,这是对权势的艳羡;一有淡心,就可以“养德”。纷华夺目,好尚为迷,这是对爱欲的艳羡;一有淡心,则可以“定志”。妖冶倾情,意所便适,这是对情欲的艳羡;一有淡心,则可以“立命”。辩口纷纭,真识我独,这是对言论的艳羡;一有淡心,则可以“寡尤”。横逆所加,一朝欲逞,这是对怒气的艳羡;一有淡心,则可以“远祸”。时事伤心,非人满眼,这是对丑恶的艳羡;一有淡心,则可以“广量”。正是以白菜为师,吕坤才向士人呼吁:即使居住在冲漠之室,亦应该存一分恬静之心,做一个淡泊之人;即使身处岑寂之境,亦必须行雅素之事,与淡如水的君子相交。凡是俗尚所饕餮,以及世俗称为“鲜浓”者,其实并非“道腴”,而是“鸩毒”,不要垂涎,不要染指,不要脍炙于身心。可见,吕坤之比德于白菜,就是从白菜之淡中,悟出了士人必须清心寡欲的真谛。
白菜味淡,已是如此。若是咬得菜根,那么其人之德,更可想象。明人洪应明所著《菜根谈》,菜根之说,别有深意。宋儒朱熹《朱子全书·学四》曾说:“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言外之意,是说只有咬的菜根,方可不违本心。自号“三山通理达夫”者,对“菜根”之名的本义亦有揣测,认为菜因有味而成为日用不可缺少之物。但菜味由根而发,所以,凡是种菜,必须厚培其根,其味方显淳厚。《菜根谈》一书,其中所论“世味”与“出世味”,无不都是培根之论,理应受到重视。古人有言:性定菜根香。其意是说,菜根虽属弃物,但若是性尚未定,则很难识得菜根之香。于孔谦亦认为,书名称为“菜根”,说明其中所谈所言,固然是作者自清苦历练中得来,亦是自栽培灌溉里得来,至于在这些言语的背后,作者之颠顿风波,备尝险阻,更是可想而知。洪应明曾说:“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以遇,吾高吾道以通之。”细绎其旨,不过是一种自警自力之语。综合上面两人所论,大多侧重于人品的修养,有励志警策的作用。换言之,书名“菜根”,不仅仅是自况,更是以菜根喻德,希望人人从菜根中获得真味。
明代士大夫除了以竹之节自喻之外,尚比德于鹤,甚或竹、鹤并论。如唐寅以鹤为友,抛弃名利之俗。他有一首《题友鹤图为天与》诗,云:“名利悠悠两不羁,闲身偏与鹤相宜。怜渠缟素真吾匹,对此清癯即故知。月下吟行劳伴侣,松阴梦觉许追随。日来养就昂藏志,不逐鸡群伍细儿。”可见,唐寅之以鹤为友,在于鹤之“缟素”与“清癯”,借此养就自己的“昂藏”之志,不与“鸡群”“细儿”为伍。吴廷翰所居读书之室,称“竹鹤山房”,种竹养鹤以居。取名“竹鹤”,显然面临如下两个疑问:一为究竟是取德于竹,还是取德于鹤,或者兼有竹、鹤之德?二为究竟是“亭亭如竹”,还是“矫矫如鹤”,或者出而如竹“挺然”、如鹤“昂然”,处而如鹤“飘然”、如竹“潇然”。这两个问题,其实涉及在竹、鹤品格之间如何折中。对此,吴廷翰认为,未可一端而尽。在他看来,君子之德,无不归趋一致。所以出处异用而同体,夷险异迹而同心,竹鹤异物而同理,未尝偏离中庸之道。竹、鹤品格,无论是忠直,还是强毅,无论是屡空而乐,还是清风高节,均不能完全概括竹、鹤之能。唯有或出或处,不凝于时;可夷可险,能通其用;为竹为鹤,靡滞于物。如此四气一贯,万里一息,只有孔子之“时中”方可概括而尽,并非竹、鹤之德所能尽。
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喜以鹤比喻高人韵士,但归庄对鹤则别有一番理解,甚至认为现实社会几乎如同一幅“煮鹤图”。苏东坡曾作《放鹤》《招鹤》之歌,归庄亦作二歌,其一云:“威凤兮在笯,文雉兮罹罿。危哉鹤兮,石鼎调而桑薪烘!”歌中揭示的时代,无论是“威凤”,还是“文雉”,无不都被笯罿,不得自由。即使是鹤,亦是身出石鼎,被桑薪所烘烤。言外之意,显是说高人韵士所处环境,一如鹤之被煮,难以幸免。
(三)世俗生活与雅致生活并存
明代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凌翰有一段记载作了很好的解释。根据这一记载可知,当时士大夫相与交往,除了叙寒暄、道旧好之外,或谈星命,或论相术,或指画地理,或以职任之炎冷为忧喜,或以升迁之迟速为欣戚。这是生活的庸俗化。至于那些在京城的缙绅之士,为了博取美名,则是动辄称围棋、金华酒、杜诗、《左传》文章,互相崇尚,以为高致。这又是生活的雅致化。可见,士大夫生活,已是世俗与雅致并存。一方面,士大夫受到商业化思潮的影响,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地位,过着一种穷奢极欲的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士大夫终究是知识人的典范,与一般的暴发户不同,又可以避俗,进而追求一种雅致生活。
从史料记载可知,明代士大夫相聚在一起,所行大抵不过是饮酒、博弈与戏谑而已。饮酒与赌博,通常会形影不离。明代的士大夫,同样视赌博为风流之举,并将赌博作为一种娱乐,成为他们闲适生活的一部分。明人江盈科对此有诗予以揭示。诗云:“年来诸仕宦,眼中可睹记。如展百官图,掷骰相赌戏,得么多者钝,得四多者利。须臾至保傅,只销几个四。收图裹骰子,谁轩复谁轾?”这是将官场形容为“百官图”一类的赌博游戏。至于具体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如:苏州府长洲县人祝允明,“好酒色方博”;长洲县人皇甫冲,“通挟丸、击球、音乐、博弈之戏,吴中轻侠少年咸推服之”。浙江余姚人谢木斋致仕归家,“每日与诸女孙斗叶子以消日。常买青州大柿饼、宣州好栗,戏赌以为乐”。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常州一带,士大夫的赌风大盛。一些士大夫致仕归家以后,开设赌坊,赌徒借此躲避朝廷的禁令。到了万历末年,更是出现了进士“以不工赌为耻”的奇怪现象。至于赌博的方式,尤其是马吊牌兴起于江南之后,自南而北,很快风行全国各地。
饮酒之时,士大夫同样需要“红妆”陪伴,并由优伶、声伎唱曲侑酒。明季文人江盈科在一首诗中,就咏出公安派文人少年时的“拥红妆”生活。其中云:“少年词赋满天涯,偶泊金阊问酒家。笑倚青楼调妓女,新裁丽曲度琵琶。”可见,狎妓听曲,也是明代士大夫风流雅致生活之一。在明代,士大夫挟妓饮宴较为盛行。至明末,一些轻薄文人甚至用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所谓花榜,又称“花案”,其实就是选妓征歌。以南京为例,自弘治、正德以来,就相当流行,至万历末年达到极盛。所评之榜或案,其说有“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等。明代士大夫大多顾曲自娱,甚至家中养有戏班。如谭纶,家居以后,以声伎自奉,增损海内曲调,俪之和平,形成独具一格的“四卒腔”,一直为优伶所习用。江南的文人雅士对戏曲也有特别的嗜好,家中蓄有声伎,养着一些家乐班子。如何良俊“畜家僮习唱”, “又教女鬟数人”。张岱家的声伎,始于万历年间其祖父张汝霖,经过祖孙三代的经营,组建了很多戏班,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
公安派文人袁宗道有一首诗,足以证明文人士大夫聚会时,无不以谈谐为乐。诗云:“良朋投合真有时,十载闻名不相知。偶尔相逢杨子宅,剧谈浪谑忘还期。”袁宗道在另一首诗中,也直说自己与其舅舅相处之时,多有“雅谑”。诗云:“舅甥多雅谑,文酒是名流?”又据李日华记载,其门生陈汝言作有《笑笑录》一书,凡是市里秽杂之语,经其挑拨,极有奇趣。此书之叙也写得极是诙谐可喜,引述如下:
仆有笑癖,实出愁肠。拍手可呵,腰里只差破布袋。花头簇簇,口中却有薄皮刀。玉笑还让老天,铁心也须倒地。只图眼饱,那管口酸。造杀老黄牛,顽石尚然会倒;赶走黑蝴蝶,黄河那怕不清。人世难逢,偏我得餐笑蕈;机心不测,对人一味虚花。女号蚌浮,人称鸟说。肠多绞断,分明吃尽酸汤;嘴若笑歪,情愿赔他冷面。如有同道,将来凑淘。若尽无知,拿去扯碎。 注释标题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4,万历四十年壬子十月七日条。
仔细考察文意,这些文人士大夫确实具有一种“笑癖”。撮拾生活琐事,略加点缀,即可起到造杀黄牛、跌倒顽石、笑歪口醉的喜剧效应。当然这些谑言、笑事,尽管被人指责为“蚌浮”“鸟说”,有些却确是出自吃尽酸汤的“愁肠”。
与这种世俗的生活相对,明代士大夫中尚流行一种避俗之风,于是以耽情诗酒为高致,以书画弹棋为闲雅,以禽鱼竹石为清逸,以噱
谈声伎为放达,以淡寂参究为静证。如此种种,已成了当时士人普遍崇尚的流俗。明季盛行“清客”“韵士”。凡是啜茗善弈、种竹栽花之人,均被称为“清客”;凡是甄别古玩、谈谐诗骚之人,则被称之为“韵士”。
在士大夫群体中谈谐大为风行的同时,别有一股清谈之风,值得引起关注。按照明代士大夫的普遍观点,所谓的“士君子”之流,无疑应与俗语、纤语、诨语绝缘。在明代文人士大夫中间,流行一种清言,显然与他们讲究一种清雅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这种清雅生活的构成中,谈谐固然是语言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有俗化的倾向,但他们同样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精神风貌,时常聚在一起,有一些“清谈”的生活场景。而这些清谈的生活内容记录,就是许多清言集的风行。
早在弘治二年(1482),苏州一带的文人士大夫,就有将自己的清雅生活的场景以及文人相聚所说的清雅之言记录下来,并编成集子的习惯,于是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清言集。如朱存理,就著有一本《松下清言》。据他自己所言,自他僦居松下之后,经常与他过往或到他舍中清谈之人,有杨君谴、都玄敬、祝希哲、史引之、吴次明、尧明宿等人。所交往之人,一概不是“势利之人”,而所谈也不是“势利之事”,不过是一些品砚、借书、鉴画之事。松下所设,有一几,可以摊书,以便主客共赏。来客以后,主人也不用酒宴招待,而只是“啜茗”。朱存理将每天过客之谈记录下来,也就成了这本《松下清言》。
士大夫的清雅生活,所交往者都是一些文人雅士,或者是骚人墨客,决无说“势利之事”的俗客。而他们所谓的“清言”,就是谈论一些品砚、借书、鉴画一类的雅事。而在晚明,最典型的清言集代表著作则是洪应明的《菜根谈》与郑仲夔的《清言》。
一般的论者均认为,晚明的清谈之风,多少与晋、宋之际的清谈存有一些关系。晋室之亡,是清谈所致,而明室之屋,也是清谈所误,这似乎也成了学界的共识。其实,一朝一代之亡,其因相当复杂。清谈固然于国家、社会无益,但士大夫聚在一起清谈,其危害也确非可以大到亡国。尽管如此,直到嘉靖、隆庆之间,《世说新语》一书,尚未在明代学者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读书人都不知有《世说新语》。自王世贞《世说补》出,而当时的学界始重《世说》一书。其后,学风骤然一变,学者旁求百家杂撰,尤沉酣于《世说》以为奇。正如薛冈所言:“《世说》片语只词,讽之有味,但可资口谭。近日修词之士翕然宗之,掇拾其咳唾之余以饬文,而文斯小矣。”可见,习《世说》,尚“清言”,在晚明文人士大夫中已风行一时。
这无疑就是生活风尚的艺术化,且在居室的美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当时的文人雅士看来,家中布置,必须以美为准,置办怪石、名琴、好书、奇画、法帖、良砚、宝镜、净几、古磁、旧炉、纸帐、拂尘,并以此为友。尤其必须置办文房供具,借此快目适玩。但文房供具的摆设,也有一定的讲究,铺叠如市,颇损雅趣。所以,其点缀之法,唯有罗罗清疏,方能得致。
那么,如何美化居室,提高自己生活的品位,无非是收藏、养金鱼、放置瓶花之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士大夫居家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无不体现出休闲、闲适的生活主旨。
士大夫雅好收藏,并成一时风气。古玩、古董(一作骨董),是历代常见之词,人们崇尚古玩,甚至将其当作清雅之物,并不足怪。在明代的士大夫群体中,同样兴起一股收藏古董之风。如浙江永嘉人谢廷循,性嗜清玩,收藏颇富,自称其斋为“米家船”,后杨士奇将其改名为“翰墨林”。当时士大夫,大多喜欢书法法帖,若是遇到定武、兰亭诸帖,即使已经残缺,亦不惜出重赀购买。嘉靖末年,海内宴安。一些富厚的士大夫,在建造园亭、教唱歌舞之隙,其兴趣间及古玩。很多士大夫家中,大多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如常州嵇应科、松江朱大韶、嘉兴项锡山等,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此外,南京则有姚汝循、胡汝嘉,亦以“好事”著称。此风间及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进而流播吴越之间,一些浮慕之人,亦纷纷收藏古董,自称“大赏鉴”。在这股收藏古董之风中,尽管董其昌最晚出,但名头最为响亮,藏家甚至以“法眼”称之,家中箧笥之藏,更是为时所艳。当时绍兴府山阴县人朱敬循,亦以好古知名。董、朱两人,为了争夺古董,互相倾轧,那些古董商人又交搆其间,最后甚至借助考功之法,迫使董其昌外迁,于是,东壁西园,遂成战垒。更有甚者,当时江南的士大夫还专门置有书画船,通过流动的展览,互相比较书画收藏。如董其昌外转之后,沈德符正好告归而至苏州。董其昌将他的书画船移至虎丘,与韩古洲各自拿出所携的书画,互角胜负。当时正值盛夏,参与者除了沈德符、董其昌、韩古洲外,尚有董其昌所昵一位吴姬。四人披阅竟日,成为一时佳话。
自古以来,古董就多赝品,尤以苏州为甚。明代苏州各种生产技艺,号称甲于天下,但又擅长伪造古代器物。如新写的画绢,刚铸的铜鼎,通过一定之法,都能使之变为陈旧,再在上面系以秦汉之款识,标上唐宋之题记。收藏者为其所眩,慷慨付出数百两银子买得此物,欣欣然自以为收藏了一件古物,其实不过是赝品而已。所以,当时的苏州有“宋板《大明律》”之谣,就是专门讥讽这些假古董。
在这股造假之风中,一些文士也借此糊口。在前辈文士中,张凤翼有修洁之称,但亦不免向此中讨生活。至于王稚登,则完全将造假古董作为致富之门。尽管王稚登以造假著称,但有时亦会走眼。据记载,当时太仓曹举人家有一姓范之仆,住在苏州城内,也喜欢收藏古董,曾经购得阎立本所画《醉道士图》,真是堪称绝笔。王稚登看上这幅名画,希望以廉价购得此画。但范姓之仆索价千两银子,经过讨价还价,还是要价数百辆银子。一些好事者每天前去商评,不知范姓之仆素来狡黠,事先已经让苏州人张元举另外临摹一本,形模仿佛。王稚登最后以10两银子购得此画,就是临摹之本,而真本已高价卖给他人。张元举眇一目,偶然为王稚登所侮,因而大声在外宣扬,道:“若双目盲于鉴古,而诮我偏明耶?”这句话传遍整个苏州城,被人引为笑端,王稚登因此匿不敢出。造假之风,起于苏州的一些文士,其后徽州的一些商人亦参与进来,造假的书画,如钟繇兄弟之伪书,米芾之假帖,不一而足,却被一些贵公子、大富人珍为异宝,如同饮了蒙汗药,甘之若饴。尽管如此,但确乎反映了当时的收藏之风。
按照一般的常理,玩好之物,理应以古为贵。但明代出现的“时玩”这一新名词,倒是颇令人瞩目,而且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注意。诸如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虽说都是出于明代的时玩,但其价格已经可以与古玩相匹敌。这股好时玩之风,始于一二雅人的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的好事缙绅,最后经徽州那些巨商大贾的推波助澜,在全社会形成了一时的风气。于是,沈周、唐寅之画,文徵明、祝允明之书法,无不成为人们收藏的抢手货。
时玩之风,完全建立在明代诸多能工巧匠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那些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才使得明代的诸多器物精益求精,完全可以与古时的名器相媲美,以至于被保守人士称为“物妖”。以工匠制作的名器为例,明代凭借“小技”著名的工匠很多,尤以“吴人”为多。如龚春、时大彬之砂壶,胡四之铜炉,何得之之扇面,赵良壁之锡器,一时好事家争相购买,唯恐不及。为此,收藏时玩成为一种“时尚”。这股风气的形成,始于吴中儇薄之子,转相售受,借此欺骗富人公子,获得厚利。随后,甚至浸淫至士大夫间,形成一时风气。其实,这些所谓的时玩,确实器物精良,他工不及,可谓名不虚传。
士大夫的收藏之风,其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民间的一般富贵人家。如松江府有一位富人,尽管目不识字,但喜欢收藏古代的法书;又北京的贵戚人家,动辄花数百两银子,购买宋人的数幅大画。尽管如此,这些富贵人的收藏,显然有附庸风雅之嫌。如上述那位松江府的富人,在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后,对人说:“此公武弁,更自难得。”闻者掩口。显然是误认“右军”为武弁。至于他们出重金购入的宋人大画,即使是真品,亦未必属于佳作,更遑论是赝品。
在明代士大夫家中的厅堂挂幅中,通常流行写两句诗,不知始作俑者为何人,但在当时已是“群然师效而不察”, 成为一时风雅时尚。除此之外,还流行挂一些描绘香奁士女故事的装饰画,“以资玩好”。一些好古之家,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买上数十幅画册,藏于家中。等到客人上门,就悬挂于中堂,“夸以为观美”。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这些人并非真正懂画,不是“鉴赏家”,不过是“好事家”而已。但用绘画作品来美化自己的居室生活,这种风气的形成,无疑反映了当时生活风尚艺术化的倾向。尤其是在书画的悬挂方面,更是有了诸多的美学要求。譬如,厅堂斋室所悬挂的对联字画,大小规格都必须与堂室的高度相配。换言之,书画要与空间相互配合。根据文震孟的描述,堂与斋因空间不同,而有不同的挂画方式。堂尊严庄重,较为气派大度,宜挂大幅横批;斋较为小巧精致,则宜挂小景花鸟之画。在书画的悬挂上,尤其忌讳左右对列,这样会缺乏美感,显得较为俗气。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一般人家无书,有一些书,也不过是用作应付科举考试的书籍。更有甚者,庸夫将书当作枕头,村店用书来糊窗格,市肆中用书覆盖盛酱的坛坛罐罐,甚至使婢老妇拿书夹鞋样,这样的例子触目皆是。然在明代江南,图书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时风。以苏州为例,在明代以前,藏书家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不大,如北宋的藏书家,大多以四川、江西居多,南宋的藏书家则多在浙江、福建。收藏图书成为苏州民间文化生活内容之一,应该说发端于元代,而后始盛于明代。为此,明人胡应麟对苏州、金陵两地士民的藏书之风有如下记载:“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藉藉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这有具体的例子可以举证,如陈天枢家住南京秦淮上,“一室之内,图书木石左右映发,如高人隐者之居也。”
当然,江南人藏书虽众,并非都是通过藏书而增加自己的学识,大多是因袭流俗,附庸风雅,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此风更盛。但是,不论是为了藏书癖好,或者仅为游观赏玩,甚至借此沽名钓誉,藏书活动在明代江南士人生活中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性。就此而言,在晚明一般有钱人家出现一种以藏书为风雅的习俗,尽管不免附庸风雅之嫌,但还是一种生活风尚上追求艺术化的反映。
在这股藏书之风中,士大夫案头流行“清供”之书,则更为值得关注。晚明士大夫过着一种比较清雅的生活,案头多有“清供”。书籍当然也可以作为清供之物,但并非所有的书籍均可以作为案头清供,一般比较常用的清供之书有:《阿弥陀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楞严经》《圆觉经》《法华经》《清静经》《黄庭经》《道德经》《南华经》《离骚》《太玄》《陶渊明集》《白乐天集》《苏东坡集》、唐诗、《李攀龙集》《王世贞集》、汪道昆《太函集》、李贽《藏书》《焚书》、传奇。
在江南杭州,士大夫家中几乎家家都养观赏鱼。所养之鱼为红鲫鱼,俗称“火鱼”。其品不一,如鹤顶破玉、红颊白喙、牛鬣素尾、阳背阴腹之类,都可以算是观赏鱼中奇品,一尾就值千钱。养鱼之盆、盂,或为金,或为玉。将这些鱼盎放在客厅的几案上,有客人到来,“出相夸示,以为娱”。苏州府嘉定县的游闲子弟,也开始畜养“朱鱼”用来观赏,品类奇绝,一尾可值银一两。家中厅堂以观赏鱼作为装饰,在晚明已是蔚为风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士大夫相当注重书斋布置的艺术化,种植一些与书斋这种文化氛围相宜的植物,诸如:竹,“碧玉可留题,紫萌堪敌肉”;桃、李,“春来玩其花,夏至摘其子”;桕、枫,“秋霜杀伐后,醉叶满林红”;蕉,“清绝枕边声,碎露滴其上”;杨,“爱他容易活,早植晚乘凉”;枣、橘,“枣橘芒刺多,牛羊见而怵”。
在一些文人士大夫居室的案头,总是布置一些与四季相配的瓶花,即在胆瓶中插时花,借此引类连情,境趣相合。这些花各有相宜,如:梅芳傲雪,偏绕吟魂;杏芷娇春,最怜妆镜;梨花带雨,青闺断肠;荷气临风,红颜露齿;海棠桃李,争艳绮席;牡丹、芍药,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开笑语;幽兰盈把,堪赠仳离。为此,在江南一些城市的郊区,形成了一些花市。根据近人的研究,明代苏州的花市主要集中在虎丘山塘,早在正德以前,鲜花盆景销售就已形成规模。而杭州鲜花盆玩的鉴赏、营销则大多承接南宋以来的消费传统,其花市的地域分布也是如此。明代杭州花市除了东西马塍之外,又有所扩张,包括西溪及位于城南满家巷的特色花市。
江南文士酷爱赏花,时常将花引入室内,借此以看花之姿态,嗅花之香气。为此,花瓶的搭配也就可以衬托出整个空间的气韵。如在寒冬中,轻折蜡梅,“若瓶一枝,香可盈室”。更增居家雅致。松江府华亭县人张鼐“尝以时花数本,盛以瓦筒,置碧纱窗下,花气袭帘幕间,扁其前楹曰 ‘花舫’”。于是,就瓶花的插植、摆放、瓶与水的选择与灌注方面,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均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以瓶的选择为例,屠隆认为,“堂供须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最忌繁杂如缚。又忌花瘦与瓶,须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在季节方面,应“春冬用铜,秋夏用磁”,这样可以避免花瓶因过冷而冻裂。在居处方面,厅堂华厦则宜用大瓶,方显落落大度;书斋小室则宜小瓶,才具雅意。且瓶忌有环、成对,若将屋舍摆置成祠堂、佛寺,皆不得体。以插花为例,必须按照居家的时宜依各类花种的性情,以独具的慧心,作巧妙的安排。如苏州地区,菊花盛开时,一些“好事家”必取数百本,五色相间,高下次列,以供赏玩。然就真正的赏家看来,这不过是夸耀富贵而已。若是真是能够赏花之人,就必须寻觅异种,再用古盆种植一枝两枝,“茎挺而秀,叶密而肥,至花发时,置几榻间,坐卧把玩,乃为得花之性情”。
在生活日趋富裕、闲暇日多以后,其中的幽人开始优游玩弄,仿照古代的名笔,修剪花木,点缀盆池,弄一些盆景,作为家里的摆设。明代的盆景栽种,在历史上有极高的评价。尤其在江南一带至为盛行,如史称:“盆树之尚,天下有五地,最盛南都苏淞二郡,浙之杭州,福之浦城,人多爱之,论值以钱万计,则其好可知”。除了福建浦城一地之外,南京、苏州、松江、杭州四地,均属江南。据正德《姑苏志》卷13《风俗》记载,苏州虎丘人“善于盆中植奇花异卉、盘松古梅,置之几案间,清雅可爱,谓之 ‘盆景’”。此条记载,已经足证苏州盆景流行一时。
盆景将自然与艺术之美带入屋舍之中。如史料记载:“盆景以几案可置者为佳,其次则列之庭榭中物也。”几案之上,明人常摆放盆景,以作装点,其方法是“务取其根干老,而枝叶有画意者,更以古瓷盆、佳石安置之”。如枸杞“老本虬曲可爱,结子红甚点点,若缀其叶,初萌取炙,点茶甚美,吴中好事者植盆中为几案供玩”。当时江南人所制作的盆景,老干虬枝,奇葩绣错,掩映成林,而高不盈尺,小巧玲珑。不过一个盆景的培养,常常需要花费十多年。在生活时尚上已是如此精致,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在明代江南士人的崇尚之下,盆景艺术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换言之,明代的盆栽,无论在立意、选材、加工、用盆、点石、配架等诸方面均有极高的水平。文人常以相当的艺术修养,创作出意境深远的盆景作品。
明代士大夫居室的命名特点,同样可以作为解剖他们闲雅生活的又一范例。士大夫的居室,照例都有一个比较中听的名字,而且大多用意颇深。具体说来,这种风气,在古今之间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变化,也就是从古人重治身、不重外在之名,一变而为明代士人之重名。根据明初学者宋濂的揭示,明代士大夫居室的命名,已经达到“务极其美”,大而日月风云、雨雪霜露、江河山岳、林泉丘壑,小至竹树草卉、鸟兽鱼虫,凡是可以“托情而比德”者,无不都是取以为名。换言之,自明初以来,士大夫大多喜欢将自己的居住之处,取一个比较美丽的名字。这种室名或者说斋名,如果加以仔细的考察,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士人观念,乃至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生活细节。而其风气的变化,则更可说明社会和文化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发展。
通观明代士大夫居住之处的命名意义,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宋濂所说的“托情而比德”。但就是这种托情比德,同样出现了两分的趋向。
一是借助于室名,既体现自己在道德上的持身与践履,又借此矫正世俗之风。为示说明,不妨引明初“持敬斋”“贞白堂”为例,加以分析。持敬斋,是洪武年间吏部员外郎翟大年的斋名。关于他特意取此为名的用意,翟大年自己明白道出:“大年顷诖于吏议,继蒙大宥。预有禄食,列于英俊之后。追思旧愆,未尝不惕然惴慄。因以 ‘持敬’名所居斋,庶或善其后也。”心不持敬,就会流于荡潏;行不持敬,更会招致偾跌。可见,取“持敬”之名,显然是为追思旧愆,借此善后。至于贞白堂,这是洪武年间临川人许仲孚所取堂名。堂取“贞白”为名,其意有“贞”“白”两层含义:从“贞”这一层含义看,无论是天地、日月、阴阳,无不以贞为其精髓。即使是人,也以贞为其内心的主干。若人不贞,就会陨厥生命。而从“白”这一层含义来看,则无论是天地、日月、阴阳,也无不以白为其精髓。即使是人,也必须清清白白。人若不白,就会“为暗为僻”,甚至戕身丧德。其用意,显然是为了“矫夫侧媚污浊之弊,以治其身”。嘉靖时期的士大夫顾玉英以“寒松”名其斋,显然寄托了自己一种愿做“寒松”之志。据史料记载,顾玉英自河南按察副使谗归秦淮之后,居住在旧庐之东偏。沿街小楼,广不逾丈,坐卧其中,借训蒙数人糊口。有客人到家,从邻家乞火煮茶。曾经绝粮,有人馈赠斗粟,却被他所拒。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寒松斋”,自己已明白道出,就是为了“自砺”。这就是说,自己生平耿介,颇能自信。但年逾四十之后,沟壑见逼,恐不能自坚,流为小人之归,故以“寒松”自砺,砥砺自己在“天地冻塞”的寒冷之日,“当为寒松之荣,毋为靡草之死”。
二是在室名上追求美名,更多地通过室名以体现一种多样化乃至艺术化的生活情趣。正如宋濂所言,尽管一室之废兴,为事甚微,但可以“占世之治乱,人之劳逸”,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却并非简单徒然。道理很简单。正当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惧不能保,即使有居室,也无暇完葺。相同的道理,正当糗粮刍茭之需,交号征逮者填于家门,虽有花木之美,诗酒之娱,又有谁能有心思去娱乐?只有拨乱致治,生民各安其业,才有心思去修缮、修饰家室。为示明晰,可引浙江绍兴府诸暨县为例,加以说明。元末之时,诸暨的市庐大多毁于兵火之中:“崇甍巨室,焚为瓦砾灰烬,竹树花石,伐斫为楼橹、戈炮、樵薪之用。民惩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间,弃故址而不居,过者伤之。”直至明初建国,百姓各安生业,才有精力去重新修饬室庐。而张仁杰的“新雨山房”就是其中一例。张家居住在诸暨北门之外,故宅已全部毁于兵火。等到战后,兵靖事息,张家才辟址夷秽,重新创屋十余楹。又在宅旁植修竹数百,四时之花,环艺左右。琴床、酒炉、诗画之具,咸列于室。张仁杰处此室庐之中,号为“新雨山房”,以文墨自娱。
尽管明代士大夫居室命名呈现出两分之势,然从明代士大夫精神或生活史的演变来看,居室命名,更是体现为从道德践履向追求美名的转变。明代士人好“清”,其居室喜称“清斋”,而清斋中的布置通常也有一定的讲究,一般喜欢辟佛室供佛。如文震亨辟一佛室,“内供乌丝藏佛一尊,以金鏒甚厚、慈容端整、妙相具足者为上。”又有一小室,中设一小佛橱,“供鎏金小佛于上”。可见,居室已经普遍受到时风的浸淫。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