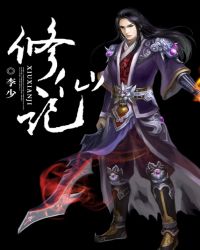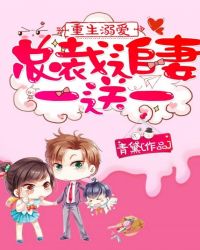他乡为己乡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亲子”不如“远子”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他乡为己乡
一个星期来,不是加拿大国庆,就是美国国庆。十岁的小侄女吵着要买一面枫叶旗。
那天我们一行十多人,年纪最大的是八十岁,最小的有十个月大,四代同堂,浩浩荡荡地前往多伦多湖边的明珠酒家。
这种人多势众的家庭场面,往往羡煞不少人丁单薄的外国朋友。
小侄女举起那红白的加拿大国旗,在前面领行。几乎全部是黄面孔的一族人,大摇大摆地走在异国的天空下。我说“几乎”,是因为二姐夫是英国人,他刚与二姐由伦敦乘飞机来探望母亲。
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移民家庭,连最老的祖母,都曾经唱过加拿大国歌,宣誓效忠异土。
入籍考试前夕,两个十多岁的侄儿为祖母恶补:加拿大有几个省份?谁是上一届总理?如果加国与中国开战,你会站在哪一方?
临老学英文,老祖母上了几个月课,只会说“哈佬”、“How乜殊”?
面对当年移民潮的冲击,本来足不出户的老人,为了害怕被下一代遗弃,千里迢迢,神推鬼拥地做了加拿大人。
怪不得中国人总是把“国”与“家”连在一起,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老祖母的移民梦,原不过是为了要跟家人聚在一起。
这一代的中国移民,与一个世纪前的铁路工人已经大有分别,但当中仍然有一个不变的道理:为了寻找他乡的梦想。
十九世纪初,加拿大人为了建筑铁路,从中国招来了很多苦力。当铁路于一八八五年完成时,很多工人便定居下来。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对居留的中国人,每人要征五百元人头税,等于当时两年的工资。因此,很多中国人离乡别井,长年与妻儿不能见面,就是因为付不起人头税。
这项种族歧视的政策,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强调多元化国家的污点。加拿大政府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国庆日,正式通过一项排华政策,限制华人入境,这政策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很多华人因而天各一方,不能与家人团聚。因此很多上一代的中国移民,称七月一日国庆日为中国人的耻辱日(Chinese Humiliation Day)。
上一代的老华侨,被迫把家人留在故乡,自己走入餐馆及洗衣店的行业。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多伦多只有二千多华人,却有近四百家洗衣店。
《多伦多邮报》的一位华侨女记者Jan Wong,就特别在加拿大国庆日,报道了一个三代为人洗衣的华人故事。
这位华人姓周,他的洗衣店至今依然用手洗熨。熨斗、洗衣板、收银机……全部老古董,店铺像个洗衣业历史博物馆。
在这“一小时干洗”的年代,周老头的洗衣店却要三个星期才起货。
有趣的是,他的顾客多是城中讲究衣着的知名人士。不但不嫌久等,还把老头子当作大恩人,把最贵重的衣物交托在他手中。
我不知道这个象征加拿大历史一部分的故事,对现代的中国移民有什么意义。这一代的移民家庭,对他乡的历史并没有太大兴趣。
以我们的老祖母为例,她最怕的是大孙儿会交金发女友,将来会为她带来一个碧眼的曾孙。
香港移民,对家庭以外事物的漠不关心,是十分明显的。
我刚从迈阿密回来,主要是参与美国家庭治疗师一年一度的研讨大会。大会中特别有一个有关移民的专题讲座,内容大部分以南美拉丁语系移民经验为主,提供的资料虽然涉及亚洲移民,但纯粹只是陪衬。
问题是,中国移民至今仍然不显眼,没有自己的声音。
大会中有两个讨论小组,一组是“白人会员对话”(“White Member's Conversations”)一组是“有色人种会员对话”(“People of Color”)。有色人种的小组,大部分是黑人。我因为飞机误时,错过了这个讨论。后来问其中一位参加者玛莎讨论的详情,她说:“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难堪的交谈,谈起不同种族及肤色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勾起太多不安的情绪,让我久久不能平复。”
玛莎是纽约甚有地位的特派专员,很多重要决策都由她主理。她是黑人,连她都因为肤色问题而不知如何为自己定位,可见一般平民小卒岂非更难自处。
妙的是,这两组以肤色分组的讨论,是由黑人会员提出的,因为他们觉得,黑人与白人的经历不同,如果放在一起讨论,就会忽视很多细节和特性,尤其是在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如果父母没有为子女准备怎样面对不同肤色所带来的歧视,子女将无法应付那意想不到的成长挫折。
美国黑人的挣扎,中国人往往无法认同,加上加拿大人标榜多民族和平相处,在多元文化的吸引下,我们很容易便暂且忘忧,安安分分地认他乡为己乡。 “亲子”不如“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