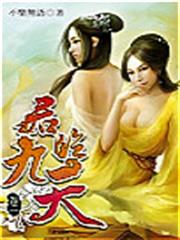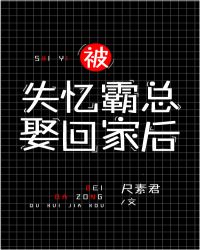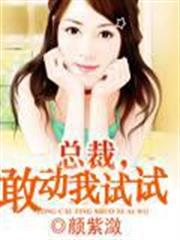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家庭生病了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卡夫卡的境界
《蜕变》(The Metamorphosis)是捷克作家Kafka的作品,说的是一个四口之家,大儿子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的故事。
这部作品写于二十世纪:一个平凡无奇的上午,一个平凡无奇的家庭,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大事——这个家庭的长子,早上一觉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反而手脚变形,长出吸盘,让他毫不费劲就爬上墙壁,躲在房子里的一角。他感到极度惊愕、恐惧,发出求救的呼声。但家人却完全无法听懂,只听得一阵阵嗡嗡之声,难以入耳。
一个大男人怎的忽然变成一只大甲虫?这当然是个怪异的问题。Kafka是二十世纪疏离主义的掌门大师,他描绘人的疏离与孤寂,以及如何为自我生存而互相排斥,至今仍是对人际关系的一记当头棒喝。《蜕变》曾经多次搬上舞台,好几年前在巴黎演出时,由怪诞导演Polinsky亲自扮演那个大甲虫的角色,演出了三个月,风靡了整个欧洲。
《蜕变》也是我十分喜欢的舞台剧,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舞台,都有不同的演绎。这剧本的寓意是,有时为了生存,一个社会或群体会不惜摧毁属于它的一分子。那么可怕的一回事,却可以甚有趣味地展现在眼前。
以下介绍的是冰岛西港剧团所演出的一个版本:打开帷幕,舞台上出现一栋两层高的房子。下层是爸爸、妈妈与妹妹,三人正一起吃早餐。爸爸集中精神看报纸;妈妈忙于一些家庭琐事;妹妹则充满少女特有的气息,蹦蹦跳跳的。三人各干各的,好像互不相干,他们围绕着彼此转动,却又各人有各人的专注——也许这就是Kafka心目中的典型家庭形象。
直到爸爸突然发觉儿子的一双皮鞋,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前,才引起全家一致的回响:哥哥不是上班去了吗?怎么他的皮鞋还在家里?这个奇怪的问题,打破了这家人那一成不变的作息习惯,为习以为常的古板家居生活带来一番轰动。这时,儿子的老板也来到了门外,查问那从不迟到的员工,怎么没有如常在办公室出现。
人人不得其解,满腹疑团地走上阁楼,好不容易打开房门,却每个人都立时发出一声尖叫。那一向循规蹈矩,做事毫无差错的青年人,竟然变成一只倒立在天花板,面目狰狞的大甲虫!大甲虫当然也同样被吓得尖叫起来,青年人也不明白自己怎会突然变成如此模样。他努力向家人及老板解释自己的迷惑,并哀求他们说:“请等一下,我很快就会没事,很快就会照常上班。我不是从不生病的吗?很快就没事的了。”但是其他人只见到一只大甲虫向他们张牙舞爪,妈妈吓得往后猛退;爸爸更是舞动棍子,把他赶回房中;老板也立刻落荒而逃;只有小妹,仍然记得给哥哥送食物,甚至愿做中间人,要求父母与兄长进行沟通——那异类毕竟是她家中的一分子,不能说除就除。
哥哥也知道自己不能老是困在房中,他十分为难地走下楼来,想与父母沟通。只是妈妈一见到儿子如此模样,立即哮喘病复发,禁不住要晕倒;爸爸见到儿子,立即就找棍子追打他。至于妹妹这个不断为他调和的角色,也不能持久——家里来了一名房客,让妹妹十分倾心,为了取悦这名男士,必须要把大甲虫的秘密收藏起来,连饭也忘了为他送去。青年人饿不可当,不断呻吟,房客开始生疑。为了让大甲虫住声,连本来最同情他的妹妹,也毒打了他一顿,直至他晕死过去,不再作声。
楼下是笑语频频,楼上是一片死寂。青年在饥寒与孤独中醒来,楼下传来妹妹为房客弹奏的琴声,他心中还只想着:“我一定要赶快复原,回到工作单位,赚钱供养家人,让妹妹可以继续学习音乐,她那么有天分,一定不能浪费!”青年人为了接近家人,拼命在地上挖洞,当他终于成功地从上层挖到下层,在天花板上现身时,楼下每一个沉醉在悠扬乐声中的男女,都被吓得晕的晕、跑的跑,房客也立即逃之夭夭,打碎了妹妹求偶的梦想。
这一次,没有一个家人可以原谅青年人,他们决定,这大甲虫必须被除去——他并非家中一分子,他完全是异类。青年人终于明白,自己再也不能被家人接纳,他哀伤地回到房中,用窗前的布帐十分艰辛地把自己勒死。除去心中大患,落幕前,我们看到舞台下半层是一个温馨家庭的景象,爸爸、妈妈与妹妹三人,陶醉在阳光遍照的欢乐中,一幅升平景象,而上半层,那仍吊在半空的青年人,在黑暗中无声消失。
这出舞台剧,我看过很多不同版本,每次都带给我不同的震撼。Kafka的作品总是那样地扑朔迷离,却又有无限创意:谁能想得出,一个好端端的青年,会变成一只大甲虫?舞台导演嘉德森自己解说:“《蜕变》是一个教人惊栗不安的故事,妙想天开而令人毛骨悚然,荒谬可笑却十分悲哀。它探讨的是人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面对极端境况时的反应。”
他又说:“看过《蜕变》后,会令你久久不能释怀,也令你很想进一步了解它的内蕴。我们听到一个声音向我们呼唤,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这个声音以不同的方式呼唤着,亘古亦然。”这是一个什么声音?它向我们呼唤着一些什么?
Kafka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区家庭,父亲自幼便觉得他一无是处,恣意批评,让他陷入长期的抑郁、自我憎恶及社交焦虑症中。怪不得在《蜕变》里的爸爸,一见到儿子就不由分说地拿起棍子去追打。也许在Kafka父亲的心中,儿子真的是一只大甲虫,也许正因如此,Kafka才能创造出如此荒诞却感人肺腑的杰作。
不幸的是,Kafka的写作才华也没有被父亲接纳。为了听从父命,他攻读法律,当小文员为生,一生郁郁不得志,四十多岁便病逝。在他生前,他的作品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几部未完成的小说,例如《审判》和《城堡》,都只留下杂乱无章的遗稿。好在他的好友并没有依照他的遗愿,把这些稿件烧掉,后人才有机会走入这位后来被誉为“对西方文坛影响最深远的文学家”的内心境界。
在《审判》中,那种虚无缥缈——被告人不知被告何罪,审判者也不知审判何人,谁是犯人、谁是法官,人人问非所答、答非所问,让读者陷入一片迷惑:一个无可脱逃的噩梦!
《城堡》的故事内容不同,描写的却是同一心态,整个故事围绕着一个找寻城堡的青年人,却总是无法抵达。没有地址,向人问路也不知从何问起,到最后,连目的地是否城堡也不清不楚——所谓城堡,不过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形象。
数年前我曾经去过布拉格,第一件事就是拜访Kafka的故居,我尤其留意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不自觉地找寻那可能仍躲在一角的大甲虫。布拉格著名的城堡,是个旅游胜地,在城中不同地段都可遥遥张望,如此瞩目的建筑,为何在Kafka的世界里,却总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也许受了Kafka的影响,我也始终没有到达那座城堡,也许所有的城堡都只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向我们心底处发出呼唤。也许这就是《蜕变》舞台剧导演嘉德森提出的那一个声音。它来自盘古,唤起那居住在我们灵之深处的犹豫、恐惧、自我否定,却又同时怀着不能放弃的一种向往,一种寻寻觅觅的孤清,一种猛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的冀望。
Metamorphosis,是心理分析中的一个常用字,也是了解个人内心的一个重要概念。香港艺术节上曾经把它翻译成《变形记》,但我觉得前人《蜕变》的译名,更加能够表达Kafka的境界。这境界好像很抽象,其实它描绘的是隐藏在每个人心底最基本的内在世界,各式各样的形象,隐隐约约,不停地泛起各种涟漪,依依稀稀,只有在梦的意识中,我们才可以真正经历个人与外在世界的冲击。 家庭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