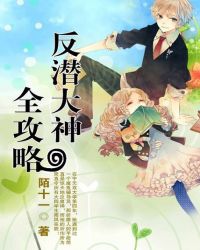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家的万花筒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新春谈死
下班回家,满脑子工作计划和安排,突然收到电话,我侄儿去世了。
没有准备、没有安排,这个消息我无法接受!
独个儿呆坐。侄儿与我同年,我们一向像姐弟,一同长大,一同分忧,他没有可能突然逝去。
我无法接触自己的感觉,脑子麻木得很,零散地浮现着一些过去的影像;那年我往台湾升学,侄儿渴望与我同往,但是他没有考上学校。来送我上船时,船逐渐开走,那留在岸上的少年,竟是如斯落寞;而我,至今仍记着他的失落!
记忆回到更早,那年父亲去世,迷失在一堆扰攘的大人当中,两个孩子自然地向彼此伸手,我们就是那样手拉着手一同度过我生命中的一个大难关。
不知道是何人作弄,我生命中的至爱,总是那么莫名其妙地突然被攫走。父亲只病了一天;母亲突然倒下;而侄儿,活生生的一个人,半天内就不复存在!
一生的理想、挣扎、计划、安排、得与失,一下子便灰飞烟灭,一下子便再也不重要!
我仍然呆坐。他们每个人的离去,都剥夺我生命的一部分,使我支离破碎。
只是我不明白,既然不能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为什么却感到自己的一部分已经随着死去。
那年回港,第一件事就是为医管局主办一个为期两日的讲座——“如何协助弥留病人的家庭面对危机”,想不到这重担子立刻就落在自己身上。
当时那个讲座的题目,的确勾起很多切身感受,令我十分伤感。想起一生中失去的亲人,便怀着日后不知再要失去哪些亲人的恐惧,更加明白哲学家尼采之言:“人生下来,就是怀着死亡的焦虑。”
死是铁一般的事实。从生理角度而言,生死是界限分明;但是从感觉而论,生与死是互相重叠的。死的固定是生的不固定;死的铁证是生的无依。
年幼时在父亲的祭堂前守灵,穿着一身麻衣,听着和尚诵经。当时那一股陌生而无助的感觉,我以为长大后就有办法把它控制,没想到年长后,那种感觉更因为情况不断重演而愈更熟悉,愈更无奈。
记得父亲祭堂前挂着一对挽联:“且向不生求不死,还从如去见如来。”
守灵时,我眼睛不断地盯着这对挽联,心中把它念了一万次,只是至今仍不明白,如何从不生求不死?分明是去了,又怎样当是来?
这个儿时疑问,一直没有解答。
只是,我知道,父亲至今依然没有消失。在我的梦境中,他仍是活生生地住在故居。每次梦醒迷糊时,我会十分释然地安慰自己:“看!他并没有死去,那消息是假的!”
母亲病逝的消息,由电话隔洋传来。那是春天的早晨,园子里充满早春的小白花,我却被一阵哀伤笼罩,对自己说:“从此我就是一个孤儿了!”
如何处理死亡?我那为期两天的讲座,勾起参加者不少新愁旧怀,彼此泪眼相对。问题是,这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远观他人挣扎的情况,而是我们人人身处其中,一个无法逃避的过程,只是处理方式因人而异。
死终归是死,无论怎样包装或粉饰,都是一个终结。无论身体在火中燃烧,或在黑暗中腐化,都是给生者留下一番苦涩,一种啼笑皆非。
有人美化死亡,从死中看到天堂,嗅到花香;有人较量死亡,猝死胜于长病,或一睡不醒是好死;又有人视死如归,为这生的悲剧加添一番意义。
记得一次在纽约看家庭治疗师Peggy Papp做治疗工作,她面对着一对夫妇,他们的小女儿患有重病,忧心的父母谈起家中的情形来,却发现原来两人各自的家族中都死了很多近亲。谈起“死的人多”的现象,夫妻禁不住都笑了起来。
当时,另一位在单面镜后观察的治疗家对Peggy说:“这一家人谈起死竟然笑嘻嘻的,表情与说话内容毫不配合,你为什么没有加以纠正?”
Peggy答:“我不知道什么是处理死亡的最佳办法,能够笑着谈死,又有何不可?”
当时我想,Peggy必定对死亡有深切的体会,才能作出如此有深度的回答。后来才知道,她的儿子刚刚因为艾滋病去世。
人要有切肤之痛才明白很多话最好不说,很多事会愈帮愈忙。最苦恼的莫如碰上道行不深的辅导员,凭着辅导指南向你大篇说理,“好意”地侵犯你的悲哀。
这一股悲哀,我们有时需要特别珍藏。心爱的人去了,化成灰,变成泥土,我们的悲哀,是一种维持他们活着的方法。这股悲哀会冲淡、会深藏,但永远不会消失。
这股悲哀,也提高我们对生的醒觉,让我们珍惜活着的时刻和活着的人。
在这新春时分,一切都是喜气洋洋、万象更新。而我的生,却被死烘得透彻玲珑。
我对八十多岁的婆婆说:“你要答应我,三年内一定不能死!”
婆婆笑说:“好,我答应你,三年不死就是!”
我多渴望,可以与死亡讨价还价。 家的万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