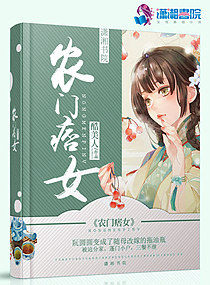第六章
画中麝香
午膳过后,烟落叫人准备了一辆马车,坐马车来到皇宫正门。
天空蓝澄澄的,如一块碧玉,没有一丝云彩,清澈明净。她的心境亦是寂寥而安静。
到了殿门前,两名御前侍卫循例上前。烟落撩开车帘,亮出手中金令,灼亮的金色很刺眼,御前侍卫立即跪下恭送。
马车继续滚滚行驶,碾过青石板,“咯咯”作响,一路景色飞快地向后退去。
有凉爽的风徐徐送来,天终于有了一分秋日的味道。不多时,烟落已来到刑部大牢。自古春夏是万物滋生蓬勃之际,不宜杀生,所以风晋皇朝贯来奉行在万物凋落的秋冬行刑。眼下已入秋,她要救爹爹,剩下的时间已不多。
再次出示手中金令,烟落顺利地进入天牢中,无人阻拦。
天牢里幽暗无光,唯有墙角烛光如鬼火跳动。走至天牢深处,刑部尚书李文清迎上来,他见过烟落手中金令后,跪拜道:“不知皇后娘娘大驾有何事?”
烟落冷觑李文清一眼,声音饱含威仪,道:“本宫探望父亲,尚书大人要阻拦吗?”
李文清目光闪烁,犹豫片刻后才道:“皇后娘娘,实不相瞒,令尊在狱中感染疫病,已经送去狱台所救治了。娘娘今日来恐怕见不到。”
怦然心惊,烟落的舌尖咯咯而颤。疫病,可是指瘟疫?爹爹好好的怎会得疫病?况且狱台所从来都是送人去等死的,哪来的救治。她似不能相信,声音止不住地颤抖,问:“什么时候的事?”
李文清恭敬答道:“昨日一早,此事臣已经奏请皇上。是皇上亲自下旨送楼尚书去狱台所救治。”
什么?昨日一早?烟落更加惊诧。风离御昨日一早就知道了,他竟然没告诉她。他明明知道自己问他要金令是想探望爹爹。难怪他轻易将金令丢给她。原来他一早就知道她会扑空。竟是这样的。他竟然这样子待她。
她怒了。只觉一股脑儿的气愤直冲上来,几乎要将她淹没。风离御今日表现得那般喜爱孩子,可却处处要致孩子的外父于死地。他如此狠心薄情,竟能流露出慈父般的神情。而她,竟还有一丝触动。她心中懊恼、气愤,几乎要呕出血来。
烟落甩袖奔离天牢,步履生风,无论如何,今日定要找风离御讨个说法。
刚上马车,忽见不远处有白光闪动。烟落望去,竟是慕容傲。慕容傲向她走来,步履格外沉重,似是一脸沉痛。当下烟落心中有不好的预感,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问道:“出了什么事?”
慕容傲迟疑了下,似不忍,又似咬牙。在烟落催促的眼神下,终开口道:“烟儿,我得到狱台所的消息,令尊……病重不治,过世了。你且节哀。”
噩耗似晴天霹雳,突然地,在烟落耳畔轰然击下。
她震惊了,整个人似在瞬间坠入冰川,彻骨的寒冷将她覆没。她呆了傻了,面颊上不断有温热的液体滚落。她的爹爹竟成了一具冰凉没有生命的尸体。她的爹爹,半年多未能相见,如今连面都见不上了。这样的噩耗,叫她怎能相信?怎能接受?
爹爹的音容笑貌似在眼前。慈祥的微笑,曾经看着她与映月一同写字;严厉的神情,曾经责罚她与映月的顽皮;无奈的眼神,曾经目送她登上花轿,进入皇宫。想不到,最后爹爹淡淡却充满温情的注视,竟成了永别。
慕容傲不忍,上前握住烟落冰凉的手,劝道:“烟儿,人已逝,你要节哀。”垂眸,他瞧见她小腹隆起,更是柔声宽慰:“就当是为了孩子,也不能过分伤心了。”
他的话,令她更伤心,泪水奔涌倾泻下来,止也止不住。连慕容傲都知晓她伤心会动了胎气。那风离御呢,他就不能从轻发落爹爹,令她宽心养胎吗?风离御那样绝情,他根本就不曾考虑过她的感受。
烟落猛然吸气:“傲哥哥,我想……”
慕容傲似知道她要说什么,摇头叹息道:“烟儿,令尊身患疫病,为防传染,遗体已是焚化处理。是我无能,连让他入土为安都做不到。要不,我想想办法弄些骨灰出来,也好立个衣冠冢。”
烟落不再说话,木然听着,眼泪早已是凝结在了颊边,绷得肌肤生疼。整个人若灵魂抽离般。片刻后,她只淡淡道:“那就有劳侯爷费心了。”
语罢,她转身。
秋风吹过,红了霜叶。偌大的天地间,仿佛只剩下孤零零的她,她的身后是黑墙冷脊,疏桐槐影的天牢,她的身前却是白茫茫的一条道,不知通往何方。
风又起,几片枫叶飘飘摇摇,落在她肩上,鲜红如泣血。烟落攥紧衣裙一角,用力之紧,几乎将其揉得粉碎。风刮痛了她的双眼,她平静得近乎可怕,冷静得近乎骇人。缓缓登上马车,她淡淡的声音泠泠响起:“起驾,回宫!”
慕容傲见她神色不对,忙上前阻拦,焦急道:“烟儿,你可别冲动。皇上不好惹……烟儿……”见她不语,他欲再劝。他拉住她的衣袖,不想却被她狠狠甩开。
烟落冷声道:“侯爷多虑了,皇上是我的夫君,我能奈他若何?”
马车微微一摇晃,徐徐启程。慕容傲无能为力,只定定瞧着烟落的侧脸。烟落心中涌起感激与愧疚,却不敢去看他。放下车帘,他的身影立即模糊起来。她垂首轻轻道:“家父身后事,我这个做女儿的不便出宫,只能依赖侯爷。此大恩,我没齿难忘。”
车夫挥鞭扬下,马儿嘶鸣声刺破长空,绝尘而去。身后传来慕容傲焦急的呼喊,久久回荡在耳畔,“烟儿,保重。”
她终忍不住转过脸去看,一片朦胧中,只见慕容傲的身影往后退去,越退越远。马车拐过街角,终于,什么都看不见了。
回到宫中时,夜幕已降临,薄纱般的黑色将世间万物都照得朦胧。天边月儿浑圆如冰盘,明亮而冷冷地俯视大地。圆月象征着合家团圆,可她已是家破人亡。烟落一路询问了数名宫女,获悉风离御今晚去了玉央宫。她说不清心中是何感觉,只知脚下已控制不住地朝玉央宫奔去。
夜来风过,拂过她瘦削的脸庞,却有如薄薄刀刃缓缓划过,刺痛般的感觉。
玉央宫中宫灯辉煌,歌舞丝竹之声萦绕,热闹的氛围与烟落心底的悲恸相去甚远。徐徐袅袅的琴声带着似有若无的缠绵,三回九转,时而如大珠小珠泻入玉盘般清脆,时而又如高山流水般绵长。再美的琴音,此时听在她耳中都是尖锐刺耳的杂音。
“砰”的一声,烟落陡然推开两扇宫门。晚凉的夜风跟随她的怒气一道涌入,惊动了屋中正在惬意抚琴与聆听之人。
梅澜影与映月一脸茫然地看向神情阴冷的烟落,面面相觑,不明所以。半晌,梅澜影最先缓过神来,出席叩拜,恭敬道:“皇后娘娘金安。”
烟落环顾四周,她要找的人已经走了,眼下只余映月和梅澜影相聊甚欢。
梅澜影见烟落四处张望着,她会意,忙解释道:“尉迟将军有要事奏禀,皇上移驾去了御书房。皇后娘娘要不……”她停下,不敢再说,小心地觑着烟落的脸色。
烟落淡淡扫过紫檀桌上精致的金盘,数样精致的小菜错落摆放,碗筷皆是搁着,显然风离御是用完晚膳走的。巡视一圈,最终烟落将眸光落定在映月身上。方才梅澜影抚琴,映月聆听,两人好不惬意。
再看映月的装扮,品红色桃花纹上衣,及地的闪珠缎裙,头上绾着坠珠流苏金钗,华丽出彩。相较自己一身素白,简直是天壤之别。
烟落喉头一紧,像有一双手狠狠抓住她的心,揉搓着,拧捏着,让她透不过气来。明知是为何,她还是忍不住问了:“映月,你怎会在这?”
映月展颜轻笑,道:“梅姐姐邀映月前来与皇上共进晚膳,映月为何不能来?难不成,姐姐原本想邀映月与皇上一同用膳吗?”映月的言语中,嘲讽之意毫不掩饰。
梅澜影心一惊,倒吸一口凉气,忙拉了拉映月的衣角,示意映月不要再多言。
烟落心早已麻木,并不痛,只是空落落的难受。她上前拽住映月,冷声道:“家道中落,爹爹获罪,你却穿得这般艳丽,简直不成体统。”用力扣住映月的手腕,她拽着映月朝门外拖去:“赶紧跟我去景仁宫换下来!”
映月本就对烟落不满,现下怒意更甚,她用力甩开烟落,愤然吼道:“凭什么?”她目光如刀,刮得烟落脊背发凉。
烟落咬紧下唇,眉间蕴满阴霾,盯着映月,她一字字道:“就凭我是你的亲姐姐!你走不走?”
“亲姐姐?”映月齿间嚼着这几字,讪笑起来:“亲姐姐待我如何?从前你霸着皇上,何曾想过我?如今梅姐姐对我好,你凭什么不让我留在玉央宫?你也能算是我的亲姐姐吗?”
烟落痛心疾首,长叹一声道:“好,你不认我这个姐姐,罢了。”她极力克制着怒气,正色道:“我问你。爹爹总是你的亲爹爹吧,总不曾待薄你吧。你方才瞧见皇上,可曾替爹爹说过半句好话?”
映月一怔,喃喃道:“爹爹的确是罪臣,皇上自有圣断,映月相信皇上绝不会冤枉爹爹……”
“啪”的一声响起,声音凄厉清脆,震撼了殿中每一个人。烟落甩手狠狠给了映月一个耳光。她怒不可遏,大喝:“给我闭嘴!”
烟落无法控制盛怒,一字字从唇齿间犀利迸发出来,带着撕心裂肺的痛:“你还是不是爹爹曾经捧在手心里疼宠的女儿,竟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这样一掌,拼尽全力。她的手火辣辣地痛。她的心在淌血,缓慢地一滴,良久,又一滴。
映月一手捂住脸颊,那里高高肿起五道指印。她难以置信地瞪着烟落,几乎要瞪出火来:“你竟然打我?!”
烟落眸色沉痛,怔怔瞧着自己的手。打在映月脸上,痛却在自己心上。她竟然打了映月,从小自大,她从未跟映月红过脸,更不用说动一根手指头。
映月连连摇头,泪水滚滚而出,尖声叫道:“你竟然打我?你真是太可怕了!你处处压制我,不让皇上与我亲近!算了,我只想与梅姐姐交好,亲近皇上,难道有错吗?”
映月哭得不能自已,冷冷盯着烟落,突然她大笑起来,神情怨毒无比,字字嘲讽:“我一直以为皇上爱着姐姐,原来竟不是。姐姐你不过是和映月一样孤寂的下场。怎么,你妒忌了?疯狂妒忌梅姐姐了?不能容忍了?那你终于体会到从前我的心情了!”她一直笑,笑得满头珠翠亦随之瑟瑟抖动。
烟落麻木站着,一言不发。毒辣伤人的话,映月轻易就说出了口,丝毫不念姐妹情分。
映月犹不肯罢休,继续道:“与其姐姐独占宠爱,我宁可皇上爱的是别人。如今看来,皇上从前只是将姐姐当做替身。想必姐姐已经知道了,不然怎会毁去容貌呢?怎样?当替身的滋味好受吗?”
映月的话,字字如钢刀戳刺着烟落心底的最痛之处,每一刀都戳得她鲜血淋漓。更令她心痛的是,映月竟恨她至此,不惜用最恶毒的话语伤她。颓然垂下双手,烟落只觉全身力气都被抽干了,只想软软倒下。
烟落强撑着,语气极轻,如白云飘忽不定,至最后已哽咽不成声:“爹爹在牢中,身染疫病,已经过世了,尸骨都无……”她凄然转身,映月会是何种表情,她已无勇气去看,只怆然说着:“如果,你还是爹爹的女儿,就把一身红衣换下吧。”
烟落跌跌撞撞走至殿外,踏上冰凉的白玉地面。身后传来阵阵干呕之声,她以为是映月,可待回身,却见梅澜影捧腹干呕不止。她是过来人,梅澜影那样子,极像怀孕。可梅澜影入宫不足一月,难道他们从前就暗通款曲……烟落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消失,那时风离御与自己,正当浓情蜜意……
殿外是无尽的黑暗,月儿似不忍瞧她的悲苦,躲入云后。噬骨的秋寒,将她尽数吞没。她脑中一片空白,心里只单调重复着一句话:“梅澜影有了身孕。”
从今往后,后宫于自己,只怕会更冷。
烟落不知自己是如何走回朝阳殿的。殿内轻纱飞扬,在她眼中却似灵幡飘舞,宝鼎散出的气息清香宜人,在她闻来却似香烛徐徐。再多的烛火,再明亮也只是多了阴森之气。
本来,她想靠自己救爹爹,如今也不需要了。
她倒在床上,也不脱去衣裳,疲倦到不能动弹。
第二日醒来时,烟落发觉身上外衣与鞋子皆有人替她褪去。初秋夜凉,一袭薄被搭在她身上,替她抵去夜寒。身周似缭绕着淡淡的龙涎香,再闻便没有了。难道是风离御来过?苦笑一番,她甩一甩头,自己真是睡糊涂了,他怎可能会来呢,如今他的心思全在玉央宫。
烟落木然坐起身,穿戴整齐,靠绣花打发了一阵时间。到了中午的时候,有宫女来禀,果然不出所料,梅澜影有了身孕。
红菱正立在一旁缠丝线。听罢,红菱愤愤将手中绣线扔在地上,不齿道:“狐媚!”
烟落放下手中缝制的小衣,端起菊花茶,徐徐咽下一口,面上无一丝波澜。梅澜影有身孕,她昨日已猜到。想想有什么呢,这么多痛苦她都承受了,还差这一桩吗?
红菱气愤难平,喋喋不休道:“不就是有孕吗?有什么了不起,还派人通传,弄得人人皆知。梅澜影毕竟曾经是先皇的宠妃,也不知害臊。皇上也真是的,指派卫风照料她。那我们这边怎么办?娘娘你可是怀着双生子呢,难不成还没她重要吗?”
烟落本不想计较,红菱一番话撩拨得她平静的心湖再度泛起波澜,她深深蹙眉。风离御让卫风照料梅澜影?如此重视?难不成,风离御还怕自己会害了梅澜影的胎儿不成?
想到这,烟落神情骤冷,捡了一块雪花糕慢慢嚼了,徐徐道:“红菱,日后我们得小心行事。”
红菱挑眉,诧异地问:“为何?”
烟落冷哼一声,道:“梅澜影怀孕弄得宫中人人皆知,万一她的胎儿有个三长两短,矛头还不都指向我。谁人不知,我曾让她跪在殿外,容不下她。”
红菱凝思片刻,问道:“照理梨妃有孕,咱们该送去贺礼。娘娘,那咱们还送不送?”
烟落颔首,红翡翠珠钗轻轻打在耳边,凉凉似小雨。她缓缓道:“当然要送礼,还得送上一份大礼,免得叫人留下话柄。红菱,你去准备笔墨,我亲自绘一幅画给她。再附上一对龙凤金镯,就是上次西番进贡的那对,有精巧的卡扣,能打开的镂空雕花镯子。”
红菱皱眉,一脸不情愿,道:“那可是皇上特意留给娘娘的。凭什么给她,哼!”
烟落无所谓地笑笑:“不过是身外之物,算了。皇上那样喜欢她,那她啥样的宝贝没有,别嫌弃咱们的就是了。”顿一顿,她想了想,仔细叮嘱道:“梅澜影此人太假,三番两次无故晕倒。我不想惹麻烦上身。红菱,你切记:但凡梨妃来,就说我身子不爽,一概不见。还有你们所有的人都离她远远的。否则,万一她有什么事,咱们说不清。”
红菱应声,无奈地叹息一声,道:“好,那我去准备笔墨。”
自从梅澜影有孕后,烟落的朝阳殿更是冷清。
西风透着新凉,不声不响地来到了人间。一阵风过,便凉一阵。
醉兰池边百花凋落,却并没有清冷萧条,取而代之的是盛开的清秋菊花、有金芍药、一团雪、胭脂香等。菊花锦绣盛开,不似春光又胜似春光。诚然,天地永远是美的,梨花谢了,开了菊花,菊花谢了,还有梅花。风离御身边总会有鲜花盛开,有没有她自是无所谓的,更何况她容貌已毁,只是一朵残花。
一个多月中,风离御仅来过两次,每次不过是稍坐片刻,问问孩子情况。其余的时间,他总是陪着梅澜影。
烟落足不出户,白日里靠绣花打发时间。到了晚上,她静静坐在花园中,瞧着流萤飞舞,流星划过,兀自出神。她什么都不想,只满心期待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
然而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下来。
这一日傍晚,落霞红得如血泼彩绘一般,染透半天。
烟落小腹隆得愈来愈高,双腿也浮肿着,为了能顺利生产,她每天都坚持走上一个时辰。这日烟落自湖边散步回到朝阳殿,迎面碰上红菱焦灼地赶来。见了烟落,红菱慌里慌张道:“娘娘,梨妃娘娘小产了。”
烟落一惊,脸色微变,立即斥道:“她小产了,你慌什么?关我们什么事!”
红菱面色煞白:“娘娘,皇上龙颜大怒。”
烟落心中有着不好的预感,面上仍维持着平静,摆手道:“玉央宫一定炸开了锅,我们就不要去凑这个热闹。红菱,回宫。”嘴上这样说着,她心内却直打鼓,梅澜影好好的突然小产,定有人暗害。放眼后宫,唯有她与梅澜影有过节。该不会这脏水要泼至她头上吧。
正想着,刘公公踏着愈来愈暗的霞色奔来,见了烟落,恭敬道:“皇后娘娘,皇上请您移驾玉央宫。”
“何事?”红菱骤然问出口,声音含了些许紧张。
刘公公斜觑红菱一眼,冷了声:“皇上的吩咐,奴才怎知详细?还请皇后娘娘移驾。”
烟落心中一沉,心知不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问心无愧,不能自乱阵脚。当即她回宫换了套衣裳,跟随刘公公一同去了玉央宫。
走近玉央宫内殿,浓重的血腥气并着草药浓郁的气味扑面而来。绘春嬷嬷跪在床边哭泣不已。一名小宫女抱了被鲜血浸透的云缎褥子朝殿外奔去,不小心撞了烟落一下,却也顾不上了,只匆匆道歉一声,旋即飞快跑离。
那血红得刺目,红菱只瞧了一眼,惊得掩面,回头不敢去看。
烟落凝眉走上前。
宽阔的沉香木雕花大床上,梅澜影正缩在风离御怀中嘤嘤啜泣着,长发散落,楚楚可怜。风离御好言安慰着:“影儿,别哭了,朕会查清楚,若有人害你,朕绝不姑息。你这次伤了元气,不能过分伤心了。听话。”
温馨的场面,烟落别过脸去,不自然地轻咳一声。
风离御闻声望向烟落。她更清瘦了,唯有小腹高高隆起,腿也浮肿着。他心中一软,嘴上已道:“皇后身子不便,赐座。”
绘春一愣,不情不愿地搬来椅子。烟落狐疑地望着风离御,他唤她来,不是要质问她吗?
梅澜影见状,哭得更厉害,哭声撕心裂肺,哭得小脸惨白。她的声音颤抖,嘤嘤控诉着:“皇上,孩子没了。皇上都不过问吗?”
风离御柔声哄着梅澜影,道:“谁说朕不过问了?毕竟皇后怀着龙嗣,朕怎么也得顾念。”说罢,他看向烟落,冷了脸:“梨妃流产,你果真不知缘由?”
烟落淡淡摇头:“臣妾应该知道什么?臣妾每日在朝阳殿绣花,足不出户,又能做什么?”她虽这么说,心中却明白,她既然站在这,肯定已是入了别人的陷阱。
“呵呵。”风离御轻嗤:“皇后一向冰雪聪明,若真想做什么,何须出门?”
烟落偏过头,半晌才道:“皇上什么意思?”
“绘春!”风离御寒声唤着,眸中幽黑似一汪深不见底的寒潭。
绘春会意,取来一对龙凤金镯,打开卡扣,轻轻一抖,从里面倒出一些细小颗粒的香料来,哭诉道:“皇上您看,这对镯子设计精巧,是空心的。御医已验过,里边香料中混着麝香。这种香料香气浓郁,掩盖了麝香的味道,又有安神的作用。麝香自细密的镂空花纹溢出来。梨妃娘娘戴着镯子,日日闻着麝香,这胎才没能保住。”
风离御冷冷质问:“皇后,你有何辩解?”
烟落望一眼那镯子,神情淡淡的,道:“镯子的卡扣谁都能打开,我若放入麝香,岂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再者,若有心人栽害我,也是轻而易举的。”
梅澜影一听,哭得更凶。
风离御冷哼一声,道:“皇后果然善辩。单单只有一对镯子,朕也不会叫你来。绘春!将画呈上来!”
绘春抹了抹眼泪,取来一幅画,徐徐打开。那画笔法精妙,以黑白浓墨写意的梅林为背景,衬托出画中彩衣女子风致嫣然,肤白胜梨花,连衣褶纹理清晰可见。此画甚至将梅澜影眉间一点轻愁都描绘得惟妙惟肖。
烟落凝眉:“此画有何不妥?”
风离御瞥她一眼,冷冷道:“泼墨写意,除了皇后,还有谁有此绝妙之笔。”
烟落轻哼一声:“此画出自臣妾之手,亦是臣妾相赠梨妃。这点无需隐瞒。”
“啪”的一声,风离御一掌重重击在床榻上,吓得众人面面相觑。他盯着烟落,眼底折射出冰冷的锋芒,厉声道:“皇后真是好巧妙的心机!”
烟落扫他一眼,眸中难掩失望与鄙夷。镯子的事情不算,他还想栽赃她什么?在他眼中,自己如此不堪吗?
鄙夷的神情,令风离御脸色瞬间铁青,握紧的拳头“咯咯”直响。
绘春嬷嬷继续哭诉道:“皇后娘娘所赠之画,梨妃娘娘爱不释手,时常欣赏。哪知……这泼墨处的墨汁都是染了麝香的。皇后娘娘犹嫌镯子里的麝香不够,连画中都做了手脚,可怜梨妃娘娘的胎,就这么没了。”
梅澜影听绘春提到孩子,怨恨地看了烟落一眼,双手紧紧抱着膝盖,哭泣着,蜷缩着,颤抖着。
瞧着眼上演前的一幕又一幕,烟落只觉像是在看戏。可惜她深陷局中,便没了听戏的闲情雅致。树影透过窗格映入室内,黑影在地上纵横交错,诡异难测,一如她此刻的境地。宫女们忙来忙去,殿门时而开,时而合。秋寒肆意侵袭,令烟落脊背阵阵发冷。
风离御自床榻上起身,几步逼至烟落面前,他寒声问:“究竟是不是你?”
烟落徐徐起身,后退一步,眼波凌厉地拂过他的俊颜,复又瞧了瞧梅澜影。她安静垂目,字字咬牙道:“臣妾确实容不下她!但……”
“啪”的一声,他狠狠一掌打在了她的脸上。
这巴掌极是突然,烟落痛得脸颊发麻,眼前金星乱晃,怔在当地。相识以来,他强占过她,羞辱过她,抛弃过她,甚至无情利用过她,却独独没有打过她。如今为了梅澜影,他竟动手打她,他甚至都没听她说完。
她的心猛然往下一沉,胸口闷得极疼,眼中掠过一丝悲戚,却很快被从容取代。她没有哭,也不想哭。有什么好哭的呢?为了眼前这个本就不值得的人。
气氛似胶凝,叫人窒息。
风离御眯起眼睛,眸中冷光似针刺出,吩咐刘公公道:“自今日起,晋月昭仪封为月妃,协理六宫。皇后戕害龙嗣,罪不可赦!念其身怀龙嗣,暂不处置,即刻迁飞燕宫禁足,无诏不得外出。”
烟落默默听着,手抚着脸颊热辣辣之处,喉间咽下的皆是带着血腥味的咸涩。禁足飞燕宫,形同打入冷宫。不过,现在的朝阳殿与冷宫何异?先皇在时,她曾在飞燕宫渡过漫漫长日。现在,她的日子又回到了从前。飞鸟尽,良弓藏,她对他没了利用价值,会有今日的下场,她早就料到了。
她千算万算,费尽心机避祸,依旧被人陷害。镯子里的麝香可以后放,只是将麝香掺在墨料中,谁能知道她会送画给梅澜影,谁又能在她的东西中做手脚?除非是……
烟落心中陡然一惊,忙望向不远处的红菱。只见红菱垂首站立,身子微颤,正无措地搅动着双手。难道真的是红菱?烟落心内大震,红菱怎会如此糊涂?如此一来,她这罪认也不是,不认也不是。
风离御上前一步,紧紧捏住烟落下巴:“你太令朕失望了。”
烟落抬头仰望着他,俊颜近在咫尺,却那样陌生,仿佛从不相识。有片刻的沉静,耳畔风声簌簌,他们站得那样近,风撩拨着他们的衣衫,飘飘纠缠在一起。可心却是愈来愈远。
烟落突然莞尔一笑:“皇上既有圣断,臣妾何须多言。”她冰凉的小手,缓缓将他捏住她下颚的大手,一点一点地掰开。
眼底皆是寒冰,她望着他,他的眼中正倒映着两个小人,却是同样的冰冷。
她用力将他推远,屈膝一福。轻轻一笑,灿烂的笑令天地万物皆蒙羞,她字字清晰道:“臣妾谢皇上圣恩!”
转身,天青色的长裙瞬间如绽开的荷叶般凄美飘落。她头也不回地离去。
心,也许早死了,才会这般没有感觉。 烟锁御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