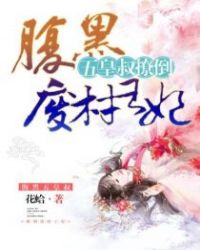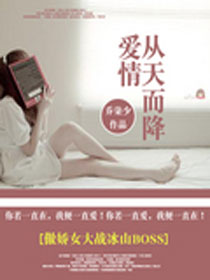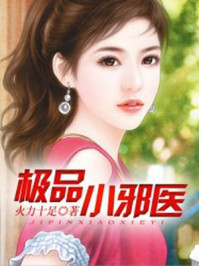年纪稍长的人都记得,陶一碗最早出现在金沟大垸的样子。寒冬腊月天,顶着光溜溜的青皮头,鼻梁上架着一副亮晶晶的眼镜,肩扛一床棉被,斜挎一只帆布包,帆布包带子上用毛巾系着一只很大的白色搪瓷杯,村里人叫它洋瓷缸。村里人日后统称他的光头、眼镜和搪瓷杯为三光。由此给他取了一个诨名:三光政策。开始人们是偷着叫,慢慢地就公开了。陶一碗不得不时常威胁说,谁敢叫这个诨名,就让谁到宣传队演节目。大家都怕到宣传队演节目,很快就没人叫了。陶一碗在“文革”中曾就这事,向下来串联点火的红卫兵作过检查。他说自己不能接受这个与日本鬼子凶残相关的诨名,因为他的父母、姐姐和哥哥都是让鬼子兵杀死的。
作为“右派”的陶一碗,是在监狱中服刑两年后,被派遣到金沟大垸进行劳动改造的。村里人已在广播中听惯了“右派”这个词。如同当年的“鬼子”与“日本人”要来一样,大家都在猜测这么让人憎恨的可怕的“右派”,会是什么模样。陶一碗来到村里时,正值黄昏,夕阳照在他的头上、眼镜上、搪瓷杯上,闪射出灿烂的光芒。陶一碗冲着人群用纯正的普通话问,这是金沟大院吗?村里的人都被这话问愣了。并不是因为陶一碗像所有外地人那样,将金沟大垸错念成金沟大院。令村里人发愣的是陶一碗说话的语气。往后很长时间,他们都说陶一碗这是明知故问,别有用心。
三姑那时正是迷人的年纪,她抢在所有人面前反问了一句。
她说,你就是那个“右派”?
陶一碗回答说,是的,右派分子陶一碗。
村里人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
陶一碗在回忆中分析,大家发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光头,二是他的名字。
据我了解,金沟大垸的人第一次冲着陶一碗大笑,没有任何具体内容,仅仅是村里人觉得想笑,便笑了。
细姑当时站在自家门口,让她最注意的是那只搪瓷杯。她对大姑说,陶一碗的那只搪瓷杯,很像她家当年煮参汤用的。大姑要她上前问一问,是否是从她家分浮财获得的。细姑没有去问,她知道大姑在说反话,不过她俩都没想到,细姑与陶一碗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因正是这只搪瓷杯。
陶一碗来时正值大饥荒开始的一九六〇年。夏秋两季几乎颗粒无收。
陶一碗同冬天一起来到金沟大垸,似乎也将饥饿带给了金沟大垸。
实际上,最苦的人是陶一碗。他还没有学会山上哪些野生的东西可以吃。等他学会了,那些东西也快被人挖光了。大家一样样地吃,先是草后是树皮,然后是树根,最后是观音土。
哪怕是到了吃观音土的时候,多数人家仍或多或少藏着一点米,或是半斤或是一斤,非是紧急关头需要救命,绝不动用。村里的人一向吃自己种的粮食,一旦自己种的粮食收不起来,也会想办法自救,而不寄希望于任何其他人。
陶一碗不清楚,他固执地相信上面不会让人饿死,很快会有粮食运来的。他也不明白,生产队长给他分基本口粮时,在秤杆上做了手脚,贪污了两斤谷。这是“文革”时,红卫兵批斗生产队长,生产队长自己交代出来的。他还交代说,那两斤谷救了全家人的命。他老婆连糠带米一起煮,整整吃了一个月。所以他家的人没有谁被观音土胀死。
那个时节,几乎没有人在家里开伙,都怕炊烟一起,将周围的人全引过来。找到点什么,就在野外挖灶,用随身带着的小锅煮熟后,就地吃个精光。
从严格意义上说,三姑就是在那时开始找男人要饭吃的,只要谁给她一点可吃的东西,她就睡在谁的床上。
大姑家里本是存米最多的,可她看不下别人的惨样子,这家给半把,那家给半把,到剩下几两米时,才知道要顾自己。这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草木迟迟不泛绿。大姑和细姑被观音土撑得苦不堪言之际,李小林让人悄然送来两斤半米。她们准备到野外挖灶熬点清水粥,为防止吃大户,她们要用两只锅。
细姑想起陶一碗的搪瓷杯,就要去借。
大姑在一念之差中同意了。
她当时想,只有找陶一碗借搪瓷杯才不会惊动别人。
细姑去找陶一碗时,他正在自家的破屋里,抱着肚子狠命地哼,连点头的气力也没有,只是眨眨眼表示同意。细姑问他是不是让观音土撑的。陶一碗又眨了眨眼。细姑怕拿了东西就走太轻慢人家,又搭话问他爱人怎么不来看看,或者接他到城里去躲躲灾。一直没有开口的陶一碗忽然清晰地说,我离婚了,没有爱人。陶一碗曾对我说,他那时连救命都喊不出来,可不知怎么的,竟对细姑说出了那句话,可见这也是有缘分的。
不要说细姑,所有在金沟大垸里土生土长的人,那时都没见过离了婚的人。细姑拿了搪瓷杯回去,说起陶一碗同妻子离了婚时,连饿得面黄肌瘦的大姑,也产生了几分兴趣。
细姑也没想到,因为这搪瓷杯而救了陶一碗一条命。
大姑和细姑在山坳里躲着将一把米熬成一大杯粥时,尽量找些不冒烟的干草枯枝,而且将时间也选在山上到处在冒烟的时候。她们还将另一只锅里放些水和草根树皮,发现有人来时,就将搪瓷杯从灶上撤下藏起来。大姑她们正吃时,山冈上出现了三姑,她问她们吃什么。细姑说你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三姑正要走,大姑将她留下来,将两人吃的清水粥分作三人吃了。三姑后来说,细姑当时有意见,别人想办法躲,大姑却招人来分食,真是不会顾自己。大姑要这么做,细姑也没办法,因为李小林的米本来就是送给大姑的。大姑在三姑喝粥时劝她这时千万要小心,若是怀上了毛毛那就麻烦了。大姑给三姑粥吃,是要她少找男人。三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果然没去找男人,并且从此以后铁着心跟上了大姑,直到大姑让我将她称作三姑。
陶一碗住的屋子是生产队春夏两季炒茶用的,它孤零零地建在村边。陶一碗被观音土撑得快死了的呻吟,因而更加微弱,在这人人自危之际,没有人还记得要照顾到他。
细姑是第一个发现陶一碗情况不妙的人。细姑送还搪瓷杯时,发现陶一碗的情形更加不妙了。陶一碗脸上尽是青色,眼睛里除了悲哀,再也没有其他。细姑的心被打动了,她当时没流泪,回到家里,同大姑说时,却流泪了。
细姑求大姑救救陶一碗,找个人将陶一碗的屁眼抠通。
天底下的人,只要吃了观音土,哪怕服用最厉害的泻药,依然拉不出来,非得有人用手指从其屁眼里,一点点地往外抠。大姑被细姑说得动了心,就去找生产队长,让他派个人帮陶一碗抠一抠。队长不敢派人,让贫下中农去给右派抠屁眼,是要犯大错误的。
大姑说,你就不会派个地主富农去吗?
生产队长说,别的地主富农都派出去修水利了,村里的“坏分子”,只剩下你们两个。
大姑想了想说,谁愿意帮陶一碗抠屁眼里的观音土,我就送他一把米。
生产队长听了,连忙表示,这么大的政治风险,还是自己承担为好。
细姑拿着一把米,守在陶一碗的屋门口。看着细姑手上的米,生产队长喃喃地说,放在平时,还不够喂一只鸡。
毕竟心里不舒服,生产队长下手时狠了些,加上手指比较粗,陶一碗的屁眼被他抠得鲜血直流。
日后,生产队长到西河镇小学找陶一碗,希望他开个后门,将儿子安排在学校当勤杂工。陶一碗说他当年心太狠,用力太大了,给自己弄出一个肛裂的毛病,三天两头就会发作。当年的生产队长说,救命就得下猛药,他不用力抠,那些快要成为石头的观音土就出不来。的确,村里死的几个人,家里的人不敢用力往外抠屁眼里的观音土,是其原因之一。陶一碗最后收下他的儿子,让其在食堂里当炊事员。
早几天就应当拉出来,却一直拉不出来的观音土,被生产队长用手指抠出来后,大姑又让细姑给陶一碗送来二两米。细姑在屋里烧火给陶一碗熬粥。大姑在门口守着,防止有人进来吃大户。
吃完粥后,陶一碗不让细姑走。他要细姑留下来听自己说说心里话。
陶一碗告诉细姑,两年前,前妻拿着他的日记去找组织,他被打成右派不说,还判了两年徒刑。前妻同他离婚不到三个月,就同本校里的一名干部结了婚。陶一碗直到出狱后才知道,那女人之所以出卖他,正是要同他离婚而同别人结婚。
听完陶一碗的故事,细姑站在屋里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怎么开始的,在自己家里几乎什么都不干的细姑,居在帮陶一碗收拾起屋子来。细姑自进金家门以来,还没有做过如此重而累的活儿。细姑并不是不能干,陶一碗的那间破屋,被女人的双手摸了一遍之后,竟也变得有模有样起来。
金沟大垸的后人,对鱼儿祖上的崇拜与怀念,永远都是有理由的。
鱼儿祖上选址建村,留下的福分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又显出来。金沟大垸只受了一年半灾,第二年的秋收便获得了足以度荒的粮食。别处村里的人,只要一看见金沟大垸一带下雨,就骂自己的先人不会选地方。金沟大垸的人吃上三顿饱饭,就不安分了,心也好,眼也好,都在盯着邻村那些还在挨饿的女人。
据说是李小林下的指示,要在金沟大垸搞文艺宣传队,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
陶一碗就是因为搞宣传队而在金沟大垸里有了位置。
陶一碗并不懂怎么演节目,他在大学里研究历史着了迷,连看节目都很少。生产队长找到他,要他担起这项革命重担时,他伸出双手,要封住人家的嘴。
生产队长不容置疑地说,上面命令我,我就命令你,我先给你五十斤谷,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之后,陶一碗对细姑说,他宁肯修水利,也不愿当戏子。
细姑就劝他,排演节目至少可以不受日晒雨淋。
陶一碗觉得有道理,就按细姑教的,找生产队长讨价还价,说搞宣传队可以,但得给他全劳力的工分。生产队长想了想只给他九个半工分,扣下的半个工分是因为那顶右派帽子。
按照细姑的指点,陶一碗提上五斤谷,走了二十里路,找到那个被县剧团开除的演员,请他出主意,当参谋。因此,生产队长送来的五十斤谷,被这个人吃掉了三十斤。吃了陶一碗的米,就得教陶一碗演戏。陶一碗也乐得先来同他学一番,然后回去教村里人。
宣传队人员中,只有三姑是主动报名的,别人都是陶一碗点名的,说哪个节目要几男几女,胖瘦如何,然后由生产队长派工。搞了些时,陶一碗对他们熟了,就亲自点了几个人作为固定的。陶一碗有了这种权力后,村里的人便有些敬畏他,害怕被点名去宣传队演节目,特别是演节目中的反面角色。三姑谈到宣传队,总是眉飞色舞地说,那段日子真快活,年轻男女大大方方地挤在陶一碗的小屋里,或是扮夫妻,或是扮父女,或是扮兄妹,真真假假的有意思极了。她说陶一碗那时唱歌唱得真好,只要一开口唱《想起往日苦》,全村的人都感动得号啕大哭,连狗子的叫声,也呜呜地悲哀得很。
《想起往日苦》是由陶一碗和细姑带着一群半大孩子出演,他们扮夫妻,孩子们则演他俩的儿女。细姑从开始起就拒绝到宣传队演节目,大姑也不要她去,担心一个寡居的女人混在其中,惹人家闲话。陶一碗偏偏每个节目都看中了细姑,都要细姑出演。别看大姑和细姑成分不好,就是国家干部和工作组也不敢在她们面前说狠话,其中原因,除了李小林的威力之外,大姑和细姑作为女人的魅力,也在起作用。
大姑的冷艳、细姑的妩媚,都是方圆数十里的不争事实。
细姑说不演,谁也不能强迫她。
是那年秋天最后一次在屋外乘凉聊天之夜。
陶一碗来到大姑门前,又开始做细姑的工作。陶一碗先将这节目的安排说了一遍。对于筹划过程,大姑和细姑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只要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会仔细地问问清楚。其专注程度,使人绝对不会相信,转眼之间就会遭到她们的拒绝。这种拒绝总是发生在最后发出邀请的那一刻。那种冷酷和毫不留情,使人难以相信刚刚发生在眼前的那些火一般的热情。
村里人早就预言,陶一碗若能请到细姑演节目,他们就请陶一碗到西河镇上餐馆去喝肉汤。他们又补充说除非石头说话,公鸡下蛋。
陶一碗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最感吃惊之处,并非最终请出了细姑,而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从没有考虑过要大姑出演什么。他进一步说,如果记忆没有差错,甚至连大姑的名字也没有人提到过。对于这一点,陶一碗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好解嘲地说,金沟大垸有一种妖氛,能控制人的思维,使他不能朝不许想的地方想。
那次,说到最后,陶一碗便将要演的节目唱给大姑和细姑听:
想起往日苦哎,
两眼泪汪汪哎哟,
家破那个人亡啊好凄凉哎哟啊嗬哎哟,
穷人哪好心伤哎嗨哎嗨哎嗨哟……
歌词我也记得,从我小时起,细姑就一直在我耳边小声哼唱着。
陶一碗没唱完,大姑就掩面而泣,哽哽咽咽地对细姑说,你去演吧,这个节目好。
这个情节,只是到了取消阶级成分以后,陶一碗和细姑才将其公开。他们成分不好,早些时若说了出去,会引起麻烦。大姑和细姑想起的的确是一九六〇年的苦。陶一碗和细姑演完这个节目引起了共鸣,共鸣点也在一九六〇年的灾祸上。紧接着,金沟大垸开了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一个靠要饭为生的老太婆痴痴呆呆地上台去发言,她说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苦是苦,但没有去年那么苦!一九四九年以前,遇到大灾,金九叔还能放赈粥给我们吃,去年,连他家的大姑,都差一点饿死了。
不管政治,单从艺术上讲,《想起往日苦》这个节目是最成功的,其他像《十爱》和《十恨》效果都在二三位上。陶一碗和细姑在稻场中间的人圈里手挽着手,穿着要讨饭的破衣服,做出一副歪歪倒倒的样子,边说边唱,在别人那里只有感动,在他们自己心里却是震动。
那年冬天,细姑半遮半掩地在村子前面的水塘里,给陶一碗洗了几次衣服。人们正式发现他们之间的恋情,是细姑给陶一碗洗被子。陶一碗的被面是枣红色印花丝绸,大姑家以前曾有几床,土改时都被穷人分走了,穷人又将它作为女儿的陪嫁之物,流落到外面村里去了。
陶一碗来时,村里已经没有丝绸被面了。
属于陶一碗的唯一的丝绸被面,自然成了女人们议论的主要话题。
三姑就曾公开说过,她太想在那丝绸被子里面睡一觉。
细姑将陶一碗的被子往水塘里一摆,满塘水就红艳起来。
细姑还未将被子完全泡湿,三姑就将情况告诉了大姑。
大姑当时叹气说,她早就料到这出假戏,会演成真的。
一九六二年,从前的蒋总统在台湾岛上大喊大叫,要反攻大陆。夏天到来时,陶一碗同细姑坐在一块青石板上。二人之间,相距只有一尺远,手也没有拉在一起。那道缝隙可以完整地看清月光下的倒挂金钩山。
就这样,他们第一次谈到一起过日子的话题。
事隔不久,在天气炎热,让人坐卧不宁的一个正午,细姑一边用扇子给大姑和自己扇风,一边将自己打算同陶一碗结婚的事告诉了大姑。
大姑半天不语,然后一个人戴上草帽,拿上粪勺,用水兑了一桶很稀的粪水,到菜园里去给苋菜发汗。下午,她没有同细姑一起薅秧,另外让生产队长派了一份活,独自到坡地上去给红薯锄草。在那种思绪万千的时刻,大姑也没忘记偷偷刨出两只还未长成形的小红薯,揣进怀里。天黑收工回家后,将其切成小块,熬出一锅清香的红薯粥。但饭桌上只听见喝粥的哗啦声和辣椒刺激出的咝咝声。
大姑吃过饭,洗完澡,又独自在村边走来走去。
稻场上的儿歌都停歇了,男人们的鼾声此起彼伏。
忽然,有人轻声叫大姑,声音很熟悉。
大姑在月光下细看一阵,才认出是“小拐子”。
大姑将“小拐子”领到三姑的屋里。“小拐子”在说正事之前,先将三姑打量了好几遍。三姑也在看“小拐子”。虽然大姑说三姑不是外人,“小拐子”还是让三姑到外面,暂时回避一下,确信三姑什么也听不见,才小声地告诉大姑,细姑爷可能没死,先前死的那个可能是个替身,有人传信来说,细姑爷在台湾那边当上司令官了,马上就要坐美国人的飞机,带上一万兵马从天上跳伞下来,就像当年共产党的刘邓大军一样,也搞个心窝开花。“小拐子”说,这叫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拐子”正忙着联络从前的兄弟做内应。
大姑问他消息确不确切。
“小拐子”说,没见到亲笔信,但传话的人口气很恳切,不像是搞煽动。
“小拐子”走时,特意对在门口望风的三姑说,等几天,我会再来的。
大姑的行为不是平常人逻辑所能判断得准的。
在那之后,在外乘凉的大姑,没有在下半夜露水下来时回屋里去睡。细姑和别的女人都回屋里了,稻场上就剩下大姑和男人们。
大姑需要凉风和露水帮助自己保持清醒。
天亮后,大姑告诉细姑,与陶一碗的事,自己看着办。
细姑高兴地说,她已经想好了,等年底队里分红后就办喜事。
大姑对这一点有异议,她说,其实早一点也没什么不好,早点到一起,大家心里都踏实。
大姑没有将细姑爷可能没死,可能随军队打回来的消息告诉细姑。只是在事情发生变化,她又不同意细姑再婚时,才随口说,细姑爷说不定没死,说不定哪天回来了,细姑若同陶一碗结婚,到时候就麻烦了。
三姑曾同细姑这样开了个荤玩笑,她说,细姑的婚事没办成,所以蒋光头无法攻占大陆。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随着“小拐子”被捕,蒋介石反攻大陆之事在金沟大垸一带就成了泡影。“小拐子”供认,那些相关故事都是他捕风捉影编造的,包括细姑爷要回来的说法。他知道蒋介石没这个本事,他只是想从那些家里有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又不知道音讯的人那里骗点钱财,改善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直到前些时,“小拐子”才说了实话,他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消息,真想细姑爷能活着回来,才主动做些荒唐事的。
这时,大姑也变了卦,她说自己想了快半年,还是觉得细姑应该守节到底。细姑爷要回和回不了都是一种假定假设。假定要回,大姑同意细姑再婚;假定回不了,大姑又不同意细姑再嫁。大姑如此反复,实在有违人之常情。
细姑此时心旌已动,情怀满是春意。
她打定主意非要下堂,再结一次婚,再嫁一个男人。
那天,陶一碗正按照队长的安排,在墙上写“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三姑忽然跑过来,说大姑牵了一只羊往家里走,情况可能不妙,要他快去看看。陶一碗听说过羊的故事,却不太相信,以为这是山里众多迷信传说的一种。他坚持将那条值五个工分的标语写完。陶一碗刚走到大姑家门口,就听见细姑在里面惨叫,一声声地说她怕羊,快将羊牵走。陶一碗一直在那门槛前等待细姑叫他的名字,只要细姑一叫,他就会冲进去。
这是陶一碗解释自己当年没有跨过那门槛的堂皇理由。
他说,细姑又没喊他,他有什么理由进去哩!
我曾经反驳说,我们家从没有明确规定过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才可以进去;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不可以进去。我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陶一碗的灵魂深处也还存在着畏惧。
陶一碗自己也承认,如果当时他硬着头皮一下子冲进去,从大姑手中接管细姑,我们这个家庭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就连我能否生长到如今,也是无法猜想的。
在那边门槛前,陶一碗等了好久,终于听见细姑哀哀地说,姐,饶了我吧,我和你一起守节就是了。
寒冬时节,又有消息传来,细姑的父亲逃到广西,改名换姓后当上生产大队长,他像“小拐子”一样,为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而露了马脚。“小拐子”只判了二十年徒刑,他却被判了死刑。又有消息说,细姑的母亲在过湘江时被土匪抢走了,生死不明。多年后真正准确的消息将传闻否定了。可在当时,那传闻都快将细姑压趴下了。
像是冷水浇头,细姑身上的爱情之火一下子就灭了。然后就将日子过成现在这个样子。每年的一个固定日子,陶一碗就拿出一只又旧又破的白搪瓷杯,放上一把米,将水添满,寻来三块旧砖或石头,用枯枝败叶烧起来。煮上半个时辰,又独自掇下来,用汤匙舀起水一样的粥,细细品味。
与一九六〇年不同的只有这最后一点。
一九六〇年,陶一碗是大口大口地吞咽。
大姑干涉细姑的婚姻,后来受到李小林的批评。
李小林带信给她,包括她自己在内,谁都可以做到婚姻自主,恋爱自由。
大姑让带信的人也给李小林带句话。她说包括李小林在内,没有人能真正自主自由。她又说只有王八蛋的男人要女人自主自由,也只有王八蛋的男人才在女人身上自主自由。 往事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