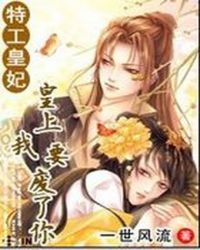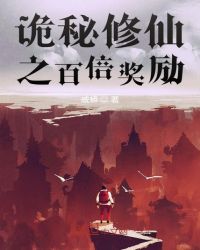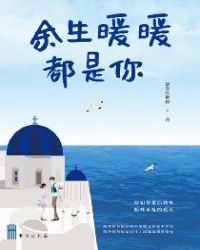§耦合之妙
在自然界占优势的是杂交,是粗纤维。
物理学上叫“耦合”。两个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乃至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人类世界的法则是不断分裂,不断重新组合。分分合合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到一对男女,一对相声演员,一个运动员和他的教练,突然间分道扬镳了。熟悉他们喜欢他们的人还在惊讶惋惜之中,他们又找到了新的搭档。
文人的离合就没有这般轻巧。因为创作是艰难的,联手创作就更不容易。我曾见过一对亲亲爱爱的夫妻,要合写一部书,经常吵得天昏地暗,严重的时候可以僵持一个星期谁也不搭理谁。有的合作一两次,不等交恶便明智地分手。也有的因署名或稿酬分配等问题发生龉龃,甚至对簿公堂,不欢而散。所以文学界盛传“创作是个体劳动”。合作的不多,能够长期而成功的合作,更是凤毛麟角。
他们似乎是这“凤毛麟角”里的一对。
因是好朋友而合作,因合作而更是好朋友。他们从起步就合作,这合作打出了风格,打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两人都得益于这合作。到目前为止,这十年合作本身就是一桩佳话。
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写这篇短序想起到“结婚证书”的作用,认为他们的合作只能“白头到老”,否则就不是“佳话”了。恰恰相反,我倒认为他们今后可以继续合作,也可以“放单飞”。“从心所欲不逾矩。”不要让合作成为一种不自然的拘束,成了一种非尽不可的义务,非负不可的责任,那今后便成了负担,反会束缚创作。
这本书印证了合作的最佳境界:自然和神秘。
他们是自然走到一起来的,不求而遇,非合不可。一个是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参军,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报社当记者;一个是七十年代初被上山下乡的大潮冲到内蒙古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都被鄂尔多斯高原深深地吸引,在痛苦不幸的现实面前怀上了文学的种子,同时认识到自己又是非常幸运的、意外地“得到了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一个开掘不尽的文学富矿”。他们感到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便联手开矿。开掘见宝,于是一发而不可收。
两个从里到外完全不同的人,合作进行精神生产,这个产生成果的过程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作品有风格,这风格不是张少敏的,也不是肖亦农的,更不是两个人简单的综合。而是经历了一个神秘的精神化合反应。
这反应产生新的生命,这生命独立存在。它躲开了浮华的世界,但没有从难以理解的复杂的乃至荒诞的现实生活面前逃跑。不追逐新浪潮,也没有被新浪潮丢下。充满自信地扑向鄂尔多斯高原,这是真情地一扑,全身心地投入。渐渐从高原上站起来,并不断升高和扩展自己的视点。色彩强烈,感情饱满,这生命带着动荡时期的明显印记,是鄂尔多斯的儿子,又有一颗属于中国人的灵魂,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基本上是汉人的文化心态和鄂尔多斯高原结合的产物。有的甚至可以说是蒙人其表,汉人其里。在它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当代人的精神苦痛、历史和现实的重负,有地域性,也有普遍性。
这构成了两位合作者的明显特色,不同于地道的蒙族作家,也不同于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其他汉族作家。
张少敏和肖亦农的合作得益于对鄂尔多斯人情风貌的共同迷恋。不是靠聪明,写点子,而是真杀实砍地写生活,写人物,写故事。每篇作品都很好读,人物和故事亲切感人。也许他们太喜欢鄂尔多斯的传奇色彩了,往往被故事所局限。而能令人深长思之的又常常是超越故事本身的东西。正像对现实生活有足够的忠诚和责任感是强大的优势,倘若太拘泥于现实,又会失去深刻的警喻力量。张、肖二人的合作如此流畅,几近天衣无缝,跟他们全身心投入合作、依靠合作有关。因合作而成功,与每个人获得成功之后再合作可能有所不同。
合作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要求合作者视合作为自己的创作生命。
我在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常常忘记作者是两个人,甚至会生出疑问:一部完整的作品怎会出自两个人之手?出于对成功合作的好奇和有感于真诚合作的魅力,写了以上这些与书的内容不甚搭界的话,再要议论书的内容反成多余,只好就此打住。
1993年5月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