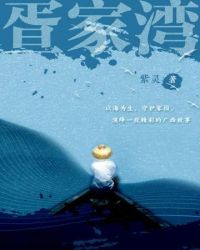孤立的美景
—— 《穿过漆黑·穿过钢铁》 注 《穿过漆黑·穿过钢铁》,黑沨所著诗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 附录书评
了解一位诗人的世俗人生无益于我们享受其诗歌,因为对比的恶习将使我们有限的感知力大打折扣,从而慢待诗歌本身所呈示的美。“诗如其人”令人悲悯,“诗歌即人生”几乎是对诗歌的无情鄙视。遗憾的是,对某位诗人的了解和对万物的了解一样,很多时候并非出自我们的本意。但我们应该庆幸,在少数不由自主的既成事实边上,我们尚有选择缄默的自由。当我们面对一种美景,比如诗歌的美景,我们尚能克制某些饶舌的冲动。那么,我们在欣赏、谈论诗人黑沨的作品时,或许可以信任博尔赫斯发明的“多事的是另一个人”这个不无狡猾的二分法—— “另一个人”当然包括了另一个黑沨。基于上述理由,这篇短文将对她的人生佯作无知。
1986年或1987年,我在一本油印诗刊上第一次读到黑沨的几首诗,印象深刻的一首名叫《某夜铁铃关》。铁铃关是苏州郊区一个著名的地点,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一个可供遐想的地点,因为我从未到过那里,而闻其名却已长达十几年,最重要的是,这个包含三个汉字的地名本身具有某种横亘时间的散漫诱惑。诗中的某些诗句部分地印证了我的遐想:
铁铃关有百年前鹧鸪的影子
啼我的陈泪
作孤灯
这些显然包含了回忆和神游的诗句,有一种专横的抒情魅力,正好对应我对铁铃关历史和现状的一无所知(同样也对应了当时我对诗人黑沨的一无所知)。神游的诗句,感怀自伤的诗句,那时我已经读过不少,但在几行诗中如此迷离地将两者糅合一处,对我来说的确不无新奇。我想,这位诗人高人一筹,把不少成名诗人都比下去了。不过在黑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作的诗歌中,这一首虽然令我印象深刻,却还不是我认为十分出色的。真正令当时的我吃惊并钦佩的,是以下这些篇章:《那夜》、《有乌鸦和麦田的风景》(可能出于世俗的、私人的原因,诗人并未将此诗收入这本诗集)、《〈W的悲剧〉最后画面的联想》 、《古莲之死》。这份小目录,是我诗歌记忆中十分牢固的部分。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起二十年前第一次读到它们的感受。第一首,旁若无人的情诗,其一气贯通的强烈语调和妙喻偶得的抒情幻觉构成了难以抗拒的专制的风情,或许正是它开创了黑沨诗歌风格中的一种:向死而生的坚定的迷醉。第二首,魅惑的挽留。死亡的台阶蓦然出现在黄昏的低沉色调中,某些异样的美景攀缘而上,直达喃喃自语的绝望的享乐。此诗虽是情诗,却已闪现了命运的严肃身影。第三首,人生舞台角色的悲怆美化。诗题中的日本电影当年曾给许多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但黑沨的“观后感”将自我角色投身其中,把爱情的绝望当作美化悲剧角色的起点,在美的意义上逆转了“人生如戏”的悲观结论。然后,对于这份小目录上的最后一首,《古莲之死》,我愿代表二十年前的我,表达加倍的赞赏。二十年前的中国诗歌虽已不乏优秀之作,但在一首短诗中能够情思贯通地综合多种感受的作品,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似乎十无其一。也许我可以稍稍夸张地说,这是一首绝对惊艳的诗,它在那个草创的热情年代十分罕见地将我性、人性、时代性,批判、嘲讽、情欲,一并纳入某种冷燃的大胆情怀,此情怀之丰富绚丽,在我看来已接近那个时代的读者所能看到的最动人的诗歌美景。至于此诗运用语汇的泼辣和不羁,我想已不值一提。
但是,我不得不说,二十年前我对黑沨诗歌的阅读是十分有限的。二十年前,她还写出了比上述诸篇更为优异的诗,其中至少有一首,我直到几天前才刚刚读到。我愿将这首诗全文抄录于此,以表示我个人对它的敬意:
损失
矿泉水,安眠药,落月也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风很大,他们在电话亭不停地拨号
我还目睹了别的,譬如,酒,在中国
又通常是药;你肯定是我的药。
香水名片是虚拟的人是虚拟的,城市:道具。
譬如畅销书、口香糖,譬如三毛。
像祥林嫂不止在鲁镇的妇道人中抹着泪说
“苦啊……”她还说虚无。
戈多肯定虚无他们边说边抱紧乡间一条路
一棵树。
黄昏。
他们站着不动。现在:不停拨号。
再譬如,这本摄影挂历上狗类幸福发光
我通常在繁华地带遇见它们
如果说有时也在水一方
更十足是有闲阶级的好姿态了——
我这样不出声地端详越来越满的酒杯
我在祈望
我越来越红的发带要导致一场真正的火灾
火光迟迟不来,这是今晚无可挽回的损失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深圳的秋天
却这样来了。
我摔开今晚所有的杯子
祈求满天的落叶将我覆盖——
1987年11月20日 深圳
这首诗的饱满、从容令我在二十年后再次感到吃惊。我一直认为黑沨是一位性情诗人,她的诗歌虽不乏佳作,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剑走偏锋,并不具备主动均衡的诗歌全局观,即使是像《古莲之死》那样容纳了多种感受元素的作品,在语调、节奏和意象诸方面,也颇多即兴,略无精到的节制。但《损失》一诗成熟的形式感,节奏、语词、情感(包括对自我的和对时代的)等各个诗歌要素的全面均衡和克制,呈现出只有真正具有远大诗歌抱负,并且拥有丰富写作经验的职业诗人才可能具备的一流的诗歌综合素养。这首诗让我感到,尽管多年来我一直欣赏黑沨的诗歌,但我还是低估了她的诗歌潜力。我不清楚她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她愿意,她完全能够站到中国诗歌的最前列。
据我所知,黑沨的诗歌写作连续性不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或许是她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个写作阶段,她的名篇和大部分重要作品(这两者之间永远不可能画等号)都出自那个时期。从这部诗集收录的作品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至2007年之间,黑沨的诗歌写作有着长达十几年的停顿。我猜想她自己可能更看重九十年代的作品——对她来说,那些作品更贴近她的个人情感,写得更为恣肆、透彻、过瘾。相比之下, 八十年代的作品除个别篇章外,大部分颇受唯美倾向的制约;2007年的作品则似乎因为打上了更多时代和个人的隐秘烙印,而显出某种欲言又止的策略性拘谨。制约和拘谨,我猜想都有悖于黑沨天马行空的天性。然而从另一方面考虑,我如此猜想也许是错误的:很少有诗人愿意让旧作而不是近作占据个人成就的中心地位,事实上对许多诗人(我也在其中)来说,旧作的一再被提及几乎等同于对诗歌活力最严厉的批评或最无知的误读。我无法确定黑沨是否也在其列。但我幸好能够确定,在当代中国诗人中,她的诗歌才华、诗歌立场、诗歌状态、诗歌骄傲之间颃颉变化所造就的诗歌事实,乃是令人迷惑而又魅力十足的独特景象。
夏多勃里昂说:“所有的装饰都过时了,只有美这种严肃的装饰留下来。”这个夸饰的说辞在很多方面站不住脚,唯独与某些孤立的美景十分契合。我用它来结束这篇菲薄的短文,是因为我看到,黑沨的诗歌正是这个时代少数孤立美景中甚为隐蔽动人的一种。
2009年8月9日 远望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