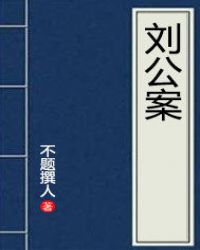且看史称“刚毅”的吕后如何“以吕代刘”
“欲王诸吕”的三部曲
惠帝丧礼既毕,葬于长安城外东北隅,号安陵。
继惠帝而立的便是那个用“移花接木”的办法制造出来的张皇后之子,此时才一两岁,史称少帝。还在哑哑学语的少帝自然不可能处理政事,实际执政的只能是吕后。于是中国历史便翻开了此前从未有过的一页:一个女性成了国家最高统治者。
高后元年为公元前187年。
与历史上大多数继体守文之君即位之初大都要显示一番喜庆吉祥、皇恩普施一样,据《汉书·高后纪》记载,吕后临朝称制后,也接连颁发了这样几道诏令:
一、大赦天下。
二、赐民爵,户一级——汉沿秦制,实行从“公士”到“彻侯”的二十级爵制。如原是“公士”,进一级便是“上造”。
三、除三族罪、妖言令——三族罪,亦称夷三族、罪三族,即一人犯罪,戮及父、母、妻三族的酷刑。韩信、彭越,都被夷灭三族。妖言,指怪诞或诳惑人心之言论。妖言令,实即凡发表不利于帝王制度的言论即被视为有罪的一种律令。惠帝生前曾说过要废除三族罪、妖言令,但议而未决;吕后称制正式宣布废除。
但这是幕前,是做给别人看的。在幕后,刚刚登上极位的吕后却深深陷入了孤单和寂寞。
这种孤单和寂寞同样源于她是一个女性。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社会自从由母权制转为父权制后,女性把失败的痛苦深深埋入心底,承认男性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已渐渐积淀为她们的一种潜意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直接间接地企图反抗男性的统治也渐渐积淀为一种潜意识。譬如她们对出嫁于夫家,内心很难接受这只是转换了一个新家,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被猎获或征服的感觉。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的甚至终其一生,都认为只有娘家才是她的家。基于同样原因,她们往往会把娘家的侄儿辈看得比自己子女还亲。不妨说,这是男性征服女性后遗留给社会的一种病态心理。
如今的皇太后吕雉,就经受着这样一种病态心理的折磨。
每次临朝,她面对的是一个由清一色男性占据的未央宫正殿。依班位肃立在她面前的,除了刘姓诸侯王,就是那些非刘姓的功臣宿将。难得能看到一两个吕姓的,她就会油然升起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和可以信赖的安全感,可惜现在却还只有很少几个。因而她在强作一脸庄重、接受百官跪拜和山呼的同时,却常常无法遏制从心底生出的恐惧。为了坐稳朝堂上这个正位,她觉得最先要做的事,就是提升吕氏家族的地位,向非刘氏不得为王的“白马盟誓”发起挑战,封诸吕为王。
但她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而坚实的刘氏堡垒,进击的每一步都必须十分谨慎小心才是。
她先作了个试探:把“可否封诸吕为王”作为一个议题,交付廷议。
果然有人站出来反对了,他就是右丞相王陵。
王陵此时该已是六十开外。高帝临终在与吕后谈话时对王陵有过一个评价,说他“少戆”。这一“戆”字,简明扼要地点出了王陵的性格特征。戆,不妨解释为耿直而至近乎愚。王陵一生行事都带点戆相。他与刘邦在沛县时就相识,刘邦还曾像尊敬兄长那样尊敬过他。刘邦率兵入关,他也聚党数千人,却要到刘邦还定三秦后才勉强归属于汉。刘邦把曾经一度背叛过他的雍齿视为仇敌,王陵却一如既往地与雍齿结为好友。就因了这些缘故,王陵迟迟不得获封,至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才被封为安国侯。这回吕后想要封诸吕为王,他的戆劲又发作了,大声说道:此议断断不可!高祖皇帝曾与臣等刑白马而盟,誓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此誓书如今尚藏于宗庙,锁于金柜石室。倘若封诸吕为王,那便是背盟弃誓,定然招来天人共怒!
吕后听了自然十分恼怒,却也不便发作,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一向善于观察,且曲伸自如,这时便说道:既然高祖皇帝平定天下,曾封子弟为王,如今皇太后临朝称制,分封吕氏子弟为王,当也无所不可!听陈平这一说,太尉周勃等大臣也随之跟上,戆老头王陵就显得十分孤立了。吕后转怒为喜,雍容大度地说道:此事有关大体,今日也只是提出来一议而已,议而不决可也。就此退朝吧!
群臣依次退出,走在未央宫的殿阶上。王陵紧赶几步追上陈平、周勃,怒气冲冲说道:请问二位,何谓“封王诸吕,无所不可”?若诸吕为王,置刘氏江山于何地?当年高祖皇帝与诸臣歃血为盟,二位也在其列,如今口血未干,言犹在耳,因何就将盟约抛至九霄云外?二位此等阿意背约行为,日后还有何面目见高祖皇帝于泉下!
对这一连串劈头盖脑的责问,陈平倒也并不生气,顾自微笑着说道:请公息怒。今日面折廷争,仆诚不如公;他日安汉室社稷,定刘氏天下,只怕公还不如仆呢!
陈平的这番话,意在说明他的附和吕后正是为了一旦时机成熟就定计安刘,不是阿顺,而是一种策略。后人对此多有诟病。譬如清代的龙启瑞在《陈平周勃论》一文中,以极普通的救火为例诘问说:连里巷的人都知道应当一看到哪里起火就去救,不能等到自己房子烧着了才开始救,因何“以平、勃之贤,处可预防之势,而其计乃出于救火者之下”呢?作者接着指出:平、勃阿顺吕后是“自知不义而惧为大臣所责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坚持高帝之约,吕氏虽横,安能重违大臣而恣行己意”(见《古文辞类纂》)。
论人品,王陵和陈平,当有正直、坚持与机巧、善变之分;若论二人的政治主张,在当时自然也是泾渭分明。但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似乎没有必要再像古人那样把视刘汉为“正统”的观念奉为天经地义,把“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种在家天下思想支配下的霸道盟约当作金科玉律。问题不在封王的人是姓刘还是姓吕,而在封王后他们做了些什么。不过我们还是赶快回过头来看看吕后的应对吧!
经过廷议试探吕后现在已经知道“欲王诸吕”的障碍所在了。几天后,她发出一道制敕,授任王陵为少帝太傅。太傅与太师、太保并称“三公”,名崇位尊,但无具体职掌,是张空椅子。所以吕后的这一授任形为迁升,实是剥夺了王陵的相权,叫他靠边站。王陵自然也看出了吕后用心,索性上书托病求免,从此杜门闭户,不再朝请,几年后默默死去。
王陵免相后,吕后就授任陈平为右丞相,并擢升审食其为左丞相。审食其本是舍人,自然不具备做辅相才资,仍是监管宫中诸事,其职司犹如郎中令。但因吕后对他宠眷日隆,廷臣奏事往往由他取决,因而其显赫的气势,更远胜于惠帝在时。
不过到此为止,吕后还只是走了她计划中的第一步。
她很清楚,多数大臣在廷议时对她“欲王诸吕”的认同其实是很勉强的;白马盟誓依然是一个强势的存在;文武百官都还享受着刘汉俸禄: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分封诸吕,将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因而第二步她采取的是迂回战术:活着的暂时还不能封,就先封死了的——
吕后之父吕公,刘邦为汉王时已封为临泗侯,此时追尊为吕宣王;
吕后长兄吕泽,高帝时已封为周吕侯,此时追尊为悼武王。
几天后,看看没有因此引起多大的波澜,就又接连封了六人。这回封的全是惠帝名下的儿子,当然他们同样都是吕后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制造出来的。这六人是:
刘强,封为淮阳王;
刘不疑,封为恒山王;
刘山,封为襄城侯;
刘朝,封为轵侯;
刘武,封为壶关侯;
刘太,封为平昌侯。
这期间恰好鲁元公主病故了,于是又封其子张偃为鲁王,并尊鲁元公主为鲁元太后。
与此同时,又使出“刘吕联姻”一法,将吕氏诸女嫁与刘氏。如赵王刘友、梁王刘恢、营陵侯刘泽、朱虚侯刘章等,他们的正妻皆为吕氏女子。这样做,表面上可给人一种刘吕亲和的印象,暗地里则藉以起到监视和提供情报的作用。
现在吕后就要走计划中的第三步了。她依然小心翼翼,把一步分作几小步走:先封她的一个侄子吕台为王。
就是这一小步,也不想自己先迈脚。而是希望大臣们能揣摩到她的意图,提出奏请,然后由她来点头认可。
她在等待着。
令人惊奇的是,最先揣摩到吕后意图的,既不是她身边的侍从,也不是朝堂上那班大臣,而是一个与宫廷权力角逐完全无关的局外人,他叫田子春。
田子春是齐人,喜好游历,几年前来到京师长安,那时他就看出,具有强烈权力欲望却又势单力薄的吕后,定然会将她的母家人一个个置于要位,成为她的左臂右膀。他觉得这倒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充分施展聪明才智并从中获利的大好机会。他找到了一个目标,用他的智慧和机巧,导演了一场不妨名之为“权力交易”的游戏。
田子春找到的目标叫刘泽。此人原是刘邦的从祖兄弟,当时已可算是刘氏宗族中的老长辈,却还只封了个营陵侯,眼看着小辈们已一个个先后封王,做梦都在想着有朝一日王冠也能落到自己头上来。田子春摸准了刘泽的心思,找上门去说,我有妙策确保你不久便可封王。一番巧舌如簧,说得刘泽心花怒放,当即赠金二百斤,托他代为钻营。不料田子春得了厚赠,满载归齐,竟不再复返。刘泽一怒之下,声言与之绝交。原来田子春回到齐地,只顾忙于买田置产,经商发财,竟忘了为刘泽谋划封王之事。受到责备,大为愧疚,立即带着他的儿子再次来到长安。他没有去见刘泽,而是租赁了一座大宅第先住下,然后让他的儿子去结交受到吕后宠幸的那个大谒者张泽,以金银和谦恭去换得对方欢心。待到儿子与张泽已成深交,田子春方始亲自出面,将他请来宅第,大设供张,盛宴款待。张泽见田宅富丽如同王侯,大为吃惊。酒过三巡,田子春屏退仆婢,从容对张泽说道:仆来京师,所见王侯府邸,鳞次栉比,皆为高皇帝功臣。未知足下是否也有意封侯封王,入主华堂高阁,尽享人世荣华?
张泽道:先生取笑了。想我一个内侍,位卑禄薄,何来如此美事?
田子春说:在仆看来,如此美事足下唾手可得。足下久侍太后,应知太后心思。想当年,太后母家吕氏也曾鼎力佐助高皇帝得天下,其功至大,其亲至重,只是至今尚未沐受隆恩。如今太后春秋已高,意欲多封母家子侄,又恐大臣不服,故至今尚犹豫中。足下若能将太后心意婉转讽喻诸大臣,由诸大臣奏请立吕台等为王,太后必然深感足下,何愁无缘封侯万户!但足下若明知太后心意而不为之奔走,只恐祸且及身,难逃一劫!
张泽慌忙离席一揖说道:多承指教!事若有成,必以厚礼酬报。
几天后,吕后升殿而朝,问群臣有何奏请,几个大臣联名请立吕后长兄吕泽之子、原为郦侯的吕台为王。吕后大喜,准之,立吕台为吕王,时间是在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四月。这是高帝与群臣刑白马而誓“非刘氏不王”后出现的第一个活着的异姓王,吕后把它看作是实现“以吕代刘”计划的第一次胜利。后来知道大臣的奏请是张泽暗中四处游说的结果,便对张泽大为嘉勉,并赐金一千斤。一夜之间获得了大富大贵的张泽,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分出五百斤金来酬谢他的教导者。但田子春却坚辞不受。原来对田子春来说,这只是他计谋中的一个前奏,接下去才进入他的本题:使刘泽受封为王。稍有意外的是中间出了个小插曲。吕台封王不过几个月,突然因病去世,依制由其子吕嘉嗣封。谁知吕嘉是个花花公子,当上吕王后,骄奢淫逸,恣意妄为,吕后大为失望,决意废去吕嘉,另由吕台之弟吕产嗣吕王之位。但她仍然不想自己先开口。于是乖巧的张泽来了个故伎重演,私下劝说大臣们进奏,这样吕产很快成了吕后称制后出现的第三个异姓王。吕后为奖赏张泽这个吹鼓手,特地封他为建陵侯。田子春的预言应验了:宦官出身的张泽终于跻入了王侯之列。此时张泽对田子春自然更是感佩不已,言听计从,任由摆布。田子春觉得实现计划第二步的条件已经成熟,便伺机说道:诸吕为王,足下为侯,固然可喜可贺;但据仆新近探知,高皇帝诸功臣内心不服,私议纷纭。古人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足下须设法预为调定才好。张泽听了不由一惊,当即请教调定之法。这样田子春便因势利导地推出了让刘泽受封为王的本题。他说:要平息大臣私议,唯有一法:封刘氏为王;但多封刘氏,又为太后所忌;为两全计,莫若从刘氏中择一年长者封之,当可保吕氏与足下无虞。今有营陵侯刘泽,为高皇帝从祖兄弟,如今已是刘氏宗室中长老,应是最合适的封王人选。足下不妨趁时向太后进此“封刘安吕”之策,计若成,则足下便可永享富贵。
吕后出于安吕考虑,果然听从了张泽的建议,从齐国辖地中分割出一个琅邪郡来,封刘泽为琅邪王。
到这时候,田子春才去登门拜谒刘泽,奉礼道贺。刘泽已知自己能够受封全是田子春之功,自然前嫌顿消,盛筵款待。但田子春却一再催促撤席。刘泽不禁大疑,问是何故。田子春道:大王很快就会知道,这会儿无暇细说。请速速整装登程,即赴琅邪就国,切切不可延留,仆当随大王同行!
田子春是估计到吕后可能反悔,才教刘泽赶快离开长安的。后来吕后果然忽而省悟:我既然要以吕代刘,怎可再封刘氏为王呢?当即派人追赶。但此时刘泽一行人已出关东去,吕后只好悻悻而罢。
偏在这时候,后宫内侍匆匆赶来禀报一个惊人的消息。吕后在一阵暴怒过后,决心加速推进“以吕代刘”计划的实施了!
前后两个少帝和三位赵王
原来内侍禀报的是这样一句话:皇帝有反状!
我们现代人实在无法想象,一个还穿着开裆裤的孩子,却戴着一顶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冠,会是怎样一副滑稽模样!
在孩子自己,大概觉得很好玩。因为那顶模样怪怪的帽子,有十二串亮晶晶的珠子,它们在你眼前摇晃起来的时候,就像满天星星。
这个孩子如果永远处于这种朦胧的童真状态,那该是多么幸福啊!偏是时间老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对这个被称为少帝的孩子也一样依据岁月的推移,给了他相应的认知周围世界的能力。于是他也逐渐懂得了“母亲”、“真母亲”、“假母亲”以及“人被杀就会死”这样一些概念和事理。当他终于知道人都是母亲生的,他也曾经有过一个生他的真母亲,可是早被人杀死了;现在这个当上了皇后的母亲是个假母亲的时候,童年的幸福立刻离他而去,留下的只有痛苦、伤心,还有一种很陌生的情绪:仇恨!
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少帝可能已有六七岁。一次他在后宫对前后左右侍奉着他的那一大帮子人说:皇太后怎么可以杀死我母亲,又让一个陌生女人认我做儿子呢?等我长大了,一定要为母亲报仇!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不知道说这样的话将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当日黄昏,少帝被人送到一个后宫下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的地方:永巷。
尽管少帝只是吕后手中的一个玩偶,但当这个玩偶内心已对她萌发了仇恨的种子,她也决不会容许他继续存在!
吕后发了这样一道诏书:
凡有天下治万民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乱,不能继嗣奉宗庙,守祭祀,不可属天下。其议代之。(《汉书·高后纪》)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小皇帝不管用了,要换一个。
此时王陵已免职多年,朝堂上再也没有一个骨鲠之臣。大臣们内心虽多有不平,却谁也不肯站出来做第二个王陵。于是右丞相陈平、左丞相审食其等联名上书道:皇太后为天下黎民计,废暗立明,以安宗庙社稷,臣等皆愿敬遵诏制,竭忠尽命。
大臣们都知道,皇太后诏制中的“其议代之”,自然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无非是要大臣们去揣摩她早已属意的人选,然后由他们以奏请的方式提出来而已。经过一番幕后活动,陈平等终于摸准了吕后的心思,奏请立刘义为新君。吕后认可后,即布告天下。这刘义原名刘山,是吕后用“移花接木”方法制造出来的惠帝诸子之一,原封为襄城侯,后因恒山王刘不疑死,又继而封为恒山王;立为新君后,再次改名为刘弘。刘弘也还是个孩子,为着区别,史家称原来的少帝为前少帝,此少帝为后少帝。吕后继续临朝称制,也不改元,仍以高后为纪年。这一年是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
被幽禁在永巷暗室的前少帝,不久便夭折而亡。
接下去,吕后准备再封她的另外几个侄子为王,不料这时从邯郸匆匆赶来一个女子,一番哭哭啼啼的声诉,中断了她的这一计划。
这个女子原是吕后母家人,为执行吕后“刘吕联姻”之策,嫁给高帝之子赵王刘友。高帝在世时,刘友为淮阳王,赵王是刘如意;后来吕后鸩杀如意,徙刘友为赵王。刘友与吕氏女的结合,完全是出于权力角逐需要的拉郎配。刘友对这个已被立为王后的女子怎么也爱不起来,而对后宫中的一个姬妾却偏是卿卿我我,缠绵不已。吕氏女不远千里从邯郸赶到长安来,本意只是为了诉诉感情上受到的这种委屈,恳求皇太后动用一下至高无上的权威,让本该属于她的男人回到她的枕边来。但说着、说着却说出了这样的话:皇太后你不知道,赵王还说了很难听的话呢!他说:皇太后怎么可以立诸吕为王呢?当年高祖皇帝有过誓约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等到皇太后一归天,我就非把那些封了王的诸吕一个个全都击杀不可!
吕后听了不由一怔,却不作理论,只是冷冷说道:你且回自己家去歇息吧,我自有主张。
当日即发出急诏,将赵王刘友召回长安。各封王在长安均有官邸,以供来京朝觐住宿之用。吕后命刘友就居于自己官邸,然后派禁卫军坚守,下令不得供给饮食。这么一两天下来,刘友饥饿难忍,痛苦不已;随行的王国官员动了恻隐之心,暗中送他点吃的,却被卫兵逮住,拘系下狱论罪。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刘友,作歌鸣冤,泣泪唱道:
诸吕用事兮,刘氏微;
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
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
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寤通“悟”)
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
自决中野兮,苍天与直。
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于通“吁”。自贼,自杀)
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
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汉书·高五王传》)
几天后,刘友在饥饿忧愤中死去。吕后下令以民礼葬之,也即废去了刘友的王侯身份。
刘友一死,便空出了一个封国的王位,吕后立刻想到用她的母家人来填补。这回她玩了个花样:先一道诏旨让已立为梁王的刘恢去当赵王,再改封她的侄子吕王产为梁王,并授以太傅之职;吕王则由惠帝名下那一大串儿子中一个平昌侯刘太充当。吕后如此安排真可谓煞费苦心:这样,吕产既可拥有梁王封号,又因任有太傅之职而不必就国,继续留在内廷成为她的帮手;同时,新立的小皇帝刘弘身边也有了训教管束的人,不至于再发生类似前少帝那样的事。
现在再来看看被改封为赵王的刘恢。
刘恢为高帝之子,梁王彭越灭族,高帝立刘恢为梁王。他对吕后的专权早已不满,这回吕后幽死他的兄弟赵王刘友,又强行徙封他为赵王,自然更为愤恨。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二月,刘恢在不断受到催逼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由梁都定陶出发,一路颠簸北上,劳顿半月有余才抵达赵都邯郸。刘恢的正妻也是吕后依据“刘吕联姻”之策硬性配置的吕产之女,连王国的主要官员也大多是吕氏安插的亲信,刘恢的一举一动全都逃脱不了密布于他四周的眼睛。来到这个漳水之畔素称繁华的都会,他却深深感到了孤单和寂寞。邯郸多美女,目挑心招,吸引四方来此交易的商贾,当年濮阳大贾吕不韦就是在这里遇上了后来成为秦始皇母亲的赵姬的。处在逆境中的刘恢,竟意外地也在这里结识了他的红颜知已。从此唯有与爱姬的幽会,才让他感受到了自己几近枯竭的生命还有着些许温馨与美好。后来他把爱姬接入王宫,吕氏王后居然表示可以接受,这更使他喜出望外。但他太天真了。不过三两天,当他再次进入爱姬帷房时,横躺在床上的已是一具七窍流血的女尸。刘恢悲愤交集,欲哭无泪,作歌四章,令乐工依谱歌之。就在这哀怨凄切的歌吟声中,他投缳自尽,永远离开了这个本不属于他的王国。
耐人寻味的是,对刘恢的死,吕后完全沿袭了传统的男性观点,说是为了一个女人而居然可以抛弃宗庙社稷,不仅不配当王,甚至也不配当男人。因而“废其嗣”,即剥夺了刘恢子孙继嗣赵王封号的资格。
吕后派出使节赴代国,让代王刘恒去当赵王。刘恒对使节的回答是:请公代为向陛下转致铭戴之意。臣情愿长留代地,永为朝廷守边。刘恒是刘邦与薄姬之子,他的婉拒,表现出他的智能和卓识。读者很快会看到,就是这个刘恒,不久由大臣们迎入京师,拥立为被后来史家称为明君的汉文帝。
也许吕后徙刘恒为赵王,原本就带有几分做给别人看的虚情,刘恒的婉拒恰好给了她一个理由,于是立她的次兄吕释之子吕禄为赵王,仍留官都中;同时追封吕释之为赵昭王。在这期间,从燕都蓟县传来了燕王刘建病故的消息,吕后又突然动了心机。刘建是刘邦之子,他是在燕王卢绾叛汉后被立为燕王的。刘建仅有一子,且为庶出。按照礼制,正妻无子,庶出之子也可承袭封号。吕后暗中派人刺杀了那个庶子,然后以刘建无后为由,绝其嗣,另立她的侄孙,即已故吕王吕台之子吕通为燕王。
至此,吕氏先后封有吕产、吕禄、吕通三人为王,六人为侯。其中吕产、吕禄一面遥领藩封,一面执掌南北军大权,威震宫廷,势倾内外。朝野人等莫不惕息惊心:不知刘汉宗室还能支撑多久?一旦“以吕代刘”这天下将会怎样?
这是帝王制度带给中国历史的一个奇特的时期。这样的奇特时期两千多年来屡见不鲜。在这个奇特的时期里,高端政局成了一盘失去规则的残棋,扑朔迷离,变幻莫测;成千成万局外人全都处于莫名的惊恐和不安中。所有这一切的终结,既不取决于民意,甚至也不决定于权力角逐双方的实力,而是要看躺在病榻上那个垂暮老人究竟还能活多久。
这回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位垂暮老人是女性。
此时吕后该已年届古稀。这个女人确如司马迁所称“为人刚毅”(《史记·吕太后本纪》)。她的刚毅既表现在称制十余年的政坛上,更表现在诛杀功臣、封王诸吕的权力擂台上。吕后对权力欲望之强烈可谓无以复加,甚至达到了无视“天罚”的地步。我国古代流行一种“天人感应”观念,以为人间帝王如果行为不正,上天就会显出种种异常的天象、地貌来,如日蚀、月蚀,地震、旱涝等等,以示警戒;若不及时改正,还将降下更严厉的惩罚。这种观点自然并不科学,但多少会对毫无监督的帝王权力产生些许制约效用。《汉书·五行志》载: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正月发生了一次日蚀,“高后恶之,曰:‘此为我也!’”但就在这一年,吕后幽死了赵王刘友,接着又逼死了继位的刘恢。这就是说吕后是在明知上天已经发出警告的情况下,依旧顽强地“顶风作案”的。撇开政治、道德评价,单就人性而言,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量啊!这个坚强的女人,就这样在代表吕氏家族向刘汉宗室夺取和扩展权力的斗争中耗尽了自己全部精力和心血。现在她已经精疲力竭,在恍恍惚惚中觉得无数鬼魅在近旁出没。这已是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看看三月上巳已到,民间习俗多在这一天到水边去祛除不祥。吕后不得不向鬼神表示妥协了,在上巳这一日亲临霸上,于渭水之滨举行称之为“祓”的祭祀仪式,目的自然是想驱逐身旁那些讨厌的鬼魅。祓毕回宫,途经那座名为轵道的古亭,忽见一物张大血嘴迎面扑来,吕后一声惊叫,只觉得腋下疼痛难忍,一面紧紧捂住腋下,一面大声喝令身旁侍卫:恶狗!恶狗!汝等快快与我击杀那条大恶狗呀!……
侍从赶紧过来扶持,卫士也纷纷拥来车驾周旁护卫。但他们谁也没有看到什么狗或任何凶猛的生物。吕后怒骂几声过后,环顾四周,也不见有狗的影踪,也只好忍痛下令起驾回宫。到未央宫解衣看时,腋下已是青红一片,越发惊恐狐疑。当即召来太史占卜。占卜的结果,使吕后很难相信,却又不敢不信。太史说:这是屈死的赵王如意在作祟!
吕后腋下之患经太医百般医治仍难以痊愈;又命人至如意墓前代为祷免,也未见有效。自知大限已近,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如何巩固吕氏家族已经占据的局面。于是下诏授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由吕禄和吕产分掌南北二军;又立下遗诏,任吕产为相国,以吕禄之女为后少帝皇后;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并大赦天下。然后把吕产、吕禄召到跟前,作了一番告诫和嘱咐。她说:
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史记》本纪)
这说明吕后直到临终时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预计到随着她的死大臣们将会生变,而且很可能是一场武装政变。因而一方面赐金给诸侯王和大臣以及文武百官,想以此稳定一下他们的情绪;另一方面暗中严命她的两个侄子要紧紧抓住刀把子,守住皇宫;要先发制人,切切不可为人所制!
同年七月,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制的女性逝世于未央宫。
吕后死后与高帝合葬于长陵,并得配食高庙。但汉人只称其为主,不承认她是皇帝。如《汉书·翼奉传》载录的一道奏书就有“八世九主”这样的话,其中未列入“世”单称主的,即指吕后。至东汉初,光武帝下旨,以为“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因而将其神主搬出高庙;另尊刘邦的一个小妾薄姬(详下节)为“高皇后,配食地祗”(《后汉书·光武帝纪》)。
吕后临终前的部署不可谓不周密,只是一个即使威风八面的帝王,一旦死去,那么他生前的所有嘱咐或安排,都将随着权力易主而很快变成一纸空文,随风飘去。接下去将要发生的,正是吕后病危时深为忧虑而想要设法防止的那血雨腥风的一幕。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