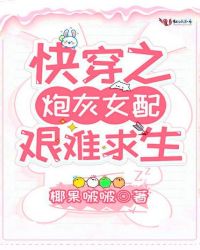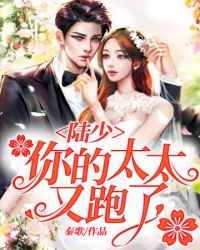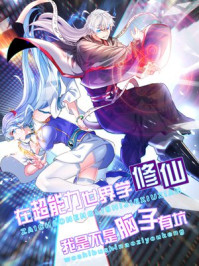从班彪评论看新末历史走向
班固的父亲班彪,在新末大动乱中,曾一度依附于在家乡天水成纪一带起兵反莽被众人推为上将军的隗嚣。当隗嚣问起眼前这场动乱与战国的七国纷争、秦末的群雄角逐有何区别、其结局又将会如何时,班彪作了这样回答——
周之废兴与汉异。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以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讴吟思汉,乡(通“向”)仰刘氏,已可知矣。(《汉书·叙传》)
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王莽“不根于民”。与周行帝王封建制、诸侯得以自治其国不同,汉行帝王集权制,郡县隶属于中央,其长官不得自行为治,也即引文中说的“臣无百年之柄”。而王莽的和平变革这种权力传递方式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朝廷变革了,郡县以至乡里,特别是臣民的心理,都还没有来得及作相应的变革,所以王莽只是“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
其二是群雄“咸称刘氏”。正是由于王莽的和平变革“不根于民”,所以当反莽之兵“远近俱发,假号云合”之时,各路英雄豪杰大多仍以恢复汉统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他们“不谋而同辞”地“咸称刘氏”。
我把次序倒一下,先说第二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新旧王朝更迭之际,假托拥立前朝后裔揭竿而起的,并不罕见;但像新末动乱中这样“咸称刘氏”,而且表现得如此突出、频繁,却是绝无仅有的。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
在这场大动乱中,先后有十一人自立或被拥立为帝,其中有真刘氏六人,冒牌刘姓二人,共八人,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六个真刘氏的简况如下——
刘玄:汉宗室后裔。初投绿林军平林兵,任安集掾。地皇四年(公元23年)被拥立为帝,年号更始。三年后败于赤眉军,被缢杀。
刘望:汉宗室,曾受封为钟武侯。起兵略汝南,地皇四年(公元23年)自立为天子。不久即为更始军所杀。
刘婴:即王莽先曾立以为孺子、后废为定安公的那个小男孩。建武元年(公元25年),平陵人方望等拥以为帝。后为更始军所击杀。
刘秀:刘邦九世孙。更始三年(公元25年)即帝位,改元建武,定都洛阳。为东汉王朝创建者。
刘盆子:刘邦庶孙城阳王刘章后裔。为赤眉军所掠,留在军中牧牛,称牛吏。更始三年(公元25年)在华阴被赤眉军首领樊崇拥立为帝,建号建始。时年十五,见诸将跪拜,吓得差点哭了起来。后降刘秀,受赐荥阳均输官地,得以食税终身。
刘永:梁王刘武八世孙。被更始帝封为梁王。更始三年(公元25年)自立称帝。后为刘秀军所杀。
两个冒牌刘氏其中一个叫王郎。王莽建新时,曾杀过一个自称是成帝之子刘子舆的人,王郎就借此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成帝之子刘子舆,并编造出离奇故事,说他母亲原为成帝歌女,一次偶受皇气成孕而生了他,居然有许多人相信。王郎就靠了这点政治资本,被一些人拥立为天子,又是封相拜将,又是移檄颁诏,着实闹腾了一段时间。后败于刘秀军,死于逃亡途中。另一个叫卢芳,谎称自己是武帝曾孙刘文伯,在安定三水一带起兵反莽,后被地方豪强推举为上将军、西平王。建武元年(公元25年)又被匈奴单于迎去立为汉帝,曾一度与东汉政权相对峙,后病死于匈奴。
即使与刘氏毫不相干的其余反莽群雄,也大多以拥刘兴汉为号召。譬如上面提到的隗嚣,在家乡被众人推举为上将军后,就采纳他的军师方望的建议,第一桩大事便是立庙祭祀汉高、文、武三帝,并与诸将割牲歃血而盟。盟誓特别强调一点:“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倘若有谁心“怀奸虑”,则听由“高祖、文皇、武皇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后汉书》本传)。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刘”这个姓在当时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符号,刘汉王朝在灭亡十余年后,依然是一座有着巨大开发价值的政治矿藏。之所以如此,就要说到上面引文中班彪说的另一点意思了:王莽“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西汉王朝的大厦虽然倒了,但其坚实的根基继续存在。分析起来,这个“根”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元素构成——
一是已成为天下第一豪族的刘氏宗室。由于皇室成员享有当时最优越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加之妻妾成群,因而刘氏家族在西汉两百余年间繁衍极为迅速。《汉书·诸侯王表》称:“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而至元始五年(公元5年)据一份诏书中对刘邦及他哥哥刘喜和弟弟刘交三个谱系“宗室子”所作的统计,已多达“十有余万人”(见《汉书·平帝纪》)。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但仍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刘邦还有一个长兄刘伯,早卒,其子刘信在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被封为羹颉侯,史书未记其“亡后”,他也应有子孙的。此外,所谓“宗室子”通常指男性,不包括宗室女性成员。如果全都统计在内,刘氏宗族总人数估计不会少于二十万吧?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考测,西汉前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12%;后期约为7%。而刘氏宗族的增长率即使按“十有余万人”估计,也要高达45%左右,即比全社会的平均增长率高出四五倍!更为重要的还不在数量,而是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宗室成员多数被封为诸侯王,其封国遍布关东关西,大江南北,全都成了雄踞一方的豪门大族。从刘邦多次对功臣赐以刘姓也可看出,在西汉两百余年间能有刘这个姓是何等的荣耀!王莽称帝后,虽接连采取将汉诸侯王改称为公,后又降为民,赐原汉宗室刘龚、刘嘉等三十二人以王姓,以及悉罢京师刘氏宗庙等措施,但刘氏在全国各地长期扎下的坚实根基不仅依然存在,其社会影响力还因新莽王朝的迅速败落而日益提高。
二是世受汉禄的官吏及其家人。《汉书·百官公卿表》有个汉官吏总数的统计:“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其中不包括县以下的亭长、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等,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单是亭长就有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人。汉时又有不少功臣受封为侯,并得世袭。如高帝时萧何任相国,封为酇侯,其爵位一直延续到王莽建新才绝。据以上框计,西汉两百年间,曾享受朝廷食邑或俸禄的,该是一支何等庞大的队伍!他们起而维护汉统,除了理性上对刘氏正统的认同,还有感性上世受朝廷俸禄的感恩。就像九章末节已介绍的那样,还在王莽称摄时,先父曾为汉相、自己历任三郡太守的翟义,就以聚众十余万的规模作了殊死反抗。至于对新莽表示不合作或反对的,粗略翻检了一下《汉书》,就有六七十人之多。如新都相孔休,与王莽曾是挚友,但当王莽入京专权,再要想见他时,孔休托病拒绝;王莽称帝欲召以为国师,孔休杜门谢客,竟呕血而死。哀帝时曾奏民有“七亡七死”(见九章二节)的谏大夫鲍宣,宁愿在狱中自杀,就是不肯附莽。大司空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都在王莽专权时上书乞骸骨,罢官归里。南郡太守郭钦、兖州刺史蒋诩,一听王莽居摄,皆弃官自归。曾为郡掾祭酒的薛方,王莽征而不至,又以安车相迎,薛方辞谢说:“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这些世受汉禄的官吏及其家人,在新末乱起时,自然大都在感情上以至行动上站到了农民起义军一边。
三是依旧怀念着刘汉的多数农民。作为汉帝国基础的农民,他们曾先后为秦末战乱、楚汉战争和对匈奴等周边战争承受过巨大牺牲,也曾参加过被称之为“盗贼并起”的对朝廷或官府的抗争,但当他们对新莽从寄望到失望以至绝望时,就会不由转过头去回望那个渐行渐远的大汉帝国,怀念起祖祖辈辈传说中的那些文景之世的富庶安乐,以及武帝时期的激情高扬的日子。新末起义军的主力是绿林军与赤眉军,二军主要由农民构成。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农民大多数是由奴隶和部分自由民或没落的小奴隶主转化而来,作为一个阶级,大体形成于秦帝国建立前后。他们的生活史是与帝王集权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自他们出生起就笼罩在他们周围的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因而他们造反的终极目的便是:如果自己不能做皇帝,那就选择一个好皇帝。就以赤眉军为例吧。在这支以樊崇为首领的起义军中,当年那个在诛灭诸吕中立了大功的城阳王刘章,是被作为降福祛邪的神灵来祭拜的。有人建议当立刘氏而共尊之,樊崇马上就想到了刘章子孙,在军中一寻找,果然很快找到七十多人。于是就选了其中三个血缘最近的,用抓阄的办法,最后确定立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为帝。偏是盆子几次哭哭啼啼地要退掉这个皇帝,情愿回去干他的老本行放牛。樊崇却总是恭恭敬敬地挽留,开口闭口“臣有罪”、“臣无状”、“臣负陛下”(《后汉书·刘盆子列传》)!这个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之所以要对一个小男孩如此卑躬屈膝,唯一的原因就为他姓刘,可以充当汉帝国的象征。
因而不妨说,新莽末年的群雄逐鹿,同时也是争夺刘氏这座政治矿藏的一场大竞赛。刘秀最后能逐个削平群雄,独得全鹿,成为一统天下的共主,固然有绿林、赤眉二军为他造就了有利形势,他个人的胆略、才智以及辅将的得力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带有决定意义的,还应是他能最有效、最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这座政治矿藏。
有这么一个细节。绿林军拥刘玄为更始帝,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受命赴洛阳整修宫殿,以备建都。洛阳是东周故都,刘邦建汉初期也曾定都于此。洛阳人以身居于天子之都为荣,自视风雅,鄙薄俗制。因而当那些衣着粗劣、杂乱的更始军初次闯入这座皇城时,他们或是聚而在一旁讥笑,或是远远躲避不屑一顾。这一日洛阳街头忽而出现了数十个一律整齐地穿戴着汉制冠服的官员,立即引起两旁行人纷纷驻足而观,众人“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后来得知这些都是刘秀带来的官吏,“由是识者皆属心焉”(《后汉书》本纪)。你看,刘秀只是用了几套汉制冠服,便收到了如此巨大的政治效果!
刘秀是在新末动乱中继刘玄、刘望、王郎后第四位称帝者。他称帝时,刘望、王郎已先后被杀,更始帝刘玄正在筹划攻打长安。刘秀是在鄗(今河北高邑)即帝位的,二帝并存,东西隔数千里之遥。刘秀学的是当年刘邦做下的榜样:群臣一再推拥,他却一让再让而至于三。有所不同的是,他还动用了据说是上天降下的一个叫《赤伏符》的符命。所谓符命当然是人编造出来的,只是是否由刘秀暗示或指使已无从稽考。共三句:“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后汉书》本纪)“四七之际”与“三七之厄”一样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4×7×10=280,指自刘邦建汉至刘秀初起,其间历经280年。“火为主”刘汉为火德,一度被王莽以土德篡夺,现在上天命刘秀仍以火德承续汉统。既然上天已经下令,刘秀便以“皇天大命,不可稽留”(同上)为由,祭告天地,望祀群神,宣布即皇帝之位。建元为建武,称更始三年为建武元年(公元25年)。
几个月后,更始帝刘玄,兵败于赤眉军,降后被缢杀。
巧的是同在这一年,在巴蜀之地又冒出了一个皇帝,而且用的也是符命。
此人叫公孙述,汉时曾为清水长,新莽时任蜀郡太守。新朝一倒台,他又立即转身傍上了汉,伪称有汉使从东方来,授任他为辅汉将军,兼蜀郡太守益州牧。一年后,看看关东依旧乱个不休,想到巴蜀之地有关山险阻颇可自守,有千里沃野足以自恃,还挂刘汉这块牌子做甚,索性自立为蜀王。这年四月一日黄昏,他在恍惚间看到殿内有条黄龙若隐若现,闪烁其光。恰好这天夜里他又做了个怪梦,梦中有人对他说了八个字:“八厶子系,十二为期。”他以为这些都是上天降下的符命,便忍痛在自己手掌上刻了“公孙帝”三个字,又急命几个智囊人物为他可以继汉称帝从古籍中找点根据出来。根据果然很快找到了,那是一些说神道鬼的谶纬书,其中有一部里明明白白写着:“孔子作《春秋》……而断十二公。”既然连《春秋》也断于十二公,那就说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于是便举行隆重典礼,宣布“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龙兴元年”(《后汉书》本传)。
这是一场有趣的“符命之战”。
东边刘秀的符命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汉统历经280年后,火德复兴,由我刘秀把它前后连接起来。
西边公孙述的符命说:“汉至十二历数尽”,“一姓不得再受命”。你姓刘的已做了十二世皇帝,气数早尽,应当换姓了,该由我公孙述来当这个皇帝!
两人打出的牌完全相反:刘秀要连续汉统,公孙述要切断汉统。
一续一断,一东一西,断断续续一直争战到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续”胜“断”败的结局才开始浮出水面。
在此前后,其余诸路反莽英雄已相继被降服或歼灭,包括先后称帝的刘婴、刘盆子、刘永、孙登、李宪等,也已不复存在。
这年十二月,刘秀命大司马吴汉统兵西征,向公孙述发起最后决战。次年正月攻打武阳,七月破广都,十一月大战成都获得大胜,公孙述被创而死。作为统帅的吴汉,为庆贺此次完胜又做了两件事:“屠成都,夷述宗族。”(《后汉书·光武帝纪》)就是说不仅杀了公孙述全族,还血洗了整个成都城。正是在这一片血光中,刘秀最终成就了他的统一大业,实现了十二年前符命所说的汉统的复归,刘氏前后四百年基业的对接。
所谓符命自然是虚妄的,但在虚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千千万万人的意愿。你不能不承认,这并非全是个别称王称帝者的意志使然,它应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他的代表作《历史研究》第三章中,专门研究了希腊与中国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他所说的希腊模式大略相等于我国周代的帝王封建制,即有统一的文化认同,政治上各封国相对独立;中国模式则指我国自秦起所行的帝王集权制,文化和政治都实现高度统一。汤因比认为这两种模式各有长短,互见利弊。接着他作了这样论述——
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同希腊模式的早期阶段结合在一起,组建成一个改良的模式。这一文明史的组合模式显示这些社会在开始时存在着文化统一,却没有政治统一。这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但代价是地方各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随着这个社会的成长壮大,这种战争变得越来越惨烈,迟早要引起社会的崩溃。在旷日持久的“麻烦时期”过后,混乱局面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所治愈。这个统一国家周期性地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无论这类中间期长短与否,它们总会被政治统一所克服。在最初的统一过去以后,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维持着这种治乱交替的过程。统一被修复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在极为漫长混乱、以致传统上可能认为无法修复的“中间期”过去之后,仍会恢复统一。
读汤因比的这段统一一再被破坏又一再获得修复的论述,不由人想起《三国演义》头里那句在我国几乎老少皆知的开场白——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东汉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新一轮分后之合的开始。这一“合”,使西、东两汉前后四百余年成为一个整体,成为显示帝王集权制度生命活力的一个强大而坚实的存在,成为象征正统观念的一个崇高而神圣的典范。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此后千百年历史产生极其深远的、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
不过无论如何,所谓“蝉蜕蛇解,游于太清”(《淮南子·精神训》);所谓“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周易·革卦》),大凡社会经过一次大的变革,总会出现一些新气象,给人带来新的希望。对生活在一至三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君临着他们的东汉王朝,大多数时间政治还算清明,社会也较为安宁,相对于西汉末世称得上是一次“复兴”。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与那时的先祖们一起对又一个刘汉王朝的诞生表示庆贺吧!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