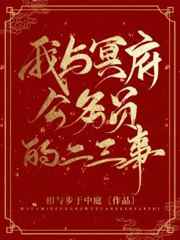渐台悲剧留给后人的思考题
王莽在未央宫太液池渐台被杀后,《汉书》本传有一段因其触目惊心而在民间流传极广的记载:莽首“县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老百姓把挂在宛城闹市的王莽的头颅捅下来抛来掷去耍弄,后来有人索性割下他的舌头炒了吃。
我相信这是事实。人在愤怒和混乱中,是很有可能做出平时无法想象的事情来的。但以为据此便可以得出人民群众都对王莽痛恨到了极点,因而必须予以彻底否定这样一类结论,则恐怕未必。
历史结论切忌草率和情绪化。
王莽以他这样一种独特方式革汉建新,是中国数千年帝王制度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个特例。像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梳理,空间的分析和比较;需要反复的认识和再认识,才能逐步接近真理。
我在九章四节引了王充、班固把王莽称之为历史上最恶、最坏的“乱臣贼子”和“无道之人”那两句话。其实,历史上最早对王莽作出评论的并不是他们两人,而是桓谭。古人有关王莽的评价,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桓谭的见解。原因是桓谭小王莽五岁,恰好亲历了两汉之间那场剧变。他多才多艺,遍通《五经》,自哀、平、新莽至东汉,多数时间都在朝廷做大夫、议郎一类小官,对王莽有过近距离观察。更为重要的是桓谭为人正直耿介,从不随波逐流。据《后汉书》本传记载,还在王莽红得发紫的“居摄篡弑之际”,当“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时,桓谭却孤独“自守,默然无言”;而到东汉初年,当“众恶归莽”成为一种政治时尚时,他也没有随风转舵,加入痛骂王莽的行列。其时谶纬之学因光武帝的提倡而甚为盛行,桓谭上书直言谶纬之非,由是触犯帝怒,险遭杀害,后出为六安郡丞,病卒于途。著有《新论》一书。桓谭是我国古代一位极为难得的具有特立独行品格的杰出学者。
桓谭对王莽的评论,我们现在可以在严可均辑的《全后汉文》十三卷中读到。侧重点是总结王莽败亡教训,虽也揭露了王莽的残暴,如“生烧人,以醯(醋)五毒灌死者肌肉”等恶行,但其基调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客观冷静地依据事实作出分析。他认为王莽有智、辩、威三绝,但因过于自恃,反而导致败亡,其最大的失误是“不知大体”。文中称:
维王翁(即王莽)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辩)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
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兵(共),苟直意而发,得之而用,是以稀获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
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后东击青、徐众郡赤眉之徒,皆不择良将,而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或无权智将帅之用,猥使据军持众,当赴强敌。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咎在不择将。将与主俱不知大体者也。
桓谭评论的可贵处,在于他不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所左右,直面其人的行事作出分析和结论。这样评论即使并不一定公允,也还是能给人以不同侧面的启发。遗憾的是桓谭的这种独立学术品格和求实精神,很少有人继承。班固在《汉书·王莽传》赞语中,将王莽的辅政、摄政及建新称帝这个历史阶段称之为“篡盗之祸”。此后对王莽的评论大都没有脱出这个基调。若论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当数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一的下半首:“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诗人以为王莽为人就像一个谜,谜底要到他“即真”时才大白于天下,那便是一个丑恶的“篡”字。
其实认定王莽“篡汉”,是因为先已有一个不容别人置疑的前提,即把刘汉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的“正统”,无论已衰落到何种地步,也不容许他姓他族来作任何更新。在这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样一种固陋而又霸道的认识,不仅距离现代国家学说何止十万八千里,甚至也落后于此前的古人,譬如“五德终始”说和“三统论”就认为天命归属是循环不息的,没有哪一个王朝可以永享其统。
公元1911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从此,古老的中国终于宣告了帝王制度的终结,向现代民主国家跨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辛亥革命对学术界也有“解冻”意义,在学人心目中帝王制度及其正统观念逐渐褪去了神圣的光泽。具体表现在对王莽的评价上,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仍持“篡盗”论,或讥之为欺世盗名的大奸,或斥之为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两面派;却也已有不少学者重新面对尘封了近两千年的渐台悲剧,开始冷静地思考它的本质和含义。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是用启发式的句式提出这个问题来的。他说:“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斥外戚,诛锄异己,皆势不能避免,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论也。”翦伯赞在多部著作中评论了王莽。如《中国史纲》第二卷说:“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收入《历史论文集》的《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一文说:“不能说王莽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不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王莽的车子是向前开的,他希望把他的车子开到他理想中的新朝;但途中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强烈反对,被迫折回”。柏扬在《中国人史纲》中热情赞扬了王莽的抱负和理想。他说:“王莽是儒家学派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胡适在1928年发表过一篇专文,题目就令人一惊:《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文中“称王莽是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原文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转引自《剑桥中国秦汉史》)。我没有查到原文,不知道胡适先生是在怎样的含义上使用“社会主义”这个现代概念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说:“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的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博学的胡适博士,不知是否是在“西方作家好奇心”的激发下,形成这样一个独特的观点的。无论如何胡适的这个评价,不仅肯定王莽有理想,而且还是一位具有超前理想的古人。
我想谈一下我对这道思考题的一点看法。
坦率地说,我在感情方面是不大容易接受王莽这位古人的。追溯起来,这可能与童年在故乡钱塘江畔看鲁迅先生曾描写过的那种“社戏”受到强烈刺激有关。那些我不止一次看过的社戏中,有一出常演不衰的绍剧叫《斩经堂》,主角吴汉是被称为做到了“忠孝两全”的英雄。吴汉本是实有的历史人物,新末因犯法而亡命,以贩马为生;群雄蜂起时,归附于刘秀,后成为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的大功臣。但《斩经堂》中的人物关系和吴汉的行事,则全系出于神化汉统需要而虚构出来的。吴汉“忠孝两全”的一个经典情节,也是全戏的高潮,便是他奉母之命提剑入经堂去斩杀他的正在虔心拜佛以求保佑公婆、丈夫的妻子王兰英。这位美丽、善良、贤惠的女性之所以必须死去,唯一的理由,就为她是窃汉之贼王莽的女儿。唱腔高亢入云,台下万人惕息。我那幼弱的心灵,随着男女主人公一步紧一步的生死搏斗、挣扎而在颤抖、哭泣,因同情兰英而深深痛恨那个叫王莽的大坏蛋。回家路上我问乡里父老这个大坏蛋的下场,于是他们便向我讲起了王莽死后“骷郎头被人当皮球踢,舌头割下来酱油麻油拌拌过老酒吃”的故事。当然,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理性思维已经完全能够清理童年的蒙昧了,但留在感情上的这块胎记,却似乎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
我在感情上与这位古人存在距离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关那段历史的最初记载,都只能依赖由以维护汉统为己任的班固写的《汉书·王莽传》,我无法完全摆脱这位杰出的古代历史学家笔下的王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作为一个经历曲折坎坷而又年逾古稀的老人,我最厌恶虚伪,偏偏出现在《汉书》中的王莽几乎是古往今来虚伪的典型。写完第九章通读一过,才发现我在叙述王莽的有些段落的字里行间,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嘲讽的笔调,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曾想过是否改一改,后来决定还是保留原样。相信读者诸君自有明鉴,我又何必矫饰呢!
至于从理性上说,我大体赞同翦伯赞先生的观点,以为王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很有胆识的政治家,他的车子是沿着他的理想之路朝前开的,但由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多种原因,结果却是车毁人亡,身败名裂。
不过我以为,渐台悲剧最值得后人冷静思考的,还不是王莽是否称得上有理想,他的种种改革是该肯定还是否定,以及后来因何失败等等问题上。最值得思考的应是王莽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角色定位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从班固开始的传统历史学家做得很对,确实应该定在一个“篡”字上,只是对这个“篡”字,我们应作出新的诠释。王莽用毕生心力创造了一种新的不妨称之为“和平变革”的国家权力传递方式,并以自己生命为代价作了一次尝试性的实践。尽管最后还是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但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尝试最初曾经是成功的,他建立了一个称之为“新”的王朝,在中华大地上存在过十五年。传统历史学家对这十五年不屑一顾。《汉书》既不承认新这个王朝,也不承认王莽曾做过皇帝,因而将他逐出“本纪”,写入“列传”。当然,这样做的动机是崇高而堂皇的,因为是为了使前、后汉拉起手来,将夹在中间这个名叫“新”的杂种小子活活挤死或挤掉,以维护刘氏四百年皇皇汉统的一贯性。但世界上凡是存在过的事物都已有了自己的历史,而历史是抹杀不了的。你可以将众恶归之于“新”,却不能否认它的曾经存在,即使刀削斧砍也一概无用!
为着了解先哲时贤们对新莽的种种不同评论,我在上海图书馆阅览大厅整整浏览了三天。偶尔翻到一个薄薄的单行本,是周桂钿写的《王莽评传——复古改革家》,令我眼前一亮,不由大为惊喜。原来周先生已先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从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用打的方法夺取政权,所以叫打天下,或叫武装夺取政权,也叫暴力革命,项羽、刘邦起义,朱元璋起义等都是这种方式。另一种是不经过战争,用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过去叫禅让,后来叫篡位,也可以叫和平演变。尧、舜、禹是传说中的禅让典型。周公摄政是暂时性的。王莽立新、武则天建周,大概都是历史上比较少有的和平演变或和平过渡的例子。
我很赞成这个概括。至于王莽首创并尝试过的这种国家权力传递方式究竟是叫“和平演变”或“和平过渡”好,还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称“和平变革”似乎更确切些。变革,意味着要提出新的治国方针,要来一番革故鼎新,是两种治国思想、策略在竞争中的优胜劣败。
即使是在古代,国家权力也不可能永远为一姓一族所据有,只能在外力的作用下,在或长或短时间内被迫向外姓转移,方式无非是暴力与和平两种。但自从班固将王莽的和平变革贬之为“篡盗之祸”,一脚踢进十八层地狱以后,此后凡是想尝试用这种方式取得政权的,还没有行动,就先已背上了这个烙着“篡”字印记的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令人不解的是,难道血淋淋的暴力夺取就那么道德高尚、那么美妙如诗吗?
其实,历史上,当汤第一次用武力将夏桀攻灭、自己建立商朝的时候,他所受到的舆论和道德压力肯定不会小于王莽的“篡汉”之初。不然,汤怎么会像我在八章一节中引录的那样“惟有惭德”:内心深深感到惭愧呢?后来是左相仲虺那一番一切决定于天命的话:桀被灭是他违逆天命,汤建商是顺应天命;才使汤在获得国家权力的同时,道德上也仿佛忽而崇高起来。但真正使汤成为圣王贤君典范的,还不是仲虺那一番话,而是商朝享国四五百年这样一个巨大的成功。在这里,“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设想一下,如果商朝也像新一样短命,汤会不会也像王莽一样被人斥之为弑君夺位的乱臣贼子呢?是汤与后来仿效者周武王的巨大成功,迫使历史学家们慌忙制造出一种理论来,硬是将商汤和周武的这种暴力夺取政权说成是一场顺应天命的、吊民伐罪的、崇高无比的“革命”。实际上即使这样,对汤武的这种暴力方式是否具有正义性,至少在汉及汉以前还是颇有争议的。大略说来,儒家以为汤武伐桀纣是义举,而黄老则多持否定态度。《孟子·梁惠王下》和《荀子·正论》就记下了双方的一些对立观点:齐宣王和“世俗为之说”者认为汤武是“臣弑其君”,是“篡而夺之”;孟、荀二子则说汤武是“诛一夫”,“未闻弑君”;是“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汉代景帝时,还为此在朝堂上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此事《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皆有记载。争论的双方,一个是治《诗》而任为博士的辕固生,另一个是持黄老观点的黄生。黄生责难汤武篡弑,认为他们既非正义,更谈不上受命。辕固生则坚持认为汤武行为是正义和顺应天命的,他说:“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在反驳时用了一个帽子与鞋子的比喻,以为“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因为总得有个“上下之分”。同样道理,“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处于下位的臣子怎么可以犯上作乱、弑君自立呢?辕固生感到有些窘迫,为摆脱被动,便把问题从历史转到现实,由学术引向政治。他说:“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他的这一着很厉害,使对方再也没有辩驳余地:有谁胆敢在刘汉朝堂上说刘邦灭秦兴汉是非正义呢?黄生默然。争论出现了僵局。这时景帝说了一句幽默话,才使这场剑拔弩张的争论得以在轻松的气氛中收场。景帝说:“食马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未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写到这里,我不禁油然升起一种怀念,怀念一位可敬的古人,他就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我忽发奇想:如果《汉书》不是出自班固之手,而是由司马迁或司马迁的传人来写,后人看到的王莽和他所建立的新朝将会是一个什么模样呢?
按照英国哲学家R·阿特金森的说法,“历史”一词包含着历史Ⅰ与历史Ⅱ双重含义。历史Ⅰ指过去出现或发生过的人和事;历史Ⅱ则是人们对过去那些人和事的记载或研究。事实上历史Ⅰ早已远逝而去,后人能够看到的只有历史Ⅱ,即已经从客观进入主观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作为实际存在的王莽及其所建立的新朝早已成为过去,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是班固依据原始材料,经由他的主观意识作用而形诸文字的一种记载。所以准确地说,它是班固心目中的王莽和新朝。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假如由司马迁或他的传人来写这段历史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会与班固写的一个样。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将只是一度统治过九个郡的西楚霸王项羽列为“本纪”,而君临天下达十五年之久的新朝创建者王莽,班固的《汉书》却只将他归于“列传”。因而若是由司马迁或他的传人来写这段历史,十有八九会承认王莽的帝王地位,为其撰作“本纪”。果真那样,我们就将有幸读到一个记述更确切、细节更丰富,因而也更接近于历史Ⅰ的王莽和新王朝。尤为值得期待的是,“本纪”之末那常常给人读后有醍醐灌顶之感的“太史公曰”。对王莽革汉建新前后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相信在“太史公曰”中定会作出合乎历史进程的梳理和评述,并给后人留下烛照幽微的启示。如果这个假设成为事实,那么这部出自司马迁或他的传人之手的《汉书》历经千百年的传播,人们就有可能早已接受了王莽,至少不会把他看得那样可憎可恶;中国历史的演进也或有可能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并存,至少不会几乎每次王朝更迭都要用无辜民众累累白骨堆叠而成……
好啦,还是赶快打住吧!我的这个假设只能算是躲在书斋里的喃喃自语,或者干脆说是痴人说梦。历史没有“如果”。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受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制约的固有规律,譬如新末乱起时那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同样也还是有规律可寻的。这就要说到“结语”的最后一点想法——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