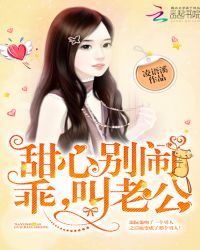第三节 柳宗元的净土观:以《东海若》为中心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三节/
柳宗元的净土观:以《东海若》为中心
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又因其始祖慧远曾在庐山建立莲社提倡往生净土而称“莲宗”。早在东汉时,净土经典就开始传入中国,支娄迦谶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般舟三昧经》等,后来竺法护译出《弥勒菩萨所问经》《佛说弥勒下生经》,支谦译出《大阿弥陀经》,畺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经》,于是在中国出现了净土崇拜。净土崇拜大致可分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两种,一般认为弥勒净土信仰由道安(312或314—385)首创,弥陀净土信仰则始于东晋慧远(334—416)。南北朝时期,净土信仰十分兴盛。隋唐时期,弥勒信仰衰落,弥陀信仰遂成为净土信仰的主流。此时,佛教中国化过程大体完成,各个宗派相继建立,在这种背景下,善导在前人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净土理论及仪轨,从而使净土信仰具有了宗教形态,因此善导是中国净土宗的实际创立者。
净土宗奉的主要经典有“三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世亲的《往生论》。这些经论都宣扬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是—个极乐世界,众生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称念其名号,临终便可往生。由于净土宗教义简单,法门易行,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善导以后,历代名师辈出,先后有慧日、承远、怀感、法照、少康等等。
柳宗元对净土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其发展也大力支持。除了为三祖承远、承远的弟子日悟等净宗大德作碑铭外,还写专文宣传净土思想。南宋宗晓编《乐邦文类》,专收弘扬净土思想的诗文,其中收录柳宗元的《东海若》《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三篇,由此可见柳宗元在净土宗发展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一、《柳集》净土材料考
《柳集》中有关净土思想的材料主要有:《南岳弥陀和尚碑》《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东海若》《巽公院五咏·净土堂》。涉及的净土宗人物主要有:承远、法照、日悟、景秀、无姓和尚等。
(一)《南岳弥陀和尚碑》
开元七年(719),在印度等国历时十三年学习净土的高僧慧日(680—748)回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热情接待,并赐予“慈愍三藏”称号。慧日归国后大力弘传净土法门,开创了中国净土宗慈愍派。《南岳弥陀和尚碑》的碑主承远即是慧日的弟子。
承远(712—802),俗姓谢,江州(今四川广汉)人。开元二十三年(735),至荆州玉泉寺谒见惠真和尚,从其披剃出家,又在惠真的指引下到衡山学习经律,再赴广州慧日处归于净土,专修念佛三昧。天宝初年(742)返回衡山,建立弥陀道场,代宗赐名“般舟道场”,德宗又赐名“弥陀寺”,承远也被世人称为“弥陀和尚”。由于承远在弘扬净土信仰方面的突出贡献,志磐《佛祖统纪》把他列为“净土三祖”之一。贞元十八年(802)示寂,柳宗元为其撰碑铭,立石于寺门之右。弟子千余人,以法照、日悟等最为著名。
《南岳弥陀和尚碑》是柳宗元应承远的弟子法照之请而作的。法照,生卒年、籍贯均不详。代宗永泰元年(765),因慕慧远之高风而入庐山,结西方道场专修念佛三昧。一日于禅定中蒙佛开示,往南岳师事承远。大历二年(767),居衡州云峰寺修持;四年,在衡州湖东寺开“五会念佛道场” 。此后,法照长期往来于五台、并州、长安之间念佛化人,因其在弘扬净土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代宗尊为国师。《历代佛祖统记》把他列为净土宗第四代祖师。
后人一般根据承远的卒年,把《南岳弥陀和尚碑》系于贞元十八年(802)或稍后,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柳宗元贬谪永州以后的作品 。我认为,在掌握更为确凿的证据之前,最好不要把它放在贬永以后。
(二)《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
《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的碑主是承远的弟子日悟和尚。此篇碑文作于元和三年(808)十月,柳宗元根据日悟弟子景秀的亲口介绍,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日悟的生平及思想情况。
日悟(735—804年),零陵人,俗姓蒋。先师事东林恩大师学习戒律,又师事承远学习净土念佛三昧,最后又师事津公修习律学,嗣法于津公。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诏令天下名寺各置大德七人,日悟被推举为南岳大德之首。日悟于南岳辟林莽、刳岩峦、作精室,建起净土念佛道场,南方专习念佛三昧者无不出于此处,其道场也因此被称为“般舟台”。日悟卒于贞元二十年(804),四年后弟子景秀请柳宗元为其撰写碑铭。此碑名为“第二碑”,可能是与承远“第一碑”相对而言,因为两人都在南岳般舟道场弘扬净土念佛三昧,且是师徒关系。
(三)《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
龙兴寺本为天台宗寺院,永州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曾在此设净土堂,以作念佛场所。元和二年(807),柳宗元与重巽、刺史冯公及其他信士一起重修净土堂,他还把托名智顗的《净土十疑论》书于墙宇,以期观者起信,并作《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以记之。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较集中地表达了他对净土宗的理解与态度。
除以上三篇文章外,《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虽为天台宗主所作,其中也包含净土宗材料;《巽公院五咏·净土堂》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作者对净土宗的理解。尤其重要的是《东海若》,这是一篇以寓言的形式写成的专门弘扬净土信仰的文章,是研究柳宗元佛学思想的十分重要的材料,下面对其进行专题讨论。
二、《东海若》的净土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注释标题 此部分内容曾以《论柳宗元的〈东海若〉》为题发表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可能由于其浓厚的宗教色彩,《东海若》很少为历代“柳学”研究者所问津。其实,在《东海若》对净土信仰及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提倡的背后,隐含着柳宗元火热的现世关怀与冷静的理性思考。
(一)《东海若》的净土思想
《东海若》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寓言,第二部分揭示寓意。第一部分大致说:东海若(即东海之神)捡到二个大瓠,挖空后把夹杂着粪土等污秽之物的海水填入其中,又用石头堵住口,扔进大海。过了一段时间,东海若再次经过此海时,听到一个瓠中的海水大喊:“我大海也。”东海若感到好笑,要帮它取出秽物回归大海,它很不高兴地说:“我固同矣,吾又何求于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秽者自秽,不足以害吾洁;狭者自狭,不足以害吾广;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秽亦海也,狭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来,孰非海者?子去矣,无乱我。”另一个瓠中的海水则哭嚎求救,于是东海若抉石破瓠,荡涤秽物,海水复归清净,回于大海。前面的那一个则永远与臭腐为伴。
第二部分揭示寓意:
今有为佛者二人,同出于毗卢遮那之海,而汩于五浊之粪,而幽于三有之瓠,而窒于无明之石,而杂于十二类之蛲蚘。人有问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卢遮那、五浊、三有、无明、十二类,皆空也,一也,无善无恶,无因无果,无修无证,无佛无众生,皆无焉,吾何求也!”问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与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无乱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尽吾力而不足以去无明,穷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离五浊,而异夫十二类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问者乃为陈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说。于是圣人怜之,接而致之极乐之境,而得以去群恶,集万行,居圣者之地,同佛知见矣。向之一人者,终与十二类同而不变也。夫二人之相远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注释标题 《东海若》,《柳宗元集》第二册,第567页。
文章的前后两部分一一对应。“大海”喻“法性”,“粪土”喻“五浊”,“瓠”喻“三有”,“石”喻“无明”,“蛲蚘”喻“十二类” 。两位学佛之人,一位坚持“无修无证”,另一位则接受“念佛三昧”,两人在解脱的根据、方式与途径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析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的差异。唯心净土,谓净土是唯心所变,存在于众生心中;西方净土,指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又称极乐净土、极乐世界等,存在于“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处。《东海若》中,一人说“秽亦海也,狭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来,孰非海者”,这其实就是说,自性是佛,净土就在自己心中,而另一位则相信“西方之事”“极乐之境”,前者持“唯心净土”观,后者持“西方净土”观。
第二,自度与佛度的差异。一人说:“我佛也,毗卢遮那、五浊、三有、无明、十二类,皆空也,一也。”他认为,诸法性空,无佛无众生,因此解脱只能靠自性自度,而不能靠佛度他度。另一位则说:“吾尽吾力而不足以去无明,穷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离五浊,而异夫十二类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他认为,自力、自智不足以去“无明”、超“三有”、离“五浊”,即使能做到的话,也要用不知多少劫的时间,所以必须靠佛度。
第三,无证无修与念佛三昧的差异。在修行方式上,一人说:“无善无恶,无因无果,无修无证,无佛无众生,皆无焉,吾何求也。”既然诸法皆空,“无善无恶”“无因无果”,当然也就无须修证了。另一位则主张修“念佛三昧”。
最后,不离世间与欣取乐邦的差异。一人认为,秽者自秽、狭者自狭、幽者自幽,自心的“洁”“广”“明”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秽”“狭”“幽”而改变,即心即佛,不假外求,解脱不离世间。另一人则严格区分世间与出世间,厌舍秽土,欣求乐邦。
文中,修“念佛三昧”者最终被接引至“西方净土”,“无修无证”者则永远与臭腐为伴。柳宗元又立足于“中道”立场分析了“无修无证”者的病因所在。先简要介绍一下“中道”的内涵及柳宗元的理解。
“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是大、小乘各宗派弘法的基本态度。关于“中道”一语的内涵,大、小乘诸宗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大乘中观学派之“中道”立场是:主张缘起即空,空有不二,反对堕于“断”与“常”两边。《大智度论》卷八十说:“若人但观毕竟空,多堕断灭边;若观有,多堕常边。……离二边故,假名为中道。” 只知“毕竟空”会堕入“断灭边”,只知“缘起有”则会堕入“常边”,只有即空的缘起而不落于“断灭边”,即缘起的性空而不落于“常边”,方为缘起与空寂不偏的“中道”。因此,佛陀正觉与善巧方便、缘起性空与修行实践不可偏废,偏重任何一方都会失却“中道”。
柳宗元对佛教之“中道”有很深的理解。他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中说:“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故虽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 “假有”非真有,“借无”非真无,“假有”“借无”都蕴含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之意,两者融通,便契入万法之实相。“事与理并”表达的也是这一意思。“事”,指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即宇宙间千差万别的现象,“理”则指平等、无差别的本体,理事相即方为“中道”。下面一句中的“无生之生”,巧妙地把“理”与“事”圆融起来。依“理”而言,一法不立,故无生;依“事”而言,万法宛然,故生;真不碍俗,故生亦无生,无生亦生。只有理解“无生之生”,才会明白登上“无生”之岸离不开“有生”之舟筏的道理。柳宗元这几话要表达的意思是,不要因过分强调对性空的悟解而忽视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的必要性,所以他说:“故虽往生之因,亦相不舍。”在《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中,柳宗元更明确地说:“无得而修,故念为实相;不取于法,故律为大乘。” “无得”,即“无得中道”,由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八种概念组成。柳宗元说,依“中道”修行,念佛而不着于相、持戒而不取于法,念佛、持戒即是实相。
再看柳宗元在《东海若》中对“无修无证”者的批评。“无修无证”者站在诸法缘起性空的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毗卢遮那、五浊、三有、无明、十二类,皆空也”,既然一切皆空,那么心之外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实有的“西方净土”,解脱也只能靠自性自度而不能靠佛度他度,因此,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都是多余的,只需在日常生活之中做到“无证无修”就行了。柳宗元指出这种观点的症结之所在:“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与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性”,即本性、本质,与“理”等意。从“性”上来说,诸法性空,“极乐世界”当然是不存在的,“无修无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性”不能离开“事”而单独存在,空性的证得也离不开修行实践,“性”与“事”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须臾分离的,此人只知“毕竟空”而不知“缘起有”,因此偏离了“中道”而陷入“断灭边”。
综上所述,《东海若》描述了两种学佛方式,一是“无证无修”,一是“念佛三昧”,柳宗元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这是文本的基本内容。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柳宗元写这则寓言的目的是什么?
南宋僧人宗晓编《乐邦文类》,专收弘扬净土信仰的诗文,其中收录有柳宗元的《东海若》《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三篇。宗晓把《东海若》誉为“《乐邦文类》之冠”,并说:“昔人以净土为诞妄,柳公故作斯文以讥其失。大哉!达佛旨者也。” 他认为,柳宗元作《东海若》一文的目的在于讥讽那些“以净土为诞妄”者。章士钊先生说:“此殆子厚久处贬所,郁闷不堪,援者绝迹于外,而己亦无意求援于人,因自陈愿安粪秽之本怀,更借一乞于人者以为衬托,遂成为全篇反语之形状云。” 他认为,柳宗元写本文的目的在于“自陈愿安粪秽之本怀”。孙昌武先生说:“在他的意识中,入佛逃禅有着不得不然的悲哀,对净土的迷信也就有着自我麻醉的意味。” 孙先生认为,柳宗元宣扬净土信仰,“有着自我麻醉的意味”。从文本内容来看,《东海若》的主旨的确如宗晓所谓“讥以净土为诞妄”者;从柳宗元对净土信仰的热情鼓吹来看,孙先生所谓“自我麻醉”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章先生所谓“安粪秽之本怀”,可能相差较远。问题是:难道柳宗元写《东海若》的目的就是为净土宗“护教”吗?抑或仅仅是安慰自己受伤的灵魂吗?这背后还有没有其他动机呢?
(二)《东海若》的宗教意义
要搞清楚《东海若》的写作动机,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禅宗与净土宗的对立情况,了解禅宗对净土宗的批评及柳宗元的反批评。
《东海若》是在中唐禅宗与净土宗对立的背景之下写成的。禅净两宗对立的深层理论基础是“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的对立。“唯心净土”是禅宗最典型的思想特征之一。惠能说:“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 大珠慧海也说:“若心清净,所在之处,皆为净土。……其心若不净,在所生处,皆是秽土。净秽在心,不在国土。” 惠能、慧海都是用“唯心净土”来否定“西方净土”。关于净土宗对禅宗“唯心净土”的批评,赖永海先生说:
禅宗倡即心即佛,心外无别佛,“唯心净土”是其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净土宗人对此种说法很不以为然,认为“唯心净土”的说法,是把真俗混为一谈。依净土宗人看来,六祖之否定西方,乃是依常住真心立说,不是约俗谛言。就真不碍俗说,佛国在心,不妨十方净土宛然。他们认为,对于内证工夫很深的利根之人,说佛国在心自无不可,但对广大凡俗众生,不可妄唱“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之高调,而应把西方净土作为追求的目标,只要能进此极乐世界,成佛便可指日可待。 注释标题 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7页。
净土宗人认为,惠能对“西方净土”的否定,是就理上来说的,若就事上来说,“西方净土”是宛然存在的,对一般信众来说,“唯心净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调”,“西方净土”才是切实可行的修行目标。
“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的对立,导致了禅净两宗在解脱途径与方法上的对立。南宗禅倡导“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顿悟法门,往往对净土宗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持否定态度。如大珠慧海说:“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调心不调身,愚人调身不调心。” 他甚至说:“汝若能谤于佛者,是不着佛求;毁于法者,是不着法求;不入众数者,是不着僧求。” 有研究者说:“在大珠的时代,主要论敌仍是律师和法师,他重点斥责的佛事是诵经、念佛和净土。他称诵经为‘客语’,‘如鹦鹉只学人言,不得人意’。‘念佛’则是‘取相’,取相是为凡夫所立的‘随宜说’,不是究竟之语。‘秽净’在心,不在国土,离开净心,别无净土。” 如果说作为一代高僧大德的大珠慧海,对诵经、念佛的否定,是为了对治“愚人”对外在“佛”“法”的执求,那么,某些禅宗后学则由于过分强调“明心见性”“教外别传”而彻底否定净土宗持戒、念佛等修行实践,把宗教实践等同于世俗生活。柳宗元对此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柳宗元说:“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嚚昏,放于淫荒。” “空愚失惑纵傲自我”之徒,常常借修禅之名而废弃必要的修行实践,结果走上了“嚚昏”“淫荒”之歧途。柳宗元又说:“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 “方便”,又称“权假方便”“善巧方便”“权巧施设”等,它相对于“真理”而言,是指为引导众生证悟真理而权设的法门,包括坐禅、讲论、持戒等。达摩以来,南宗禅一直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但中唐以后,有些禅宗学人把“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发展到了极端,一味“迭相师用,妄取空语”,完全抛却经论的研读和必要的修持,混淆宗教修行与世俗生活的界线,导致宗教信仰的泛化,清规戒律的荒疏。柳宗元认为这种修行方式“陷乎己又陷乎人”。
某些禅宗学人对持戒、念佛等修行实践的否定,不但造成禅宗与净土宗之间的对立,而且造成对世俗礼法的破坏。柳宗元批评说:“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 某些“为释者”不理解佛教的真谛,以为参禅修道就是“去孝”“遗情”而求“达”、求“虚”,岂不知“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 ,失去“孝”“情”等道德内涵的“达”“虚”,只能是“流荡舛误”“妄取空语”。柳宗元还批评那些所谓“文章浮屠”说:“代之游民,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悫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以故为文章浮图,率皆纵诞乱杂,世亦宽而不诛。” 那些“为文”“为心”均不虔诚之“文章浮屠”,一方面“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另一方面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既以方外之士自居而不尊世俗礼法,又以文章之士自称而不循佛门清规,纵诞自肆,放荡不羁。柳宗元把这类人称为“游民”,甚至埋怨国家法律对其“宽而不诛”。
柳宗元还从思维方式上找出上述“禅病”的根源。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柳宗元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 他认为,造成上述“禅病”的最主要根源是“言体而不及用”。体,即体性,指毫无分别的、不变的真理实相;用,即作用,差别现象之具体表现。体用相即,是中国禅宗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贯穿、统摄着禅宗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神秀说:“我之道法,总会归体用两字。” 惠能也说:“定惠体一不二。即定是惠体,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时定在惠,即定之时惠在定。” 惠能以后,南宗禅尤其是洪州禅,愈益朝生活化方向发展,洪州后学常常把日常生活本身混同于禅修实践,导致“言体不及用”之“禅病”。“言体而不及用”与上文所言“妄取空语、脱略方便”,是对同一现象的批评,只是角度不同,后者是从具体现象入手,在形而下层面展开,而前者则是从思维方式入手,在形而上层面展开,两者都是指某些南宗后学由于过分强调“顿悟”,以空寂之“体”上的无差别性遮蔽了现象之“用”上的差别性,结果,一方面弱化了修行实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消解了现世生活实践的道德标准。柳宗元在《东海若》中批评“无证无修”者为“言性不及事”,意思与“言体而不及用”是完全一致的。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东海若》中两位学佛人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代表了中唐禅宗与净土宗的对立。柳宗元因对某些禅宗学人宗教信仰的泛化,清规戒律的荒疏及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极为不满,转而倡导为南宗禅所抛弃的“西方净土”观念及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以对治“狂禅”之流弊。南宋高僧祖琇称赞说:柳宗元“嫉逃禅趣寂而脱略方便”,有“深救时弊,有补于宗教”之功效 。从中国佛教史来看,柳宗元对“西方净土”信仰及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的提倡,预示了中唐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宋代以后,禅宗与净土宗走向合流,又带动了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同归净土,净土信仰及念佛法门由此普及于各宗派。《东海若》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三)《东海若》的时代意义
葛兆光先生说:
尽管南宗禅尤其是马祖之后的南宗禅以呵佛骂祖、毁弃经论、棒打口喝的方式弄出一副潇洒的面目,开启了纯任自然、追求平常的风气,表面上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喝彩,但当思想真正要负担起人生和社会的重任时,它却无能为力了,只好将意识形态拱手相让,因为它只能解决个人心灵的宁静和适意,甚至只能在纯粹心理层面上抚慰自己。……在人格提升上,它无法做到让人自觉向上,所以在中国思想大转型的中唐、儒道佛全面融会建设一个新型思想体系时,以儒家思想定位并吸取道释思想的那一批人,表面上看来是从南宗禅那里得到思想资源,但在汇入新思想时那些资源却剥落一层还原为近乎北宗禅的理路。 注释标题 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作为中唐思想文化大转型时期儒家的代表,柳宗元极力主张“统合儒释”,发挥佛教的“佐世”功能。当时,南宗禅一枝独秀,出现了“凡言禅皆本曹溪”的局面。由惠能开创的南宗禅,标举“顿悟”为其禅法特色,其实,惠能强调“顿悟”,并不是全然否定修行实践的必要性,而是强调上根之人无须长期按次第修习,一旦把握住佛教真理,即可突然觉悟而成佛。但某些南宗后学,常常以“顿悟”为借口,不但反对诵经、持戒等修行实践,而且出现以修禅为名破坏礼法的现象,此时的南宗禅已经难以担负起“佐世”之重任了。
柳宗元提倡“西方净土”信仰,固然有为自己找寻精神寄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目的还在于“佐世”。纵观柳宗元的一生,儒家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即使在贬谪永州穷困潦倒之际,他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儒家身份。他说:“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 。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也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尝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 他对净土信仰的提倡,也是与其儒家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形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局面,连年兵乱造成国库耗竭,政府加强对人民的盘剥,苛捐杂税日益严重,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中唐兴起的以啖助、赵匡、陆质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继承了西汉“公羊学”之微言大义,大力倡导“尊王”,意欲结束强藩跋扈、宦官弄权的混乱局面,重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治。作为“新《春秋》学”的服膺者,柳宗元大力标举尧舜时期“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之“大同社会”,主张以此垂法于万世 。与此相联系,柳宗元认为“西方净土”信仰也具有这种终极指向意义。他说:“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 又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中描绘“极乐世界”曰:“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 这与他在《晋问》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柳宗元鼓吹“极乐世界”的意义在于,为处于乱世之中的人们提供一个美好的精神归宿,这对稳定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据《柳州复大云寺记》记载,柳州人信鬼嗜杀,社会治安极为混乱,国家在此建造大云寺,引导当地人信仰佛教,情况出现了好转。后来,大云寺被大火烧坏,一百多年没有修复,周围三百多户人家“失其所依归”,又出现了混乱。柳宗元贬到柳州以后,修复大云寺,安居僧人,宣传佛法,于是人们“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 。柳宗元特别强调,人们的精神“失其所依归”是造成社会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此说法是极其深刻的。
为了发挥佛教“诱掖迷浊”之“佐世”功能,柳宗元在宣扬“西方净土”真实不虚的同时,又再三强调持戒等修行实践的重要性。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在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中,礼是最根本的,它是通达仁义的基础与前提,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 ,无“礼”则仁义坏。在佛教的修行实践中,戒是最根本的,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戒为“三学”之首、定慧之基,离戒则定慧无所依持。在柳宗元看来,佛教之“戒”与儒家之“礼”在目的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以“克己”的手段来达到道德境界。柳宗元在《东海若》中否定“无证无修”的修行观,强调戒律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规范佛教,从而让它更好地担负起“佐世”之重任。清人彭际清曰:“其(按:柳宗元)为言尊尚戒律,翼赞经论,以豁达狂禅为戒。” 此语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柳宗元佛教观的特点,此特点是由他对佛教“佐世”功能的重视所决定的。
结语
《东海若》以寓言的形式,反映了中唐时期禅宗与净土宗在解脱根据、途径与方法上的分歧。柳宗元站在“中道”立场之上,批评某些禅宗学人宗教信仰的泛化与清规戒律的荒疏,指出其“言性不及事”之病,同时充分肯定“西方净土”信仰及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的重要性,预示了中唐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东海若》也因此被认为是“护教”之作。在“护教”背后,《东海若》更寄托了柳宗元远大的社会理想与火热的现世关怀。“西方净土”其实是柳宗元儒家“大同”理想的折射,它虽然在现实之中不可能实现,但能给处于乱世之中的人们提供一个美好的理想,成为他们精神的依托,从而引导他们“趣于仁爱”。柳宗元对持戒、念佛等修行实践的强调,目的在于规范当时比较混乱的南宗禅,从而让它更好地担负起“佐世”之重任。《东海若》对净土信仰的提倡,从表面来看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选择的背后却隐含着作者理性的思考。祖琇赞曰:“盖子厚深明佛法而务行及物之道,故其临事施设有大过人力量也。如此可不美哉!” 这个评价极其精当!有唐一代,深明佛法之士不少,但大部分人所欣赏的只是佛教闲情安性的一面,而像柳宗元这样注重从佛法之中挖掘“及物之道”之人还是不多的。祖琇之赞绝非虚言。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