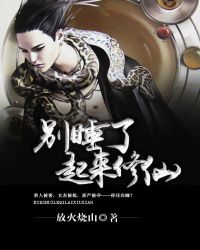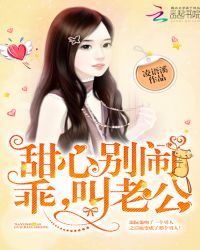第二节 柳宗元三教观的宋后回响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节/
柳宗元三教观的宋后回响
一、释氏眼中的柳宗元 注释标题 本部分内容曾以《释氏眼中的柳宗元》为题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
佛教《大藏经》中有大量关于柳宗元的记载与评价,透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释氏眼中的柳宗元,这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柳宗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三教关系的影响。
先来看佛教史传典籍对柳文的收录情况。南宋天台宗僧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把柳宗元列为天台宗法师重巽的俗家弟子,并收录其《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及《碑阴记》、《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送僧浩初序》。南宋沙门祖琇编撰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除了收录上面四篇文章外,还收录柳宗元《南岳云峰寺和尚碑》、《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南岳弥陀和尚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及《碑阴》、《龙安海禅师碑》、《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送濬上人归淮南觐省序》、《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送文畅上人序》、《送琛上人南游序》、《送元暠师序》、《送方及师序》、《送玄举归幽泉寺序》、《柳州复大云寺记》及《韩漳州书报彻上人亡因寄二绝》等诗文。南宋沙门宗晓编撰的《乐邦文类》,主要收录弘扬净土思想的诗文,该书收录了柳宗元的《东海若》《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还收录了苏东坡、橘洲和尚为《东海若》作的跋。元代禅宗名僧念常编撰的《佛祖历代通载》,收录了《南岳云峰寺和尚碑》、《送濬上人归淮南觐省序》、《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南岳弥陀和尚碑》、《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及《碑阴》、《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等九篇文章。
以上所列,都是收录柳宗元全文的佛教史传著作,其他涉及柳氏的佛教典籍还有很多。如编成于宋代的《南岳总胜集》、元代觉岸著的《释氏稽古略》、元代怀则口述的《天台传佛心印记》、元代熙仲编的《历朝释氏资鉴》、明僧心泰编的《佛法金汤编》、明居士夏树芳撰的《法喜志》、清僧呆翁行悦编的《列祖提纲录》等,这些著作或介绍柳氏事迹,或节录柳文,或征引其观点,如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以上介绍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多部佛教史籍对柳文的收录、征引情况,不但时间跨度大,而且涉及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等多个大乘佛教宗派,由此可见柳宗元对中国佛教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再来看释氏对柳宗元佛教观的理解与评价。
(一)“深明内教”
柳宗元涉及佛教的文章数量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最多的。《柳集》四十五卷诗文中,释教碑占两卷共十一篇,记寺庙、赠僧侣的文章各占一卷共十五篇,一百四十多首诗里,与僧侣赠答和宣扬禅理者达二十多首。从这些材料来看,柳宗元所接触的佛教宗派主要是禅宗、天台宗、净土宗与律宗,他对这四大宗派的理论学说都有很深的理解,并以十分理性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价,其中对天台宗评价最高,对禅宗批评最多。有研究者说:“在有唐一代思想家中,真正对佛教义理有着深刻理解并富有相当同情心的是柳宗元。” 这种评价是很准确的。
下面来看佛教内典对柳宗元的评价。《释门正统》是南宋沙门宗鉴编撰的一部以天台宗为正统的佛教史书。在此书中,宗鉴评价柳宗元说:“深明内教,广赞台崖。审思笃信,明辨力行。”又说:“其见之明,其辞之确,世未有如子厚之至者也。” 他不但高度赞扬柳宗元对佛法的深刻理解,而且赞扬他在弘扬佛法上的实际行动,认为柳宗元在柳州修复大云寺是“弘阐诚实”之举。志磐在《佛祖统纪》中,逐句点评柳宗元的《送僧浩初序》,分析柳氏对韩愈“不斥浮图”指责的反驳,赞扬柳氏对佛法的深刻理解,批评韩氏“不知佛,所以斥佛” 。宗晓称赞柳宗元的《东海若》“诚为《乐邦文类》之冠”,并说:“昔人以净土为诞妄,柳公故作斯文以讥其失。大哉!达佛旨者也。”
(二)“深救时弊,有补于宗教”
柳宗元赢得释氏的好感,不仅仅是因为他同情、支持佛教,还因为他出于规范佛教之目的而对其进行的批评。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南宗禅一枝独秀,出现了“凡言禅皆本曹溪”的局面,但某些南宗后学过分执著于祖师所倡导的“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完全抛却经论的诵读和必要的修持,结果造成宗教信仰的泛化、清规戒律的荒疏及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对此,柳宗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说:“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 在《送方及师序》中,批评那些“文章浮图”说:“代之游民,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悫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以故为文章浮图,率皆纵诞乱杂,世亦宽而不诛。” 他不仅在理论上对“狂禅”进行批评,甚至还呼吁以法律手段对之进行规范。
祖琇十分赞赏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称其“深救时弊,有补于宗教”:
子厚赠诸僧之序,篇篇无非以佛祖之心为心。……于琛序,嫉逃禅趣寂而脱略方便;……于方及,讥业文而昧己;于玄举,诫窃服而苟安。是皆深救时弊,有补于宗教。凡吾人当代主法,亦未必深思伟虑、宏范真风委曲如此。呜呼!古今缙绅作者以翰墨外护法门,如子厚之通亮典则,诚未之有也。 注释标题 《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二三,《续藏经》第75册,第224页下。
祖琇列举了柳宗元在诸篇赠僧序文中的主要观点: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批评某些禅宗学人“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在《送方及师序》中,批评“文章浮图”的“纵诞乱杂”行为;在《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中,批评某些僧人的“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祖琇认为,柳宗元的这些思想有“深救时弊,有补于宗教”之功效,其见解远超于其他好佛之文人士大夫之上,甚至连佛门“主法”之大德也自愧弗如。祖琇还赞扬柳宗元的《龙安海禅师碑》与《送僧浩初序》:“《海师碑》称‘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计当时禅宗方盛,未必皆然。迄今垂四百载,遂果如其言。妙哉《送浩初序》!使世之儒者待吾人若此,顾不幸欤?” 宋代临济宗禅僧大慧宗杲也说:“柳子厚以天台教为司南,言禅病最多,诚哉是言!”
某些南宗禅后学,不但自己“妄取空语,脱略方便”,而且对净土等教宗的念佛、持戒活动大加批评,从而造成禅教之间关系的紧张。柳宗元对此极为不满,大力倡导为南宗禅所抛弃的“西方净土”观念及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以对治“狂禅”流弊,并站在“中道”立场之上,宣导“统合禅教”主张。宗鉴赞曰:“唐柳子厚举龙安海公,斥晚学皆诬禅以乱其教,其道遂隐,乃太息而言曰:‘呜呼!吾将合焉马鸣、龙树之道也。’信哉斯言!实万世学佛者之指南矣。” 从中国佛教史来看,柳宗元对“西方净土”信仰及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的提倡,预示了中唐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宋代以后,禅宗与净土宗走向合流,又带动了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同归净土,净土信仰及念佛法门由此普及于各宗派。
(三)“和会儒释”
柳宗元在《送文畅上人序》中明确提出“统合儒释”主张,这是他处理儒佛关系的基本立场。元和十年(815),唐宪宗下诏追谥惠能为“大鉴禅师”,柳宗元奉诏撰《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概括惠能禅的基本精神曰:“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 用“性善”来概括惠能禅的基本精神,是柳宗元的精心设计,这体现了他会通儒释的良苦用心。苏轼在《又跋大鉴禅师碑》一文中对此大加赞赏,以“妙绝古今”许之 。祖琇十分赞成苏轼的说法,他说:“故子厚著吾祖之碑,而东坡称之,以谓推本其言与孟轲氏合。於戏!子厚奭然不以儒佛为异趣,抑妙乎性教者欤?贤哉!” 祖琇高度赞扬这篇文章,不是因为它如实反映了惠能的禅学思想,而是因为它起到了一个价值导向作用,把禅宗意旨导向儒家的“性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儒释会通。
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在得到释氏赞赏的同时,也遭到来自佛教界的批评。清代大居士彭际清在《居士传发凡》中说:“柳子厚制诸沙门碑铭,为苏子瞻所推服。然如曹溪一碑,和会儒释,与《六祖坛经》之旨全无交涉。” 他认为,柳宗元作此碑铭的真实用意在于“和会儒释”,其实并没能正确传达惠能禅法的特点。这虽是批评之语,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柳宗元的用意之所在。
(四)“深明佛法而务行及物之道”
祖琇说:“盖子厚深明佛法而务行及物之道,故其临事施设,有大过人力量也。如此,可不美哉!” 诚哉斯言!有唐一代,深明佛法之文人士大夫很多,如王维、梁肃、刘禹锡、白居易等等,但大部分人所欣赏的只是佛教闲情安性的一面,而像柳宗元这样注重从佛法中挖掘“及物之道”者是很少见的。在《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中,柳宗元说:“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 明确交待自己鼓吹“极乐世界”的意义,在于为处于乱世之中的人们提供一个美好的精神归宿,这对稳定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据《柳州复大云寺记》记载,柳州人信鬼嗜杀,社会治安极为混乱,国家在此建造大云寺,引导当地人信仰佛教,情况出现了好转。后来,大云寺被大火烧坏,一百多年没有修复,周围三百多户人家“失其所依归”,又出现了混乱。柳宗元贬到柳州以后,修复大云寺,安居僧人,宣传佛法,于是人们“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柳宗元特别强调,人们的精神“失其所依归”是造成社会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此说法是极为深刻的。
为了发挥佛教“诱掖迷浊”之“佐世”功能,柳宗元在宣扬“西方净土”真实不虚的同时,又再三强调持戒等修行实践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规范佛教,从而让它更好地担负起“佐世”之重任。彭际清说:“其为言尊尚戒律,翼赞经论,以豁达狂禅为戒。” 此语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柳宗元佛教观的特点,此特点正是由他对佛教“佐世”功能的重视所决定的。
以上介绍了佛教内典对柳宗元的评价及收录、征引柳文情况,由此可以看到释氏眼中之柳宗元形象:对佛法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批评当时佛教界的混乱局面,为其发展指明正确方向;努力调和儒佛矛盾,充分发掘、利用佛教“辅时及物”功能,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些评价都是很中肯的。历代佛教典籍对柳宗元评价之高,收录其作品之多,这在唐代士大夫中是极为少见的,这可从一个侧面看到柳宗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二、宋后“三教融合”思潮中的柳宗元
中唐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继续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在这股强大的潮流之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柳宗元的身影。下面以契嵩、宗杲、元贤、宋濂等人为例,来看柳宗元对宋以后三教关系的影响。
1.契嵩
宗密之后,佛教界大力推行“三教融合”思想的首推北宋名僧契嵩。契嵩(1007—1072),云门宗僧,通晓儒佛,提倡“儒佛一致”,其“三教融合”论集中体现为儒佛会通。所著《镡津文集》十九卷,是研究宋代儒佛关系的重要史料。
契嵩对儒学的发展历程十分熟悉。在《纪复古》一文中,他梳理了儒学的发展状况,从先秦的尧、舜、文、武、孔、孟、荀,到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杨雄,再到隋代的王通,线索十分清晰。关于唐代儒学家,他说:“唐兴,太宗取其徒发而试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韩愈、柳宗元复以其文从而广之,故圣人之道益尊。” 在他看来,最能代表唐代儒学水平的是韩愈、柳宗元两人。对于韩愈,他著《非韩》三十一篇,对其辟佛言论及伦理观、道统说、心性论等重要问题进行集中批判。关于隋唐时代的好佛之儒士,契嵩说:“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结、李华、梁肃,若权文公,若裴相国休,若柳子厚、李元宾,此八君子者,但不诟佛为不贤耳。不可谓其尽不知古今治乱成败与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谓佛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诸君益宜思之。” “八君子”中也有柳宗元,再联系前面那句话,可以看出,在契嵩眼中,既能代表唐代儒学水平又不排佛者只有柳宗元。
契嵩的儒佛会通思想也与柳宗元十分接近。他曾针对欧阳修等人的辟佛言论作《辅教篇》,提出“孝为戒先”命题,并以佛教的“五戒”会通儒家的“五常”。在《中庸解》中,他又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 儒佛相通于“治”,且有内外之分,可以相互补充。这些思想都是与柳宗元一脉相承的。
2.宗杲
宋代临济宗禅僧大慧宗杲(1089—1163)是“三教融合”的大力阐扬者。他说:“三教圣人立教虽异,而其道同归一致。” 大慧对柳宗元也有很高的评价:“故柳子厚以天台教为司南,言禅病最多,诚哉是言!” 作为禅宗祖师,宗杲并没有从维护本宗名誉出发而否定柳宗元的观点,相反,他对柳宗元“言禅病最多”的批评态度表示赞赏。
3.元贤
明代永觉元贤(1578—1657)提倡“三教融合”论,他说:“人皆知释迦是出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 这是从入世与出世的统一来论证儒佛融合。元贤还从人品、文品等方面对柳宗元这位儒家“三教融合”论者进行高度评价。他说:“予考柳子厚,终于柳州时仅得四十七岁,则作八司马时,年齿甚少。使其洋洋得志,不受拂郁,不知后来竟作何状。却得一番贬谪,乃能安于寂寥,肆力学问。故其文到柳州后始造其妙,其居柳日久,百姓爱之,卒乃血食其乡,不贤而能之乎?朱晦翁曰:‘子厚却得柳州力’是也。”
4.宋濂
明代儒者宋濂(1309—1380),受柳宗元“三教融合”思想影响很深。宋濂博通经史,深研儒佛道三家经典,皆臻其妙,自谓:“予儒家之流也,四库书册,粗尝校阅,三藏玄文,颇亦玩索。” 他把自己定位于“儒家之流”,主张以《春秋》《尚书》《大学》等儒家经典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深得明太祖的欢心,受诏修《元史》,并策划明朝之礼乐制作等事。他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三教融合”观,不但深研儒典,而且颇精佛老之学,曾三度阅藏,暇则修习禅观。宋濂的“三教融合”思想深受柳宗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阴翊王度”。与柳宗元一样,宋濂十分重视佛教因果论对教化民众的重要性,他说:“西方圣人历陈因果轮回之说,使暴强闻之,赤颈汗背,逡巡畏缩,虽蝼蚁不敢践履,岂不有补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谓‘阴翊王度’者是已。” “阴翊王度”,出自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这种说法在明代很受重视,不但宋濂多次征引,就连太祖、成祖也把它作为对待佛教的基本原则。所谓“阴翊”,就是利用佛教因果报应理论来威慑邪恶,褒扬善良,这是以佛教思想来弥补儒家治化之不足。柳宗元在柳州重修大云寺宣扬佛法,其目的正在于此,结果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第二,“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宋濂谓:“柳仪曹有云:‘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人知向方。’诚哉是言也!盖宗儒典则探义理之精奥,慕真乘则荡名相之粗迹,二者得兼,则空有相资,真俗并用,庶几周流而无滞者也。” 受柳宗元影响,他主张“空有相资,真俗并用”,这样就可以避免柳宗元所批评的“言体不及用”之“禅病”。他高度评价那些既能“妙悟真乘”,又能“旁通儒典”的高僧大德,赞扬他们“处乎世间,不着世间”的人生态度。
第三,“与《易》《论语》合”。宋濂自谓:“予本章逢之流,四库书颇尝习读。逮至壮龄,又极潜心于内典,往往见其说广博殊胜,方信柳宗元所谓‘与《易》《论语》合’者为不妄,故多著见于文辞间。……呜呼!孰能为我招禅师于常寂光中,相与论儒释之一贯也哉?” 这里,他明确指出“与《易》《论语》合”思想来自柳宗元,这是其“儒释一贯”思想的主要依据。宋濂还常常本着“儒释一贯”原则,用佛教思想著文谈政,与明太祖一起探讨佛教“觉悟群迷”“幽赞王纲”之道理。
第四,“由孝而极业”。宋濂致力于论证儒佛在孝道上的相通相融性。他说:“大雄氏言孝,盖与吾儒不异。” 又说:“身居桑门,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说《大报恩》七篇,皆言由孝而及其业。” 这句话是直接借用柳宗元《送元暠师序》所谓“释之书有大报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由此可见柳宗元的深刻影响。
宋濂去世后,其遗文由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袾宏(1535—1615)辑成《护法录》一书,此书对明代“三教合一”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袾宏是明代“三教合一”思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归心净土而又兼重禅教律的修行方式,以及三教“理无二致”“三教一家”的主张也都是与柳宗元的思想相一致的。说柳宗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明代“三教合一”思潮,应该是没问题的。
以上我们仅以几个事例来说明柳宗元对宋以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影响,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清代高僧憨山德清(1546—1623),曾提出过著名的“为学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术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狭,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 柳宗元是中唐“新《春秋》学”的重要人物,又精通老庄、深研佛法,非常契合憨山德清的“为学三要”,柳宗元的三教观极大地推动了后世“三教融合”思想的发展。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